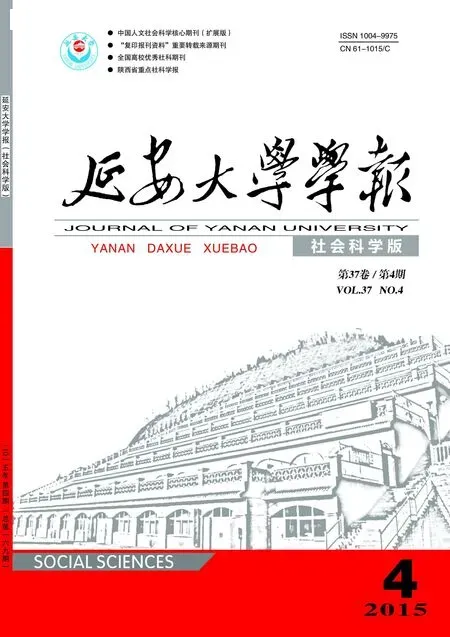论整风前的延安文艺与外国文学
2015-12-08常海波
常海波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论整风前的延安文艺与外国文学
常海波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在延安文艺史上,外国文学有过一段难得的繁荣期。整风前的政策导向、鲁艺专门化、演大戏风潮、一组批判性杂文等四个环节表明,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分歧日益凸显。“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身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外国文学基因深入骨髓。而毛泽东承袭马列主义的思想资源,一方面将之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批评这种知识分子的文艺表现形式脱离了革命的主要基础,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另一方面又竖起高尔基这面方向性大旗,不断暗示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苏联经验。
延安文艺;外国文学;毛泽东;苏联
对于延安文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国内现有资料呈现出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延安文艺是封闭和保守的,在无法消解的中国传统深层结构中找到了利益增长点,用农业文明的民间价值体系支撑起整个社会,民族化和民间化的艺术手法大行其道,与外国文学那一套审美理念完全是绝缘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延安文艺具有宽广的开放性,很多受到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翻译、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连同《解放日报》文艺栏都发表过许多评论外国文学的稿件,还上演和编印了很多外国名剧、名作。这两种观点似是而非,模糊了延安文艺在不同历史阶段结构方式上的变化,没有与当年复杂多元的历史语境建立联系。外国文学的输入为延安文艺的发展提供过动力、资源和革故鼎新的范式,引起延安文艺内部结构的变迁,而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文艺与外国文学关系史上的分水岭,本文对整风前的情况略作梳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追本溯源,探讨延安文艺与外国文学的影响系谱,希望把真正属于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
一、政策导向上的分歧
在工农武装革命斗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不仅军队中排斥知识分子,就是地方党支部,也不太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许多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的理想主义、怀疑精神以及与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肃反过程中备受猜忌。为了发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谈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自己知识分子的生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一决定借鉴了苏联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显然是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列宁在1918年《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说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他们有着软弱性、无纪律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毛病。后来在1921年的《论粮食税》中又提出利用资产阶级的砖瓦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构想。《决定》还指示“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620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所普遍缺乏的惊人智慧,他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矛盾特殊性的解决,普及优先,极力促成的是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
整风前党内负责理论建设、干部教育与宣传、文化等工作的主要领导是张闻天。他本人在俄苏文学方面有着深厚的修养,1921年以2万多字的篇幅发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1932年11月,以“哥特”的笔名发表了《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借鉴苏联批判“拉普”的错误经验,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40年10月张闻天针对党内轻视、厌恶、猜忌文化人的心理,为中央起草《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要求:“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戏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2]246可以说正是张闻天给予文化人充分的理解和宽容,比较尊重他们独立与自由的工作方式和个性特点,作风民主,才夯实了外国文学空前繁荣的政策基础。
抗战爆发后各大中心城市相继陷落,延安成为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象征,众多痛失原来的生存空间的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奔赴。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着良好的外国文学修养,例如周扬翻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至今都是非常经典的译本,他善于根据现实需要译介有实际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引述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支撑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逐渐受到重用,再如萧三,精通俄、法、德、英多种语言,入苏联共产党,结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与法捷耶夫等苏联作家私交甚好,到延安后任鲁艺编译部主任。外国文化浓郁的氛围还表现在大批外国文人来陕甘宁边区访问和工作,涉及美国、苏联、加拿大、日本、德国、朝鲜等十几个国家,尽管这些人的身份主要是记者、医生、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学生领袖等。
1942年整风前,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虽然1936年丁玲发起的中国文艺协会,由于毛泽东的介入从而开创了政党对延安文艺社团直接领导的模式。随着知识分子的汇聚,延安政治环境空前民主化,出现了第二种文学社团活动模式,即作家对文学社团的控制。正是由于这种相对自由的出版体制,才促成了外国文学的空前繁荣。抗战爆发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结束了十年紧张关系,国民党“暗禁明不禁”的政策,也使得一批著名的苏联文学翻译作品得以重版传入解放区。当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意识形态造成这一时期文学的题材主要集中在战争和卫国方面。
毛泽东认为张闻天的导向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既不能“大众化”也不能“化大众”。早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讲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不大好吃,山上弄出的东西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他后来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报告中指出党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包括先前陈独秀、瞿秋白等主要领导人也没有从组织化的高度来制定一个全盘的文艺政策。事实上张闻天、陈独秀、瞿秋白永远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斯大林模式的全盘文艺政策,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五四”新文学背景和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断裂,主要从欧美文学引进科学主义、个性主义,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观念深入每一个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人心。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性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3]43这种“大众的”理解模式显然与张闻天“民主的”理解模式有分歧,任何一个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必然和外国文学的启蒙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会像鲁迅一样认定“大众”身上有着很强的专制愚昧的力量。只是文化领域的矛盾暴露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1942年整风运动前,毛泽东或许是出于延揽人才的考虑,或许是忙于军事斗争,还腾不出手来整顿文化方面的问题,知识分子也在短时期内无法扭转惯性,迅速跟上主席的节奏。
二、“鲁艺专门化”的是是非非
整风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自由民主学院化的氛围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外国文学的繁荣。周扬担任副院长时增设了文学系,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建院初期的鲁艺图书馆,大约有三四千册图书,文艺类图书约占到三分之二。虽然鲁艺首任副院长沙可夫讲《苏联文艺》,但是俄国文学却是最受欢迎的对象。“拿文学系来说,较之苏联小说,学生们勿宁说更喜欢俄罗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沙汀在文学系讲授世界文学名著选读课时,给学生们讲过果戈理的《死魂灵》。他说《死魂灵》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到小说中的人物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这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4]1940-1942年间,周立波在鲁艺讲授《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延安当年物资极端匮乏,书籍奇缺,难以找到参考资料。周立波凭着在当时延安所能找到的一些图书资料,凭着他已有的文学理论、文学史知识和文学名著鉴赏的功底,竟然把这门课讲活了。“不仅是文学系的同学为之痴迷,也受到其他各系同学及教职员工的热烈欢迎,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学知识和欣赏写作水平”。[5]他在当年备课时所写的讲授提纲,经过长年的战乱多所散失,幸存下来的残缺不齐的部分讲稿,按原貌在《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3、4期上连载完毕。内容涉及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还有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西欧作家。
周立波的《讲稿》融会贯通,善于比较,剖析名著随处流露着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就已经具有的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观点。在讲莫泊桑的《羊脂球》,谈到所谓“纯客观”与“写真实”的问题时这样阐述:“大凡艺术,一定积极的引导读者,一定不是人生抄录,而有选择,剪裁。因为实际的不是真实的”;他进而发挥:“而我们更不同于莫泊桑,不但要表现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这种论述显然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翻版,苏联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写光明”,自始至终地宣扬大写的人、崇高的人、乐观的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语),应该像高尔基的《母亲》一样,呈现不同于过去现实和现在现实的“第三种现实”,即“未来的现实”。
《讲稿》中俄国文学9篇,苏联文学4篇,其中托尔斯泰独占5篇,成为整个讲稿中最受关注的作家。托尔斯泰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勇敢而又严肃的文学态度,晚清时期,托尔斯泰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宗教家与道德家身份传入中国;“五四”时期,托尔斯泰揭发沙皇专制政体、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与资本主义愤怒的声音,使得鲁迅和郭沫若都把他看成“轨道破坏者”和“文艺革命的匪徒”;“革命文学”时期,托尔斯泰又成了艺术圆熟,但是思想落伍的“卑污的说教人”;周立波对中国四十多年托尔斯泰的译介做了系统的总结,批评托尔斯泰人和作品“喧嚣着矛盾”,“对恶的无抵抗”,不过《讲稿》仰慕的是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生命的力和单纯的歌颂者”、“一切人性的洞察者”,并密切结合作品对艺术特色有着深入细致的分析,表明延安文艺界对托尔斯泰的接受已经达到从思想层面转向艺术自身的高度。这些批评显然是有着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背景的:普列汉诺夫将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断然割裂,认为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和拙劣的思想家”。[6]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托尔斯泰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俄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对邪恶不抵抗,是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列宁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或时代挂钩,从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角度分析托尔斯泰作品的方法奠定了延安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经典模式。
为了系统培养文艺方面的专门人才,鲁艺制定了正规化的教育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学制由原来的6个月改为3年,大大减少了各种应酬性的文艺演出,不再派学生到前方实习,确保高雅纯粹艺术教学计划的按时完成。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关门提高”的偏向。胡乔木回忆说:“这里面有一个环境问题,当时是一种战争环境,特别是农村环境。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毛主席很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他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7]鲁艺是一个专门培养革命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重视艺术作为宣传工具和战斗武器的作用。“鲁艺”的成立,是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与实践,标志着一种战时政治文化体制的开端。早在“鲁艺”成立周年纪念时,毛泽东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希望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而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现实主义指向现在和过去,用一种超越生活表层现象的哲人的慧眼来描述人世间的一切,虽有着过来人的冷静和深邃的智慧,但少有情绪化的主观渗入,不属于青春与热情。这种忧郁哀伤的调子,在一个善恶分明、需要行动,呼唤英雄的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三、“演大戏风潮”的争议
1938年8月鲁艺实验剧团成立,随着教学上专门化提高方针的确立,实验剧团强调提高技术,开阔视野,在剧作上,学习契诃夫、易卜生,在表演理论上,学习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1940年元旦以介绍世界戏剧名著为己任的延安“工余剧协”准备演出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主要演员病倒,毛泽东委婉建议可以上演一点《日出》之类的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当然在看过之后也是鼓掌称赞的。由此引发1940年至1942年初,20多部“高、精、尖”的外国戏剧纷纷上演:《婚事》《钦差大臣》(果戈理)、《钟表匠与女医生》(苏联罗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德国沃尔夫)、《破坏》(拉夫列尼耶夫)、《伪君子》《悭吝人》(莫里哀)、《求婚》《蠢货》《纪念日》(契诃夫)、《铁甲列车》(伊凡诺夫)、《生活在召唤》(洛契诃夫斯基)、《婚礼进行曲》(卡塔耶夫)、《带枪的人》(苏联包戈廷)等。甚至一些儿童戏剧也受到了“大戏”的影响,1941年延安少年剧团演出《公主旅行记》、《勇敢的小猎人》、《糊涂将军》、《它的城》等,都是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
毛泽东当初提议可以演一点,没想到膨胀为“一大片”,喧宾夺主,很快就被质疑成一种偏向。这些后来被命名为“大戏”的演出原本是为了学习技术的,只是后来展示为政治服务的热情,结果文不对题,吃力不讨好。例如欢迎周恩来等回延安,演出苏联独幕剧《钟表匠与女医生》,庆祝八路军大礼堂落成演《伪君子》。“所谓‘大戏’,乃是外国的名剧和一部分并非反映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和政治任务的戏,而这些戏,又都是在技术上有定评、水准相当高的东西”。[2]225从客观条件上讲,演出这些戏服装、道具、灯光、布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延安当时的条件是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的。当然,这些外国戏剧中有演出相当成功的,例如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剧《带枪的人》,革命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戏剧的舞台上,引起了轰动。某种程度上讲群众接受这类戏剧跟意识形态朝圣和电影放映有关,延安当年在影片奇缺的情况下,大量放映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保卫斯大林格勒》等。但是大部分外国戏剧还是不合工农兵的胃口,这些名剧所反映的内容,大多因为时代和地点的关系,同工农兵的现实生活较为疏远,不能使延安的多数观众切身锐敏地感受和领会,以增高他们的斗争情绪。毛泽东文艺需要的是能够及时反映当时、此地火热斗争生活,能够给延安的现实生活以直接反映、刺激和推动的东西。整风时期,“演大戏风潮”遭到公开地、强烈地批评。
“演大戏风潮”争论的背景,跟1938年到1941年全国性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有关,始作俑者还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对中共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范畴内提出“民族”问题更是有其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共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权及相应意识形态的政党;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过分强调继承外国的东西也不利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34政治领袖最终一锤子定音。毛泽东坚持一种功利性的取舍机制,认为外国的好东西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按照中国的特性才能应用。“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3]41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以母本为主,“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毛泽东是党内公认的大文学家,一贯倡导搞群众喜欢的形式,普及只能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普及。作为延安文艺规则最高制定者,他本人文艺思想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一切无助于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外国理论视为教条,一切对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外国资源坚决抛弃,衡量艺术的好坏一定要看社会效果。高尔基是他为延安的文艺家们竖立的一位旗帜性人物,高尔基的出身和文学道路使他天然地承担起代表底层民众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他的实际斗争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能有效地纳入到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框架之中。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强调:“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8]延安文艺服务的主要基础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文艺家的作品才能开花。因此1942年文艺整风的总方针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3]94高尔基就这样成为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造就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典范,同时也是学习美丽言辞,提升艺术技巧的一面大旗。
四、“一组批判性杂文”的前前后后
整风前《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丁玲推出的一组批判性的杂文,这组杂文与外国文学有着潜在的联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借延安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进行个体关怀,她不久前发表的《在医院中》连同罗峰的《还是杂文时代》直接继承了鲁迅的基因,进一步追溯就是果戈理等俄国“自然派”暴露黑暗、解剖“国民性”的启蒙笔法。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认为文学目的在于自尊:“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这与他的留法背景以及认同戈蒂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有关。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对“同志之爱”的酒在延安“越来越稀薄”的现象强烈不满,这里边的“人性论”和“永恒的爱”,背后是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的影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批判延安当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种斯大林模式的等级差序制度,批判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毛泽东“天塌不下来”的言论。他英语底子扎实,经张闻天挑选,供职于延安马列学院翻译室,这些思想跟他对外国书籍的直接阅读想必大有关系。
鲁迅被毛泽东树立为延安文艺家的总司令,是另一位旗帜性人物,他身上“百十来本外国小说”的背景,使得外国文学的思想火种在延安潜移默化地播撒。仅以当时轰动整个延安的王实味为例,他的《野百合花》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陈西滢说鲁迅是“放冷箭者”,毛泽东也批评王实味的风格是:“冷嘲暗箭”。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宣扬“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而且把揭露的解剖刀指向自己人阵营,“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这样的论述明显脱胎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9]表面上王实味承袭了鲁迅解剖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实际上折射的是外国文学中的自我意识、民主意识、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的思想基因,只不过当时的批判者把它们全部置换成了托洛斯基文艺的话语系统。
托洛斯基由于政治上受到斯大林的打压,延安文艺界对他讳莫如深,其实在文艺上,他比较重视文艺自身的特点,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对同路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鲁迅晚年时期左倾化,在政治判断上有列宁主义的痕迹,但在审美判断上的观点和托洛斯基比较接近,他曾称赞托洛斯基“深解文艺”。[10]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文艺论争,几乎在中国重新演绎了一遍。创造社和太阳社主要接受“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影响,而鲁迅、茅盾等人则接近托洛斯基的观点。三十年代斯大林开始抓文学工作,国家政权干预,苏联文化体制随之发生了大转变,理论被迅速提升到列宁的“党性原则”阶段。但是延安的知识分子受鲁迅影响,接受的是苏联二十年代的看法。
这组杂文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直接导致了《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停刊。“王实味事件”还直接成为延安文艺整风的导火线。《讲话》甚至将“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列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的一个例子。认为这些道理都是从抽象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鲁迅精神明显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反抗性和战斗性,一个是基于外国文学独立自由思想资源而形成的的启蒙性和个体性,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论鲁迅》概括伟大的鲁迅精神:“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将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170显然凸显了第一个维度而遮蔽了第二个维度,而整风前延安的文艺家们主要理解的是鲁迅的第二个维度。毛泽东认为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2]327嘲笑和讽刺主要是对付敌人的,对于自己人,应该用保护、教育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其理论背景,正是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光明”。
建国后由于读书环境的改善,毛泽东可能读了好些外国文学作品,如《茶花女》、《简爱》、《红与黑》、《被开垦的处女地》、《死魂灵》等。但是在延安时期,他对外国文学的接触主要集中在苏联文艺方向上,如《毁灭》、《铁流》和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这方面周扬、胡乔木是他的重要顾问。再就是他一直敬仰的鲁迅,众所周知,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始终将20卷本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鲁迅抱着“救急”的态度,在1927年后把译介的热情转向苏联,他不顾自己不懂俄文这一翻译大忌,始终是苏联文学最热烈的宣扬者,俄苏文学的译作占他所有译作的一半以上。鲁迅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是毛泽东《讲话》中唯一提到的一部苏联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记叙了西伯利亚东部背景下苏联共产党与白军势力和日本人之间的斗争,这种政治、军事态势与中国在陕北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处境非常类似。毛泽东希望作家们以法捷耶夫为榜样,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充分认识到什么样的作品才会产生全国意义和世界影响。
综上所述,整风前延安文艺并不存在统一的文化领导权,民主宽松的政策促成了外国文学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纷涌而来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的思想分歧也开始日益凸显。知识分子经历“五四”新文化洗礼或者出国留学,身上外国文学的血脉绵延不绝。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独尊苏联,但是旧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欧美文学中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因素还是深入延安知识分子的骨髓。而毛泽东吸纳马列主义的文化资源,将知识分子的文艺表现形式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一种不能为革命的主要基础——工农兵服务的严重偏向,由此导致整风期间用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摧毁外国文学传统中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延安文艺整风的实质就是用中国作风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解放”主题取代已往外国文学话语传统中的“启蒙”主题,“解放”主题认为悲剧发生的根源不在于人性自身的劣根性,而在于阶级压迫,是罪恶的社会把他们逼成那样的,只要推翻了旧社会,一切皆大欢喜。在表现形式上,扶植宣传性远胜于艺术性的大众文艺。所有的一切,都因为当时的战时状态和农村环境,获得了合法性的支持。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艾克恩.延安文艺史:上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3.
[5]周立波.周立波鲁艺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60.
[6]倪蕊琴.俄国托尔斯泰研究简论[M]//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514.
[7]胡乔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M]//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0.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5.
[9]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6.
[10]陈国恩.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8.
[责任编辑 王俊虎]
Yanan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before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HANG Hai-bo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In the history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foreign literature had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boom.Policy guidance before the Yan'an rectification,specialization of LuYi(鲁艺),agitation of play foreign drama,and a set of critical essays,showed grow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al leader MAO Zedong.Since the“May 4th” Movement,foreign literature gene,such as liberalism,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deeply embedded into intellectuals.MAO Zedong inherited the thought resources of Marxism-Leninism.On the one hand,MAO Zedong labeled those foreign literature gene as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etty bourgeoisie's emotional appeal,criticized this kind of literary form of the intellectuals out of the main basis of revolution,can't service for the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On the other hand,MAO Zedong raised Gorky as the directional flags,constantly suggest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which literature and art serve for politics.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foreign literature; MAO Zedong; the Soviet Union
I206.6
A
1004-9975(2015)04-0041-06
2015-03-08
延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延安文艺与俄苏影响研究”(YDQ2014-29)
常海波(1981—),男,陕西米脂人,延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