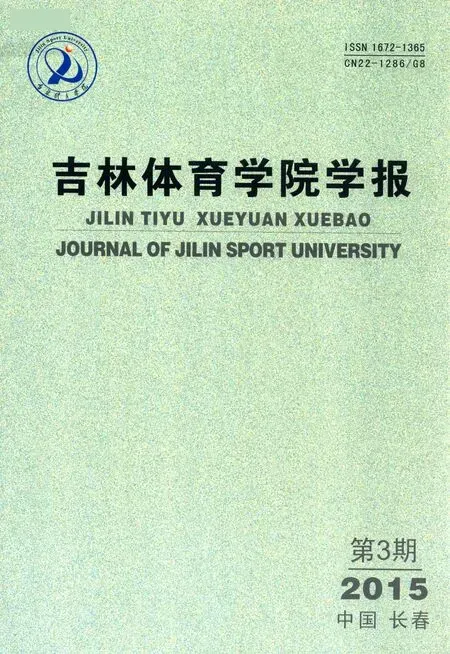徽州武术与徽州傩的共性及融合展望
2015-12-05曹红敏胡惠芳
曹红敏 胡惠芳
(1.池州学院 体育系,安徽 池州 247000;2.池州学院 历史文化学系,安徽 池州 247000)
1 前言
徽州文化指的是古徽州一府六县土地上所承载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它所具有的理学、篆刻、建筑以及徽剧和徽民俗等众多广博、深厚的文化内涵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所青睐,并名列三大地域文化之中,徽州武术和徽州傩是徽州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徽州武术以其独特性、亦武亦儒的个性被誉为徽州文化的一颗明珠,是武术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徽州傩同样也因其原生态而被誉为“汉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徽州武术和徽州傩是在徽文化这一共同母体之中孕育而来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共识,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分支而已,研究徽州武术与徽州傩在文化上的关联,对解决二者在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增光添彩。
2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的共性分析
2.1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的文化共识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众多的相同之处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受到了同样的文化熏陶。
2.1.1 同受古山越文化的影响
徽州地区丛林茂密、山峻岭峭,以“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而著称[1],古时称这样的地理环境为“山越”,山越人有“好武习战”的个性,这种个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衰退,反而越来越兴盛。以明清两朝徽州府所在地歙县为例,明时武榜举人有75 人,进士有21 人,清时,武举人达226人,其中进士65 人,在歙县的江村,明朝时,武榜举人8 人,进士有3 人,比文举人还多,中武举者11 人中进士即有2 人[2]。
山越人除好武之外,另外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好傩”,因徽州曾是吴、越和楚国的领地,吴、楚文化在此结合,史有“吴头楚尾”的美誉,楚国人喜欢巫术、吴国人信奉鬼神,百越被称为傩的发祥地,傩在徽州的盛行,使好傩成为徽州人又一典型特征,这在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如《橙阳散志,歙县风俗礼教考》有“傩礼颇近古,而不举于官.....亦即玄衣朱裳黄金四目驱疫遗意”、清道光《祁门县志》亦有“正月元日集长幼列拜神祗......傩以驱疫”、茗州村《吴氏宗谱》也有在正月的社祭中都要有傩人表演的记载、《徽州府志》中也有歙县沿袭吴楚习俗,每年也都有傩礼等众多文献的记载。
2.1.2 同受宗族文化的洗礼
徽州经过数朝宗法制度的积累使宗族制度高度发达,聚族而居是徽州宗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聚族而居”使得各族之间为了确保和扩大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斗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械斗之风颇甚”[3],为了生存和本族的壮大,徽州各宗族组织人习武,组建自己的武装势力,徽州史上出现的“拳头庄”或称为“郎户”,就是宗族之间用于械斗的工具,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保卫宗族的财产和为主家充当保镖[4],至清朝徽州团练组织组建,徽州武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祭祀是宗族祠堂的主要功能,也是宗族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徽州宗族祭祀仪式的过程中,傩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到正月和其它的岁时节令,祭祖都伴随着傩祭,傩祭从宗族祠堂出发,绕遍整个村落,最后再回到宗祠,把傩神面具在祠堂中供奉起来,傩班都是宗族的傩班,也就是跳傩之人都是同姓中人,在徽州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无傩不成村”,说明了傩与宗族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明确记载的如清代《祁门县志》中有:在过年时全族人都要按照辈分、年龄的次序拜祭祖先,表演傩舞驱疫祈福。现如今在歙县的叶村还一直保存着“五兽会”,在江西的婺源的沱川、庆源、李坑、长泾等村的傩舞依然十分兴盛。
2.1.3 同受宗教文化的熏陶
中华武术四大门派都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少林派属于佛教、武当派亦是道教、峨眉派亦僧亦道、南拳的“五大名家”亦出自福建的南少林,也是佛教,作为徽文化和徽商发源地的徽州,佛、道教也极其兴盛[5],九华山、白际山和天目山这些佛教名山与齐云山和天柱山等道教圣地,就分布在徽州的四周,徽州完全被包围在一个宗教浓郁的环境之中,不但如此,徽州与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渊源也颇深。程宗猷之所以棍法精湛,是经少林武僧洪转、洪纪等僧人的指点而得到了少林棍法的精要,且这些僧人也曾经来过徽州,促成了二者之间紧密的技艺切磋与交流,使徽派武术吸收了很多少林派武术的精要技理[6]。宗教文化的浓郁,使徽州武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了佛家慈悲之理的熏陶,形成了不求伤人、只求自保的徽州武术基本要义,而且道教老、庄的思想也使徽州武术在技理上要求虚灵自然、以静制动,且明显的体现在徽州太极拳上,据《徽州志》记载,徽州太极拳的创始人徐宣平也是道教中人,这就更加增加了道教的文化色彩。
傩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祭礼,加之徽州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和地处吴、楚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处,使傩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成为徽州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影响着徽州人的精神生活。佛、道教中所提倡的忠君重义和人世间存在着因果报应,要求人向善都在徽州傩的表演剧目上有充分的体现;用傩驱疫、祈福、许愿、还愿、傩面具开光等与佛、道教的做法事驱疫、祈福、佛前许愿,如愿还愿、佛件开光等如同一辙;傩舞所信仰的对象中有观音、八仙太白金星等这些佛、道人物;除此之外,在音乐的选择上,除了民间歌曲和民间歌舞音乐之外,宗教音乐在傩音乐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
2.2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的情感共识
徽州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造成徽州地区交通不便,使徽州人养成了封闭自守的个性心理,同时也凸显了徽州地区的人们对山区地理环境的特别情感。徽州人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创造出了属于徽州独特环境的地理人文文化,徽州武术注重桩功,不轻易起腿的特点就是长期攀爬山岭对腿部的特殊要求,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智慧的结晶,徽州武术的每个技术要求,特别是短打与跌摔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徽州地属山区,山道狭窄、崎岖不平的地理环境,印证了“拳打不过力,力打不过巧,巧打不过灵”这句徽州传统武功名言。
傩是一种即神秘又古老的原始祭礼,它是人们对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现象无法用自己现有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解释而产生的敬畏与崇敬之情,也因为此,人们认为人世间存在着鬼与神灵,希望用这种形式达到与神灵沟通,从而驱鬼纳福。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并形成民俗的主要原因在于交通不便,人们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存在一种特别依恋的情感,徽州傩在徽州的盛行正是如此。
2.3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功法与器械上的共识
2.3.1 对庄功要求的一致性
武术谚语有:手像两扇门,全凭脚来打。徽州四周环山、坡陡山险,也因此,下盘的稳固性在徽州武术至关重要,同时重视步伐在展、转、进、退时的灵活性和落地要生根的稳定性[7]。从整体来讲,徽州武术拳架比较低、起腿动作较少、并且注重防卫,不轻易进攻、以自卫为出发点、强调后发制人的技术风格。这个特点从徽州地界上流传的拳种,如外来拳种杨、陈、吴、孙、武当太极、五行拳、八仙拳、黑虎拳、梅花拳、地毡拳、偷心拳、十步蹚腿等都被打上了这种技术风格烙印,本地拳种如徽派太极、板凳花、腰带舞、抽担的技术风格更是证明了这一点[8]。然徽州傩的膝盖弯曲、重心下降、顺拐、含胸与收腹,所表现出的沉但不松懈,梗然不僵硬的独特技术风格正好与太极、八卦、板凳花等拳种的技术要求基本相同,徽州傩中踩、摇、转、跳、跷、翻、打等动作也都和徽州武术中的要求避实击虚、身法灵活的技法要求如出一辙。
2.3.2 表演器械都来自于生产和生活中的器具
徽州武术中所用的兵器,大多数取自于生产和生活中的器具,如用山上的树木或者竹子这些材料加工而成的竹棍、扁担、板凳,或抽担等,再加以简单的加工和改造就成为了武术中随手拈来的器械;斧头、铁叉等生产工具,同样也成为了武术器械中的一份子,如在徽州流传很广的拳种板凳花、腰带、抽单等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总的来看,徽州武术重实用、重防守的技术风格和器械与日常生产、生活工具有很大的关系。徽州傩在祁门和江西婺源流传最为广泛,两地的傩舞古朴、生动,最具原始气息,是研究傩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这两地最有代表性的傩舞主要有《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舞花》、《刘海逗金狮》、《丞相操兵》、《张飞祭枪》等几十余种,道具主要是斧头、铁叉、簸箕、枪、木棒或竹棍,还有装饰用的羽毛等等。
2.4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传承方式上的同一性
佃仆制在古时的徽州非常盛行,且历史非常悠久,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州佃仆人数最多,佃仆之中服家兵劳役的佃仆被称为“拳头庄”,这些拳头装都是以户为单位,除了农耕之外,还要负责主家的财产、人身安全,并为主家充当保镖,因此,拳头庄们必须苦练武术以提高武功水平,并且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除非缴纳一定的赎金来赎身,才能摆脱其身份,由此徽州武术的传承是家族式的子承父业;除了拳头庄,在徽州也有其它身份的习武者,包括徽州的权贵和大户,有些武艺高超者受到人们的仰慕,拜其门下习武,这就有了另一种传承形式,即师徒式的传承方式。除了拳头庄,在佃仆中还有另外一些人被称为“傩仆”,他们被大户人家圈养着,在送灶、庙会、祭祀等活动上,承担着傩戏表演的责任和任务。根据齐琨老师的调查,婺源县游山的董氏宗族的30多户庄仆里青年男子大都是“傩仆”,在宗族祭祀和其它节气时,他们身着傩服,头戴傩面具跳傩舞、唱傩戏,且多是世袭家传[9]。除此之外,还有以此为生的傩班,他们的传承方式除了家族传承之外,就是师徒传承,在收徒时,还有严格的收徒要求和拜师仪式。可见,徽州武术和徽州傩在传承方式上基本上都是以家庭和师徒传承为主,二者在传承方式上相同。
2.5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保护困境的共识
由于近代农耕经济的解体和高度的城镇化使武术和傩的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同时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更趋向于从事一些比较赚钱的行业,现代教育模式使这种原始的传承方式失去了以往的优势,这些都导致二者在传承与保护方面遭遇困境。首先是传承人的问题:即在现代社会,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愿意习练武术和傩;其次,徽州武术和徽州傩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在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很难取得大的经济效益,资金成为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又一大障碍。
3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融合发展的构想
3.1 融合文化、技术与器械,创编一种新颖的武傩舞
徽文化是徽州人民情感的积淀,为徽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徽州文化给游客提供了一桌丰盛的文化盛宴,徽州武术和徽州傩是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并且二者有相同的文化基础,在技理上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再加上表演器械也都来自于生活与生产工具,这些都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先天性的条件。对于徽州武术与徽州傩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可以采用融合二者在文化、技术与使用器械上的共同点,创编一种既有二者在文化上的共同点,又能充分体现徽州文化的特色;既能表现出徽州武术的武技特点,又能展现徽州傩的表演风格;既能便于更多的人乐于参与,又具有健身、娱乐、欣赏等功能的新兴舞种。对于武傩舞的具体创编,必须由精通徽州武术和徽州傩的专门人才来担当,并由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协助,真正把二者的文化精髓和技理融合在一起,使之易于推广和接受。
3.2 创建有效的推广模式
对于徽州武术与徽州傩的保护与传承,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民间财团和业内人士的大力支持,要想民间财团乐于投资,就必须创建一个良好且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使之产生效益。同时,在传承人问题上,首先要打破传统嫡系传承观念,只要愿意学,任何人都可以,其次武傩舞的创编至关重要,创编出大家喜闻乐见的健身、娱乐套路,把它融合在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吸引人们主动地通过武傩舞健身,解决传承人问题。
4 结语
徽州武术与徽州傩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徽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众多的传统文化在逐渐的消失,作为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文化中的众多子文化也没能逃脱厄运。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地区精神的结晶,它应该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徽州武术和徽州傩要改变目前的发展处境就必须融合二者在文化上的共同点,创编一种新颖的武傩舞拳种,既能使二者得到保护与传承,又能为二者的发展开辟蹊径,采用一个良好的推广模式,使二者摆脱目前艰难的困境。
[1]方利山.徽州文化之成因[J].黄山学院学报,2007,9(6):4-7.
[2]黄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徽州大姓[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33.
[3]杜刚.明清徽州基层社会治安保障体系研究[D].合肥:安徵大学,2006:24-26.
[4]叶显恩.徽州与粤海论稿[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52-156.
[5]吕利平.浅谈中华民俗体育之傩舞的新内涵[J].四川体育科学.2010(3):15-16。
[6]唐小文,钟川.访嵩山少林寺武术指导马明达教授[J].徽商,2008(3).58-61.
[7]杨晓黎.徽州武术特点探析[J].徽州社会科学,2004,(5):54-55.
[8]李龙,潘丹丹.徽州武术分布现状及文化特征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4,8(5):12-18.
[9]齐琨.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J].2010(3):13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