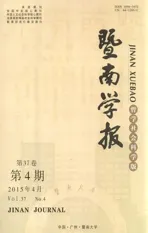乾隆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
2015-11-14石昌渝
石昌渝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古代小说专题研究】
乾隆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
石昌渝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编者按: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团队近年来科研成果叠出,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体现我校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学报编辑部特在本期推出“中国古代小说专题研究”,约请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石昌渝教授、沈伯俊教授在百忙中分别撰写大文《乾隆文字狱阴影下的小说创作》、《国士情怀与好汉气概——〈三国〉〈水浒〉比较研究之一》。两位大家的潜心之作,其功力、见地自不待言;青年学者赖晓君博士的《论科举视野下的明代江西小说》,也有可喜之处。欢迎诸位方家同仁对本专栏予以关注。
清代文字狱远胜于历朝历代,而乾隆朝又是文字狱的高潮时期,乾隆帝以索隐的方法罗致罪名,在文学创作领域制造了恐怖气氛。志人小说和以时事为题材的小说不再有人敢写,而一切小说家在创作时也不能不畏惧头上悬着的文字狱利剑。作家的关注点从时事政治转移到人和人的精神世界,却创作出《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
乾隆文字狱;索隐;志人小说;时事政治小说;红楼梦
古代因文字而获罪,数量之多,处罚之酷,没有哪个朝代比得过清朝。清朝文字狱、康熙初年庄廷鑨明史案,被祸者七百家,被处死者千人,惨烈触目惊心。康熙五十年(1711)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撰《南山集》中谈及顺治元年太子慈烺案,当时朝廷认定太子是假,匆忙处死。《南山集》考据太子灼灼是真,踩到了清朝的统治底线,被人举劾,本应凌迟,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这位五十七岁才考中进士的散文家的迂腐,从轻予以斩首,免了牵连者三百余人的死刑。这两个案子都由史著而发,被上纲为对异族新朝的敌视,故而严惩不贷。雍正朝也发生过查嗣庭科场题案、吕留良案、《西征随笔》案等等。乾隆帝登基在1736年,去明朝覆亡已近百年,大清统治业已巩固,汉人的民族情绪大体已被时光磨蚀,他本欲稍缓父祖高压态势,没想到乾隆十六年(1751)冒出了一个“伪奏稿”,词稿伪托以直谏著称的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指斥乾隆帝“五不解,十大过”,乾隆帝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这种批评自然使他有挖心之痛;更要命的是此稿在朝野广泛传抄,他却被蒙在鼓里,天下人皆知,独他一人不知,当云贵总督硕色在边陲之地偶尔发现呈报给他时,他之愤怒可想而知。由此他认为朝野肯定存在一个潜在的谋逆集团,遂下旨严加清查,顺藤摸瓜,企图一网打尽,历时一年又七个月,波及十七个行省,缉捕的人犯,上有二品提督,下至道员、守备、知县等等,总数达千人之多,弄得全国鸡犬不宁,却还是没有挖出一个逆党,连最后定案为主谋的南昌守备和抚州卫千总,明知疑点重重,也只好“葫芦提”处死结案。乾隆帝心结未释,从此对天下文字密加监视,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文字狱。
乾隆(1736-1795)六十年,文字狱有案可稽者即有三十多起,其频率大大超过雍正、康熙两朝。其对文坛影响之深刻和广泛,则远远超过前两朝。以明史案和《南山集》为代表的文字狱,著述文字范围在政治历史,所抓住的把柄,明眼人一望可知,而乾隆帝则关注包括政史和诗文等一切文字,并且采用索隐的方法,断章取义,罗致罪名,其结果是文人下笔不能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乾隆二十年(1755)内阁大学士胡中藻因其诗集《坚磨生史抄》获罪处斩,其诗有何悖逆之处?乾隆帝说:朕“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毁谤清朝,这罪名是骇人的,然而明眼人从诗中却看不出有悖逆之意,故数年来并无一人举报参奏,只有乾隆帝“明于大义”之特殊眼光,方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悖逆”二字来。首先是诗集题曰《坚磨生史抄》居心不良,乾隆帝说:“‘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而诗中隐含的反清意旨颇多,乾隆帝指出:“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熙皥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乾隆帝所举“悖逆”诗句还有许多,其诠释方法都是割裂全诗,挑出个别词句进行索隐,这种方法,可置任何一部诗集于死地。乾隆帝说他是效法雍正帝之诛查嗣庭,查嗣庭雍正四年为江西考官时,以《孟子》“茅塞子之心”为试题,被指用心险恶,有讪谤皇帝之意,其方法就是望文生义。乾隆帝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一种随意制造罪名的简单易行的方法,但其危害和流毒却不能低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这诗句是清朝数代文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一
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在统治者眼里是卑微的不登大雅的文体,小说不像诗文那样被朝廷紧盯,但它也不能完全逍遥在文字狱法网之外。清初李渔的话本小说《无声戏二集》有一篇写了“不死英雄”张缙彦,张缙彦为明朝兵部尚书,李自成攻破北京时,据说他自缢被人救活,不得已投降了李自成,后来又转投清朝,做了浙江左布政使,又据说他资助李渔编刊称颂他的小说,顺治十七年被人举劾为自我标榜、丧心病狂。清朝入主中原甚得这些贰臣之助,但清朝统治者内心对这些降臣是鄙夷和不信任的,把失节之事加以吹捧,难道要让人们慕效乱臣贼子吗?张缙彦夺官逮讯,虽免于一死,却还是籍没,流徙宁古塔。康熙三年,也就是明史案发的次年,丁耀亢的长篇章回小说《续金瓶梅》被人检举,谓书中写到清朝发祥之地宁古塔、鱼皮国,多有不敬之词。丁耀亢被捕入狱,本应绞决,幸遇康熙四年三月初二北京地震,皇帝下“恩赦”诏,才侥幸免罪。这些过往记录,对乾隆时代创作小说者来说,不能不是警训。乾隆时代文字狱的频发和酷烈,更是笼罩在头上、无以摆脱的阴影,小说创作者岂能自由信笔挥写?
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三品大员致仕的尹嘉铨为父求谥并请从祀文庙,惹恼乾隆帝,遂下旨抄家。在家中搜出《名臣言行录》一编,将高士奇、鄂尔泰、张廷玉等等悉行胪列,乾隆帝大怒曰:“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榜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则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遂将尹嘉铨处绞立决,以告诫内外大小臣工、天下读书士子均当洗心涤虑,各加儆惕,引以为戒。《名臣言行录》似《世说新语》之类志人小说,此案一出,志人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人敢写。纪昀在朝廷任官时间长、同僚友朋众多,但他只写志怪的《阅微草堂笔记》,绝不记述当朝真人真事。志人小说自魏晋以来,各朝作品繁多,康熙年间王晫撰有《今世说》八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是书全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之书,犹明代诗社余习也”“标榜声气”、“诗社余习”,就是乾隆帝批《名臣言行录》之意,志人小说在乾隆朝事实上被列为写作禁区。文言小说之志人一支,到此中断。
二
乾隆时代,凡“编捏时事”、“抵触本朝”的文字,均被视为“谋逆”,哪怕出自疯人之手,也要将作者处以极刑。典型的案例是乾隆十六年(1751)发生的山西王肇基献诗案,王肇基自幼读书不成,在各处当长随,时逢皇太后寿诞,欲求官做,做了一副恭祝皇太后万寿的诗联呈献,诗联错乱无文,俚鄙不堪,即被官府认定黄丹狂悖,又从其家中抄到一册尚未写完的文字,记有内外满汉文武大臣各事,据供都是道听途说,乾隆帝定案说:“览山西巡抚阿思哈所进王肇基书一本,癫狂悖谬,竟是疯人所为,与滇省伪造奏稿一案并无关涉,但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着传谕该抚阿思哈将该犯立毙杖下,但愿众知所炯戒。”王肇基书中所记时事,皆为他做长随跟班时看京报和听大人们闲话得来的,究竟记了些什么,无以得知,但有一点很明确,“编捏时事”即罪不容逭。
以当朝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在明末已成为小说的一大流派,这个流派入清之后未曾消歇,顺治元年(1644)有记叙甲申之变的《新编剿闯孤衷小说》(又名《剿闯小说》)十回,顺治五年(1648)有记叙清军南下常熟、福山地方惨状的《海角遗编》(又名《七峰遗编》)六十回,顺治八年(1651)或稍后,又有《樵史通俗演义》四十回,该书顺康间写刻本内封作者识语曰:“深山樵子见大海渔人而傲之曰:见闻吾较广,笔墨吾较赊也。明衰于逆珰之乱,坏于流寇之乱,两乱而国祚。随之国祚随之。当有操董狐直笔,成左、孔之书者。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传书,采而成帙。樵者言樵,聊附于史。古云:野史补正史之阙,则樵子事哉。”可见清初关注时事的小说仍大行于世。康熙三年(1664)明史案发生,时事政治小说便沉寂下来,但四十年后还是出来一部《台湾外记》三十卷,从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海盗出身写起,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爽降清为止,记叙了收复台湾的历史。
乾隆帝不但对“编捏时事”者加以严惩,并且发展到不能容忍私藏明末清初野史。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籍二品大员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获罪,彭家屏辩称“存留未晓,实不曾看”,但乾隆帝斥之曰:“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记,好事之徒,荒诞不经之谈,无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践土,百有余年,海内缙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此实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终于败露者。”遂将彭家屏处死。在这种高压之下,在乾隆时代,时事政治小说便完全销声匿迹了,就是以世情为题材的小说,也不敢标榜故事发生在清朝。
话本小说集《醒梦骈言》十二篇作品系据《聊斋志异》改编。《聊斋志异》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明末清初山东地区,彼时彼地是明军、清军、农民起义军交战的重灾区,蒲松龄笔下描写百姓所遭受的抢掠和屠杀,非常真实。《醒梦骈言》第二回据《聊斋志异》的《张诚》改写成白话。《张诚》叙说张诚夫妻在明末清初战乱中的悲欢离合,张妻是被清军掳去,清军入关来掳掠妇女和财物在当时是常态,可是到了乾隆时期,如果照写便有毁谤污蔑丑化之嫌疑,《醒梦骈言》的编撰者显然不敢冒此风险,于是把故事的时间推前至明朝初期的“靖难”,将掳掠张妻的清兵改写为朱棣的燕兵。
创作小说更不用说了,作者绝对回避故事发生在清朝。比较著名的小说,《儒林外史》楔子写王冕,这是元末明初,正文开头标明故事时间为明朝成化末年,尽管读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写的是清朝当时的现实。《野叟曝言》的故事开始于明朝弘治年间,作者夏敬渠在作品中极力鼓吹道学和吹捧帝国的强大,但他还是不敢承认写的是当朝。《歧路灯》要为子弟指明做人的路向,道学气味也很浓厚,不是什么敏感和犯忌的话题,可是作者仍要说这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往事。
《红楼梦》在时间上则采取烟雨模糊法,干脆说故事的时间无考。第一回空空道人对石头说,你的第一段故事自说有些趣味,可是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回答说:我师何太痴耶!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为了抹去时间标识,小说中的地名,有明朝的称谓,也有清朝的称谓,职官还保有宋朝的名目,人物服饰似清朝也有似明朝,曹雪芹在时间的模糊处理上较其他小说更加缜密。
三
乾隆时期描写世情的小说声明故事不发生在本朝,仅此声明还是不够保险的,乾隆帝解读《坚磨生诗集》的索隐法,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作小说者也不能不再设防线。《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在《自序》中发誓说自己的小说,“空中楼阁,毫无依傍,至于姓氏,或与海内贤达偶尔雷同,绝非影射。若谓有心含沙,自应坠入拔舌地狱”李绿园担心自己小说被人索隐,并非杞人之忧,《儒林外史》行世数十年后,咸丰、同治年间文网已松弛,就有人出来索隐,同治年间的金和《儒林外史跋》就指小说中人物皆有所指,其中有些确是人物的原型,但有些便是捕风捉影,说“《高青邱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事”,说吴敬梓影射的方法,“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这就是猜谜索隐了。《高青邱集》事见第八回和第三十五回,蘧公孙从逃亡的南昌知府王惠手中得到《高青邱集》手稿,署上自己名字“补辑”以出名;后来又写庄征君应征进京时遇到卢德,谈到卢德在京中访得的《高青邱集》,庄征君告诫卢德说:“像先生如此读书好古,岂不是个极讲学问的?但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高青邱即明初诗人高启,被明太祖所杀,其书被禁。此为明朝往事,且文人好读禁书,历来如此。吴敬梓写此情节或有感于现实,若要说他影射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则是没有根据的。吴敬梓在乾隆文字狱高潮中断无此“狂悖”。
曹雪芹写《红楼梦》更加小心,不仅时间让你摸不着头脑,连地点也让人猜不透。“甲戌本”凡例说,“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盖天子之都,亦当以此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第十五回凤姐弄权铁槛寺,修书一封派旺儿“连夜往长安县”,凤姐之所在当是长安;第十七回妙玉随师父来都中,“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先暂住西门外牟尼院,后来到荣国府大观园,贾府在长安;第五十六回甄宝玉在梦中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证明贾家荣国府确在长安。然而,第三回写黛玉投奔外婆、舅父家,从扬州乘舟沿运河北上,登岸上轿,径直到荣国府,又明明写贾府在北京。且书中一些街巷地名,为北京城内实有,一般读者皆相信大观园在北京。不过地域描写的矛盾却又令人难解,《红楼梦》曾题名“金陵十二钗”,探春远嫁,判词有“清明涕送江边望”之句,“涕送江边”当然不是北京,当是南京。这些在地域描写上的前后矛盾并不是曹雪芹头脑混乱所致,而是煞费苦心有意为之。
《红楼梦》的素材出自曹雪芹的家庭生活,但曹雪芹却并不是写自传和家史,为了避免读者把贾宝玉和曹雪芹、贾家和曹家划等号,他在描叙中用了虚拟和艺术的手法进行了区隔。贾宝玉身上有曹雪芹的影子,但贾宝玉绝不就是曹雪芹,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脂砚斋在第十九回有批语云:“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庚辰本)脂砚斋说他在生活中不曾见过宝玉其人,他熟悉曹雪芹,他不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贾宝玉其实是一个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再如贾家与曹家,隐隐约约相似的地方不少,但细细考究,又不能下一个贾家就是曹家的结论。比如贾政之女元春做了皇妃,但曹家没有出过皇妃,曹寅的女儿,亦即曹雪芹的姑母,嫁给镶红旗平郡王纳尔苏,只是一个王妃。并且王妃是曹雪芹的姑母,元妃却是宝玉的姐姐,这能说贾家就是曹家吗?时下竟有人据王妃是曹雪芹的姑母,则推论宝玉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断定《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曹頫了,真是荒唐之极。这样的论者实在不知道曹雪芹是在怎样的文化专制高压之下进行创作的,根本不理解作者何以用“狡猾”之笔(“甲戌本”眉批)。
四
政治的高压,必然会激起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有良知的作家总会通过自己个性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由的诉求,小说家也许不敢选择时事政治作为创作题材,但他们可能把这种诉求转向远离政治的人性和人的情感领域,由此产生的作品看似超越了当下的政治,可是却在大历史的高度上和在人性的深度上干预了政治。
《红楼梦》的创作就是这种转向的典型代表。曹雪芹在第一回借空空道人和石头的对话,反复强调“毫不干涉时世”,书中“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全书写的只是几个“或情或痴”的女子,她们也没有班昭、蔡文姬之德能,都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女子,作者只是要把她们的真性情写出来,所以概而言之“大旨谈情。”曹雪芹着力描写的是青春的美好,人性的丰富和光彩,爱情的细腻和轻柔。正因为这些深入到灵魂的惟妙惟肖的描写,宝玉、黛玉和宝钗以及一群少女的悲剧才具有震撼人的力量,才在大历史的高度揭示了封建礼教及其制度的不合理,为延绵了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敲响了丧钟。
《红楼梦》,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乾隆文字狱高压的产物,历史走到18世纪的乾隆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到了烂熟的程度,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深重的危机,欧洲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西方殖民者正酝酿用舰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而乾隆帝仍以君临世界的自大态度固守祖宗法度,以曹雪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已感到衰败之来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说贾府“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不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十三回又借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警告说:登高必跌重。贾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难免乐极生悲。“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曹雪芹的感悟不是超历史超现实,他的思想恰恰来自他的家庭和他的经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康熙帝关系非同一般君臣,这从曹寅的奏折和康熙在奏折上的批语可知,曹寅病重,康熙帝亲手为他开药方,为曹家后事谋画,更是明证。因此,曹家也不可避免地与康熙帝诸王子发生关系,与后来的皇位之争脱不了干系,雍正帝的政敌胤禟寄顿在曹家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的一对镀金狮子,曹寅的姻亲李煦曾给雍正帝的主要政敌胤禩送过苏州女子,均成为曹家的罪案。曹家拥有田产庄园,所以第五十三回能写黑山村乌庄头缴租讲庄园收成;曹家几代任织造官,本身就是官商,熟知江南的商业情形,贾家摆设有那么多外国产品,王熙凤对赵嬷嬷说:“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曹寅虽为织造官,但同时又是康熙帝在江南的耳目,承担着拉拢和监视江南士人的秘密使命。简而言之,曹家处在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中心,没有这种客观的历史和家庭的条件,曹雪芹尽管禀赋文学高才,也是写不出《红楼梦》的。
《儒林外史》也是写人,写在科举制度之下的士人。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吏的制度,也是教育制度。它相对“九品中正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发展到清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了。批判科举制度的小说,前有蒲松龄《聊斋志异》之《叶生》、《司文郎》、《王子安》、《素秋》、《于去恶》等数篇,其中也有对试后等待发榜的士人的痴迷近似发狂神态的描写,但蒲松龄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考官衡文的有眼无珠,《司文郎》就塑造了一位盲眼却能用鼻来鉴评文章的鬼僧,他对文章香臭的敏感,非考官所能及。《于去恶》的主人公说,主考官不是眼瞎,就是爱钱,这等考官主持科举,“吾辈宁有望耶”!吴敬梓《儒林外史》已不再指摘科举制度某个方面的弊端,他质疑的是整个科举制度,他认为科举制度扭曲了人性,刻划了一系列被科举腐蚀和毒害了灵魂的人物。吴敬梓关注的是人性,他哀怜的是被科举制度塑造的猥琐庸俗的灵魂。
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创造性的产物,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心灵活动离不开他生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环境,必定要受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宗教等状态以及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尤其突出和深刻。乾隆是清代文字狱高潮时期,文字狱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生动体现。乾隆文字狱压制了时事题材的写作,并且使得那个时代的创作具有了特殊的印记,但政治的高压迫使作家把关注点转向人和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产生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这大概是制造文字狱的乾隆帝未曾想到的吧。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206.2
A
1000-5072(2015)04-0018-06
2014-11-05
石昌渝(1940—),男,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