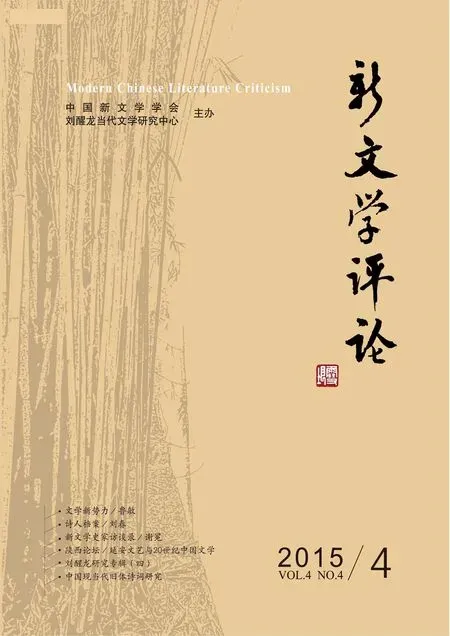论刘春:通向内心的现实主义
2015-11-14李小建
◆ 李小建
论刘春:通向内心的现实主义
◆ 李小建
一、由语言开始向内心逼近:刘春诗歌中的“元诗歌写作”
说出这个词,天色就暗了下来
旧相册收拢飞翔的翅膀
哦,这是八月的镰刀,这是血,这是
一段感情的惨淡开端。主角
是一块风华正茂的岩石
稻草已经燃尽,雪花扑向
独居者的屋檐,有人在暗中写字
他写下“恨”,他所暗恋的
女人就永无宁日,而他写的是“爱”
隔壁传来了幽暗的灯光
——刘春《生活》
在刘春的诗歌中,“写下”、“说出”这些词语极其常见,甚至成为具有特色性的“刘春式”写作方式。“如果我写下:‘草垛’。我清贫的二姐刘青禾/是否会从歧路村某一块土地里/抬起头?”(《坡上的草垛》“在雪白的纸上,我打算写下这样一些词语:北方、风、忍耐、内在的火……”(《二十四节气:大雪》)“那一年我写下‘青草’/邻家的少女远嫁到了广东/我写下‘黄花’/秋风送来楼上老妇人咳嗽的声音。”一种从词语开始的写作,“写下”、“说出”意味着将词语带进现实,“他写下‘恨’/他所暗恋的女人就永无宁日/而他写的是‘爱’/隔壁传来了幽暗的灯光”。这种与书写动作同步出现的现实叙述,让人感觉诗人在纸上进行一场“词语召唤术”。“当说出这个词,天色就暗了下来。”词语本身带着一种巨大的魔力,它听从于诗人内心的召唤和引导,但“写下”、“说出”这种写作行为产生时,现实的境况就随之发生转变。当然,这只是诗人内心的现实发生转变,词语的“写下”、“说出”构成了诗人内心发生转变的共时性的推动器,是一种主体行为对词语的关照和审视,也是诗人内心被词语照亮。诗人的现实和生活被“写下”的“词语”映照,进入一种“主观真实性”的叙述语境和氛围,但同时又在提醒读者,叙述者正在“写”一首诗,在诗中,事物作为“词语”而不是事物自身出现,它是经过诗人内心审视的、关照的,带着诗人个人经验、回忆和审美取向的。
刘春这种在诗中由词语开始,展示一首诗如何形成到完成的写作,类似于一种“元诗歌”写作,即关于诗本身的诗。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意在表达诗人对语言呈现/展开过程的关注,使写作行为等同于写作内容。在这类诗人看来,诗歌“语言言说”的可能性实验,本身已构成写作目的,诗不仅是表达“我”的情感,更是表达“元诗”本身的。在刘春很多诗作中,我们能看到诗人在通过“语言本身”说话。在《坡上的草垛》一诗中,刘春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也在表达诗人对词语/语言呈现和展开的过程:
而我写下它,义无反顾。我甚至写下了
另一个破旧的词语:“坡上。”坡,山坡的坡
土坡的坡;上,上面的上,上方的上,甚至是
上帝的上、苍天在上的上,而不是
上司的上,高高在上的上
接着是“草”,青草的草,干草的草,“离离原
上草”的草。偶尔也是草包的草、草率的草
但必须有激情,有泥土的清新和炊烟的温柔。
然后是“垛”,柴垛、土垛、棉垛、木垛
它暖、踏实,与土地和乡村有关
与一家人的生计和冬日的长短有关
再深入些:与一个叫小朵的女孩有关,那一个
下午,她红着脸站在十二月的土坡上
期期艾艾手足无措,她的情人还来不及
替她拾掉鬓边的稻草
是否缺少了什么?我再一次写下
这个婉约的词组:“坡上的草垛”
哦,“的”!我的?你的?坡上的?还是命运中
无法避开的?
今天,我站在街角,看到一个酷似二姐的女人
坐着别人的运草车从中山路一闪而过
——刘春《坡上的草垛》
刘春在《坡上的草垛》一诗中以巨细靡遗的方式向我们展开了“坡上的草垛”这个词组拆解和组装的过程。也许受益于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刘春在这首诗中进行了“文本细读”式的“文本细写”。如果说“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以近乎严苛的方式拆解一首诗,让人看清一首诗从整体到一个词语的所蕴含的结构、细节、真实含义和肌理的话,那么刘春这种诗歌元写作则是反向向人展示一首诗歌如何从一个词语、一个词组、一个意象开始,如何一步步展开、深入、融汇,从而形成一首诗歌的。这首诗歌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任何解读和阐释了,因为解读和阐释已经在诗中完成了。这样的写法在刘春的《广西》、《兴安》等诗作中也出现过,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拆词游戏”,刘春像一个语言学家一样以手术刀般的精细、专注向自己的内心深入、逼近,发掘一个普通词语、词组、意象对诗人所蕴含的特殊意义。这首诗看似从一个词组“坡上的草垛”开始,实际上是从诗的末尾“今天,我站在街角,看到一个酷似二姐的女人/坐着别人的运草车从中山路一闪而过”这个景象开始。诗人在唤醒、拆解、阐释语言的同时也被语言映照,“坡上的草垛”这个词组像一个光源,诗人在持续为这个光源注入能量,最终探照出内心深处所不为人知的部分。而这个过程是语言和诗人情感表达的互相发现和照亮,诗歌写作行为和诗歌内容是同步发生的,最终汇聚到最后一句,其情感也随着一步步的能量聚集而达到顶点。
“我的诗歌的一个秘密(如果算是秘密的话)就是常常设置障碍物,将通向最终目标(意义)的路途一阻再阻,有时候是句与句之间的有意拖沓,上一句是肯定、陈述,下一句就有可能出现否定、递进、蔓延等不同的意向;有时候是词与词之间的互相证明或反驳;有时候这些方式甚至在句群,在段与段之间进行。”在通向最终目标(意义)的路途上,刘春在诗中沉迷于词语的浮现,事物的去蔽,意义的延宕,在词语/语言的引导下最终到达一种澄明与敞亮的存在本真。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人在语言中,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预先给他规定了视野,引导着他的眼光,为世界赋予了意义并为世界(万物)命名,正是语言,使世界成为其所是,使万物成为其所是,语言对于人,就像生息于其上的大地,就像他须臾不可或离的家园。
“诗歌在语言中发生。”一旦“写下”、“说出”,语言就经过诗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存在。刘春的诗歌在“我说”与“语言言说”中同步进行,在叙述与内心的表达中相互交汇,彼此发出回响与和声。刘春的诗歌既不是完全“零度写作”和“冷抒情”,也不是毫无节制的抒情,他在激情和克制中冷静、清醒、反思,完成一首诗的创作。正如他在《兴安》一诗中所表达的关于诗歌的看法:“像我热爱的诗歌,从来不在高处欢呼,/也从不在低处哀号/每一笔每一画,都是对兴盛的向往/安乐的渴望,以及不露痕迹的/赞美。”
从刘春的诗歌写作中可以看出,刘春对词语/语言充满迷恋,他对那种“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这种简单概念化的诗歌写法进行了驳斥:“事实上,一首出色的诗歌并不排斥所有的词,各种词性有各种功能,各种词汇的不同组合造成了语句中的‘气’,造成了语义间的互证、互否、悖论、延绵、递进……现代汉语的功能与魅力尽显于此。”
二、基于内心的思考:从书斋到现实
还有什么不能被展览?还有什么
不会被吃掉?我在笼子里撕我的身体
围观者在笼外啃他们的良心
我的胃在冒火,而他们比我更饥饿
这是命,时代的肺结核
感染上面目模糊的祖国。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讨论的了,结果早已被商定
广场上,乡村医生对人群举起了针筒
——刘春《卡夫卡》
在通往内心的现实主义的途中,语言不是刘春诗歌写作的唯一密道。面对社会和诗歌写作的双重复杂性,刘春在诗歌写作中注入了个人经验、时代精神状况和个人思考。在刘春2002年前后所写下的一批名作《卡夫卡》、《艾略特》、《艾兹拉·庞德》、《低音区》中,展现了其在倚借大师思想资源、个人阅读经验的同时,视野变得更为开阔,思想变得更为犀利。在迅速抛开《大地的婴儿》、《忧伤的月亮》这样的浪漫主义“青春期”写作后,刘春的诗歌观念和诗艺也日益精进。
“还有什么不能被展览?还有什么/不会被吃掉?我在笼子里撕我的身体/围观者在笼外啃他们的良心/我的胃在冒火,而他们比我更饥饿。”卡夫卡式的“饥饿艺术家”在展览/观看、笼子/笼外、吃掉/饥饿、身体/良心、艺术家/庸众双重悖逆、对照中陷入一种无比清醒的思考:“而他们比我更饥饿。”在《卡夫卡》一诗中,刘春在诗歌中揭露出时代的精神状况:贫乏、无聊、贪婪与平庸。在诗歌中,刘春完成了身份角色的置换和思想的转述:“这是倦怠者对现实的否决,是普通公民的尝试:他是否有资格支配自己的一生?”
在《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创作谈)》中,刘春如此写道:“阅读和思考在这个时候展现了它们的魅力。2001年,我开始阅读各种思想性的随笔,因为不知渊源,故读得极滥。基本上是听说什么书好,就去找来读。我这人天生有些‘个性’,更易于接受那些‘背经叛道’的、边缘的、个人化的著作,它们打开了我思维的另一扇窗口,让我关注到比文学更宽广的东西。也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吸引了我的目光,趁着那份热情,我回过头阅读了不少90年代的思想文本。通过对非文学著作的阅读,我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明显的改变,诗歌在无形中也发生了变化。”
阅读视野的拓展,让刘春的诗歌写作拥有了更多基于内心和现实的思考,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有了更多的“思想性”和“智性”。刘春在完成向大师的致敬的同时,也在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思维的界限,反思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和境遇、个人的现实和生活、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很多致敬大师的作品本身其实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正如诗人杨克所说:“有的诗表面上看‘生活在别处’,例如《灯心草——献给顾准》。但别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他尝试一层层剥开‘他人’的茧子,进入自己的生活内核之中……我认为刘春这些写作是有效的。”
刘春的诗歌写作中充满了反思、质疑和诘问,当然如果这种反思仅仅来自阅读和书斋,则往往会堕入一种“假想性”的凌空和高蹈。事实上,刘春诗歌中的反思、内省气质更多是指涉现实和指向内心的。刘春除了“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外,还有一个“晚报编辑”的身份。刘春自1995年进入新闻界后,就一直在桂林日报社工作。在他的很多诗作中,“晚报编辑”、“小职员”、“小公务员”的身份和工作为他提供了观察现实和生活的入口。他身处其中,写下与内心和现实相关的诗篇。“没有必要愤怒,那事儿/发生在另一条街。没有必要/欢笑,是别人中大奖,别人捡到/钱包。没有必要惋惜。副委员长受贿/劫持人质者落网……没有必要死亡,正如/没有必要生存。”(《晚报新闻》)没有必要愤怒、欢笑和惋惜,因为那都是报纸上他人的故事,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个“晚报编辑”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变得不再激情和热血,甚至有些冷漠,直至绝望:“没有必要死亡,正如/没有必要生存。”而在《榕湖北路一号》(榕湖北路一号为桂林日报社地址)一诗中,诗人描绘了一个“晚报编辑”的一天:“必须八点钟以前进入一幢七层建筑物/(四楼的某个角落有你浓重的体温)/花大部分时间,用于/与那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点头、微笑/煞有介事地讨论国家大事/他们左右你在一个城市里的形象。”诗人在“那些鸡零狗碎,那些小悲小喜,与我心存芥蒂,又充满默契”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与卡夫卡、艾略特,这些同为“小职员”的大师达到精神上的互通。
三、介入内心和现实:指向内心和自身的反思
请原谅我做一个怯懦的人
不申诉,不辩解,不高声叫喊
不斜视,不抗议,不因爱生恨
请原谅我一再降低额头的海拔
面带微笑,甚至有些谄媚
——刘春《请原谅我做一个怯懦的人》
从2005年后,刘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诗歌史的写作和研究的同时,诗风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诗歌写作的语言上由优美转向平实。刘春在2005年前的诗作多“自然性”和“抒情性”,《忧伤的月亮》这一时期的诗作姑且不提,在刘春2004年出版的《幸福像花儿一样》中,语言优美、明快,在语言上醉心于美的意象和意境,流露出“浪漫主义”的感伤。而2005年后,刘春的诗歌语言转向平实,甚至粗粝,不避俗语。他的诗歌语言既不口语,也不书面化,而是一种经过内心审视、修正的平实化的语言。在《月光》一诗中的最后一段,刘春以一种平实而不动声色的语言达到让人心灵震撼的效果。“而屋内,孩子已经熟睡/脸蛋纯洁而稚气/他的父母坐在床沿/其中一个说:过几年,他就该去广东了”。“月光”只是叙事的背景,诗人用一句“过几年,他就该去广东了”这么平白如话的语言揭示了孩子作为打工者的命运。平静而又残酷。
如果说《忧伤的月亮》时期的刘春是在云端歌颂自然的少年的话,那么《幸福像花儿一样》时期的刘春更像一个充满激情、思想激荡的青年,而进入“中年写作”时期的刘春,其诗歌关注的视角也从高远、浪漫之物,知识分子式的书斋和小职员的“晚报新闻”转到世俗、日常、底层、自身和内心。这是一个不断向后退撤,向内心收缩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原了“诗人刘春”到“刘春”的转变,他不在受限于其身份,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去观察,去感受,去反省,去写下真正属于自己的诗作。在《自省书》中,他如此深刻的剖析、反省自己:“你的灵魂终日游荡/找不着身体/你的身体出入各类场所/又不知为何而活/稍有空闲,你就沉迷网络/以游戏抵消午饭/对八卦的熟悉程度/甚于家人的生日/重要之处在于/你的怯懦与时俱进/想发展,不懂科学/去开会,不敢表达/真实观点”。诗中充满了自嘲、自省与对自我的质问:“现在,我只想问——需要多少时间/你才能像当年那样/轻狂而无畏/需要多少勇气/你才能毫不迟疑/对世界说:/‘我是刘春。’”不是高声控诉和呐喊,而是毫不迟疑,不卑不亢地说:“我是刘春。”诗人清醒的坦诚和反省让人感到震撼。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连“认识自己”都做不到,更别提反省了。
而在《请原谅我做一个怯懦的人》中,刘春深深刻画了一个“怯懦的人”的形象:自私、冷漠、健忘,面带微笑,甚至谄媚。诗人不再是传统的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的形象了,这样“怯懦的人”形象让人羞于去承认,但却是很多人内心的真实的自己。但诗人的反省没有在此止步,他更进一步:“我是否还能安静地写字,是否会继续说——请原谅我在黑暗中沉默,像一具干尸?”刘春以清醒的自我认识、真诚的反思和近乎残忍的自我剖析将反省指向自身和内心。这种源于内心的悲悯和反省是刘春“介入现实”的途径,由内心出发,写下“卑微的事物”,它比眼中所见的现实更具有“现实感”和“真实感”。内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和“对立感”。而是“如今,你已与他握手言和”(《小公务员的一天》)。
刘春对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一个诗人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就不会有出色的洞察力;缺乏对生活的深刻认知,就不可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缺乏独特而深厚的经验的文学作品,即使蕴涵着情感,这种情感也是浅薄的,没有力量的。因此,在我看来,诗歌并非缺少读者,而是缺少以一种合理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的力量。一首诗无论辞藻多么华丽,一件艺术品无论打磨得多么光亮,如果缺乏生命和生活的痛感,不能令读者惊讶、反思,那么它肯定是贫血的,没有灵魂的”。刘春对诗歌技艺的修炼和掌握已到了炉火纯青甚至忘记“技艺”的地步,而关乎生命和生活的痛感,现实和内心的力量,那才是一首好诗的源头。由内心出发,抵达现实或将纷繁的现实与日常,纳入内心的关照、审视与反思,是一种双向的回环通道,刘春作为一个具备“真诚”、“内省”与“反思”气质的诗人,似乎已找到通往内心的现实主义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