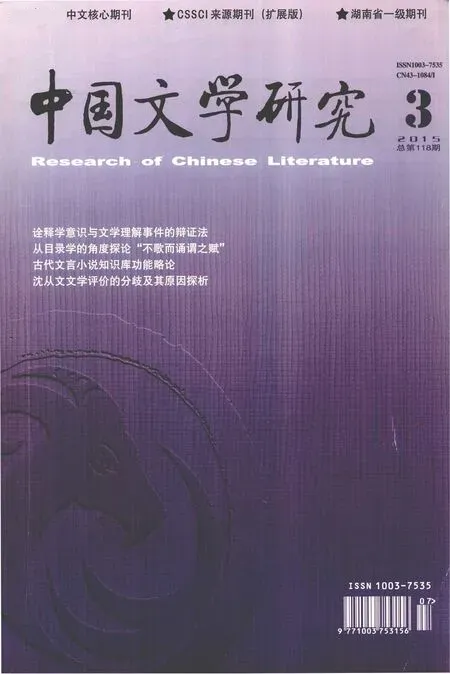挣扎而扭曲的心魂:张爱玲作品中的“怨女”形象分析
2015-11-14孟丹青
孟丹青
(南京邮电大学期刊社 江苏 南京 210042)
一、怨女的古典谱系与现代变异
“怨”生于“欲得”而“不可得”,因此,“女性”因其“被动”与“受控”的“性别史”而注定比男子有更多的“怨”。“怨女”形象自古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卫风·氓》中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外貌忠厚老实的商人热情追求女主人公,获得她的芳心。女子嫁到男家后辛勤劳动,谁知道家境好了以后,丈夫却变了心。“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主人公感慨桑叶未落的时候,枝繁叶茂,吸引斑鸠贪食桑葚。女子忠贞不贰,男人却喜新厌旧,变化无常。警告少女不要痴情,男子痴情可以轻松摆脱,女子痴情却不可解脱。最后女主人公发出“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怨言,往日男子信誓旦旦,没想到今天背叛了自己,既然已经背叛,不如分手算了。在这首诗里,女主人公从热恋到结婚到被遗弃的曲折的一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主人公内心充满哀怨和不满。《小雅·谷风》中“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同样表达了女子对三心二意的男子的怨言,男子恐惧担忧失意的时候娶了女子,安逸享乐的时候却抛弃了女子,忘记了女子的大德而只记住她小的过错。此外,像“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等诗词中也塑造出楚楚动人,饱受忧郁痛苦折磨的怨女形象。至于“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这样描写失意宫女孤寂幽怨生活的宫中怨女诗更是数不胜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与欲望受到封建礼教的严格禁锢,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怨女显而易见是没有主动性的,她们只能被动地等待远方丈夫的归来、君主的临幸或者被动地接受被遗弃的命运,或者只能在梦里曲折地表达对爱情与幸福的渴望。
“怨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男权中心社会长期压抑的结果。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人类文化基本上是由男性创造的,女性成为没有主体地位的他者和欲望化对象。波伏娃指出,“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者’”。男人是主体,女人成为只能为主体而存在的客体。封建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建立了严格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阳尊阴卑,所以男尊女卑。对妇女的要求是“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女子必须以服从为天职,“妇、服也”(《仪礼·丧服》),“妇人,伏于人者也”(《礼记·大戴》)。更为残酷的是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要求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一夫多妻,女人却只能从一而终。在男权中心社会,妇女毫无社会地位与权力可言,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客体”与“他者”,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正是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长期压迫导致大量“怨女”的产生。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走上漫长的现代转型之路,妇女解放运动也从如火如荼再到渐行渐远,其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这些“怨女”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成为浮出历史地表但仍然被遮蔽的存在。于是,“她们”在幽暗的现代性里挣扎,在没有挣脱的时候,各种来自外面与她们自身内部的不可控之力就往往使她们变异出伤己灼人的火舌。
而在近、现代时期的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进程发生得尤其惨烈,她们死命挣扎,而终于被“男性的”与“陈旧的”力量扭结住,挤压到扭曲变形,露出可怖的表情,那脸形已经失去了古典“怨女”的“哀怜”,而显示出阴森而怨毒的“鬼”似的惨白与冷漠。这也许是女性在进入“自主世界”的前夕所遗留下的异化的“蝉蜕”,只是它恰好标本似的落进了张爱玲的眼中,被她用阴冷的旷世奇笔临摹下来,封存在了“中国新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之中。从文学形象谱系来看,《怨女》和《金锁记》便是那“哀怜”的“古典怨女”的现代变异。
二、觉醒而异化的女性意识的惨烈闪露
《怨女》是张爱玲1966 年对20 多年前所写《金锁记》的重新创作,她对“怨女”这一题材的反复挖掘,显示出其对“女性之怨”有难以释怀的刻骨铭心般的生命经验。《怨女》在篇幅上比《金锁记》增加了三倍之多,内容上增加了许多细节和心理描写,尤其是对女主人公结婚前的生活和心理活动进行了刻画。语言更加平实,技巧更加圆熟,柴银娣的形象比《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加丰富生动,人物性格也更加完整。如果说张爱玲在《金锁记》中追求的是一种戏剧化、脸谱化的夸张和突兀,有一种炫技成分在里面;《怨女》则给人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感觉,矛盾冲突不再那么激烈,有一种与现实的和解妥协。
在《怨女》中,张爱玲首先交代了银娣嫁给姚家的原因,强调她是出于自愿嫁给残疾的二少爷。银娣青春貌美,充满生命活力,被称为“麻油西施”。本来她对对门药店的小刘有好感,但是当小刘托她外公外婆来提亲时,她却谎说哥嫂不回来而把外公外婆打发走,害怕结婚后和小刘过贫穷的日子,“小刘不像是会钻营的人,他要是做一辈子伙计,她成了哥嫂的穷亲戚,和外婆一样。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这时媒婆第二次上门来为姚家二少爷提亲,哥嫂并没有逼迫,而她则一口答应了。因为她不甘心平淡,想过一种舞台上的人生,“她以后一生一世都在台上过,脚底下都是电灯,一举一动都有音乐伴奏。又像灯笼上画的美人,红袖映着灯光成为淡橙色”,“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虚荣心和对物质享受的渴望使她拒绝了自己喜欢但没有钱的小刘而选择了瞎眼但有钱的少爷,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地位。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妇女被牢固地束缚在家庭里,女性的社会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必须依附男性而存在,如果没有这种依附关系,女子便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由于没有经济独立,女性只有通过婚姻获得合法生存途径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银娣也不例外。
银娣和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不同。祥林嫂所遭受的苦难完全是宗法制社会和外部环境强加给她的,她个人没有选择权,无力反抗像大山一样压在她头上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统治,她的反抗如同鸡蛋碰石头只能让自己头破血流。她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毒害,只能任由命运摆布,成为麻木的无意识的存在,她对自己所受的苦难没有任何责任,鲁迅称她的命运是人间惨剧而不是悲剧。《怨女》中的银娣则生活在风气相对开放的十里洋场——上海,在麻油店替哥嫂打工,并没有穷到非要嫁给一个残疾人,在爱情婚姻上也有相对的自由,但是她最终把自己推向了不归路,这是她卑微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也是她贪慕虚荣的结果,所以她必须对自己的悲剧命运负一部分责任。她有朦胧的自我意识,在选择中体现了她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但是她的自我意识是已经被金钱和世俗观念异化的自我意识。在她身上,对金钱地位的渴望战胜了对爱情幸福的渴望。嫁到姚家后,她似乎得到了荣华富贵,暂时满足了虚荣心,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肉体和情感上的压抑与不满足,长期积累导致她成为一个内心充满怨恨毒汁的怨女和泼妇。
《怨女》和《祝福》相比,减少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力度,但是却增加了对女性自我的批判。张爱玲敏锐地指出怨女的产生不但有其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而且有女性自身的原因。怨女的不幸,不仅是社会导致的,也是个人导致的,这里有更深刻的对人性的挖掘。银娣由于缺乏女性独立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选择不平等的婚姻,自愿走进表面风光实则冷酷无情的封建大家族中去,成为即将消失的封建家族制以及生理有残疾的丈夫的陪葬品,把自己埋进死气沉沉的坟墓,一步步由女神变为怨妇,她的自我意识刚一闪露便被金钱异化了。
张爱玲对女人是宽容的,容忍她们的小奸小坏,容忍她们的替自己打算、自私、贪图享受等等缺点,对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抱有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她曾经说:“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慈悲,了解,安息”。张爱玲塑造银娣少女时期形象时,突出了她的神性和美丽。“短短的脸配着长颈项与削肩,前刘海剪成人字式,黑鸦鸦连着鬓角披下来,眼梢往上扫,油灯照着,像个金面具,眉心竖着个棱形的紫红痕”。新婚的时候,她如同一个高贵的女神,“戴着珍珠头面,前面也是人字式,正罩住前刘海。头上像长了一层白珊瑚壳,在阳光中白烁烁的,累累的珠花珠凤掩映下,垂着眼睛,浓抹胭脂的眼皮与腮颊红成一片……”年轻的时候她风风火火,独当一面,大胆泼辣,敢说敢骂,回忆那些“大姑娘!大姑娘!”的喊声,对于她是一件快意的事,毕竟那些爱慕正是她生命价值的体现,是生命之花盛开、生命意识飞扬时期的表征。而到了晚年,她成了瘦小、干瘪、病殃殃的老太太,“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她成了吝啬鬼,舍得花大笔钱抽鸦片,却为了省钱吃咸得齁人的菜,炒菜为了省油,用一直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被亲戚们取笑。正是这前后鲜明的对比,使她的悲剧更加触目惊心。嫁到姚家后,“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一步步泯灭了银娣正常的生理欲望和爱的欲望,扭曲了她的心理,把她由“神”变成“鬼”。她摆脱不了封建家族制及男权社会的压迫,也摆脱不了黄金的锁链。古典诗词中的怨女往往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对以封建家族制为中心的父权社会毫无反抗能力,只能服从和逆来顺受。儒家伦理道德培养妇女自甘卑贱、自我奴役的心态,要求女性泯灭自我,忍让顺从,银娣并不是一个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温柔恭顺的人,她一直在反抗环境,不甘心做任人摆布的客体和他者,她嫁到姚家后产生的“怨”充满愤怒,也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但是由于个体与社会力量的悬殊,她的主体性最终没有确立。她对环境的反抗是毁灭自己也毁灭周围的人。
舍勒说:“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愤怒;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这种自我毒害的后果是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他指出怨恨产生的原因有三点:“一、在这种情绪产生之前,必须曾经受过一次他人的伤害;二、对他人的伤害不能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击,必须隐忍(挨了一耳光即回一耳光,就不会产生怨恨;三、隐忍因于一种至少是暂时的‘无能’感或‘软弱’感”。银娣在结婚前并不是一个怨女,她之所以成为怨女,和长期受到的伤害有关。她嫁到姚家,除了生理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还必须适应封建大家庭森严的等级制度,不能逾越半步。婆婆指责她起床晚,“我们过时了,老古董了。现在的人都不晓得怕难为情了,哪像我们从前”。银娣因为家穷而攀高枝,受到姚家全家人歧视。大太太、三太太在一起时有说有笑,却连话也不愿和她说。生活在这样充满敌意的封建宗法制大家庭里,就像林黛玉所感受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人与人之间毫无温暖与亲情可言,她的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又无法发泄,只能隐忍,对现实产生抱怨和无能为力感。而她的性格偏是争强好胜不服输的,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和叛逆性。她采取的反抗手段之一是对丈夫刻薄无情残忍,骂他“眼睛瞎,耳朵也聋”。她丈夫最心爱的核桃念珠找不到了,她看见了却不告诉他,而是拿出核桃钳子,把念珠一只一只夹破。丈夫毁了她的幸福,她也要毁掉丈夫最心爱的东西。她采取的另一种反抗方式就是去勾引风流倜傥的三少爷,对三少爷的喜欢既是她身体的本能需要,又何尝不是对丑陋无能的丈夫的报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大胆挑战。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分得了一部分家产,自立门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经济独立,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扭曲变态,丧失独立能力。她为了控制儿子,让儿子吸食鸦片,还许诺等他娶亲后,花钱为她买女戏子做妾,用腐朽的生活方式把儿子和自己一起埋进坟墓里。她通过对儿子的控制实现了对男权社会的报复。当姚三爷为了借钱想来勾引她时,她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做成的圈套”而拼命反抗,“这些年来的积恨,使她宁可任何男人也不要”。两人反目成仇,不再来往,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点亮色和温情也随之消失。从少女到少妇到寡妇,也是她的生命欲望和热情一点点消失的过程,剩下的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封建家长制、男权文化以及金钱的重重压制使她由女神逐渐变为怨女和恶妇,泯灭了她的人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爱玲揭示了女性压抑之下的扭曲和愤怒,就像有学者指出的:“这种隐含攻击力量的阴性愤怒和潜在声音,成为文本中可供作家运用的资源。尤其在批判父权秩序上,更布满此种潜在的阴性情绪。这些女性人物的愤怒(包括焦虑),对象征‘菲勒斯’的宗法父亲造成重大的创伤与羞辱”。女性的压抑长期被历史所遮蔽,张爱玲却掀开了这被遮蔽的一页,让妇女的怨恨从中喷薄而出。封建文学史是男性文学史,即使是那些动人的怨女诗也是由男性来书写和言说的,刘思谦说:“尽管文学史上不乏美女、淑女、贞女、贤妻、良母和女才子、女英雄形象……但她们从总体来看是作为男性言说和描写、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化、符号化而出现在文学中的,女性的经验、女性对自己生存处境生存状态的感知和思考被阻挡在文学之外,真实的女性在文学的世界里一片沉默暗哑”。当女性由被男性代言到自己为自己代言,拥有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话语和男性话语平分秋色,女性开始创造文化的时候,真正的女性文学也就产生了。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言说主体,她在中国最早写出了被压抑的女性生存经验,其塑造的怨女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使“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由平面走向立体,由浅显走向纵深,极大地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引发人们对妇女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祛怨”与女性主体性的建立
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波伏娃把“他者”定义为“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妇女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发出自己声音、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因为没有主体,她们必须依附男性才能存在,一旦丧失这种依附关系或者这种依附关系不能让她们满意,不能满足她们的精神和肉体需要,她们自然会产生怨恨、失望和不满,成为怨女甚至疯女。怨女的产生,不仅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和自身缺陷导致,还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导致,这也是她们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的原因。但是要想消除怨女产生的根源,除了社会制度的完善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外,还需要妇女自身解放和自身主体意识的确立。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思想、启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随着人的价值被发现,女人的价值也被发现,女权运动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而兴起。而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启蒙被救亡所代替,阶级解放代替了人的解放,个人的主体性并没有确立,只是被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控制。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到处能听到“男人女人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妇女变成被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的“铁姑娘”“女干部”形象,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不但没有觉醒,反而丧失了固有的女性意识,被动地转变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男性权威社会赋予她们的新形象,“五四”时期刚刚觉醒的自我意识再一次丧失了。就像戴锦华所说的:“当代中国妇女尽管在政治、法律、经济上享有相当多的权利,但与之相适应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性别群体意识却处于匮乏、混乱,至少是迷惘之中”。
一直到今天,中国妇女似乎满足于她们的现状,没有发出过一致的声音,就像波伏娃所说的,女人没有过去、没有共同责任感和群体感,她们散居在男人中间,紧紧依附于某个男人,所以很难形成一个维护群体利益的、和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也许她们满足于自己的依附地位并为之自豪,也许她们在与男人的同谋中得到了利益,也许她们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了这个世界,总之对于心甘情愿做奴隶的人来说,大谈自由与解放是毫无意义的。只要女性的依附地位和心理没有改变,那么怨女产生的土壤将永远存在。妇女解放的当务之急是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由他者变为主体,自己对自己的生存负责,而不是让别人对自己负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如同手足的亲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既没有占有也没有牺牲。刘慧英指出:“女权主义与男权传统文化的冲突并非是一种权利争夺或替换,女权主义并不是一种企图推翻男权统治,进而取代男权主义统治世界的政治主张”。女权运动的关键是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是她也看到妇女解放道路的艰难和漫长,“妇女解放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变革,它不是仅仅仅靠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能完成的”。这是因为人们意识深层和文化观念隐匿着的男权主义残余很难消除,女人无论依附男人还是依附金钱还是依附强权,都是没有自由的被外物控制的奴隶,是女性主体意识尚未确立的表征。总之,只有当女性获得真正自由之际,银娣、七巧、白流苏之类的怨女才将不复存在。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张爱玲.怨女〔M〕//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张爱玲.谈女人〔M〕//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5〕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刘思谦.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问题与反思〔J〕.新华文摘,2005(14).
〔7〕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