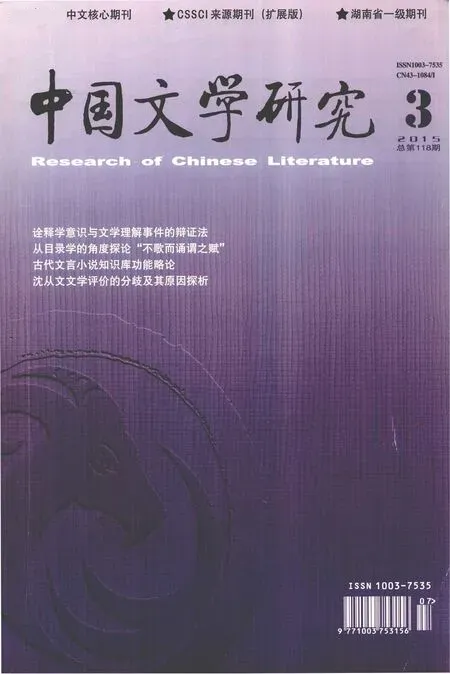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经典个案:库切
2015-11-14黄怀军
黄怀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乐黛云先生近年来一直倡导比较文学学者要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也不妨多关注具有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作家。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20 世纪末期开始活跃于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它对美国的传统信条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是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指出这一信条既无视美国是多种族、多民族的事实,又抹杀了其他社会群体对美国文明的贡献,因而提倡“差异政治”说(politics of difference),不仅拒绝融入WASP 主流文化,而且要求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以及不同文化的平等,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白人作家J. M.库切(J. M.Coetzee,1940—)在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反对激化因为历史原因而导致的文化对抗,提倡平等地对待和包容各种文化,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堪称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经典个案。
一、库切的流散生涯:超验他者视角与多元文化观的形成
从童年时代开始,库切就一直过着流散的生活,或者处于内心的流散状态。流散(diaspora)又译散居,最初指公元前586 年犹太人被驱逐出家园,现在泛指一切被动或主动离开祖居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的行为。库切认为,欧洲殖民者出于掠夺、占领、传教、控制等目的提倡殖民地的人们学习他们的语言,被殖民者在学习这些语言的过程中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殖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久而久之,学习殖民者语言的被殖民者就既不属于殖民地国家,也不属于殖民者宗主国。库切的父母是荷兰裔布尔人,他在家中通常讲英语,与其他孩子交往则操南非荷兰语。在南非历史中,说英语的英国人与说南非荷兰语的布尔人曾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不同的语言承载不同的文化,说两种语言的库切必然会遭遇这两种敌对文化的碰撞与撕裂,所以他在《凶年纪事》中说:“语言从来没有给我栖息的或归家的感觉。”
英国评论家安德鲁·格尔在《流亡的作家》一书中指出:“一个在殖民地出生的艺术家意识到他所在国家的文化从属地位,作为文化从属感的补偿,他就会被迫流亡入大都市。”作为欧洲白人的后代,库切内心深处缺乏对非洲本土文化的认同感,1962 年22 岁的库切去了英国。他本希望在南非的宗主国找到文化之根,但英国人对他异常冷漠,库切被局外感、排斥感、孤独感所萦绕。美籍巴勒斯坦裔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这样阐述流散者的双重体会:“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
浮萍般的漂泊感催促库切在流散的路上继续前行,1965 年他带着“不可弥合的裂痕”和“无法克服的哀伤”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做了大学文学教师。库切在美国获得归属感了吗?他在《我是如何认识美国和非洲》一文中给出了答案:“现在我在美国,可我寻找的青山,在我眼中就像英国萨里乡间一样疏远。我所想念的仿佛是某种空旷——空旷的大地,空旷的天空,那是我在南非所熟悉的。”可见他在美国依旧孤独,对非洲有着无法割舍的乡愁。问题是库切对南非的感情也是矛盾的:既止不住思念,却又想逃避。他曾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自己复杂的心境:“他思念南非吗?尽管他在英国和美国都没有找到家的感觉,但是他不想南非,也没感到怎么特别不开心。他只是觉得自己是局外人。”最终库切没有获得“自由国家”美国的绿卡,起因竟然是他追求自由的行动:他曾参加反越战游行,被警方拘捕,上了政府的黑名单。
1972 年,库切回到南非。回归故土的库切发现个体言说永远无法同社会总体话语抗衡,个体要保持独立的空间,只能选择精神流散,于是他不再说教和规劝,而是深入私语空间。2002 年,库切成功申请到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他称这次移居是自己“一生中最佳的选择”。不过,澳大利亚是否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园还很难说。对于一个流散者来说,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已经永远离他而去,流散状态本身才是流散者的家园。
在《双重视角》一书中,库切坦承自己的身份是含混的,俨然成了霍米·巴巴所说的“夹缝中人”(in-between),因为他身处既非欧洲作家亦非非洲作家的夹缝中。库切多年的流散经历让他深切感受到“无家可归性”,并形成了超验他者视角和多元文化主义观。何谓超验他者视角?简言之,就是超越任何事物和立场的视角,是站在西方文明之外反观西方文明的观察角度。流散给库切带来的边缘感和“无家可归性”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他者,他不仅仅是南非社会的他者,也是欧美文化的他者。超验他者视角也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观的具体体现。
二、库切的创作主题:同情的理解与文化和解
库切以超验他者的视角,一方面承认南非的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要激化这种冲突与对抗,提倡双方都对对方施以“同情的理解”,最终达成不同文化的和解。此处以库切的代表作《耻》(Disgrace,1999)和他迄今唯一一部直接描写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铁器时代》(Age of Iron,1990)两部小说为例,分析其多元文化主义主张。
《耻》是库切第一部以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新南非为背景的作品。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推行40 余年(1948—1991 年),其后果是使白人迷信和留恋自己所谓的社会精英高层的地位,同时也使处于弱势的黑人对白人的积怨代代相传。在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的南非,黑人对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用从白人那里学来的手段疯狂报复白人。小说女主人公、白人女性露茜被强奸的悲剧就发生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殖民主义消退的新南非。历史上欧洲白人曾经违背当地黑人的意愿,强行进入对方的领地,对黑人进行“强暴”,今天,这些白人或者他们的后代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露茜遭遇黑人强暴一事。强奸露茜的黑人似乎不是在宣泄情欲,而是在喷发仇恨和报复的快感。露茜将黑人对她的强奸与杀人类比:一个男人“把她压在自己身体下面,把自己全身重量压在她身上的时候,那是不是有点像杀人?把刀插进去,事后一阵兴奋,走开了,听任她浑身是血——这难道不像在杀人?”
这种代价在总体上表现为在南非的白人后代日益感到孤单,地位一落千丈。露茜的农场处于黑人耕地的包围之中,“面对装备一新的佩特鲁斯(露茜的黑人帮工——引者),露茜还有坚持下去的可能吗?……要是把这比做一局棋,那可以说露茜在各条战线上都对对方胜了一筹。”白人和黑人的地位也完全被颠倒。卢里教授来到女儿露茜的小农场,女儿要父亲给佩特鲁斯帮忙,父女俩的对话颇有深意。父亲问:“我替他干活,你觉得他会给我开工资吗?”女儿回答:“让他给你开工资。他付得起。我不知道我是否还雇得起他。”最后,遭到抢劫和强奸的露茜为了自保,不仅签字把土地转让给佩特鲁斯,甚至甘愿做他的第三个妻子。正如露茜的朋友、动物诊所的贝芙·肖所说:“佩特鲁斯会把她遮在大翅膀下面。”此时待在南非的白人不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黑人抢劫和强奸,而且无处求救、无处伸冤,所以当受辱的露茜父女俩向同为白人的德国老头爱丁杰求援,得到的回答却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救自己,因为警察救不了你,根本救不了,这你得清楚。”
作品描写了白人父女俩由此对黑人遭遇产生的“同情的理解”。露茜诉说3 个黑人强奸她时的疯狂“完全是在泄私愤”,并问父亲:“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可连见都没见过他们。”卢里回答说:“他们的行为有历史原因,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这事看起来是私愤,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显然,卢里已经承认欧洲白人对南非土著黑人的入侵是“错误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露茜尽管知道自己同意放弃农场并答应做前帮工的第三个老婆的做法“很丢脸”,但她同样也明白:“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觉得自己是讨债的,收税的。如果我不付出,为什么要让我在这里生活?”佩特鲁斯就认为露茜的做法是识时务之举:“她是个向前看的女人,而不是向后看。”所谓向后看,就是沉湎于白人在黑非洲殖民掠夺、胡作非为的昔日荣光之中,所谓向前看,就是接受当下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黑人要与白人平起平坐甚至要报复和打压殖民者后代的现实,放下身段。这些都表明,白人如果要继续生活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就不能以暴制暴,只能选择和解。
《铁器时代》的主人公、白人妇女卡伦太太借给远隔重洋的女儿写家信的方式描绘种族隔离政策推行时期她眼中的南非社会以及南非黑人。在卡伦太太眼中,南非黑人多是反抗白人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斗士。她亲眼目睹黑人们在反抗白人的暴乱中的勇敢行为:“成群结队的流浪汉,那些满脸怒容、口出狂言的男孩,就像掠食的大鲨鱼,对他们来说,监狱已经吓不着他们了。”她看到自己黑人仆人弗洛伦斯的儿子贝奇和另外几个黑人男孩被枪杀,“这些被枪杀的孩子显然已经成了抵抗战士,在为自己的族群而战。”在崇尚暴力和战争的“铁器时代”,所有的黑人都不得不成为“为族群而战”的“抵抗战士”,他们坚守一种信念:“不自由,毋宁死!”贝奇的母亲弗洛伦斯太太“可谓心如顽铁”,她以自己“为国家养育着武士儿子”而自豪,声称:“他们像铁器一样”,“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
除了“抵抗战士”一类形象之外,卡伦太太眼中的黑人还有纯真如“孩子”的品性。在她看来,老流浪汉范库尔能够有益于人,并最终成为她的伴侣。在卡伦太太最后的日子里,范库尔照料她的日常起居,“在互相的撕扯中移步换形,在跌倒爬起的过程中彼此扶持”。卡伦太太更欣赏范库尔“身上有一股孩子气”,他“那双绿眼睛,动物般的绿眼睛”就如同一个婴儿,而此前她痛感“这世上已经没有孩子了”。
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点,白人妇女卡伦眼中的黑人形象可以归为乌托邦式形象。这类黑人形象蕴含着两层意义。首先,它表达了卡伦太太对白人统治者当局实施并用暴力维护种族隔离政策的强烈不满,以及对黑人的报复欲望与行动的“同情的理解”。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已经“没有了爱,现在变得冷冷清清,暮气沉沉,摇摇欲坠。太阳照在它的墙壁上,即便是非洲的阳光,也没法让它变得温暖,好像那些砖块都是罪孽之手砌就的,散发着某些难以穿越的阴郁”。黑人居住的郊区是“被天使遗弃的地方”,这里到处搭建着“火柴盒般的屋棚”。就在自己的居住地,黑人们遭到白人的枪杀,死伤无数。当人们倾听这个国家时,“只能说是一声悲鸣,悲鸣复悲鸣,像是这广阔的天帝都在那儿悲叹。”卡伦太太曾经亲眼目睹南非白人政府镇压黑人的暴乱之惨状:“黑人棚屋区的骚乱之夜,……政府军控制了那个地区,暴力与杀戮的结果是一场大悲恸。”正是白人的示范教会黑人甚至黑人孩子成为疯狂的复仇者。卡伦太太看到仆人弗洛伦斯的儿子贝奇和几个黑人男孩被枪杀之后,她记起他们“那铁器般的冷血性格,让她想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戾、残忍,想到了斯巴达人的严酷、冷漠,想到了加尔文主义的铁血教义”。换言之,黑人以及黑人孩子的冷血性格完全复制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古希腊斯巴达人和加尔文主义者的强权、暴戾与冷酷。
其次,卡伦太太眼中的黑人形象宣示了一种主张:白人和黑人应该也完全可以尊重对方,实现文化和解,达成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和谐相处。卡伦太太秉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身无分文又爱酗酒的黑人流浪汉范库尔必须要有些钱,卡伦太太没有像施舍乞丐一样的无偿地给他钱,而是让他做一些清理庭院之类的劳动。这是一种尊重,正如卡伦太太所说:“慈善是什么?是菜汤?是钱?是为心而做的意思,接受比施舍更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所以他不让被施舍的人失去尊严。卡伦太太后来“毫无顾忌地思量着”与范库尔交合的念头,最后和他“合用一张床……可谓老伴,可谓室友,可谓比翼鸟、连理枝”,并自称“范太太”。库切在小说中喜欢用男女交合的意象象征不同文化的交融。此处白人妇女和黑人流浪汉交合的念头和行为无疑寓意着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交融与和谐相处。
三、库切的批评立场:超越政治,呼吁文化和解
库切既是当代世界的顶级小说家,也是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他迄今已出版3 部文学评论集。库切热衷于消解传统文学批评中的阶级、经济乃至政治对抗的成分,而将文学批评视为凸显文化隔膜与冲突,寻求不同文化和解的手段与途径。此处以库切评论199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白人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创作与思想的两篇论文《戈迪默和屠格涅夫》、《纳丁·戈迪默》为例,管窥他的文学批评主张与立场。
首先,库切质疑戈迪默“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的主张,认为作家的首要原则是秉持艺术良心。
戈迪默虽然是白人作家,但常常站在黑人以及黑人作家的立场发声,明确表达对南非种族歧视行为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库切发现戈迪默的作品中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伦理诉求。他在《戈迪默和屠格涅夫》一文中指出:“1975年,纳丁·戈迪默在一场演讲中谈到了南非作家所面临的压力和要求,对这些来自极端种族主义的压力和要求,黑人作家的感受尤其强烈。戈迪默说,首先,黑人作家需要有‘表达自己深切感受到的观点’和‘他亲历的真相’之权利。其次,黑人作家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人民把他看做是自己的代言人,他们期望他将个人才能用来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期望他能以‘斗争的语言’来从事创作。我认为,戈迪默之所以发表上述演讲是因为她迫切感受到,她自己也正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在库切看来,戈迪默以黑人作家自居,致力于描绘“亲历的真相”、以“斗争的语言”进行创作、最终“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
库切从戈迪默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态度转变这一事件上看出她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伦理诉求。1970 年代末期以前,戈迪默最佩服的欧洲作家就是屠格涅夫。戈迪默佩服屠格涅夫,首先是因为此时的南非同屠格涅夫时代的俄国有某种相似性,南非总统沃斯特和博塔“没有能够取消种族隔离政策,没有能使经济现代化”,与“俄国末代的几位沙皇……没有能够结束俄国的封建主义,都没有能使俄国现代化”的情形非常相似。更重要的是因为戈迪默发现,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顶住了来自当时俄国革命者阵营左派和右派的压力,既“没有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正面的、革命的、有效的、俄国的主人公形象”,也“没有把小说解释成是对激进青年的攻击”,由此,“屠格涅夫超越政治的、只响应自己内在艺术良心召唤的艺术家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但在1970 年代末期之后,戈迪默却放弃屠格涅夫,转向别林斯基。库切这样解释:“戈迪默在1984 年决意标举别林斯基而不是屠格涅夫之名,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把别林斯基标举为首要的革命形象,比较可信,而标举屠格涅夫则行不通。”换言之,1970 年代末期以前的戈迪默以屠格涅夫为榜样,是因为戈迪默本人的政治追求也是温和的,而此后戈迪默政治热情高涨,成了激进派,所以抛弃并不热心政治的屠格涅夫,而转向政治热情极高的别林斯基。
库切并不欣赏戈迪默的这一转向,也不欣赏她过于旺盛的政治意识和社会道义感。他指出,虽然“戈迪默始终坚信,艺术家有着特殊的感召力,有着特殊的才情,而掩盖这份才情就等于死亡;艺术之真超越历史之真”,但“同时她又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担当起社会道义来”,“戈迪默认为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时常援引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一些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虚假的艺术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艺术,其精神意识已经崩溃,因而看不见未来,这种艺术与真正的艺术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艺术(指“真正的艺术”——引者)的目标就是要变革社会,就是要把被搞得四分五裂的东西重新整合起来。”戈迪默明确主张“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认为“真正的艺术”必须履行“变革社会”的责任,库切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库切对戈迪默起初崇拜而后抛弃的屠格涅夫一直欣赏有加:“他在谈论艺术和文学时,往往会把它们包裹在唯心主义哲学术语中:艺术是公正的,与利害无关;伟大的艺术家是圣人或预言家,它们超脱于日常生活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库切主张艺术家要超脱政治立场、坚持艺术良心。
其次,库切赞赏戈迪默对“公正”的诉求,呼吁不同文化和谐相处。
库切在《纳丁·戈迪默》一文中承认追求公正是戈迪默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他说:“如果有某个重要的原则,使戈迪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南非民主化期间的作品充满想象力,那就是对公正的追求。……戈迪默所渴望的公正,要比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政治分配更广泛。在某种较不容易定义的程度上,她还渴求私人领域的公正关系。”“她本人一生著作的伦理框架,根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时种族隔离的铁幕正落下,而也是在这时,她首次阅读让—保罗·萨特和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加缪的作品。在这种阅读的影响下,她担当了南非命运的目击者的角色。”不过,库切虽然对戈迪默追求“公正”的创作原则持肯定态度,但对她致力于描绘种族隔离政策实施后激烈的文化冲突及其严重后果从而有意无意地激化这种冲突的做法则持保留态度。他将戈迪默与堂吉诃德并提:“在《堂吉诃德》结尾,出发去纠正世界的错误的主人公,悲伤地回家,意识到他不仅不是英雄,而且现在这个世界已变成没有英雄了。戈迪默作为一位剥光一般幻想之衣服和撕掉殖民地不诚实之面具的作家,是塞万提斯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在那个传统里,她得以颇令人满意地作业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然后她明白到,对南非黑人——而她是南非黑人的斗争的历史见证者——来说,……她太欧洲化了,她在那些对她最重要的人眼中根本不重要。她这个时期的随笔表明她正没有结果地在一个问题的泥潭中挣扎,这就是为一个民族写作——为他们而写和代他们写,以及被他们读——意味着什么。”戈迪默如同堂吉诃德一样的失望与醒悟,以及她不明白为黑人写作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的“挣扎”,象征性地表明她对自己过往的创作主题与倾向的反思。相反,库切对戈迪默1990 年代以后尤其是21 世纪创作的那些不再直接为黑人创作的作品则表现出欣赏的态度:“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和随着曾经在种族隔离统治下以其紧迫性遮盖所有文化事务的意识形态的放松,戈迪默亦从自寻烦恼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在新世纪出版的小说,显示一种令人欣喜的就绪状态,随时准备描写世界的新场所和新感觉。我们能感到,如果这些作品与她重要时期的作品相比显得有点儿无实体,有点儿粗略,如果体现在她最佳作品中的对真实世界的肌理的全力刻画如今只是间歇性地表演,如果她有时满足于向她要表达的意思打打手势而不是用文字确切地突显出来,那也是因为她觉得她已经证明自己了,不需要表演那些大力士式的重活。”所谓“大力士式的重活”,就是直接描绘南非黑人反抗白人的斗争、明确表达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对立与冲突的主题的做法。
显然,库切在文学批评中不仅体现出超脱政治立场、坚持艺术良心的态度,而且不欣赏文学创作一味表现文化对立与冲突的诉求,他渴望不同文化尽快摆脱因为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冲突和对抗,达成和解,和谐相处。
〔1〕(南非)库切.凶年纪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2〕(英)安德鲁·格尔.流亡的作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Edward 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0.
〔4〕(南非)库切.我是如何认识美国和非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5〕(南非)库切.双重视角〔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6〕(南非)库切.耻〔M〕.译林出版社,2002.
〔7〕(南非)库切.铁器时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8〕(南非)库切.异乡人的国度〔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9〕(南非)库切.内心活动〔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