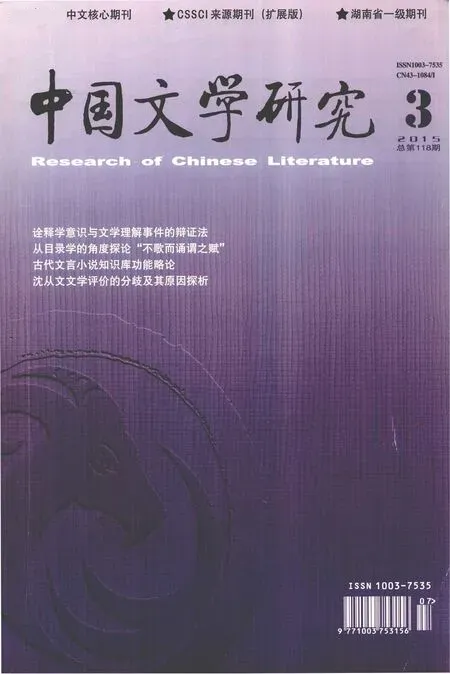论新英雄传奇从“家仇”到“国恨”的叙事策略
2015-11-14戴莉
戴 莉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124)
新英雄传奇是指肇始于20 世纪40 年代一类表现抗日战争生活的作品,以《新英雄儿女传》、《抗日英雄洋铁桶》等为代表,多讲述抗日战争中的传奇故事。这一类小说创作在建国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创作潮流,涌现出一大批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为代表的战争传奇作品。以传奇为名,是因为此类故事情节上跌宕起伏非奇不传,表现出强烈的非现实性。但是仔细考察此类作品写作模式,话语主题,我们会发现,非现实性只是情节上的,这一类新英雄传奇作品背后隐含着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的主动思考,内含无产阶级作家整理经验世界以解释、构成有序世界的写作理想。
一
无论是建国前的抗日英雄传奇,还是建国后的解放战争传奇,新英雄传奇有一个共同的叙事起点,就是“血债”。日军犯下的血债,土匪犯下的血债,“血债”构成传奇叙事的起点,也是作家“家—国”一体制理想世界建构的前提。《新儿女英雄传》第一回就是“事变”,开篇之前引用当地民谣说明:“炮声一响,眼泪满眶”;《吕梁英雄传》以“日本兵兴兵作乱 康家寨全村遭劫”开始全篇的故事;《林海雪原》的第一章题目就是“血债”;《烈火金钢》则是从“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开始。以“血债”开始故事,这一点已为研究者注意:“‘革命历史小说’亦往往从灾难或失败开始。……这些都不是前世的报应或天定的劫数,不仅仅是小说的‘话头’,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故事多从杀戮开始,“复仇”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是这一类写作的基点,而支撑多不是来自民族大义,更多来自于血缘亲情的天然合理性。
“血债”的讲述方式大体分为两种:“家仇”和“国恨”。延安时期的新英雄传奇多侧重从个人的角度来处理灾难。主人公目睹家园被毁、亲人遭难,迫不得已参加民兵保家自卫,所以这些小说的主人公经常单独活动,更具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比如孙犁的《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一》,孙老头因为女儿被鬼子杀害,于是萌生了报仇的念头。地雷英雄李勇的故事曾经在解放区广为流传,邵子南根据李勇的故事创作的新英雄传奇《李勇大摆地雷阵》,讲述了李勇如何利用手中的地雷为姐姐报仇的故事,其行为动机也是指向个人。周而复描写11 岁的儿童英雄小六儿发动思考巧妙杀敌,故事也从小六儿目睹嫂子的惨死开始。
延安时期的新英雄传奇其写作指向还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此时战争还是一场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自发性质的保卫传奇,其写作目的更多是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战斗的勇气,“血债”的后续动作指向无数个人而非集体。建国后新英雄传奇小说则担负着解释并构建现实有序性世界的目的,所以更强调从“国恨”层面来对敌人犯下的“血债”进行控诉。“家仇”和“国恨”虽然同为“血债”,但是从叙事功能上来说,二者是不一样的。“家仇”强调的是个人的行为动机,而“国恨”则是“家仇”的升华和集体化,强调的是“集体”的行动力量和后果。所以建国后新英雄传奇中的“血债”这一情节模式以个人始,却以集体终。我们以《烈火金钢》为例,看看个体仇恨是如何转化为民族仇恨的:何世清老人在敌人走了之后看见孙家大院血迹未干,于是找了一个坛子,拿上一个饭碗,将地下的血,收满了一坛。因为死者是全村各姓各族的都有,所以命名为“民族血”:
这时候,何世清又大声喊着:“乡亲爷们!听着我说:咱们的亲人已经死了!家也破了!常说家破国亡,咱们眼看就要成为亡国之奴,丧家之犬!难道我们能够甘心吗?”当他说到这儿,大伙一齐喊出了:“不能甘心!”何世清又继续喊道:“在过去咱们张王李赵,是各管各家,各管各院,各扫门前之雪,不管他人瓦上有霜。总有人想着,谁来给谁纳粮,作顺民,乐忍耐。如今看来,这都是作梦了!这个梦葫芦,叫日本鬼子的刺刀给穿破了!咱们的界限,让这一坛民族血给联起来了!咱们要把这一坛血埋葬起来,叫咱们的子孙万代都要记住!再磕头,要三叩首。”《烈火金钢》)
“个体”的界限因战争而消融,集结为一个整体不分彼此。建国后的新英雄传奇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全民总动员的民族保卫战,更注重“血债”集体层面的提高,这也可以看出新英雄传奇所担负的现实功能的变化。战争来临,家园被毁,但是,仇恨如果停留在“家仇”阶段,就不能打响这场全民族的保卫战。《吕梁英雄传》开篇写到抗战爆发,康家寨全村遭劫,所有的人都对敌人的暴行恨之入骨。但是,由于不能抛弃小私有者的“家庭”观念,每家都只惦记着自家被敌人抓去的亲人,因此无法凝聚力量统一行动,不仅大仇不能报,反而被敌人利用:维持会建立起来,活着的人被强拉去修炮楼,敌人越来越猖獗。所以,如果仇恨只停留在个体、家庭的层面,民族自卫战就无从打起,只有万众一心,团结起来,首先实现民族的解放,才能说得上个人报仇。当然,必须要对“血债”有切身体验,这是激发每一个个体产生仇恨的第一步。所以,血债中的“家仇”是“国恨”写作中必要的一环:“家仇”必须升华为“国恨”,“家仇”的叙事功能使情节的展开成为可能,而“国恨”的叙事功能则指向现实世界的构造,是对具体的、血亲意义上的“家庭”的否定。
“家仇”“国恨”虽然同为“血债”,但是实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前者是个人话语,后者是集体话语,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话语体系是作家面对的难题。把“血债”落实到“家仇”层面,当然更容易激发作品主人公和读者对仇恨的感同身受,对主人公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也更有说服力。但是“家仇”和“国恨”虽然同为“血债”,前者强调的是个人的行为动机,而后者则是在解释、建构一个合法秩序,是对前者的否定。二者不同的叙事功能使作家对“血债”的定位陷入两难之中:“血债”中“家仇”的“个人性”和“国恨”的“集体性”如何处理?“家仇”情节模式展开的前提是对血亲关系、血缘亲情的认可,而“国恨”实质上是对“家仇”,主要是对“家”的单一性个体性的否定。
也就是说,“家”与“国”,个人与集体,两种伦理,两种价值观在此是不相容的。这不是延安作家才面对的难题。“忠”与“孝”不能两全,当传统儒家以家族模式为原型来构筑治国理想时,两种伦理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产生。“国”以“家”为模型构建的前提是“家族”伦理的合理合法性,但是“家族”伦理的正义性也是对“国家”伦理的妨碍。如何处理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古典传奇的做法是在肯定两种伦理价值的前提下,分时、分地、分别对待。特殊战争时期,“国”压倒“家”,彰显“忠”的“大家”观念,肯定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行为;一旦回归和平时期,其乐融融的“小家”氛围又会成为书写主流。在漫长的宗法制社会里,战乱和和平的交替以及“大国”和“小家”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和矛盾并不激烈。可以说各得其所,各自安逸。因为究其实,这两种话语体系内核是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大的拟血亲的共同体,“家族”伦理的正义性是受到肯定和保护的。
二
新英雄传奇和古典传奇在此分歧:新英雄传奇以“家仇”始而以“国恨”终的过程中,以战争的集体性、阶级性否定个人性,家族性,不同于古典传奇从始至终还是肯定家族伦理的正义性。面对“家”“国”难题,新英雄传奇通常采用的做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以《林海雪原》为代表,在“家族”亲情叙事中穿插凛然正气的“国家话语”;另一种则是以《平原枪声》为代表,强调“家仇”和“国恨”的同一性,把“地主”和“鬼子”合并同类项,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同时进行。
首先来看《林海雪原》。小说一开始就是敌人的疯狂进攻,少剑波接到上级的命令赶往杉岚站,也就是少剑波的姐姐所在的县。通过少剑波的眼睛,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已经被血洗一空的残忍场面:
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
在这垛被铡的尸体周围,狼藉地倒着二十多具被害者的遗体,有老头,有小孩,绝大多数是妇女。看得很明显,这些死难者是想扑向铡刀去救自己的亲人,或替亲人去死,或是去拼打而被乱枪狂射杀害的。《林海雪原》)
这些受害人都没有姓名,没有具体所指,是集体的灾难。可能作家也觉得这样来解释少剑波的愤怒不足以服人,或者为了加强读者和作品主人公对于血债的感同身受,接下来作者就交待了少剑波姐姐的下落:
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
“工作队!鞠县长!”老乡领剑波登上山坡,头磕着地,手蒙着脸,不敢看这九个被害的同志。
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〇三!二〇三!”一面哭泣,一面喊。(《林海雪原》)
这些无名的群像尸体,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做法类似,让群众以无名的群像形象出现,让“家仇”不仅止于“家仇”。同时,为了加强活着的人的仇恨心理,让读者也能感同身受,又着重以聚焦的方式重点说明一个受难者,就是少剑波的姐姐。作者特意交待敌人所袭击的正是少剑波的姐姐“鞠县长”所在的县,其用意除了解释少剑波的悲愤,以及使读者对敌人这种残酷的行为产生更为深切的仇恨之外,也把之前集体层面的“血债”描写具体到个人。“鞠县长”就是“姐姐”,被杀害的那些群众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兄弟姐妹。亲人的血不能白流,一定要为亲人报仇!这是“鞠县长”/“姐姐”双重身份所要告诉读者的。
把具体的、国家的“血债”个人化,在国家仇恨中突出个人仇恨,使个人仇恨和集体仇恨统一,这是作家在写作“血债”一节处理“家”“国”矛盾时经常采用的做法。这种写法的弊端在于“民族”话语仍然难以摆脱“家族”话语的阻碍,个人仇恨往往削弱“血债”叙事在整个小说中的功能,使得“家族”叙事无法升华成为“民族”叙事,亲情阻碍国家主义感情的萌生。另一种做法则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平原枪声》一开始就交待了马英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苏金荣!当马大娘难以理解自己的孩子连命都不要了闹革命时,马英就会向自己的娘解释只有闹革命才能报家仇的道理。马大娘曾经作过一个梦:
马大娘昏昏沉沉,觉得身上热呼呼的,低头一看,怀里抱着马英,马英还是童年时的马英:方方的脑袋,圆圆的小脸,大大的眼睛,握着小拳头对她说:“娘,我长大给爹和姐姐报仇!”这时突然窜出一条狼,把马英衔走了,她喊叫着去追,这时才看清那不是狼,是鬼子,马英也长成大人了,她哭,可是哭不出来,这时她忽然看到一个人对她狞笑,这是谁呢?苏金荣!(《平原枪声》)
这个一个有着强烈寓意的噩梦。苏金荣是马英不共戴天的仇人,二人之间的仇恨属于“家仇”层面。而抗战爆发后,苏金荣成为卖国求荣的汉奸,马英是带领家乡人民保卫祖国打鬼子的英雄,所以马英实际上是借“国恨”――民族解放这一大的集体叙事,实现自己报“家仇”的目的,“家仇”和“国恨”由于地主/汉奸身份的合并达成同一,也就是“家”和“国”叙事达成统一。不过这样的处理最大的问题是敌人身份的混淆。马大娘这个梦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苏金荣是使“家仇”转向“国恨”的关键人物,但是苏金荣本身并不是日本人,敌人的身份在仇恨升级的时候悄悄转向。日本鬼子的身份在马大娘的梦中模糊不清:突然窜出来的像狼一样的动物,和马大娘的家仇好像没有必然的关联。抗日战争的敌人到底是谁?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在“新英雄传奇”中却找到另一个答案:苏金荣(《平原枪声》)、康锡雪(《吕梁英雄传》)、何世雄(《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枪声》、《吕梁英雄传》等作品都是通过地主/汉奸的双重身份来实现从“家仇”的个人复仇到“国恨”的民族战争的转变,解决“家”“国”之间的难题。也就是说,新英雄传奇以亲情唤起民众的仇恨情绪,亲情如不存,那么所有的后续动作都无法开展,但亲情的效应一旦发生作用,“家仇”一旦转化为“国恨”,新英雄传奇又最大限度地取缔家族、亲情对个人的牵绊,取缔个人性,让人成为“国家”的人,“集体”的人。
遭人诟病之处也在于此。从“家仇”到“国恨”的叙事策略,多被认为是一种妥协或投降,它以“救亡”为当务之急,将重塑国民性、社会批判等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学传统置之一边,放弃了文学对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等启蒙思想及精神资源的探讨,意味着对自身责任的完全放弃,而沦为政治的附庸。果真如此吗?
三
新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济世救国”之愿,试图以人的发现唤醒国家的自强、自立,但直到四十年代文学才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参与现实建设的路径。其中原因之一,如众多批评家所言,“旧瓶装新酒”,旧形式,或者说民族形式的改造与利用,是文学成功介入现实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旧瓶”装的到底是“新酒”还是“旧酒”,需要仔细考量。30 年代左翼文学没有解决的“阶级性”书写为什么在四十年代穷且贫弱的边区取得成功,这恐怕不是“形式”一词能完全解释的。以新英雄传奇而言,传奇的形式只是包装,更重要的是,传奇书写的内容实质上和宗法制下的“家—国”一体观念是一脉相承的,“阶级性”、“集体性”在新英雄传奇写作中是以拟血亲共同体形式存在的,这和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形象是一致的。五四以降的新文学,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都有一个强大的未曾忘却的现实理想,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梦。较之社会主义改造者的政治乌托邦理想,四十年代这种“家—国”一体的拟血亲共同体更具政治实用性和接受性。对传统思想的选择性回归是接受了现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精英写作者们不愿认同的一件事,那就是,以新英雄传奇为代表的20 世纪40—70 年代的无产阶级写作,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利用旧形式,同时也在利用和改造“旧思想”。新英雄传奇写作之初的“家国梦”也包含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的现代性诉求。
新英雄传奇的家国梦溯其源其实是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下“家-国”一体的社会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制首先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统治者提出了“家长”的要求。“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君王作为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只有“爱民如子”,才能享有天命,维持统治。鉴于这样的现实,蔡元培先生在总结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特色的时候就说:
吾族之始建国也,以家族为模型。……父兄之责,在躬行道德以范子弟,而著其条目于家教,子弟有不师教者罚之。政府之责,在躬行道德,以范人民,而著其条目于礼,人民有不师教者罚之。……故政府犹父兄也。
“作民父母”,“爱民如子”,“政府犹父兄也”,传统儒家以“家庭“为模型对国家的管理者提出了最高要求,而另一方面,被管理者,民众,“一直被认定为是呵护教养的对象,而不是掌握权力的主人。”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制下人身关系特色时就指出:宗法制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国’一体化的拟血亲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自然人’的宗法纽带与‘孤立人’的‘狭隘意识’都极为强固,人的社会化与个体化进程特别艰难,因而人的依赖关系也极为坚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对于宗法共同体以及拟血亲共同体(其最高级形式为国家)的依赖一直存在,并不断被越来越完备的“家族制”管理方式所强化,直到晚清“家—国”一体制始受到挑战。及至20 世纪初,当时的新文化先驱们从两方面系统深入地批判了传统儒家“家—国”一体制的危害:一是“家—国”一体制对国家的危害:吴虞先生在其《读荀子书后》一文中,把政治、家族和儒教三者联系起来,指出“君兼父母之恩(养育、教诲)……此实乃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而君主们即握政教之权,更兼家长之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离。”其次是“家—国”一体制对个人的危害,“家—国”一体制中国家以父母自居,承担民众教养之责,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明确提出:“青年之戒,第一在扶墙摸壁,依傍他人。”个人只有摆脱对宗法共同体的依附关系,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公民,真正觉醒的人。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从国家建设与个体觉醒两方面批判传统儒家“家—国”一体制,而新英雄传奇则另辟蹊径,以底层民众最为熟悉的传统“家—国”一体制来实施并构建其“家—国”理想。
以战争为契机,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依赖,以传统的“爱民如子”的形象塑造政府形象,将民众纳入集体的保护之下。在从“家仇”到“国恨”的升华过程中,国家就是一个和蔼可亲,对人民负有养育、教化之责的“家长”。我们前面已经论述,新英雄传奇多从“杀戮”欠下的血债开始。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群众往往举手无措,被放置到一个急需保护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人多具党代表的政治身份,是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化身。他们带领群众起来闹革命,反抗压迫,组织自卫武装,同时恢复生产。这个人在《新儿女英雄传》中是“黑老蔡”,《平原枪声》中是“马英”,《林海雪原》中是“少剑波”,《铁道游击队》中是“李正”。他们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而且肩负向上汇报工作和向下传达指示的任务,所以他也可以视为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群众对他的依赖和信任,他对群众的保护和责任,也是政府和群众关系的一个具化。从新英雄传奇文本来看,新英雄传奇中的这个党的代表,更多的是群众的“家长”,而不仅仅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从最具体、细微的日常生活着手的。新英雄传奇中的政府管理者都是从关心群众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来表现,而不是从国家政策等大角度来刻画其领导人。《林海雪原》中,当少剑波带领的小分队到达夹皮沟地区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不是土匪,而是要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由于座山雕、国民党的抢掠,夹皮沟群众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的心是在焚烧。他现在的忧愁,已超过夹皮沟所有的一切人。“我管打仗,可是我是共产党员,在夹皮沟屯里,我是党的最高领导者,也是党的政策的体现者,眼看群众这般情况,难道可以坐视不理吗?但是,要管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怎么管呢?我怎么来当这个家呢?……”(《林海雪原》)
作为群众的“当家人”,就必须解决“家里人”穿衣、吃饭的问题。少剑波先以身作则把自己的衬衣衬裤送给最困难的群众,然后从山外调来大批粮食,解决当地群众生活的燃眉之急;之后又带领当地群众修护铁路,恢复交通和生产。从之前群众对小分队英雄队伍的冷漠、不信任到后来争着抢着拉小分队的官兵们去自己家吃饭,小说用轻松、愉快的笔致写出了夹皮沟群众在少剑波的帮助下从“沙聚之邦”到“人国”的转变。《吕梁英雄传》从日本人血洗康家寨开始,之后又有“康顺风勾结敌伪”,“桦林霸施展阴谋”,建立维持会逼粮要款,刘二则含愤丧生,村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康家寨几个思想先进的青年们在一起试图反抗,却苦于无人领导。正在这个时候,马区长出现了,“大家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直要老马同志“想个法子”。老马同志详细地向他们传授了和敌人作战的方法,并交待他们,“以后有甚问题,到靠山堡找我吧!”老马同志是康家寨的救星,也是大家信赖的亲人。新英雄传奇所描写的政府形象向传统的“家长”形象靠拢,它强调政府对群众的保护,群众接受政府的保护,同时也自愿依附于政府。
从“家仇”到“国恨”,说是一种叙事策略,折射的其实是一代知识分子作家对政治制度、民族命运的探讨。从五四到左翼再到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文学的主题和表现方式一直在变,但在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梦想上,三十年的文学是一以贯之的。在从“家仇”到“国恨”的转化中,个人家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被否定,“国家”以集体的、阶级的复仇者形象出现,并以无微不至的“家长”形象介入个人生活,将个人成功地纳入集体的保护之中,达成新的“国-家”一体的想象。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同情到对时代、阶级的政治书写,以“救亡”为当务之急,以新英雄传奇为代表的延安文学将传统的道德情怀转化为新的政治理想,积极尝试了一条极具实践性的道路。如果我们不以西方文化为唯一正确的存在,以西方文化及其民主制度为唯一符合现代性存在的政治形式,那么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理念下衍生、发展并形成的政治制度的利用和变革也可以视为一种合理尝试。不过其中隐含并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的危险是,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产阶级写作成为唯一正确的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标签而不是文学属性,人性被完全抹煞,阶级的人、集体的人成为唯一合法的表现对象,这是五四乃至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作家们艰难抉择时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今日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必须警惕的。
〔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01.
〔2〕周而复.小六儿的故事——晋察冀童话〔N〕.解放日报,1944-07-30.
〔3〕尚书·洪范〔A〕.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3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张端穗.天与人归——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A〕.刘岱.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一):理想与现实〔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6〕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7〕吴虞.读荀子书后〔J〕.新青年,第3 卷第1 号,1917-03.
〔8〕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J〕.青年杂志,第1 卷第1 号,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