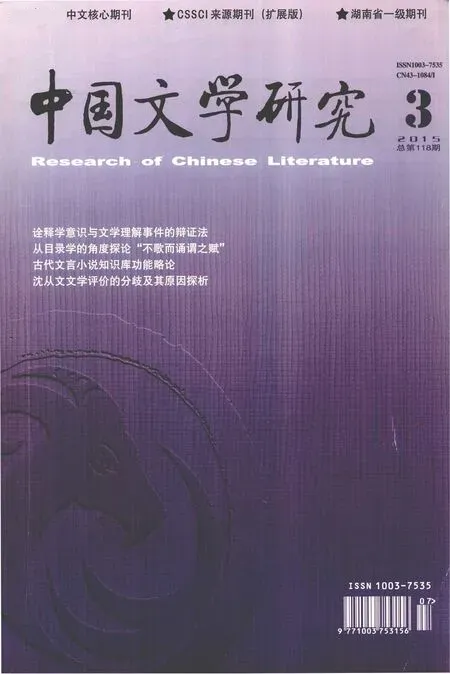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的“爱情”幻象及其小说反思
2015-11-14王蓉
王 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残雪大力宣扬学习西方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等人的文学创作手法和风格,公开批判传统文学在人性挖掘方面的不足,坚持进行了三十年的实验文学创作,在当代作家中独具一格。阎连科曾说当代作家模仿西方超现实主义,多数人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的匆匆过客,没有几个真正闯进了博尔赫斯的迷宫,真正闯入并最终找到出口者,更寥寥无几:有的刚踏进迷宫的门槛,或浅尝辄止地在门边逗留一番,或战战兢兢摸了进去,但稍稍深入就望而却步,原路返回;更多则是站在门口了望、围观,以便从各色“打道回府”的探险者嘴里接过些感奋的呐喊或扫兴的叹息。确实,读懂西方文学作品不易,模拟并自成一家更难,而残雪无疑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学、哲学影响并能开拓创新,融会中西文学传统且成名成家的人。
现实生活中,残雪埋头阅读和写作,深耕西方哲学和文学,极少抛头露面于各种公共场合,坚持自己每天一小时左右的“自动写作”和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上,她执着于新实验小说的创作,以底层人物的自我存在和精神追求为中心,挖掘其深层的潜意识和灵魂深处的冲动,向内写作,不断拷问自我,反思自我,以期达到生命探索的极限和自由意志的巅峰。同时,她还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版自己的文学批评论文,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代文坛创造力萎靡和作家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自卑,高调肯定自己作品的纯文学性和独创性,尖锐地指出王蒙、王安忆、张洁、余华等人作品的“观念”写作或者蜕变随俗,更指责中国文坛投桃报李和拉帮结派。这种自我创作特色鲜明,理论批评锋芒毕露和对自己作品的高度自信等,导致残雪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在主流文学圈和知名文学批评家笔下出现不多。其作品也较少被当代主流批评家深入挖掘、仔细研读和评论,《新世纪爱情故事》的“遭遇”就是证明。这种孤独局面虽然会遮蔽残雪在当代的文学存在,但是,只要她真正深入写出了人性、精神和灵魂的复杂深刻性,真正创造了具有通约性特点的纯文学,那么,残雪预言的读者会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变为未来的现实。本文拟对《新世界爱情故事》中的“爱情”表现与自我想象、以反常性的感情方式追求自我精神超越以及这种创作方式的得失加以探讨。
一
残雪极少写权贵富豪,而是写底层人物的卑微生活和精神世界,如《双重的生活》中的坚仪、《五香街》中的X 女士、Q 男士、《吕芳诗小姐》中的吕芳诗、《保安》中的简元等。或许,权贵富豪本来是现实中的少数,底层人物、普通人才是生活中的主体,因此对普通人的精神状态的刻画更能表现人性本真和灵魂裂变。底层人物的潜意识和生命冲动,更能表现普遍性的盲目、热烈的力量和自我原动力、生命力。这些人物常有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从而客观上展现了沉重的肉身与更为复杂沉重的精神。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和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方式,残雪极为反感,她是一位“反叛”型作家。再现现实不是其创作意图,对个体“精神真实”的多维展示才是其一贯主张。与《黄泥街》、《五香街》所展示的丑陋、丑恶的现实表象相比,《新世界爱情故事》所展示的表象较为自然清新和赏心悦目,可以说改变了早期的审丑风格。
残雪自言《新世纪爱情故事》描写了一种新型的爱情观:这种爱情不是已有的,但也不是根本不存在;有些朦胧的轮廓,但又还未正式成形。它是一种渴望,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初现,可以说它是新世纪灵魂的觉醒。这种自白说明了这篇小说不是反映现实爱情故事,只是展示某些朦胧的轮廓而已。其实,全书重在表现“一种渴望”、“人的自由意志”和“新世纪灵魂的觉醒”,与一般小说重在反映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爱情及花样繁多的物质欲望等迥然不同。表面的、形而下的世俗爱情生活,并没有被具体形象的描绘和夸张渲染;不受爱情和婚姻伦理道德约束的男女可以随着心灵的律动轻易地彼此交媾,虽部分地契合了情感泛滥的时代潮流,但绝无污秽不堪的诲淫场面和荡人春心的艳情语言。如书中主要人物之一的阿丝,曾经是纺纱厂的年青漂亮的女工,后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随大流下海,当了一名性工作者。在该书的几位女性性工作者中,阿丝最有魅力最得到男人的欢心。可是,在对阿丝与她的几个嫖客朋友的叙述中,绝无诲淫场面和荡人心魄的情爱细节,两性交往在阿丝这里变得十分简单和随意。韦伯在纱厂做兼职工作时看到阿丝,一见倾心神魂颠倒,遂尾随多日。被阿丝发现后,她径直走过去对韦伯说:“你打算出多少钱包养我?”韦伯说“我并非有钱人,但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你。”阿丝当即挽起韦伯的手臂,十分惹眼地走出了纺纱厂区。此后阿丝自作主张去温泉旅馆做性工作者,韦伯开始反对,去阿丝工作的车间看了几次后就不反对了。阿丝多次与自己的顾客恋爱,即使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也毫不后悔。狱警袁黑、肥皂厂普工韦伯、烟贩子阿援、渔夫顾大伯、下水管道口旁的男人、顾大伯的朋友流沙等都是她的恋人或者交往对象。然而,从这种一对多的交往中,却看不到作为娼妓的阿丝形象,而是凸显了一个在内心挣扎中追求自我精神发展的“超女”形象。阿丝与他人交往的历程,其实是一种精神探索,是其精神的突围表演和灵魂裂变的必然结果。因此,阿援虽形象丑陋,走私货物,带给了阿丝恐怖的恶心的体验等,但他是阿丝的引路人,还是牢牢套住了阿丝的心,阿丝也决定“死死吊在阿援这棵树上”。因为这种“恶心”感正是像阿丝这样具有冒险精神的艺术家所渴求的。
动物性的物欲原本为人的本能,在今天经济发展、欲望膨胀而又消费狂欢的时代,我们的梦,多为物质的梦。精神何为?灵魂何在?如果灵魂的真正死亡来临,我们会不会恐惧与绝望?要知道,精神的人,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残雪对底层人物如性工作者生存困境和情感堕落的叙述,主要不是为了再现时代裂变给人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根本影响,而是凸显人不满足于当下生活,渴望突破自我时空限制,进入无限自由的精神王国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灵魂裂变方式。书中常常提到人物对故乡的回忆和眷恋,对纺纱厂和仪表厂生活单调和环境恶劣的刻画,不是为了表达乡土情怀和生存苦难,全书也无明显地对金钱物欲加以讽刺或者批判。这正是残雪所倡导的“自动写作”,不预先设定创作目的,也不刻意追求社会批评效果的结果。当然,这不是说《新世界爱情故事》中没有对现实生活的叙述,高高悬挂在真空中,现实生活和经历仍是刻画人物精神蜕变和灵魂革新的重要背景和环境。其中,对纺纱厂女工龙思乡和金珠的叙述就是代表。
龙思乡因为婴儿夭折,悲痛欲绝,几近发狂,神经崩溃。半年之后,决定与丈夫小武离婚,这样才能将儿子彻底埋葬在记忆深处。经过同事,亮丽少女阿思的鼓励和安慰,龙思乡精神才恢复正常。此时,小武已同别人结婚。完全复原了的她,想去追求男人。但纺纱厂的普工没结婚的不多,多老气横秋且只想成家不想恋爱。于是她决定去厂外另辟蹊径。在父母家周边的邻居中尝试过两次,但都落败而归。常人看来,龙思乡既不漂亮也不年轻,又穷。愿意和她相好的只有那些潦倒汉子,有的想找个为自己做家务的女人,有的是想找个谈话的对象以打发漫长的时光。他们对性生活兴趣不大,能力也比较差。而龙思乡的目标是找一个在性生活方面同她相配的男人。受了挫折后,龙思乡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暗娼。但暗娼不是随便可以做的,首先要有一套单独的住房,其次得有人给她介绍客户,第三还得同警察搞好关系。这些对于她来说都是越不过去的障碍。两年过去了,城里的色情业渐渐兴旺起来,纱厂女工纷纷进入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年轻又有几分姿色的。龙思乡和同事金珠也想去色情场所找个工作,但那些老板鄙夷视之,没人愿意接受她们。当龙思乡感叹年老无望时,金珠说思乡在她眼里比谁都更有吸引力,不能打退堂鼓。“金珠说这些话时,龙思乡就赞赏地望着她的脸。她看到这张患肺病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少女般的纯洁,于是不由得想哭。但她忍住了。她回想起近来得到的种种关于色情业的信息——一些女人患上了性病,有的还患了绝症;某个隐蔽场所又出现一具女尸;一名妓女杀死了她所痛恨的嫖客,等等。龙思乡和金珠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按一般人的评估叫‘得不偿失’的行业。可是回想她们所过的生不如死的日子,她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们失去呢?在纱厂干下去无疑是一个早死的结局,但除了纺纱,她们别的事全干不了,也没有兴趣去学任何手艺——她们确信,等不到她们学会就会死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这不是对拥有打虎本领的自信或者天生性格豪迈,而是对生存处境的极度厌倦之后的反叛。然而,这种反叛是缺乏充足的条件和必胜的信心的,只能盲目地扑向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中。终于,在阿丝和韦伯的帮助下,龙思乡和金珠成功加入性工作者行列,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相好老永和驼哥。这些女性没有世俗的善恶是非观念,道德伦理观念,法律观念,只要对象契合自己的需要或者追求,就义无反顾地与之交往。金珠知道他的相好老永是水泥商,专门生产劣质水泥,发了黑心财。我们城里新盖的房子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供应水泥的,只想大大敲他一笔,可是没想到老永移情别恋,喜欢金珠的朋友龙思乡。在这里,金珠完全不关注是非善恶观念。这些女性认为性交往并不在于物质上的获取,而是她们追求“幸福”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些现实生活的叙述,只是作为心灵反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现实世界本身存在但不具有决定性和先在性。艺术创作中,主体性地位的独立性和精神性为主要条件,不是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和先在性。重视心灵挖掘而不是现实反映,这与现实主义把握世界的方式重点截然不同。在论述现代文学发生时的启蒙主义者向审美主义者的转变时,周仁政先生有曰:“在审美主义意义上,生命力则不是现实的力,而是情感或艺术的力。在尼采或柏格森那里,它体现为对理性的‘逻各斯暴力’的怀疑和反叛。这表明,就其现实性而言,启蒙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即将褪化为艺术中的一厢情愿的个人主义幻想。甚至,启蒙,连同它所带来的一切社会景观和价值准则因其现实性(即时性),都将沦为艺术所背离和所审视的对象。”将之移植到这里,可以说明残雪的创作倾向。
二
人性本真和人生本质,不是显而易见地存在于社会和现实当中,而是隐性存在于精神与灵魂深处。外在现象不过是本质与本真的曲线显露。残雪小说的人物为平凡人,行为却不尽是世俗,其中隐藏着超凡脱俗的灵魂指向;悲观颓废也不是小说的主题,有理想有追求的生存意境才是其本质旨归。《新世纪爱情故事》以韦伯、牛翠兰、龙思乡、阿丝、小袁老师、刘医生等为例,描写了他们活泼主动的心灵舞蹈和灵魂悸动,通过爱情永生的虚幻现实来彰显个体坚持不懈的自我救赎。在个体本能日益衰弱萎缩的时代背景下,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本能或许有些亢奋,情感自然有所夸张,方式当然有些离奇,想法难免异想天开,但正是这些不同寻常的表现,让我们觉得新新人类的灵魂觉醒和自我拯救大有希望,不至于坠入万丈深渊。小说中的男性和女性角色都不想建立稳定的家庭,因为稳定的生存状态与灵魂探险的深层欲望相悖。他们对异性的渴望不过是寻求精神发展的动力装置,获得灵感的源泉,重新激活审美机制的动力。阿亮对于尤先生、小袁对于刘医生,翠兰对于韦伯,阿丝对于阿援等都是如此。毫无疑问,残雪小说所展示的心灵幻界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丹尼尔·贝尔论述现代主义的特征时说:“现代主义也坚持说表面现象无意义,而试图要揭示内心想象的潜在基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格上,它设法抹煞‘距离’——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审美距离等——坚持经验的绝对现在性,即同步感和即刻性。二是主题上的,它坚持自我的绝对专断,强调人不受任何限制,迫切寻求超越。”这种现代主义式的小说创作,彰显了个体的心灵幻界,突出了个体的灵魂蜕变,理解接受实在不易。游离的文字和荒诞的故事背后,能指与所指难以落实,写作意图难以说明,主观动机扑朔迷离。
《新世界爱情故事》中“乡村”意味深长,缥缈空灵。残雪笔下的“乡村”呈现出浓重的超现实色彩,有着“故乡”的意味。翠兰对乡下老家的留恋、去过翠兰老家的情人韦伯竟觉得“那个荒凉的乡村同自己的老家有某种联系”、古董店鉴宝师尤先生也因为对翠兰的家乡背景感兴趣而在早年同她父母立下了婚约。同时,“乡村”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小说的描述中,乡村的荒凉宁静与城市的污浊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居在尤先生壁橱的流浪女阿亮来自乡村,“流浪女阿亮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他展示了一片新天地,他感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沐浴在她的光辉之中,阿亮还拓宽了他对专业的看法,因为有了阿亮,现在这个阴沉的城市充满了种种亮点。”翠兰回家乡看望堂兄和堂嫂,离开时,“翠兰走出那片稻田之后回头一望,吃惊地发现那屋子和樟树都从地上消失了。她脚下是那条鹅卵石小道,小道给她一种亲切感。她想,长着金属叶片的参天大树,艾叶浓浓的香味,银白的雕像般的人影,还有那滚动的火球,这些都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有着这样的家乡的幸运的人,用不着害怕迷路。”然而,这样的“乡村”已经无法抵挡城市文明的侵袭。村子被压缩到了地下,有看不见的暗道将它同城市连在一起。作家在此想要表达的或许是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反思,这正是西方先锋派生成的历史语境。小说中,阿亮说:“翠兰姐啊,我失去家乡了。……你是知道的,我们那里,家乡不在地面上了。我每天在地里嗅来嗅去的,然后我就找到尤先生的楼上来了。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家。可是我害了尤先生。”阿亮还对尤先生说,“我在乡下很胆小,我快离开乡下那段时间,村子已不在地面上了,我成日里嗅来嗅去的,找不到村子的入口,而且我也很少遇到村里人。可是现在,你瞧,我一下子就见到这么多村里人。在城里,我反而常常碰见老乡,莫非他们早搬到城里来了?”尤先生所在的古董店老板也激动地表示:“我也想移居乡下,可村子已经移到了我们墙壁上!”可见,小说中的“乡村”已经成为城市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即使有“暗道”相连,也始终难以摆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阿亮的“思乡病”无法治愈,小说道出了人类共同的“乡愁”。残雪《答〈文学报〉记者》一文认为,故乡就是精神和肉体共同的故乡。文学的源头,人类情感的源头,那种终极的、原始的、黑暗的所在便是故乡。有气魄、有野心的作家才能追求这样的故乡。平庸的作家则只能追求“黄土地”似的的故乡。故乡是来自黑暗地母的异质风景,它们又同我们的生活场景息息相关。它们是日常生活的本质;它们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应该说,这种故乡情结,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件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种机械生活的异化。他既不想模仿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找一个失去的故乡而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要求。”
牛翠兰、龙思乡、金珠、阿思、小袁都处在对自我当前生活和所处环境的不满当中,灵魂总是处在寻觅和探讨的过程中。所谓爱情,其实是对现实存在的不满与逆反,对当下限制的叛逆与反抗,因此,它已经蜕变为一种理想,一种自由的极致。这种自由的极致点燃了人性深处的新奇欲望与自由意志,契合人之初心与素志,因而充满诱惑,鼓舞人心。在这种理性思维的牢笼下,这些女性与男性的交往违反常伦,背离常态,双方都不管对方家庭与原配,也毫无第三者身份的羞愧与自卑,甚至说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形式越轨,内容抽象,缺乏诗性的男女爱恋情节与激情场面,多为抽象性的哲理思辨与自我反省。这种爱情,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女之爱,也不是走向婚姻家庭的现实之爱,而是一种彼此寻找、双向获取精神能量的方式,是一种精神自我突围与灵魂寻觅归宿的终极之爱。无疑,这是一种象征和暗示、幻化与异化的表达方法。“人物都处在执拗的自我寻找中,在寻找中审视自我、否定自我,不断实现自我的精神突围。那种精神跋涉的历程本身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而艺术家正是在对自我的辨证认识中实现精神的突进的。这个意义上,作品中人物的自我审视与艺术家创作中所伴随的灵魂历险,共同缔造了人类精神史。残雪强调的是精神突围的过程,至于结果如何,这并不在她的审美视线之内。也许,写作于她而言就是创造历史,而残雪本人则是身处历史长河中的一叶小舟,她要面对的是,通过对自己灵魂踪迹的反观与追索,来实现她衔接人类精神史和艺术史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雪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猥琐或者堕落的现实表象不是她要表达的对象。
宣扬自动写作,不需要刻意构思的残雪,善于想象或幻想人物灵魂裂变的片段而不是连贯的表现,用奇异的线条勾勒灵魂突围的图象,又以这种灵魂自由为审美理想。追求异性,而不沉迷于性爱,更不会淫欲无度。这种对异性性爱的追求,其实就是作者精神追求的极致象征,通过追求理想来建构自我,她们勇往直前,不知疲倦,跋涉在人生之路上。这种精神追求并不是空洞的冥思和感悟,它根植于那种令人恶心的世俗欲望。借助肉欲狂欢和性错乱的形式,个体的自由意志才能激发,追求理想人格的心理能量才能被转化,从而完成个体形而上的精神之旅。在这种精神写作的意念下,残雪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被她赋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探索性,因此,都表达了欣赏之情。如她自己所说,《五香街》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我们大家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东方和西方,也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过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讽刺世人,或针砭时弊。我的角色都是有面具的。其实我对我的每一个角色——从X 女士到寡妇,从煤厂小伙到孤寡老妪——都从心灵深处发出了强烈的欣赏。”邓晓芒《自我在何方——评黄泥街》有曰:“《黄泥街》所展示的也不过是残雪的内心,各个‘人物’只是他自造的心象,是她内心纷乱的矛盾、极端的感受、绝望的冲撞和狂热的追求的象征化和情绪化的体现。”
阅读残雪作品,不能从传统文学观念出发,从文学反映现实、再现现实的角度出发,甚至也不能仅仅从理想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之理解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如果这样,错位和误读就在所难免。走进残雪文学世界,理解残雪的文学思想,把握残雪的艺术追求,实为不易。残雪自己就《新世纪爱情故事》答《文学报》记者问,有曰:“《新世纪爱情故事》写的是可能世界里的爱情故事。但这些可能的爱情故事绝不是没有现实性的空想,它们都是将要实现和已经在实现着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凝聚着作者对于情感的深层体验,与时代精神和潮流相呼应,所以称之为‘新世纪爱情故事’。我认为新小说都是植根于现实经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向上升华,超出表层经验。这部长篇的特点是针对令现代人深深困惑的情感(爱情)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主张。但这种讨论和主张并没有学究味,整个作品是像植物一样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我以往的情感小说未曾像这个长篇一样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我的超越。”小说文本越对读者具有不可抵制的诱惑,燃烧其内心欲罢不能的探索欲望,但形散的结构和怪异的情节、离奇的氛围、交错颠倒的时空和看似非理性的语言,使得阅读残雪作品一般来说缺乏快感,缺少流畅,难以酣畅淋漓,更加难以如痴如醉。除非受过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影响,否则,难以进入残雪的文学世界。这注定了残雪小说的受众不广,读者群体易小众化而难以大众化,前卫化而难以普遍化。
残雪似乎为形式而求形式,为艺术而艺术,然细读之后就会发现,其作品具有丰富的现实向度。当然,残雪本身并不限于为艺术还是为人生的观念写作上,而是在精神动力饱满充足时,随心所欲自然而然地写,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左右的写作。不需要废寝忘食,也不需要冥思苦想,她的思绪总是如潺潺流水一样,永不枯竭。写作,在残雪世界中,是一种精神的奋发和灵魂的突围表演,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快乐境界。阅读和写作更多的是为了在这种艺术生存中寻求自我精神的发展。这种审美的自娱自乐和艺术的追求,是一种创作观念更是一种生命本然,不是排斥世俗,拒绝现实似的孤芳自赏。
三
《新世界爱情故事》封底内容简介中有曰:“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追求过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值得度过的人生——一种自由的人生。而爱情,正是自由的极致。”但是爱情是否为“自由的极致”?韦伯、尤先生、袁黑、刘医生、小贺和牛翠兰、龙思乡、金珠、阿丝、小袁等人的所谓“追求”,都是空灵的精神暗流与潜意识,基本脱离于真实生活与社会现实,因此,表面的“自由”其实遮蔽了现实中的极不自由。而“自由的人生”的彰显媒介或者载体,又以“爱情”的方式呈现,更是颠倒了人类生活的主次和情感来源先后。“最狂热的恋爱者也难支持四昼夜不睡眠;比‘爱’的要求更加不可制服的是饮食的要求:这才是一个真正无限的要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不承认它的力量,而一点也不理解爱情的人却多得很。许多更艰苦的事业都是因为这个要求,而并非因为‘全能’的爱情才完成的。”爱情世界中,其实存在很多限制和无奈,约束和无力,怎么能说是自由的极致?残雪自言能否保持爱的能力也就是人性能否发展的试金石。爱情不是野蛮任性,它的内部是有自我约束的机制的。这个机制就是自由的机制。既然有自我约束的机制,又怎么能说是自由的极致呢?当然,残雪自言新世界的爱情是勇敢的、开拓型的爱情;是蓬勃向上的、有希望的爱情。它在高超的骑手的驾驭下以罕见的原始之力驶向自由的王国。书中女主角一般情感深沉,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理解力,不论在什么样的可怕情境之中都保持着爱的能力。她们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朦胧的理想,等等。这些都表明了《新世界爱情故事》的主题取向。
残雪深受卡夫卡、博尔赫斯、但丁《神曲》的影响。特别欣赏《城堡》,除了《变形记》,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非常喜欢。当然,残雪绝非模拟复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20 世纪80 年代的小说多“展示了一个荒诞、变形和梦魇般的世界,阴郁、晦涩、恐惧、焦虑、窥探和变态的人物心理及人性丑恶的相互仇视与倾轧,在她的作品中纠缠在一起,不仅写出了人类生存的悲剧,而且写出了人的某种本质性的丑陋特点。残雪小说的这一特点与西方现代荒诞小说似乎很接近,但其传达出的生命本体的苦痛、涌动出来的对生存的深刻绝望和绝望边缘的呐喊和挣扎,绝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荒诞小说的简单模拟,而是与她所生存的现实、所经历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21 世纪的残雪文学创作,自我特色更加鲜明,中西融合的因子更多。同时,残雪反对将观念运用到创作中去,主张从潜意识出发来写作,凭直觉感到了彻底非理性的写作是最好的写作。强调写深层东西,启蒙自我、忏悔自我和建构自我的新批判精神。阅读具有超前意识的残雪小说是寻觅自我灵魂深处幽微世界的精神之旅,也是对读者心灵世界的自我审视和拷问。残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更像是一个人的战争;而其新实验小说的创作,如今则是一个人的舞蹈。荒林曾经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指出残雪创作的意义:“从男女人物形象塑造归结到男女两性语言事实揭露,残雪小说反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和环境要素,却又发挥了传统小说的叙述策略。叙述两性语言(灵魂)隔离现状与探求两性沟通和对话的途径,以及叙述者的理想主义,定位了叙述的梦幻取向。借用时间、意识、潜意识交汇的镜子,象征性点明男女两性自明和共鸣的契机——在一切生存真相之上,残雪看到了女性超越的方向,而在女性超越的灵魂层面,残雪第一次在小说中超越女性视点对人的存在问题——男女两性的对话问题作了历史性、艺术性的探索和表达。”其实,残雪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为女性立言、争取地位的作家,她也不把文学作为现实的反映和再现视为必然,她甚至不把自己视为中国本土的地域性作家,而是追求一种世界性的纯文学创作高度,成为受到东西方共同认可的作家。确实,残雪小说超越女性视点对人的存在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和反省。
残雪还旗帜鲜明地将文学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自己的作品属于在纯文学小众阅读圈子里受到青睐的作品。写作难度大,不搞所谓文化的原汁原味,只搞个人的原汁原味,自己的东西绝对模仿不了。“我学习西方文化传统,并不是学那些表层的东西,而是学习人类共有的精神的东西,学习那个文化中的人性内核。我学会了他们的方法之后,运用到我的创作实践中来,一头扎进潜意识这个人性的深层海洋,从那个地方发动我的创造力。所以我相信我这类文学是最站得住脚,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希望还有更多的同人来从事我所从事的‘实验文学’,打破当代文学的封闭状况,造成国际影响,同国外同行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赛。文学虽然是极端个人化的,但也是可以竞赛的。比激情,比力度,比深度,比形式感,比勇敢……当然竞赛的前提是承认文学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承认人性是可以相通的,作品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残雪的文学野心不可谓不大,文学追求不可谓不高,文学意志也不可谓不强。作为读者,对残雪小说的阅读,需要借助现象学派所倡导的“内在”阅读方式,才能接近其作品的意图和主旨。现象学批评的目标在于对文本进行全然“内在”的阅读,一种根本不受任何外在之物影响的阅读。“文本自身被还原为作者意识的纯粹体现:它的风格方面和语义方面的一切都被作为一个复杂总体的有机部分而把握,而这一总体的起统一作用的本质就是作者的心灵。为了认识这一心灵,我们不能涉及我们有关作者的任何实际知识——传记批评是被禁止的——而只能涉及他或她的意识在作品本身中所显现出来的那些方面。而且,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一心灵的种种‘深层结构’,它们可以在反复出现的各种主题和各种意象模式中被发现;而把握这些我们就是在把握作者‘体验’(lived)他的世界的方式,以及作为主体的他与作为对象的世界之间的种种现象学关系。一部文学作品的‘世界’不是一个客观现实,而是德语所谓的Lebenswell,亦即那个被个别主体实际上组织起来和经验到的现实。”问题是,当残雪小说中哲学语言和结构、哲理充溢的时候,小说是否会沦为哲学表达的一种工具?这样的小说还能否保持其文体的自足性和独立性?
多年前,王蒙就说过:“有才气的残雪确实没有重复任何人,除了她自己。”“一心追求特与独会不会成为一种框框呢?不用读完残雪的全部作品,也许我可以摸索出她的道道,她的模式,她的叙述程序,她的爱用的词汇。”今天,这种自我重复能否避免?毕竟,对生命的歌颂与对理想的不懈探求,张扬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求索性与创新性,说多了就难免重复;自动写作的方式用多了也难免自我因袭。以看似游离散乱、语言神游和情节虚幻的小说文本来表达生命的本质主题,难免曲高和寡,观者寥寥,更不必说它对大众的感染共鸣了。这种暂时属于深受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影响的少数读者“品味”的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积累的增加,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读者和知音。
〔注释〕
①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首刊于《花城》2012 年第6期,2013 年6 月作家出版社以同名专著出版。至2015 年初,笔者只看到王迅和张晨曦的2 篇评论文章。而同龄同乡的韩少功《日夜书》首刊于《收获》2013 年第2 期,2013年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同名专著出版。随之,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今有20 篇以上;更有卓今等人主编的《解读韩少功的〈日夜书〉》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年10 月出版。两人作品待遇截然不同,除了文学风格差异等原因外,孤高的残雪脱离于主流文学批评界为重要原因。
②对“乡村”意蕴的分析,参见张晨曦《一枝独秀的“先锋”——就〈新世纪爱情故事〉看先锋文学的现状》,《光明日报》2014 年1 月6 日第13 版。
〔1〕阎连科.作家们的作家?〔N〕.中华读书报,2002-03-13.
〔2〕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周仁政.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5〕(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6〕王迅.自我何以现身——读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J〕.创作与评论,2013(10).
〔7〕残雪.《五香街》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8〕残雪.《黄泥街》附〔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9〕残雪.答《文学报》记者问〔A〕.残雪《黄泥街》附〔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10〕(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周扬译.1979.
〔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 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2〕荒林.超越女性——残雪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4(5).
〔13〕残雪.残雪文学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英)特雷·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5〕残雪.残雪文集·附录(第四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