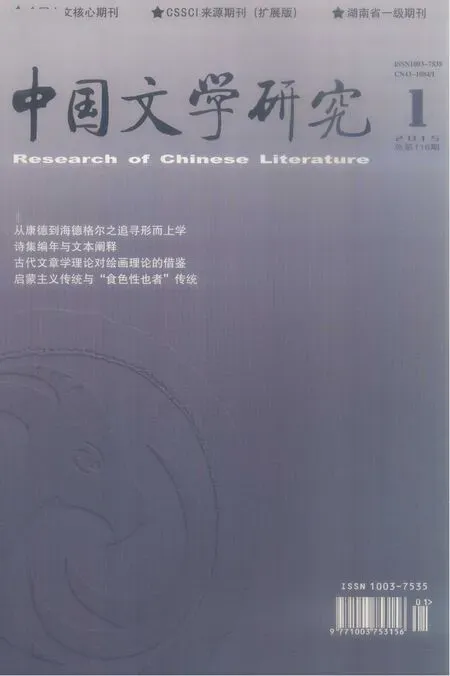对“生命”歌者的解读——评凌宇的沈从文研究
2015-11-14马新亚
马新亚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湖南省文联 湖南 长沙 410001)
作为沈从文研究的集大成者,凌宇最早在中国开展沈从文研究且成就突出。他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把沈从文作为文学家的肖像全貌做了清晰的描画,对他的文学成就第一次做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完成了一种对颠倒了的历史的再颠倒;随后他又依次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来拓展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以重经验、重历史、重实践的学术风格将沈从文研究不断推向细化和深化。凌宇对沈从文研究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在于其用披荆斩棘、敢为人先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勇气,反思并重构沈从文的“人性”——“生命观”,并在价值判断上,将“经典重塑”“民族文化重构”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共同的人文诉求,触探到了20 世纪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问题”,为“沈研”开辟了一条充满前瞻性和可生发性的研究路径。本文力图从“人性”——“生命观”这一阐释向度出发,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做出既举重若轻又切中肯綮的评价,并希望由凌宇的沈从文研究,为现代文学研究史留下“立此存照”的一份精神档案。
一
“在《水云》一文中,沈从文曾明确申明: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生命观是沈从文人生观的核心,他对人生的全部观察与思考,都是以他对生命的理解为标尺的。”以此类推,“人性”——“生命观”也是解读沈从文——这一“生命”歌者的切入口,而要客观地评价凌宇对沈从文“人性”——“生命观”的深度解析以及其对“沈研”的重要意义,我们不能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风向。
其实早在上世纪20 年代,沈从文就以他丰硕的创造成果受到文坛的重视,但直到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他一直没有得到与他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相匹配的整体性的评论和定位,在大量的沈从文作品评论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批评倾向和模式就是“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针对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和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认为沈从文思想空虚,作品中人物空洞,“湘西世界”不具真实性和典型性。尽管在此之前也不乏苏雪林和刘西渭等人的客观评价,但否定沈从文的声音毕竟是大势所趋。随着海外华文研究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对沈从文的推崇,国内学界重新评价沈从文的呼声开始此起彼伏。新一代的沈从文研究者面临这样两个问题:一、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二、如何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作为国内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以及其后的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从史实和文献出发,对沈从文20-40年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进行考证和辨析,证明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立场独立的民主主义者。这一论断的提出,“为后来持续讨论沈从文生命观中的人性问题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也彰显了论者的学术勇气和独立意识。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凌宇还将沈从文的个人经验、思想倾向、生命观、艺术观与其文学世界融合在一起,相互印证,相互生发,全面系统地对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进行了阐释。凌宇对沈从文作品中的“乡下人”形象内涵进行了分层次解析——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的角度看,“乡下人”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看,“乡下人”是“蒙昧人”;从主体精神同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乡下人”又是陌生人。论者的评论话语模式已开始摆脱意识形态论的痕迹,从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的广阔视野出发,带有“还原重构”特征。由都市乡下两种经验的互参和对“乡下人”形象的理性分析,凌宇将“人性的扭曲”与“人与自然的契合”放置在一起构成沈从文所构建的都市上流社会和乡下抹布阶级的精神坐标。与这种认识相应,论者引出了沈从文提出的两个概念——“生活”与“生命”。他认为沈从文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既非种属关系,也非交叉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了延续后代的婚姻行为”。沈从文“并非以超然尘世的态度来看待‘生活’”,而是主张在满足“生活”的基础之上,向人类的本质规定性做出思考,换而言之,要朝“生命”迈进。他在下层人民担负自己命运所做出的努力上看到了“生命”应有的“庄严”,然而这种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形态只是“生命”的初级形态,只有将“自在状态”上升为“自为状态”才能够达到“生命”的高级形态。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一文中,凌宇将乡下人的“生命”的形态进一步阐发和界定为四个层次,即原始的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这四种形态不仅是一种并行不悖的现实存在,而且也表现为“生命”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形成一种必然的“进化”趋势。
以当前沈从文研究的学术眼光来看,凌宇的学术话语属于启蒙主义的、偏重社会学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膨胀”的时代烙印,但在1980 年代初期的时代语境之下,“人性”——“生命观”的研究路径的开辟以及其后的不断深化,极大地摆脱了阶级论的窠臼,拓宽了沈从文研究的学术空间,营造了以学理介入沈从文研究的学术氛围,为之后的沈从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虽然凌宇在论及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一概念时,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进行了对比,指出两点显著区别:一、沈从文的“人性”观,不承认在现实人生中还普遍存在着共同的人性,都市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与下层抹布阶级的人性美就是例证,虽然沈从文的理论水平还没有达到阶级性的高度,但粗层次的阶级分野是他已经意识到的。二、沈从文思想中的人性,具有人的社会性的具体历史内容,与梁实秋“人性论”的“空泛”有天壤之别。虽然沈从文的“人性”观与梁实秋的“人性论”不同,但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文学的一大批作家都曾为“人性”张目,例如冰心、郭沫若、巴金等,因而“人性”并不是沈从文的“专利”。有一位学者曾这样讲:“吴立昌、凌宇等学者以挖掘人性的理性取向、阶级价值、社会内涵为旨归,就没有把沈从文表现的人性在本质上与其他现代作家区别开来,没有真正呈现出沈从文表现人性的独特性。因此,这一种学术思路,虽得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追随,却未必是正确的方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原因有二。一,这种观点没有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语境,因而对“人性”——“生命观”研究路径的意义未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上世纪70 年代末到1984 年为止,是国内沈从文研究的第一阶段,也即“反思”阶段,这个阶段的沈从文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以一种反命题代替原命题,也许同时就意味着对原命题赖以生存的理论模式的认同”。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者论证沈从文作品倾向的进步性,恰恰是对阶级论模式的认同,由此带来的是“研究者立论时无法挣脱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触及沈从文人性观建构的复杂性,就无法将沈从文研究走向深入。“人性”——“生命观”的研究路径由此应运而生,它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范畴纳入视域,在当时的沈从文研究界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这一路径背后的潜在意图在于将沈从文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中,从“现代化”“西化”“本土化”等范畴中进一步厘定沈从文创作的思想艺术价值。此外,尽管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有很大的非理性,且沈从文人生观、文学观的建构成因纷繁芜杂,沈从文所开启的文学传统也很难一概而论,但我们评论一位作家,不能够就事论事,还要拥有文学史的眼光,“必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势”,这样才能“找到打开个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能不至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凌宇的对沈从文“生命观”的深刻阐发,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期论文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印记)和启蒙话语模式,旨归在于论证沈从文对五四启蒙传统的融入,尽管其方式是独特的。二、这种观点没有将凌宇的沈从文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查,因而有断章取义之嫌。凌宇“人性”——“生命观”的阐发是与湘西的地域特色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苗——汉文化冲突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在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沈从文的“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的主要部分,都着重从道德观与价值观的角度,在更深层次上揭示苗汉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矛盾与对立、渗透与交织”,举个例子,《龙朱》里对苗人重“情”不重“利”的婚恋观到《边城》里,逐渐演化为“情”与“利”的对峙。“渡船”与“碾坊”,“走车路”与“走马路”两组意向分别象征了“情爱”与“利益”的两相对峙,也是苗汉两种文化在婚恋观上的显著体现,这种对峙,体现了沈从文作为南方少数民族的内心隐忧和文化焦虑。沈从文从湘西步入都市,从中获得了现代意识,反过来再用这种现代理性精神去观照湘西本土人生,沈从文的孤独,并非只是他的“个人孤独”,“更是他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孤独。这个民族正是在长期遭受的民族歧视里,走着自己的民族生存之路。”由此看见,凌宇的“人性”——“生命观”研究路径始终是站在沈从文所立足的本土文化(或者说是“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立场上的,这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进而言之,相对于之后国内学界铺天盖地的“国族想象”等研究视角,“重新回到‘湘西’独特的‘巫楚文化’背景下,从其特有的民风民俗情境中,深入发掘沈从文的与众不同,会比民族国家想象来得更实在,更能够抵达沈从文小说的内核。”
三
如上所述,凌宇的“人性”——“生命观”的研究路径,是建立在对湘西文化在沈从文文化心理建构的重要位置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是可以抵达沈从文创作实质的一条沉实又具有生发性的研究路径,凌宇在其后的沈从文研究中,以此为基点,在更广阔的研究视域内对沈从文创作实质做了切中肯綮的阐释。
凌宇于1992 年撰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将沈从文“对人生的文化哲学观照”与作品的“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有机融合起来,避免了“纯叙事学”解析方法的封闭性和单一性。以对《八骏图》的解析为例,他首先展开叙事学的分析,认为“八骏”中的七骏经由“八骏”中的一骏——达士的观察获得呈现与评判,达士既是“聚焦者同时也是被聚焦者”。“通过近于并列结构叙事被呈现的‘七骏’的言与形、表与里的分裂,即意识与下意识的矛盾冲突”“暗示出人物病态成因的阅读方向:人的自然本性所受的分别源于中、西方的社会、文化理性,诸如‘道德名分’之类的压抑,与人的自然本性反社会一文化理性限制的下意识冲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成了人的存在的病态尴尬。”论者将叙事学阐释作为出发点,将文化哲学(心理学)阐释作为归宿和方向,而作为沈从文文化哲学核心内容的“人性”——“生命观”仍是重头戏。《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一文,凌宇拓展并深化了他的早期论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的观点,将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放入二三十年代现代乡土小说的整体图景和流变中进行类比和对比,突出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凌宇认为现代“乡土小说”中的“乡愁”是由三种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三维)交互作用于乡土的结果,有一个“乡土乐园”——失乐园——重返乐园历时思辨的潜逻辑”,而“桃源寻梦——梦断桃源——桃源重建”则展现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家甚至百年来中国作家的精神历程。“桃源”之所以成为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型和中国文人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是因为它拥有“人性准乎自然”的田园视景和牧歌情调,而“桃源梦断”之于沈从文,不在于“乡土苦难”(卢焚作品所呈现出的),而是与准乎自然的人性并存的理性精神的原始、蒙昧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桃源重建”精神历程中,不同于鲁迅的反传统文化立场和废名的厌世主义,沈从文主张“经典重造”,“其内核便是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形式的复归”。由此可见,即使在“乡土小说”的宏大论域,“人性”——“生命观”仍然是沈从文思想情感的逻辑起点。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一文中,凌宇认为:“将人生作生活与生命二分的观点,显示出沈从文对人生的心理学把握方式。”“同弗洛伊德将求生欲繁殖看作是人的主要存在的观点相反,沈从文认定人生的价值,在于生命。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实现了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超越,而与20世纪50 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方向。”在这里,凌宇将沈从文的“人性”——“生命观”做了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阐发和深化。此外,凌宇还撰文阐释了传统文化(儒释道)的积极因子与沈从文生命观建构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1990 年代以来,国内开始盛行“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守成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西方心理学理论”,沈从文研究也面临着理论更新的问题,在《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凌宇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叙事学、心理学等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并为沈从文研究带来了新的质素,由此我们看到凌宇的学术敏感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凌宇中后期沈从文研究的多重视角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和前期的“人性”——“生命观”相互印证,相互渗透,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人性”——“生命观”研究路径的可生发性;更进一层,我们要透过现象,体察到一个评论家一贯秉持的“大文学评论观”,也即能够运用中西、古今两个维度,将沈从文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框架和体系,既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吸纳和接受,也考察中国文学传统在现代作家身上的传承和流变,从而形成一种切合现代语境的复合型的研究模式。其实,在凌宇的代表作《从边城走向世界》中,这种复合型研究模式已经初见端倪,后期的研究模式与之一脉相承。
小 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都有“道”和“术”之别,“道”是终极目标,“术”则是技术层面的方法和手段。用在做学问上,“道”则是指研究者对终极价值理想的选择和预设,也包括研究者个人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文如其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术”则是指研究者所秉持的理论基础、逻辑结构、技术方法。就方法层面来讲,凌宇所操持的可谓简单陈旧,无非是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一种方法是否得心应手,是否能够接近真理,还要看操持着的“道”。凌宇将沈从文研究的切入口和重心放在阐释其“人性”——“生命观”上,这一学术眼光,蕴含了对“人”的本质进行追寻与拷问的终极价值选择。如果说“人”的重新发现掀起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新局面,那么同样也是“人”的发现,为“五四”文学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创作与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现代内涵,这便是凌宇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
这一命题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启蒙”逐渐退场,“碎片化“代替“整体性”,“轻叙事”代替“终极命题”,价值判断走向了相对主义。这样一个文化多元、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的时代也许更需要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人”的本质,“照‘我’思索”,去理解“我”;“照‘我’思索”,去认识“人”。在此基础之上,将“自我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独立、自由与完善而努力,即‘时时刻刻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为人类远景凝眸”。这便是沈从文与我们的隔空对话,也是凌宇学术思想独具前瞻性的表现,更是凌宇借沈从文研究对“中国问题”所做的人文观照。作为一位有洞见力的人文学者,凌宇最终摆脱了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使一种貌似陈旧的方法论摆脱僵死的宿命,借助“道”,使之焕发出新的阐释能量。
综上所述,凌宇以他重经验、重历史、重实践的学术风格,将沈从文研究带入了一条沉实的道路。尽管他的话语模式带有历史局限性并且不可避免地将被后来者所超越,但他和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1980年代沈从文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框架,而这一基本格局和框架沿用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大而言之,凌宇和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杨义、赵园、刘讷、许子东等并称为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的学者,他们面临着如何在新时期将被社会意识形态所遮蔽和尘封的文学资产进行清算和重估的历史关口和文化行将断裂的历史情境,他们以不可遏抑的学术激情和人文情怀参与文化重构,完成了一种对颠倒了的历史的再颠倒,并在这种重新认知与评价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观与评价体系,完成了对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及其评价体系的解构,并为“重写文学史”运动拉开了帷幕。这便是他们那代人的学科贡献。
〔1〕凌宇.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2).
〔2〕凌宇.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2).
〔3〕赵学勇、魏巍.1979-2009:沈从文研究的几个关键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6).
〔4〕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5〕刘洪涛.沈从文价值重估——兼论80 年来的沈从文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2).
〔6〕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
〔7〕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J〕.文艺研究,1986(2).
〔8〕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4).
〔9〕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J〕.文学评论,2000(4).
〔10〕凌宇.从民族古井里汲取新鲜泉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
〔11〕本人有关“道”与“术”的概念和辩证关系的阐述以及下文的部分结论皆受王侃. 翻译和阅读的政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