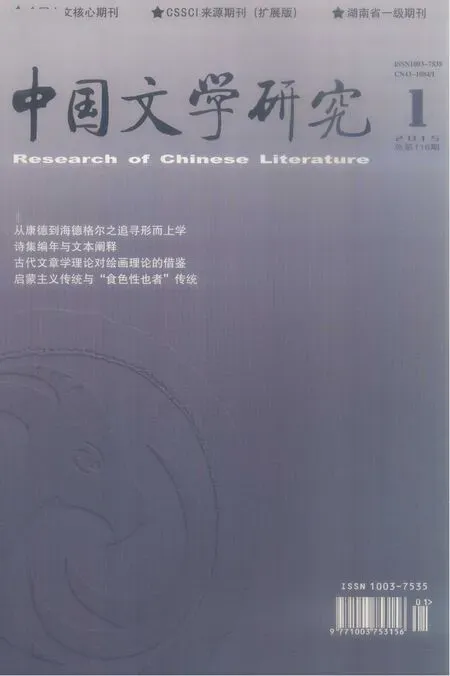诗集编年与文本阐释——以杜诗编年为考察中心
2015-11-14杨经华
杨经华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诗歌编年是自宋人率先开创的一种文集编纂形式。它打破了以往按体裁、题材的划分形式,转而以诗歌之创作年代的先后为次序。这种变化所反映的文学与批评观念,已深为国内外学者重视。刘明今将编年与诗史说看成是宋人以知人论世方法研究某一作家的典型,并指出:“它的出现必然推动人们以同样方法去研究其他作家”。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在此基础上,专门撰文系统讨论了诗人年谱、编年诗集及“诗史”说之间的相互关系。浅见之文曾经数次修订,长达数万字,由此可见他对诗集编年诸问题用功之深。此外,周裕锴先生亦指出了编年体在阐释学中的意义,他说:“按年月先后的编排,意味着把作品看作诗人对其生活时代的时事以及个人经历的出处的记述,阅读的目的在于了解诗人的人生变迁与风格变化之关系,这是一种‘史’的眼光。”
以上研究表明,关于诗集编年的知人论世功能以及与诗史说的关系等,均已成为学界公论,此不一一赘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诗集编年诸问题已经穷尽其源,再难置啄。相反,通过这些研究,更加凸现了人们对诗集编年了解的局限。诗集的按时代编次仅仅是与重视作家个人经历,重视写作背景的知人论世方法相关吗?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以为,当一个笺注者为诗歌编年时,其本身已是从事一种阐释活动。围绕诗集编年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尤有深入研讨的必要。
一、诗集编年与杜诗编辑的渊源
编年诗起于宋代,这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关于促使其产生的原因,迄今未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浅见对编年诗文集进行周详的考察,认为它的产生与宋代“诗史”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具体怎样影响到编年诗集的产生,仍然语焉不详。
周裕锴先生认为,宋代诗文编纂的编年思维是受宋代编年史观的影响,尤其是宋代伟大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所采取编年形式的成功,不仅开创了一种以时代先后顺序来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编年史观,同时它还促成年谱的产生,从而影响到诗文编年编纂的体例。周先生为诗集编年产生之思想渊源找到另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种解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在《资治通鉴》之后才出现诗集编年问题呢?换言之,编年意识是否在《资治通鉴》问世之后才开始萌芽壮大呢?
一般认为,文集的编纂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宋代以前除了白居易、元稹等人自编文集的例子外,可了解其编纂体例情况的例子并不多。而白居易的诗文集虽然将诗按照“讽谕”、“闲适”、“感伤”主题分类,但各类的内部却是按照编年形式排列作品的,尽管这种编年意识还未成为一种自觉的主导意识。
到北宋前期,王洙在编辑杜诗时,虽然主体上是按照古、近体编次,然而在分体之中,又寓编年。王洙云:“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在王编之中,编年的因素已经上升到较为重要的地位。
至北宋中后期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代,文人的自编文集已经成为时尚。除了著名的苏轼之外,其他如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等亦无不留心编纂己集。在宋代以前,文集的编纂主要是以《文选》为代表的编纂体例占主导地位。《文选》的编纂主要是以分体为标准。据今人傅刚研究,其收录题材达三十九种。在这些文体中,诗赋无疑占有主体地位。在诗歌体下又根据题材如分为“公宴”、“祖饯”、“咏史”、“游览”等二十四类。这些编纂方式在宋代已逐渐受到文人的批判。如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一中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正是源于对分类、分体的不满,编年体日益浮现他的主体地位。苏轼在自编诗文集时已经有意识采取编年方式。胡仔谈到苏轼自编《东坡前集》时说:“世传前集乃东坡手自编者,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苏轼自编的文集已是不分古、近体的编年体。
由此看来,在《资治通鉴》产生之前,虽然完全的编年诗集还未出现,但编年的意识却是积酿已久。无论是浅见等人的“诗史”说,还是周先生的编年史观影响说,都只是为编年诗集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理论背景。换言之,它论证了编年诗产生的可能性。那么是什么事件促使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呢?笔者认为,那就是宋人对杜诗的整理笺注。
自宋代中叶以来,杜诗逐渐获得经典地位,士人对杜诗的需求空前高涨。据范成大云:“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善本,琪家藏善本,雠校素精。使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杜诗的整理与编辑一度成为当务之急。当时的杜集编纂甚为混乱。据王洙云是“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序”。如何纠正当时的混乱情况,如何对散乱的杜诗进行系统的编排,无疑成为摆在整理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通过以上阐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由于不满以《文选》为代表的分体、分类的编排方式,编年意识的尝试已经屡次付诸实践。而杜诗素有“诗史”之誉,这股呼唤编年的潮流与杜诗编辑相遇合,迅速碰撞出诗集系年的火花,终于在北宋末年产生了第一部杜诗编年诗集: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今人周采泉指出:“此为杜集之最早者。”此不仅为杜集编年之祖,亦为古代诗集编年之祖。邵长蘅《注苏例言》:“诗家编年,始于少陵,当时号为诗史。”有学者据曾巩《李白诗集后序》认为曾巩曾为李白诗歌编年,但学界尚存分歧,故笔者不予置论。
关于这部编年诗集的编纂情况,李纲在《重校定杜工部集序》中说:
杜子美诗,古今绝唱也。旧集古律异巻,编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余尝有意参订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书郎黄长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辞,尤笃喜公之诗。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皆有次第。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黄伯思编杜诗乃是“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可见苏轼公开主张编纂当以编年为上的说法在北宋中期已经广为流行,黄氏只是在杜诗编纂中付诸实践而已。这里顺便提及的是,黄伯思的用“东坡之说”,日本学者浅见认为根据的“是一般视为托名苏轼的《杜诗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北宋邵武人。据莫砺锋先生考证,“伪苏注”产生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前后(即1143-1147 年间)。黄伯思作为北宋人不可能用南宋“伪苏注”。即使是作序的李纲(1085-1140)本人,也未及见到“伪苏注”,况且李纲序于绍兴六年(1136),离“伪苏注”的产生尚有十年差距。
据李纲序,此集正式打破旧集分体的界限,完全以年月为纲,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编年诗集。经过黄氏的整理,杜诗编年虽然初现轮廓,但是仍然存在编次混乱的情况。正如鲁訔云:“名公巨儒,谱叙注释,是不一家,用意率过,异说如猬。”针对这种情况,鲁訔在南宋绍兴间再次对杜诗进行编年整理。到了南宋中后期,黄希、黄鹤父子对杜诗逐一系年。按黄鹤自序云:“毎诗再加考订,或因人以核其时,或搜地以校其迹,或摘句以辨其事,或即物以求其意。所谓千四百余篇者,虽不敢谓尽知其详,亦庶几十得七八矣。”黄氏父子对杜诗年代的考订,成为后世笺注辨析、修正的基础。四库馆臣称之云:“(编年)其例盖始于黄伯思,后鲁訔等踵加考订,至鹤父子益推明之,钩稽辨证,亦颇具苦心。”在杜诗编年的影响下,宋人对当代诗人文集的整理亦纷纷采取编年形式。如《施注苏诗》张榕端序:“盖施氏体宗编年,一洗永嘉分类之陋,而援引必著书名,诠诂不乖本事。又于注题之下务阐诗,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与少陵诗史同条共贯。”邵长蘅《注苏例言》:“少陵以后,惟东坡之诗于编年为宜。常迹公生平,自嘉祐登朝,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三十余年。其间新法之废兴,时政之得失,贤奸之屡起屡仆,按其作诗之岁月而考之,往往概见事实。而于出处大节,兄弟朋友过从离合之踪迹,为尤详。更千百年犹可想见,故编年宜也。”
自南宋以后,由于编年在阐释杜诗、理解杜甫人生经历与思想变迁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杜诗编年不仅成为历史的主流,而且进一步推广到其他诗集的整理。清钱泳云:“读杜诗者有编年、编体、编类,三者之中,自当以编年为正。”浦起龙亦云:“编年最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最劣。”直到现在,古代个人文集的整理笺注大多采取编年形式,如《李白诗集编年》,。
综上看来,诗集编年的正式形成以及发展壮大,都与杜诗的整理存在不可割断的历史渊源。弥漫在北宋编年的“史”的意识与杜诗编纂相互交织,互为表里,共同促进这一诗集编纂形式的创生与发展。
二、编年与年谱之主宾关系
年谱,即将某人的生平记载按年月顺序排列整理的文献体裁。关于年谱的起源,通常认为它是始于宋代,学界对此辨析甚多,此不赘述。年谱的产生与诗集之编年几乎是同时交织产生的。那么二者是存在主宾关系,还是并行独立的呢?许多学者对此仍然语焉不详。
关于二者的关系,迄今研究最为用功的是日本的浅见洋二。但浅见给出的解释却存在前后的矛盾。他在《诗人年谱与编年诗文集》的专节中,他一方面说,“在年谱出现的同时,编年体诗文集的编纂也开始兴盛起来”,在后面的论述中,浅见首先描述了宋代年谱的盛行情况,列举了宋代出现的一百多种年谱,紧接着年谱兴盛的同时,讨论了编年诗集的编纂问题。显然在浅见看来,是年谱盛行在先,编年体出现在后,编年体诗歌的流行是受宋人年谱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是“宋代才明确起来的编年意识呼唤着年谱这种书籍的出现”,年谱是“在与诗文集的编年工作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出现的”,显然认为年谱只是为配合编年而出现,是诗集编年导致了年谱的产生。这两个方面的互相矛盾,表明了浅见对二者关系仍然缺乏本质的认识。
通过文献的梳理,尽管正式的诗集编年在北宋末年黄伯思编杜诗时才出现,实际上诗集编年的意识在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杜诗已经有所实践。而这时年谱尚未出现。根据学界的观点,我国第一部年谱是吕大防所编的《杜诗年谱》。周采泉叙云:“今世存北宋人所著年谱,恐以汲公杜韩两谱为滥觞,则此不仅为杜甫年谱之第一种,亦为我国所有年谱之第一种。”此谱编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而在这些年谱出现之时,苏轼已经在自编文集自觉进行了编年尝试。
年谱的出现,实际上是为适应诗集编年的要求而产生的。吕大防率先为杜甫韩愈编年谱,其根本的目的,并非为年谱而作年谱,而是为便于韩杜诗文集的编年整理。吕氏在韩杜年谱的题跋中指出,“余苦于韩文、杜诗之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毫无疑问,中国最初的年谱出现,乃是吕氏在编辑韩、杜之文中,苦于其中讹误甚多,故树年谱以正之。换言之,年谱的出现乃是其诗集编年的副产品。
在北宋最先出现的几种杜甫年谱,亦无不是依附于诗集编纂而存。吕大防之年谱已不遑论,杜甫的第二部年谱为赵子栎《杜工部草堂年谱》。周采泉云:“赵之撰年谱,亦非为年谱而年谱,盖赵氏亦注杜,今注佚而谱存耳。”此外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鲁訔《杜工部年谱》、梁权道《杜工部年谱》、黄鹤《杜工部年谱》都无一例外是为配合杜诗的编纂注释而作。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我国最初的年谱并非为年谱而作年谱,而是附生于诗文集的编纂与注释,为诗文的理解提供一个历史的时代背景。至于以后年谱逐渐逸出此范围,为年谱而年谱,脱离诗集的编纂注释而独立存在,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予置论。
关于年谱产生的条件,吴洪泽在《试论宋代年谱起源》中提出的原因有两条颇可注意:史学中的编年法与文集的整理促成年谱产生。由此看出,正是诗文集的编年实践导致了年谱的产生,并非如浅见所言年谱盛行才有编年盛行,而是相反。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重要资料,在史学界极受重视。在诗学研究中,宋人率先意识到年谱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意义。通过年谱的考定,可解一人之身世孤怀,体察其生命的轨迹与其文学创作的互动,揭示其思想的变迁与沿革。章学诚:“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年谱虽然在对诗人的思想阐释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年谱不能凭空产生,它必须立足于承载作者思想的作品。换言之,离开了作者的作品系年,年谱将必然失去存在的依据。在历代的文集年谱中,作品是年谱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辟有“诗”一栏,杜甫年谱更是如此。但年谱中的诗,不能囊括作者的所有作品,如《钱注杜诗》后所附的年谱中的杜诗仅四百首,约占存世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完全反映作者思想经历之变迁,还必须依据诗集的总体编年。
了解诗集编年与年谱之间的关系,即可明白,编年与年谱编纂,都是源于一种“史”的意识,在诗歌中发现史的因素,为诗歌的阐释与理解构建一个确定的历史背景。换言之,编年与年谱都是为诗歌的阐释服务,其本身也是一种阐释观念的呈现。
三、作品系年与文本阐释
在对诗集编年的研究中,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即仅仅将它视作众多诗集编纂方式的一种,这种定位无疑限制了对诗集编年现象的本质认识。我们只要稍作细心的观察,会发现在宋代以来,许多个人诗文集的笺注之作,大多采取编年体形式。这里反映的问题是,历代笺注家为什么那么偏重编年体?在编年的背后蕴涵着怎样的深层背景?
其实,诗集编年自其开始之时,其功能已不仅仅是为保存文献的编纂而编纂,而是为了指引人们对诗歌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这一点从历代杜甫的编年诗集笺注中即可证之。
宋人黄伯思为何率先为杜诗编年,李纲的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李云:“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皆有次第,然后子美之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粲然可观。盖自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肆佰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其时,犂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毫无疑问,经过黄氏编年,杜甫的人世变迁与杜诗的风格变化便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换言之,黄氏编年的目的即在于为杜诗的理解与阐释服务。
黄伯思之杜诗编年,今已不存,关于其编年原貌,我们已不可得知。现存较为完好的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则清晰地展示了编年的阐释功能。在此书的注释过程中,编年不仅成为一行重要的内容,更代表了笺注者所特有的阐释方式。通过编年的考释,该书取得的成果是突出的。黄居谊序云:“退披其编,诗以年次,意随篇释,冠以谱辨,视旧加详。至谓耒阳乃瘗宗文,高都护之非适,吕太一之非官,又皆意逆而得之,往往前辈或未及,不但成先志而已。昔杜预注《春秋左传》,世以预为丘明忠臣,黄氏父子用功此诗,谓非忠于工部不可。”
纵观杜诗的编纂笺注史,从宋代的黄伯思、鲁訔、黄鹤,到明清的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他们的笺注无不以杜诗的编年作为重要内容。
编年既是诗歌的一种编辑方式,也是阐释中意义产生的重要环节。任何事件的发生或任何情感的爆发必然是在一定的“时”或一定的“境”中发生。李清良在《中国阐释学》中指出:“当事件的承担者,即所发生之事件乃是某种特定意义的呈现时,意义承担者所处特定语境就是其呈现其特定意义之‘时’。”为某一诗歌的编年,实质就是将该诗歌所叙述的的事件或表达的情感确定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一旦事件发生的语境确定,其相应的意义亦将自然呈现。因此诗集之编年,表面上是一种诗歌的编排方式,其实质却是保证阐释活动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
杜甫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之编年即为诗歌之阐释与诗人思想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语境。此诗为杜甫同高适、岑参、薛据在长安登塔所作。关于此诗的编年,历代有不同的分歧。后闻一多通过排除法将之确定在天宝十一载(752)秋,广为学界所接受。
杜甫在此年登上慈恩寺塔写诗的时候,他们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历史语境呢?我们姑且将视野向前推移几年。
天宝五载(746),张九龄、李适之因受李林甫排挤罢相。李林甫当政后拼命排斥贤能,在天宝六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李林甫所谓的“野无遗贤”。李林甫把持朝政,暗中将所有应举考生摒落,而后上贺表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而在被摒落的士人中即有杜甫与元结诸人。另一件是士林领袖人物李邕和裴敦复被朝廷“杖死”。二人被乱棍打死之后,整个士林风气受到严重摧残。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
到了天宝七载(748),高力士当上了骠骑大将军,开启太监介入国家军权的先风。也在这一年,朝廷赐给安禄山一份可免死的丹书铁券,为安禄山之反叛准备罩上安全的保护衣。也在这一年,杨国忠“岁中领五十余使”,兜揽要权。同时唐玄宗、杨贵妃穷奢极欲、骄奢淫逸。
从天宝八载(749)开始,唐玄宗轻信边将,轻启边衅连连发动开拓疆土的非正义战争,而且屡战屡败,祸国殃民。尤其是天宝十载(751)讨伐南诏,几乎全军覆灭。但杨国忠仍不罢休,派人抓缚壮丁,送入军队,于是有了杜甫《兵车行》中描绘的惨状。
而对杜甫之个人来说,他历经了科举的两次失败,在向朝廷献三大礼赋之后,在长安已经困守多年,生活极为困顿。天宝十年他在《进三大礼赋表》的时候,已经是沦落到“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地步。
天宝十一载,当杜甫登上慈恩寺塔的时候,不仅他个人的命运已经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而且整个唐帝国的朝廷和社会也已经在糜烂中孕育着一场雷霆暴雨。在塔上,满怀有忧患意识的诗人看到的是“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感慨的是“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所以浦起龙说:“乱源已兆,忧患添胸,触境即动。”“一凭眺间,觉山河无恙,尘昏满目”。可谓句句是景,字字见情。而在三年后爆发的安史之乱,正深刻印证了杜甫对于国家与时局的隐忧。
李清良为事件发生的时间性下了一个定义,即“时者,事之会也”。即所有的事情到了不得不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情感到了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而天宝十一载,杜甫在多年的所见所历,其长期郁积的忧患情感,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遏抑的时候。可以说,此诗的编年将其意义的呈现锚定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本身就为诗歌的阐释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诗歌的编年中,其编年的分歧,本身就是阐释的分歧。杜诗的情况尤其如此,本文聊举《去蜀》证之。该诗编年历来分歧甚大。黄鹤《补注杜诗》编在广徳二年(764),其理由是:“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按公乾元已亥冬至成都距广徳二年为五载,而宝应元年秋至广徳元年秋在梓州为一年,此当是广徳二年在阆州作。时严武未再镇蜀,所以欲下潇湘。”而仇兆鳌则编在永泰元年(765),其理由是:“临去成都而作也。公自乾元二年季冬来蜀,至永泰元年首尾凡七年,其实止六年耳。所谓‘五载客蜀’者,上元元年、上元二年、宝应元年、广徳二年、永泰元年也,一年居梓者,专指广徳元年也。此诗作于永泰元年夏,将往戎渝之时。”黄、仇两家的编年分歧正是其阐释的分歧。黄氏将“一年居梓州”中之一年算在五载客蜀之内,故杜甫在四川的时间从乾元二年(759)岁末至广德二年(764),刚好五年,其间刚好一年在梓州。仇氏则将“一年居梓州”中之一年算在五载客蜀之外,那么杜甫在“蜀郡”呆了五年,加上一年的居梓州,正好在四川停留六年,以其入川的时间算起,自然当在永泰元年(765)离开成都。由此看来,编年的分歧,其反映的实质就是对诗歌阐释理解的分歧。
现在学界虽已普遍接受仇氏的算法,认定此诗歌当编在永泰元年(765)。但问题是编在此年之夏还是春季,仍然存在难以弥合的争端。编在夏季的有仇兆鳌、闻一多、陈贻焮等学者,他们认定杜甫离开成都的理由是严武在此年五月死后,杜甫在蜀无依。正如陈贻焮云:“严武死了,再在成都又有什么意思呢?这年夏天,老杜就毅然决然,携家去蜀,作《去蜀》说”。而编五月之前之春季的有浦起龙等,其理由是“公于严武交谊何如,岂有在蜀亲见其殁,无一临哭之语见于诗者,且此后去蜀诸诗,亦决无严卒始去明文也,愚意以为公之去蜀,在四月以前严未殁时。”关于杜甫去蜀的历史真相,学界争论甚多,此不赘述。但从此看出,对一首诗歌的编年,不仅牵涉到诗意的理解,同样亦关切到诗人一生的行止经历。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见,杜诗之编年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诗歌编排次序问题。杜诗之编年如此,其他诗集亦无不如此。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谈论韩愈、柳宗元的年谱时说过一句话:“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将取以证焉,不可不致慎也。”文集既为一人之史,诗文的编年就不仅仅是对于诗歌的阐释,而且更是对诗人一生经历的辨析与阐释。一旦诗之编年确定,其不仅将其创作锚定在一个特定历史时空,也同时为此诗在作者生命历程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坐标,从而为此诗意义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宋人将杜诗编年纳入文集整理笺注的内容,不仅是宋人在诗中发现“史”的因素,更是反映了宋人的一种阔大的阐释视野,从而将孟子“知人论世”之阐释理论落实到每一首杜诗的具体实践之中,为理解之得以进行奠定了基本条件。
〔注释〕
①③邵长蘅:《注苏例言》,载施元之《施注苏诗》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注杜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魏仲举辑《韩文类谱》,《续修四库全书》第552 册35页,《续修四库全书》本。
⑤吴洪泽:《试论宋代年谱起源》,载《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辑,138-139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年。吴氏长期从事宋人年谱整理研究工作,并于先后编成《宋人年谱集目》《宋人年谱丛刊》,近年其博士论文《宋代年谱考论》更是对年谱进行系统的考论,不仅批驳年谱始于先秦、唐代说,并对年谱起源兴盛于宋的时代历史原因作了详尽可信的分析。
⑥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唐诗杂论》,第63 页,中华书局2003 年。对闻一多推论的分析,参见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第167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浅见洋二.想象与距离――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周采泉.杜集书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J〕.北京:文学遗产1999.
〔8〕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李清良.中国阐释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黄鹤.补注杜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仇兆鳌.杜诗详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陈贻焮.杜甫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