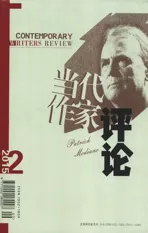如何在今天的时代确立尊严?——评陈彦的《西京故事》
2015-11-14吴义勤
吴义勤
在近年涌现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陈彦的《西京故事》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饱满的人文情怀直面中国当下的精神问题,呈现了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极为引人瞩目。作家承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以“尊严”作为小说的主题词,以具有思想和情感震撼力的笔触深刻探究着当下社会城里人与乡下人、父辈与子辈两类人、两代寻梦者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尊严问题。一方面,小说对老一代农民进城后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进行了深刻的观照与揭示,标志着城乡冲突题材小说的新探索、新突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与融合、碰撞与磨合是经久不衰的母题之一。五四时期,从鲁迅开始的“乡土文学”书写传统中,乡土文化作为落后、封闭、被批判的对象,在小说中常常是通过自省式的批判和自身弊端的挖掘来实现向现代性靠拢的。新中国成立后,宏大革命叙事话语确立,“进城”成为具有革命话语意味的词汇。城市改变了其优越的、象征现代性的地位,成为了带有腐败性、诱惑性,用于检验革命战士纯洁性的标杆。乡村文化则以其传统的道德感与善良的人性美而受到褒奖。八十年代,“城市”与“乡村”又一次处于对立面上,城市祛除了“革命话语”的规约,保留了其现代、发展、前进的文学审美性,而“乡村”也因其传统文明的留存而备受赞扬。九十年代,随着进城打工热的狂潮,描写城市异乡打工者的底层文学兴起,城市成为寓意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情感裂变的染缸,“苦难”成为“卖点”,人物形象单一化、片面化现象突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普适性的人性关怀开始回归。人性情感由单纯的苦难书写、道德批判,转为对人性复杂与丰富的尊重。城市异乡人在都市奋斗的人性美,以及都市的包容和都市人的心酸无奈,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表现。《西京故事》正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家没有理念化地将农民工作为简单歌颂的对象,也没有将城市简单塑造为欲望都市,而是站在中立的基点,在人性的视野内,审视两者的关系,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另一方面,从时代与人的关系而言,小说对新一代青年知识者所遭遇的严峻的精神命题也给予了形象而深刻的回答,是对中国当代代际冲突小说的深化与发展。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众声喧哗、价值混乱的时代,一个人生观、价值观面临新的考验的时代,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再次成为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对当下特别是来自于农村的青年一代来说尤其残酷。《西京故事》延续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开创的思想传统,直面现实,本着“为普通人立传”的主旨,紧紧扣住“尊严”两个字,努力挖掘并呈现时代之痛与当代人的心灵之痛,全面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立体而多维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人性救赎史。
“西京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作家笔下的“文庙村”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象征与缩影。如同老舍的“茶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样,陈彦的“文庙村”也是个聚集各色人物的大舞台,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生存空间。一个因孔庙著称的神圣地带,一个曾经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着的封闭与安详的村庄,现已被现代文明叩开了大门,成了地地道道的“城中村”。如今的文庙村挤满了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再有宁静儒雅的尚孔之风,不再有神圣庄严的祭祀之礼,取而代之的是拥挤不堪的嘈杂和物质欲望的喧嚣。怀揣不同梦想、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挣扎的人们,为了生存暂居一起,建构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小社会”。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一角,现代文明的工业马车张扬跋扈,以惊人的速度碾压着传统文明与传统文化。传统的文化、价值、伦理在巨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阴影之下,正在发出奄奄一息的哀叹,并以苍凉微颤的背影一步步地走向衰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里,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尊严可以说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考验。传统走向何方?传统的尊严如何捍卫?陈彦在《西京故事》中对此的思考是沉重的,但沉重并不绝望,在作家笔下的小人物身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基因的流淌,能感受到他们捍卫文化尊严和文化价值的悲壮。
罗天福是小说中充满悲剧感和崇高感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典型形象,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符号与化身,是老一代中国儿女的精神世界、伦理世界和人格境界的绝好诠释。罗天福的身上,积淀了中国传统农民最为典型的道德操守与价值观。他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保守隐忍。他一个以卖饼为生的城市异乡人身上继承了中国民族精神优秀的道德品质,同时也诠释了陕西人“不惹事、不害人、能下苦、肯背亏”的形象,他是千百万奔波在大都市的底层打工者的代表。他们默默无闻,血液里却始终蕴藏着传统民族精神的精髓,恪守做人的本分,并将这弥足珍贵的传统代代传承。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从他们心路历程的转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正如东方雨老人所说的,罗天福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以诚实劳动,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作,坚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我对他挫折频出的梦想充满期待,那两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如若不被城市急功近利的超级利己主义臭气所熏染,而以父亲的人格理想做依托,一点点去丰满自己的羽毛,我就觉得罗天福的西京梦是有价值的……”在山区老家,罗天福当过民办小学老师与村支书,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与文化性格深深烙印在他的血液中,“他身上有许多中国古代圣贤身上的东西。所谓圣贤,就是那些始终在持守社会常道,一旦发现人类恒常价值、恒定之规遭到歪曲、肢解和破坏时,就站出来说几句话,提醒人们不要有狂悖心理,要守常、守恒、守道,要按下数出牌的那些人。”他的文化自豪感和价值尊严在儿子、女儿考上名牌大学这件事上得到了极大的实现。为了捍卫这种文化自豪感和价值尊严,他决心到城市里打工以支持两个孩子完成学业。然而,他坚守的价值观和道德操守,与纷繁复杂的都市生存法则构成了巨大的矛盾:一到城市便处处遭人白眼;推销自家生意,被当成盗贼打成重伤,赔钱草草了事;房东郑阳娇怀疑他偷鞋;被人诬陷自家的饼掺假……城市的排斥与冷眼,使这个老农民举步维艰,自尊心严重受挫。房东儿子金锁轻薄罗甲秀,被儿子罗甲成痛打,罗天福步步退让,赔礼道歉,将所有积蓄赔给房东,甚至还想卖掉老家的古树。尽管饱含艰辛和屈辱,罗天福并没有屈服,但儿子罗甲成的弃学出走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村老汉,这个一心信奉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的自尊老人,因儿子的出走而彻底崩塌。儿子是他的希望所在,尊严所在,光荣所在,价值所在,是他奋斗的精神支柱,但儿子的反叛、质疑以及出走,给了他巨大的心理伤害和价值困惑,加之旧伤复发,他终于病倒了。他到矿井区求儿子回校的那深深一跪,震颤了无数读者的心。这一跪满含他对儿子炽热的爱与疼惜,饱含着一个男人无可奈何的被毁灭的自尊,也饱含着其对他所信奉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文化伦理的深深迷茫与巨大尴尬。“罗天福真不想说了,他知道,他肚子那点墨水,已经说不过儿子,也说不转儿子了,把他浑全找回来,还没死,他也就觉得自己是尽到父亲的责任了。他这阵就想放弃,放弃一切。这个西京梦,可是把他做苦了,他也不想再做了,再做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这阵儿就想躺在塔云山的那个大炕上,把凉飕飕的脊背焐暖和,过几天消停日子,你罗甲成爱弄啥弄啥,你就是再去死,罗天福也不找了,罗天福认命了,罗天福投降了,罗天福是绝对给儿子投降了。”罗天福的精神危机在小说中最终得到了某种缓解,这缓解来自于女儿罗甲秀聪慧懂事和自我价值认同的坚定,来自于罗甲成的归来与醒悟,更来自于东方雨老人的智慧与启迪。在小说中,东方雨老人与千年唐槐、老紫薇树,都是传统文明、传统文化价值的象征与隐喻,是民族精神之根。罗天福一家遭受危机时,“卖老紫薇树”一度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城市扩张的进程中,“千年唐槐”也成为被废弃和消灭的对象。奶奶死守着老紫薇树、东方雨老人整日给千年唐槐打针,这正是对日渐衰落的传统文明的守护与挽救。罗天福的痛苦,是今天所有还在坚守民族美德和传统文化价值的人们的共同痛苦。作家一方面浓墨重彩地展示着主人公人性的善与美,另一方面又深刻剖析着人物的精神痛苦与内心矛盾,从而把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思考与对传统文明危机的审视上升到了时代和哲学的高度。
在小说的人物谱系中,与罗天福等老一代中国儿女相对照,青年一代的人生困惑和价值痛苦更为触目惊心。青年一代怀揣梦想来到光怪陆离的都市,他们渴望成功、渴望尊严、渴望梦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梦想和现实注定了有着巨大的距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高考可以改变命运。高考成绩和学习成绩常常是很多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自我尊严的支撑与保障。但是,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和物质欲望的膨胀,物质对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在发生巨大的冲击。对罗甲成、罗甲秀这些来自乡村的穷困大学生而言,高考成绩与考试成绩带来的尊严远远抵抗不了他们因贫穷而产生的巨大自卑。在物质面前,在贫困面前,何为尊严?怎么才能守住尊严?这样的问题沉重而尖锐。成功与失败已被重新定义,他们究竟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的内心挣扎和痛苦由此而来,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迷惘。在这新的人生考验面前,罗甲秀以女性的聪慧和坚强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她不向命运屈服,自强不息,自食其力,以自己的勇敢、自信、韧性与毅力,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她的拾荒,表面上是放弃了人生的尊严,实际上却是对自我尊严的极大捍卫,是相信自己双手改变自己命运的高度自信的一种表现。而罗甲成则交出了一份失败的答卷。罗甲成在乡村社会一直是罗天福的骄傲,他的令人称羡的学习成绩,他的考上名牌大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耀与尊严,也坚定了他对自我的认同。但当他怀揣梦想与自信,来到西京学习,大学生活新的环境却使他渐渐迷失了自我。官二代与富二代舍友的攀比炫富之风,使他看到了自己物质方面的巨大窘迫;面对美丽的教授女儿童薇薇,他内心的自卑日渐加重。极度自尊而来的极度虚荣、极度自卑使他的内心越来越封闭,性格越来越孤僻,宿舍舍友也因此成了他内心的“敌人”和排斥的对象。他只能依靠拚命、刻苦的学习来维持脆弱的虚荣与自尊。姐姐与父亲的拾荒行为,更是让他觉得丢脸、无法忍受,对姐姐、对父亲他是暴跳如雷。他的人格和心理被极度扭曲:他羡慕同学有手机、电脑,他不愿穿母亲做的衣服,他厌恶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和贫困的家庭,为获得以童薇薇为代表的城市人的认同他不惜包场请童薇薇看电影,为竞选学生会主席他更是到网上发帖子抹黑竞争对手……当他对童薇薇的狂热而虚幻的爱情之梦最终破灭之后,他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他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与迷茫,只能仓皇出逃。罗甲成是当今时代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新时代的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以及于连等人物形象的混合体,他的矛盾与痛苦几乎是所有底层青年的普遍痛苦,只要城乡差距存在、贫富差距存在、社会地位等级差距存在,这种人物永远都会存在。罗甲成的意义在于,面对物质的压迫与权力欲望的诱惑,人生道路的选择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堕落还是毁灭?沉沦还是救赎?答案不在别人,不在环境,而在于自己的内心。小说中,作家没有让罗甲成毁灭,而是让他在东方雨老人那里获得了救赎。东方雨老人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对其心灵的洗涤,使罗甲成重新找到了自我定位,逐渐从自我迷失中走了出来。他主动帮助父母干活,并开始与人交往。这是人性的回归,也是传统价值与精神的回归。陈彦擅于用苦难的人生拷问人性的价值。一方面,为摆脱卑微的生活背景与社会地位,主人公人性的弱点在苦难中膨胀,他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对抗苦难,最终失去了自我;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与价值、个体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作为最后的信仰,仍在制约着个体的行为,并引导主人公跳出苦海,实现了自我救赎。这两种力量充满张力地不断拉扯着主人公,构成了人物思想上的撕裂感、行为上的无奈与荒谬感。小说对于罗甲成最后精神获救、人性获救的处理,虽然难免某种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色彩,但这背后突显的则是陈彦对于人性、文化和传统人文价值的坚定信念。
与对城市外来者艰辛生活的表现不同,《西京故事》对“西门锁”这样的城市暴发户精神世界的揭示也非常成功。作家没有简单化、道德化、脸谱化地处理笔下的人物,而是把人性的关怀、“善”的观念与“爱”的情感结合,对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与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西门锁是西京本土居民,是城中村内因出租房屋一夜暴富的有钱人。小说中,他一出场便因婚外情而与老婆闹得不可开交,但作家终究没有将他塑造成简单保守、站在道德天平另一端的单薄形象,而是对他充满同情与理解,并赋予他丰富饱满、有血有肉的性格。他是生活的成功者,也是失败者,他也有着他的现实困境、人性困境与精神困境,也有着他的无奈与痛苦,他也同样需要拯救与救赎。苛刻的妻子郑阳娇、不学无术的儿子金锁,使西门锁对家庭生活充满失望。婚外情的发生,既有人性堕落的成分,也有自我放逐的意味。善良的前妻赵玉茹因他的背叛,带着女儿映雪离开,也使人到中年的西门锁内心充满自责。女儿北京上学,前妻突患癌症,这给了西门锁自我救赎的机会。对前妻无微不至的照顾弥补了他内心的愧疚,赢得了女儿的认可与接纳,但也引发了与现任妻子无休止的争吵。夹缝中的西门锁最终遵循自己的内心,坚持照顾前妻直到其离开人世。对待罗天福一家,他也显现了宽容的一面。面对妻子对罗家的无尽责骂,他也总在想方设法地为罗家说话。可以说,西门锁与罗天福、罗甲成代表着西京寻梦的两个不同阶层,代表着淹没在人海中苦苦挣扎的所有可怜人,让读者看到了在每个光鲜的形象背后,都潜藏着一颗痛苦挣扎的心。在这里,陈彦兼怀历史责任感与时代意识,展示的是现代社会人生苦难的丰富光色,呈现的是普适性的人文情怀。他通过逼视生活与心灵的困境与矛盾,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描写个体在当下社会中心理结构的崩塌及重构,传达了对个体生存的人文关怀。
艺术上,《西京故事》体现了高超的驾驭复杂社会生活和多重情节线索的叙事与结构能力。小说如《上海屋檐下》一样平行展开几家的故事,故事线索清晰,情节充满张力,人物命运和情节冲突环环相扣,人物之间既平行,又交叉,张弛有度,有条不紊,显示了游刃有余的叙事能力。与此同时,小说重视对人物心理和情感的挖掘与展示,注重通过对人物的行为、语言、细节、场景的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转变方面,表现出精湛的工力。这突出表现在罗甲成身上,其性格的巨变、精神情感的苦苦追寻、灵魂的裂变与痛苦在小说中得到了层层深入的揭示。宿舍失窃事件导致的心理波动及各种本能性的反应、对童薇薇自我幻想性的情感心理等在小说中是被展现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此外,小说的语言也极具特色,既个性化又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方言俚语的成功运用,为小说增色不少。比如,蔫驴与罗甲成喝酒时的语言就极有魅力:“甲成,有啥过不去的坎你说嘛,兄弟再无能,总还是能帮上你一点忙吧。你能来找这个挖煤的兄弟,说明你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我总想你能有啥大不了的事,缺钱?兄弟没有多的,万儿八千还是拿得出来的。其余还能有啥事?要知足兄弟,咱那几面山几条沟的人,能活到你罗甲成这分上的不多,说实话,几条沟的人,除了你,我还真没看上几个,包括现在那几个掌权的货,倒是个毬,有本事吗?把沟里的日子过不前去还有脸当,有脸争,有脸斗,当毬呢,争毬呢,斗毬呢。甲成,你满足吧你,塔云山将来出不出人,也就看你了,你这一怂,塔云山还有毬的戏。来,喝。我比你大几个月,就是你的哥,你遇事来投奔哥,哥这脸就斗大了,你爱说不说。爱说,你就说出来,不爱说,你就往死里憋,憋死了我把你背回塔云山,投老祖坟去。怂啊,喝。”这样的语言,契合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故事情境,具有原生态、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体现了作家对民间语言的熟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