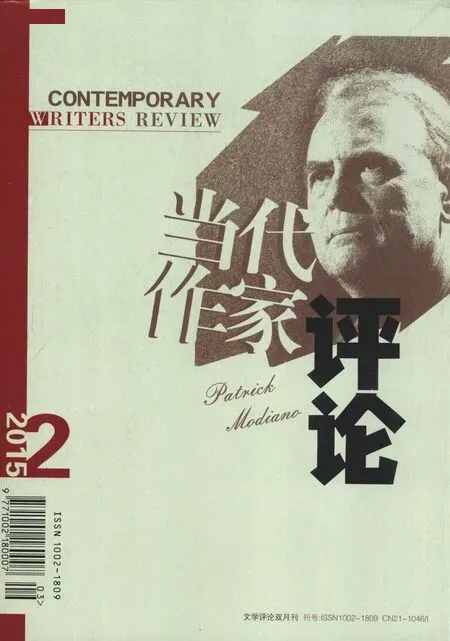阎连科式写作:以桃花源对抗乌托邦
2015-11-14张斯琦
张斯琦 曲 宁
阎连科作品中的乌托邦色彩是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他的主流作品中表露出乡土乌托邦的意味;或认为其超现实的写作风格得益于乌托邦式想象;另一些学者甚至得出,以《受活》为例的作品框架之形成是几种乌托邦形态相互斗争的产物。事实上,阎连科是否可以被纳入到乌托邦传统,这一问题应从乌托邦文学自身的特征说起。
乌托邦文学本是西式文体。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傅立叶笔下的“法伦斯泰尔”,西方乌托邦文本有着大体相当的文体特征。那就是其一,它们都把自己描摹的对象当做与不完美的现实相区别的完美世界来刻画;其二,相对于现实世界的无序与不公,这些乌托邦都建构在一套十分严整的社会秩序基础之上,该社会或尽量避免阶层的产生,或阶层按照合乎理性理解的规则进行人为的划分与控制,每人各司其职,各种事务的开展井然有序;其三,这些社会建构原则详细周到,看上去极具可操作性,使得此类文本成为后世许多国家社会改革与革命的参照蓝本;其四,各个作家都不吝笔墨满怀热情地描写了在他们各自的完美世界中人们生活境况何其安定与幸福的图景,细节周到,有如亲历,往往能使读者一读之下便对这些乌托邦心向往之,这也构成乌托邦文本经久不衰的感召力的重要来源。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考察阎连科在何种意义上与乌托邦文学有关联,而他自己的文学写作究竟是否具备乌托邦文学之本质。
一、乌托邦式图景
确然,阎连科小说中多多少少都有乌托邦色彩的展望,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十分热衷于去涂写乌托邦式的理想景象。
在一些作品中,乌托邦想象还是沉甸甸地落在大地上的。《日光流年》中三姓村居民寿命上限不过四十,村人的理想就是改变可悲的现实,好能活上六十、八十,以至一百、一百六十岁。《丁庄梦》里丁庄人乌托邦式梦想之来源,是看到其他卖血致富的村镇居民不需劳作,就可以住高房大屋,用冰箱彩电,随意领菜领肉,每日消闲游乐,钱财源源不断。另一些作品中,那想象就跳脱出现实的控制,天马行空起来。较具特色的是《受活》。其中双槐县柳县长为振兴地方旅游经济,突发奇想,要大手笔地将列宁遗体购买回耙耧山,在这里建一座列宁纪念堂,引全世界来参观。他称,如果他兴建列宁纪念堂的宏伟计划能够实现,
到了那时候……花钱成了最困难的事情呀!扩大街、盖楼房,那能用掉多少钱?把县委、县政府的大楼盖到半天里,各部、局委都盖一栋办公楼,你就是都用黄金刷墙、铺地,可楼盖起来了,那源源不断的钱也还是要往财政局的账上流的呀,像一条大河每天往县里流的都是金子呀。人能吃多少?人能花多少?全县农民不种地,每个月你都坐在田头发工资,可到末了你还是有花不完的钱;不种地你着急,你着急你就把所有的田地都种上花和草,让那田地里一年四季都青青绿绿呢,都花红花黄呢,四季飘香呢,可你四季飘香了,到处都是花草了,那游人就更加多了呢。游人更多了,你的钱就更加花不完了呢——双槐县变成了挣钱容易花钱难的县……那时候各家各户都钱多得吃饭也不香,觉也睡不着了呢。为钱花不出去家家户户做了大难了……
在阎连科的近作《炸裂志》中,乌托邦想象复现为更为无边无际的物质奇迹。几百人的村落在孔明亮的主持下一步步由村变乡,由乡而县,从地级市直接跳级成为国际化超级大都市,拥有了摩天大楼、地铁系统,乃至亚洲最大的飞机场。退伍士兵孔名耀凭着自己的军事头脑,私自筹建军队,竟然在耙耧山中开辟出一片偌大的军事基地,军舰航母在草海上游曳,军事打击范围远达欧美。
面对拘谨的现实,阎连科跳荡不羁的构想本身的确可以构成对传统乌托邦叙事反现实风格的继承,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阎连科在描述这些乌托邦图景时,与其说是满怀憧憬的,莫若说是戏拟讽刺的,甚至略带悲哀与忧虑的。因为这些乌托邦想象,未必尽是对世界的可行未来的美好畅想,也许倒是扼杀人性的可怕肇因。
二、“反乌托邦”主题
阎连科小说中的乌托邦图景之展开一般都设置在情节开端,按照人们对乌托邦文学的期待,按计划将理想图景加以实现,就是情节发展的最高宗旨。然而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此类故事的演进线索。他的主线作品的情节上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反高潮性。《坚硬如水》中文化小革命、《受活》中公社运动与列宁遗体购买工程、《丁庄梦》中卖血致富潮、《炸裂志》中孔明亮大都市运动,各自都是构筑某种乌托邦的尝试,情节主要也就是对这种尝试的详细步骤的铺叙,然而它们无一不在登峰造极之处轰然崩塌,仿佛阎连科的主题分明就是乌托邦之失败,而非达成。也许我们可以斥责阎连科是退步论者,习惯于借失败主义的刻意安排达成某种格外的文学悲怆感。但是如果深入到乌托邦传统的内部,我们将发现,事实上阎连科所表达的,也许更是他对乌托邦想象的不信赖。
乌托邦图景被实践的可行性是值得慎思的,这种观点,已在以塞拉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乌托邦研究著作中得到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乌托邦图景具有生动性与鼓动性等特点,正因此,也常常以其积极的表象取消了人们对其合理性的仔细辨析。毕竟乌托邦是某些个人对社会理想状态的想象,即便他们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做自己想象的支撑,但是他们对社会本质的理解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误。而许多时候,一个乌托邦图景又可以在它的认同者之间发挥相当的效力,乃至被鼓吹为一条兼具普世性和可实践性的革命纲领。当乌托邦从理想维度降落到实践维度时,其中潜藏的各种偏误将暴露出来,甚至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阎连科笔下凡受到乌托邦图景怂恿而走上践行之路者,无不偏激执狂。《坚硬如水》中主人公凭着对文化革命的一己之见,要抹杀程朱理学在程家庄的全部遗迹,凡有人阻挡,就斥之为反革命。柳县长要将列宁遗体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动源,作为想象来说自有其奇谲的创造力,可是一旦真的付诸行动,就无法掩饰他的荒谬。孔明耀在获悉美国误炸中国大使馆后要组建个人军团对美帝实施报复性打击,这种设想固然有其勇武可爱的一面,但是全凭个人意气就兴师动众,置万千生命安危于不顾,假设当真孤注一掷地付诸实现,可以想见将会引发何种灾难。
西方的乌托邦传统中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是,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够保证手段的合理性。因此在追求各自的乌托邦理想的时候,总是会打着实现某目的的名义,采取若干不够慎重的手段。在《乌托邦》中,为了实现社会阶层划分的平等性,避免人对物的私有感觉,莫尔让所有居民都放弃他们对住宅的永久所有权,时常轮换居所。在乌托邦的原型性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为了保证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整体,建议那些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充分投入社会生产、实现个人价值的病人接受自己命将不久的事实,不要再去消耗国家财富,用精致的饮食习惯和养生之道来损害他人利益。在特定语境下这些措施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否认它们确实触犯了人的基本权益。阎连科作品中有大量的此类事实可供佐证:《丁庄梦》致富发家的手段是卖血,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地下血站的血头们甚至一针多用,最终造成整庄人罹患艾滋病的恶果;《日光流年》三姓村四代村长用来提高寿限的手段是多生多育、种植油菜、翻耕土地、引水修渠,第一种方法可想而知将使多数妇女成为被强迫的对象;第二代人在蝗灾中为保油菜,放弃了全部粮食作物,致使村人承受了可怕的饥荒;翻土修渠更是硬生生将人累毙田间、炸死工地。为了挨过饥荒、给翻土修渠准备工具,村人更不惜自轻自贱卖皮卖肉,为谋生命而采取的措施却换来生命与尊严的抹杀。
阎连科通过一部又一部乌托邦悲剧的展现,为我们揭示出乌托邦想象自身的危险性。这种做法倒正与西方当代对乌托邦传统的反思相互应和。拉塞尔·雅各比等知识分子经过对乌托邦思想史做深入研究后认为,乌托邦从本质上讲是不可实现,当然也是不可规划的。乌托邦一词的本意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好地方”,它是突破现实的设想、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开放怀抱的自由精神。在这种自由精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有充足的理由能够宣称自己构筑的理想世界最适于人类生存,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把握能够证明自己设计的路线能将民众导向伊甸园。我们无权利将自己的想象当成集体想象,更加不能为实现这样的蜃景强迫他人采取自己臆测为合体的手段。因此不幸的丁庄、惨烈的三姓村,以及阎连科笔下所有这些为实现某些人的乌托邦而沦为牺牲品的村落,都在默默昭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索。这不仅仅是对一种理论的质疑,对一种行为趋势的批驳,更是对几代人六十年积累下的血泪历史的彻骨反思。
三、追溯“桃花源”
西方当代的乌托邦反思者对乌托邦固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多是回到穆勒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主义那里去,强调权力核心的消解,强调个体理性判断的独立,保障任何一种乌托邦理想不至于再被推广到不可控的范围。但是阎连科根深蒂固的乡土情怀决定了他不可能抛舍下对同胞家国之爱,躲到知识分子的反刍式象牙塔中,他笔下的一个个主人公无论怎样被乌托邦的蜃景蒙蔽了理智,无论如何狂热于某种荒唐的计划道路,终究都对自己的乡民始终不离不弃。因此尽管我们说阎连科对乌托邦之弊十分警觉,但他借以批驳的立足点,却不是西方的“反乌托邦”思潮。那么阎连科对乌托邦的反抗又以何为据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叙事方式上找到线索。
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同现实主义文学同根同源。西方的乌托邦按照世界应有的样子进行想象构筑,同样,现实主义也以世界应然的图景进行描述。世界的应然图景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作家从相对无序的现实中提炼理想秩序的能力和信心上。其中的重要一项即有迹可循的因果联系。特定人的特定行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必定导致特定的效应或结果,是现实主义对现代的生活观念的抽象。这种思维方法为乌托邦影响的畅行提供了便利,因为人对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与配套措施颇有自信,按照现实主义式的因果论,有善因必有善果,好的目的必然导出好的手段,所以推行乌托邦及其措施就没有任何疑虑了。从这一角度讲,逻辑在先者先行讲述,逻辑在后者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于是我们看到,尽管西方叙事形式早就发展出若干形态,但正序的叙事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却独占鳌头。
阎连科是从阅读、接受现实主义文学中成长起来的,他自己也承认现实主义式的景物描写等因素对他影响至深,但对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却持有保留意见。他在风格确定下来之后的各部作品中都着意进行叙事方法的个性化创造,其中最显著者见于《日光流年》。这部小说从时序上将三姓村四代人改造本村短寿命运的历史剪接为五段,并用倒叙的方式将五段历史从后向前一一串连起来。王一川教授认为这体现为一种索源式文体。这一命名对我们来说很有启示意义,不过我们倒乐意称之为“桃花源体”。
《桃花源记》这个文本从时序上说并无特异,但其中有三次颇具象征性的索源行动,第一次是武陵渔人对桃花源的发现,第二次是郡太守发起的官方搜寻活动,第三次是南阳刘子骥对桃花源的无果追寻。三次探寻都是溯本求源式的追索,并无对桃花源未来发展的追求。文本本身也并不执著于桃源人后来的遭际结果,只重桃花源之所以产生的条件,那就是先世避秦时乱才来此绝境。与世隔绝就是桃花源的旨归,更无其他志愿理想,要在桃源境内建设怎样一个理想的国度。
阎连科的小说也正基于这样一种要素:耙耧山脉中与世无争的村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本身并无任何理想化的追求,只愿有正常的“百姓生活”,至于说后来人们对这一初衷有所背离,那么也是因为其他外在的力量侵入了桃源。内外的对比,造成了桃源境界不可逆转的悲剧性解体。《日光流年》中人们虽然夭寿,但民生也算充裕,并无奢望,只是因为见了外来的老者才会对自己的四十寿限心生不满。《丁庄梦》中丁庄人对外界财富的抽象向往是导致整村走向“热病”村的毁灭之路的肇因。《炸裂志》中将炸裂从山中天堂带入现代化噩梦的正是从外面传来的发家致富的时代追求。最典型的《受活》一书中受活村人尽管都是残人,是外面世界中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只要生活在闭塞之中,就能保证基本的安居乐业,靠着自己的勤劳,还常常有粮食吃也吃不完的年景。然而茅枝婆到山外见到人民公社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对这种公有公做的形式心生向往,于是就造下了受活人的原罪,使受活人保留在“圆全人”的世界当中,背离了桃源的本质。
这些外来的理想——长寿、致富梦、集体生活,打破了耙耧山中桃源人平静的生活,使他们放弃本真初衷,不择手段地加以实现,造成一系列失乐园式的后果。阎连科在他这些作品中警示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真的迷失在这些光怪陆离的外来梦境中,为了追寻空幻的梦离开自己初衷太远,那么就应该暂时离弃自己的选择,抛开一切执著,回归到原点,溯源到根本。桃花源的原点,乌托邦的根本,说来至简至朴,无非民生二字。
《日光流年》的桃源文体说明的就是这样一个文体。开卷读去,我们最先看到开渠者的狂热,尔后是翻土的急切、对油菜的痴迷……一代代人将自己束缚在村长划定的乌托邦实现之蓝图中无法自拔,都忘却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界究竟如何。其实读到最后一章,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人的生命,人在活着的生命中对这个世界最细微的感受,本就是我们存活和珍视这种存活的根据。正因如此,阎连科才特意创造出广受批评界好评的独特修辞语体,来表达一个人、一群人特有的感官与情绪。他写得那样活色生香,情真意切。
归根结底,尽管反驳乌托邦是阎连科作品的一个主题,但他是不适合用西方式的乌托邦文学系统去框缚、去界定的。阎连科并不是一个乌托邦作家,而是一个外来乌托邦的本土消解者。他赖以运用去消解乌托邦的立足点,是中国最质朴的桃花源情结。这些耙耧山中天堂岁月理想状态的达成,也只是基于民生的丰足,而不曾有任何社会结构变革性的构想。
我们必须承认,尽管阎连科拒绝任何以抽象原则的名义饕夺人生存权益的乌托邦式做法,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毫无原则地回护中国本土的桃花源。他笔下的桃花源尽管原则上能够自给自足,然而总是因为自身的缺欠被世界遗忘才能够在封闭的情境下发展起来,它的理想态又何其脆弱,只需来自外界的一点点侵扰就足以地覆天翻。阎连科所讲述的并不仅仅是桃花源与桃花源之丧失的故事,而是更为深刻的悲剧,即人此在之幸福看似很容易保有,然而却更容易失落。
或许文学才是帮人呵护这种幸福的可靠途径。而这,才是阎连科在他一次又一次真挚的写作中,试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