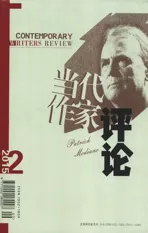探寻精神家园之路——方英文论
2015-11-14黄元英张文诺
黄元英 张文诺
方英文是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大作家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陕西作家。方英文在继承陕西前辈作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题材上做了重大开拓,艺术上实现了超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范式。但是从更深广的学术范畴来考察,方英文的文学成就已超越了地域。方英文是位才华横溢、格调高雅的作家,善诗书,能琴棋,摄影山水,崇尚素食。这位浑身散发着浓郁书卷气的作家,或许还是当今中国唯一坚持用毛笔写作的作家。这些综合元素所呈现出的深厚学养,以及他现实生活中的名士风度,让广大读者联想到五四时期鲁迅、林语堂这一谱系的经典作家。基于此,方英文二○一二年获得“中国新时代风雅名仕”的称号。这种风雅精神支撑了他的创作个性,看似漫不经心,事实上对于写作及其严谨认真,就像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刘熙载评价庄子的文章: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方英文作品自然率性又不失优雅典范,因而常被选作考试题。著名评论家李星说:“方英文本人是陕西文坛上最有个性、最具亮色的很让人喜欢的作家。”迄今为止,方英文已经发表、出版了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炊烟》,中篇小说《城市舒服》,散文集《种豆得瓜》、《短眠》,长篇小说《落红》、《后花园》,书法小品文集《风月年少》等。从他前期的中短篇小说到后期的长篇小说,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窥探方英文的创作轨迹:他从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揭示到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探索,追求“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真实与梦幻的高度谐合与交融”。方英文的创作,在探索中掘进,在超越中成熟,愈来愈显示出一种大家气象。
方英文的小说、散文皆能自成一家,独具风格。本文仅就方英文的小说创作予以简论。
一、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方英文出生于陕西省镇安县的一个农村家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五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他的成长背景和丰富阅历,使他非常熟悉农民生活的欢乐和痛苦,需求与愿望。而少年时代的艰辛生活,强化了他的世俗意识与平民情怀。他最初的几部短篇小说都是反映农民生活的,充分展现了方英文早期的文学才华与创作个性。
方英文的农村小说善于表现农村的细微生活,能够关注底层生活的“内质”,再现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的生活愿望及心理波动,短篇小说《炊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石根是一个孤儿,家贫无力娶妻,二十八岁时在别人帮助下与寡妇成亲。这个寡妇年轻、漂亮、聪明、能干,可是,原来的丈夫却是个死刑犯。“寡妇”、“死刑犯的老婆”使石根的内心矛盾煎熬。小说叙述角度非常巧妙,从结婚后的第二天写起,着重描绘石根的心理波澜,表现了作家对于农村生活、农民处境和农民需求的细微体察与深切体谅。农民的愿望不高远很实在,追求实实在在的日子,心里的波澜往往来自传统的观念与现实的生活之间的冲突。“对于农民来说,在总的方面与上层规范并无不同,但相对来讲两性关系较为宽松。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对正统观念染濡较浅,或者说由于小渠道传播接受的是走了形的正统伦理,但主要还是生活环境所致。”这篇小说意境之优美,深得沈从文小说的神韵;而心理刻画之细腻,又兼得茅盾小说的精髓。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短篇小说《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这种变迁和律动。小说构思非常独到,作家通过四个梦境来折射人物的性格与心理。小说先写村长老柯中午休息时梦见毛主席头疼,醒来很诧异。在妻子提醒下,他忽然想起几年前将毛主席石膏像搁置在老屋的阁楼上,找到石膏像后发现耳孔里藏着一个小小的马蜂窝,他捣毁马蜂窝并修补好耳孔,将毛主席石膏像“请”在新屋中堂供奉起来。是夜,老柯又梦见了毛主席,主席向他感谢并询问有什么愿望,他没有把真实的愿望告诉毛主席。巧合的是,妻子在梦中也遇见了毛主席,询问自己支持儿子复读考学的事情,请求毛主席保佑她儿子考上大学。后来,儿子果然考上了大学。老柯认为毛主席果然是神,更加虔诚地供奉石膏像。但毛主席却托梦给老柯的儿子,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灵,让赶快把石膏像磨碎点豆腐。
这篇小说深得契科夫之神韵,诗意抒情兼诙谐婉讽。以梦写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现实生活以及心里愿望。农民富裕了,住上了二层小楼,但思想观念仍然比较落后,精神生活仍然比较守旧。村长老柯不想让儿子读书,他想把“村长”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传给自己的儿子。老柯没有对毛主席说出的愿望是“升官、发财、要女人”,老柯之所以不好意思说,因为这种愿望太庸俗。这不仅是老柯的想法,也不仅是农民的念头,而是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潜意识。“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紧接着就号称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受到过市场经济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封建主义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无意识的深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这种落后的封建意识就会冲出地表,浮到人们意识的表层。这篇小说篇幅虽短,却有丰富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部分中国人为官的动机,他们当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小说艺术地揭示了部分中国人腐败的思想根源,联想当下官场的腐败,我们不得不佩服作家的前瞻性以及对生活的穿透能力。
可以说,方英文是一位连接乡村与城市的作家。他的乡村生活与城市经历使他自由出入于二者之间,自由从容地表达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当他把笔触转向进城的农民工时,就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华和深沉的思考。中篇小说《城市舒服》和《绝代》就是成功反映城市打工者生活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城市舒服》中来自农村的“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一家较有影响的报社当见习记者,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地位、荣耀与实惠,让“我”感到得意且满足。后来“我”遇上、爱上洗脚妹葱儿,她美丽、善良、纯洁,但葱儿的身份让“我”望而却步、犹豫不决。一次生病,他发现“不体面”的葱儿内心非常纯洁,比起那些外表光鲜内心龌龊的城市丽人,葱儿应该是城市里最美的人。“我”和葱儿以及难以计数的城市打工者,工作辛苦,生活很不舒服。正是这些在社会最底层过得并不舒服的打工者,才换来了城市上层人群的舒服。小说深刻揭示了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的无奈与悲哀,她们没有文化,缺少技术,只能干一些粗贱卑下的工作,甚至唯有出卖色相才能养活自己。“进城的乡村女性在尝试了精神和情感追求的失败与痛苦之后,为了迎合城市和立足城市,她们只能放弃情感而奉献身体,只好遮蔽与压抑自己真实的情感世界,将身体与情感的归属进行分离,进行自我的‘非人化’和工具化的心理与行为的转型。”方英文写出了乡村女性的美好天性与奉献身体之间的两难抉择,写出了她们的身份分裂的痛苦。
再如《绝代》中的青袖,她在城市竟找不到一个纯洁的男人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当她找到一个男人时,这个男人却永远离开了她。更为深刻的是,方英文的小说并没有回避农村女性的弱点,她们或由于家境贫穷未曾读书,或因不愿吃苦而未能掌握一技之长。她们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只能出卖青春存活于城市。小说揭示了农村打工者在城市的痛苦与尴尬,他们来到城市,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为城市的亮丽辛勤劳作,但城市没有他们立足之地。打工者亲手建设起来的魅力城市,对打工者不是接纳而是排斥,不是同情而是可怜与鄙视。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徘徊,身份在市民与农民之间摇摆。农民工的痛苦不仅仅来自微薄的收入,更是由于文化身份的尴尬。“在城市当中,这些‘农民工’不仅要承受生理、安全、人格、发展等各个层次的需要被压抑而无法实现的焦虑,而且由乡村进入城市文化背景的转换更使他们感到了剧烈的心理与生活方式和文明价值的冲击。”他们在城市无法实现真正的立足,城市生活又退化了他们的农村生活技能,他们不愿回去,也难以回去,他们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摇摆人。方英文的农民工小说,揭示了“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城市”这种严峻现实,反映了游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农民工缝隙化生存的现状,表达了作家对农民工遭遇的深切同情。
不难看出,方英文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进行了大胆探索。方英文善于选取生活中的一朵浪花、一个片段,以小见大,反映时代的变迁。在反映社会问题时,方英文一般不正面描写,而是侧面烘托或者讲述的方式予以表现。他袒露痛苦而不激烈决绝,风格委婉含蓄。在揭示底层人群的苦难时,总是不忘渲染他们的善良与坚韧,让人看到生活的亮色。
二、对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的批判
方英文说:“我在西安生活了整整二十年,西安给了我知识、友爱和写作的灵感。”多年的城市生活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浓重的乡村底色又能让他对城市保持一种有距离的审美观照。当方英文把多年的城市体验投入到创作中,创作才能得到了更自由地挥洒。二○○二年,方英文第一部长篇小说《落红》一鸣惊人地问世了,五年后在台湾以原名《冬离骚》出版,二○○九年全票获得陕西首届“柳青文学奖”。《落红》的故事发生在“百陵市”,改变了陕西作家只会写农村的印象,在题材与写法上有重大突破,被认为陕西文坛要在城市文学阵地上‘跑马圈地’,《落红》可望立此头功。小说通过主人公唐子羽的家庭生活、情场波折、仕途起伏、社会交往等,呈现了广阔的都市生活画面,鞭笞了当代官场生活的荒谬,揭示了当代官僚知识分子自由健康人格和庸俗病态人格之间的冲突和调试,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人生、世情、官场的深刻思考,是一部针砭时弊的优秀之作。
作品揭露了当代社会官场体制的僵化与不合理,讽刺了官本位文化对人性、人心、人情的异化,表现出作家对官本位文化的深度厌恶和辛辣批判。李建军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社会里的卑琐、无聊、乏味、可悲的生活,写异化社会里人格的扭曲,写权力中心的价值观对公民精神生活的荼毒。通过对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让人们毛骨悚然地警觉出来。”其实,早在中篇小说《红潮》中,方英文就揭示了农民对于权力的争夺以及权力对人性的毁灭。为了争夺村长的位子,农民杨万水想尽一切办法,软硬兼施、明争暗斗,他先是利用土办法毒害村长王问学而没有成功,然后利用妻子的色相引诱王问学以构陷他,也没有成功。他非常绝望,竟公开调戏村长妻子,然后火烧村长房子,最后锒铛入狱。而村长王问学深昧权力学与厚黑学,他表面上宽宏大量、处处忍让,以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村民的拥护,以高票当选村长。王问学故意原谅了杨万水调戏他妻子的行为,有意放纵杨万水烧毁自己的屋子。杨万水被逮捕,彻底消除了他的心头大患。杨万水猥琐、自私、残忍、丑陋、歹毒,不择手段;而王问学老谋深算、不动声色,后发制人。二人都失去了本真和自我,成为角逐权力的工具和符号。小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篇幅不长,却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揭示被官本位文化异化的所谓政治“智慧”的卑鄙与龌龊,令人感到人性的阴森与可怕。
《落红》主人公唐子羽是百陵市政府所属某局一位末位副局长,这个局“似乎可有可无,它看上去好像管了很多很多,其实什么也管不了。”这是混饭吃的一个局。唐子羽的任务是应付各种开会,当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议。唐子羽当上副局长,凭的不是他的政绩与能力,而是他会做表面文章,“认真开会、认真记录”。他没有什么具体事务,也没有什么权力。这样一个末位副局长,对唐子羽来说应该是无所谓的,在任不喜,下台不忧。然而,当唐子羽被免去副局长后,还是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失落情绪,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他开始积极活动希望保住官位,但没有成功。人们之所以追求官位,是因为官位意味着待遇,意味着某种身份、某种地位甚至知识、修养与风度。可怕的是,官本位文化不但渗透在社会公共空间之内,而且还进入到家庭的私性空间。唐子羽的妻子嘉贤想在单位里当上工会副主席,她让唐子羽给他托关系。然而唐子羽没有帮忙,嘉贤没能当上工会副主席,原本温柔的嘉贤变得非常泼辣粗鲁。嘉贤中午回家,进门就是一声喊叫:“唐子羽,我恨死你个狗日的!”一向温柔贤惠的嘉贤对唐子羽大打出手,以致夫妻反目。工会副主席算不得什么官,嘉贤无非是捞取一点虚荣与小好处而已。可见,“深固的官本位意识和权力欲在民族心理上的沉淀是何等积重难返。”《落红》发现,一个人升官的过程就是人性逐渐泯灭、自我逐渐迷失的过程,官本位意识以巨大的腐蚀性和消解力介入并规范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方英文在《落红》中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小说因而具有了形而上的品质。方英文说:“中年人的生理变化自然导致心理变化,显著的特点是懒得动弹了,有空就想与床板平行了。”唐子羽的沉浮呈现了一个中年人的生存困境,唐子羽四十五岁,按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然而,唐子羽却暮气沉沉,这既和官场升迁规则有关,也和唐子羽的心态不无关系。四十岁是一个人干事业的黄金时期,如果你有理想,四十岁正是实现理想的大好时机。然而,四十岁也是非常危险的年龄,因为这个年龄也是惰性心理最易滋长的年龄。唐子羽认为他官职已经到顶了,便无所谓了,流露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只要不出格,你谁也把我罢免不了,于是混天度日。唐子羽语言机敏,能言善辩,看似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他以俏皮的语言掩盖自己内心的软弱与无能。他当上了副局长,却又缺少真正的用心与政治能力;他不满官场却又没有笑傲商海的能力,只能是调侃政治、消解政治,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在政治上不得意,便在女人身上寻找人生寄托。他的情人梅雨妃美丽、漂亮、纯洁、浪漫,梅雨妃想找一个真正的男人寄托终身。唐子羽找错了人,而梅雨妃也选错了人。唐子羽只渴望梅雨妃的肉体,不想与她结婚,他只想浪漫,不想负任何责任。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在事业、感情、家庭的困窘不堪。最后,唐子羽仕途黯淡,情人离去,夫妻反目,一片悲凉。四十不惑,“不惑的是许多东西依然看透甚至看破,惑的是依然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目标所在,找不到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可以说,人生这个年龄阶段,往往是生命最感空茫的季节。”作家对唐子羽的命运寄以深刻的同情,同时也对他的惰性心理给以严厉的批判。一个人不能太计较个人的得失,无论充当什么社会角色,都应该做一些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只有保持自己的理想情怀,才能避免人生的大起大落。
《落红》显示了作家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作品中唐子羽是一个多余人形象,个性生动,血肉丰满,通过这一形象揭示了官场之弊、体制之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世俗交换关系,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此外,朱大音这个形象也令人过目不忘,这个出身寒门、来自外省的流浪艺术家,个子不高,相貌一般;没有学历,但头脑灵活;没有文化,却善于逢迎,所以混得潇洒自如。他希望以画立身,然而又不肯下功夫,希望借助唐子羽的提携出名。他生活放荡,没有妻子,却又一天离不开女人。朱大音一心追求事业的成功,遵循享乐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他卑陋世俗,招摇撞骗,却不乏做人的良知。这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艺术家典型形象。嘉贤与梅雨妃都与唐子羽有关系,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情人。唐子羽需要嘉贤的能干,也需要梅雨妃的浪漫;嘉贤需要唐子羽的能力,梅雨妃需要唐子羽的爱情。嘉贤与梅雨妃都非常美丽、漂亮、温柔,梅雨妃纯洁而高雅,嘉贤成熟而世俗。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寥寥几笔就能写出这个人物的神韵,因而,《落红》中的人物无不面容鲜活,形神俱似。
三、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探寻
方英文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型作家,他在《小说的难度》中说:“伟大的小说只为人类之道与爱怜,而歌吟。深切的悲悯心,是杰出小说的一大元素。”文学不是哲学,深刻的思想不能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但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有着深刻的思想。深切的悲悯之心体现了文学对人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构成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它赋予了文学超越时空限制的灵魂深度。”方英文深刻了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的尴尬位置,敏锐地发现了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那是一种信仰坍塌之后的迷茫与彷徨。长篇小说《后花园》就描绘了这种状态,小说以优美委婉的抒情笔调,描绘了秦巴山地的风物人情,传神地勾勒出生态迷离的都市景观,既是一轴山水长卷,又是一首爱情艳歌,令读者流连忘返而又扼腕叹息。作者在写意化地再现“百年中国史”的过程中,对人类精神家园予以深度叩问和探寻。“方英文在作品中涉及到严肃的问题,将思考很艺术地传达出来,作品的突出价值是人与社会的矛盾与理性的冲突。”
从《落红》开始,方英文就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发现了知识分子在都市生态中的边缘存在。读方英文的《落红》与《后花园》,我们很自然想到湖南作家阎真的《沧浪之水》。这三部小说反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变迁,他们从社会的中心滑到到社会的边缘。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位于社会中心,“士大夫阶级(亦称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为新时期社会进步提供了文化和知识,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礼遇。但在市场经济社会,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和幸福指标多元化,人的知识、修养或者人格退位于金钱和权力之后,社会各个阶层缺乏一种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知识分子与国家、普通民众失去了有机联系,换言之,知识分子再也无法充当民间代言者的身份,他们从以往的精神高地滑落下来。知识分子失去以往的精神高地之后,他们有的坚守自己的底线,有的拥抱世俗价值。然而,认同世俗价值的知识分子又不能忘怀自己的经世理想,这就造成了他们难以言说的痛苦。《落红》主人公唐子羽想既想升迁,又不愿意向官场潜规则低头,也没有反抗现实的勇气,只能在自嘲中游戏人生。《后花园》主人公宋隐乔是未央大学的一位讲师,他讲课魅力四射深受学生喜爱欢迎,甚至不乏校外的崇拜者。然而,他的生活并不如意,任职多年仍是一名讲师。校长对他虽然不无欣赏,却不过是让他充当一个为他们制造笑料的帮闲弄臣而已。宋隐乔是一个典型的边缘知识分子,不是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即构成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具有与主流社会的同质性。而唐子羽和宋隐乔皆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知识分子,我们注意到,《后花园》里有一个情节,宋隐乔被奔驰的列车抛在了深山之中,这就隐喻了宋隐乔是一个跟不上时代节奏、被现代生活所丢弃的人。唐子羽与宋隐乔不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们的弱点恰恰在于,他们都误觉自己怀才不遇,又无力对抗体制、改造现实。他们也想反抗,然而一遇挫折,便迅速败退下来,只能采取玩世不恭以证明自己的洒脱与脱俗,这其实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犬儒主义。
比如说宋隐乔,在大学任职就要遵守大学的规则,评职称固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这毕竟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一个尺度。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必须根据一定的量化规则来衡量,职称就是量化规则之一。宋隐乔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他只不过是一个“没用的好人”而已。在爱情方面,他追求那种纯洁理想的爱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者说是一种虚无主义。他始终没有找到心爱的人,人到中年仍是孑身一人。他追求纯洁爱情却又无法抵抗身体欲望,便不得不与很多女人进行交往,他的意志难以支撑沉重的肉身,“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宋隐乔本是一个俗人,偏要去追求高雅的生活,不免闹出很多尴尬。他放弃了精神贵族的立场,没有理想,不再有“舍我其谁”的担当与勇气,只能退守做人的底线。这正是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面对市场与政治的合谋,他们无能为力,自暴自弃,轻易放弃了自己心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大致就是一种超越的、非功利的审美精神。”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一种韧性和勇气,一旦失败就认同世俗、拥抱世俗,沉湎于世俗人生与感官享乐,把自己心中的启蒙立场抛之脑后。长篇小说《后花园》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叙述手法多样,视点变化不居,角度新颖,曼妙多姿,谱写出一部乡村与城市、斑驳与浮华的交响曲,透出一种历史沧桑感。写人状物都能抓住神韵而寄托深远,人物形象亲切可感,具有多维性。
《后花园》不仅仅标志着方英文艺术上的成熟,也显示了方英文思想上的成熟,这是一部隐喻性极为丰厚深远的小说,隐喻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过程。反讽是方英文艺术风格的一个独特标签,反讽也是方英文作品举重若轻的秘密。可喜的是,《后花园》的反讽来自生活本身,不再是为了炫示才情,从而使反讽具有一种厚重的生活意趣,耐人寻味。小说语言达到了“情理、意趣、声味”融合的境界,言在此而意在彼,不仅能听到声音还可以闻到味道,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轻松一笑。《后花园》揭示了一些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了人们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感和强烈的断裂感,产生了无家可归的惶惑与茫然。“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有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脉、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他们在都市感到一种疏离和冷漠,便向往宁静、淳朴的乡村生活。宁静、优美的后花园深深吸引了宋隐乔,宋隐乔的后花园之旅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猎奇之旅,还是一种寻找诗意生存的过程,目的是寻找到能安放自己灵魂的精神家园。宋隐乔从寻找后花园到逃离后花园这一过程隐喻着:后花园根本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家园,后花园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一种乌托邦。后花园虽然没有受到现代工业的污染,还保持着农业文明的优美与诗意,但是后花园已经处处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那里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暴力,那里的当下仍是贫穷、愚昧与无聊。那里的青年男子已经逃到城里打工谋生,那里的青年女子已经飞到城里挣钱,在那里隐居的智呆和尚也要去长安开茶馆。那里很快就要被开发,宋隐乔对所谓的后花园非常失望。刚开始,宋隐乔忘情于后花园的宁静优美,只不过是乡村的牧歌情调暂时抚慰了他浮躁的内心,其实,真正使宋隐乔心灵提升的是罗云衣善举的感召,真正让宋隐乔的灵魂得到升华的是来自罗云衣的善举的感召。罗云衣秀外慧中,热爱生活,热衷于公益事业,资助贫穷的孩子上学,这让罗云衣在宋隐乔的心中更具魅力。“他觉得他自己是极不般配罗云衣的。他也参加过赈灾捐款,但不过是一种随大流行为,却从未有过像罗云衣那样的,给鞋里塞张纸条的温暖浪漫的举动。现在他才明白,何以当她向他讲述她此次进山的目的时,他为什么突然发觉她是那样地美丽、那样地性感。”罗云衣的善举令她的美丽有了更深刻的内涵,罗云衣让宋隐乔明白他自己心中的后花园之所在,罗云衣隐喻的是宋隐乔心中的良知与善意。优美宁静的乡村不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只有心中的那份良知与善意才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最后,宋隐乔去西藏支教,西藏被认为是未被污染的一块净土,宋隐乔西藏支教就是再次踏上追寻精神家园的道路。“飞机腾空而起,只爬高天,一阵摇晃颤抖让他眩晕不已。但他不至于昏迷过去,他照常可以清晰地思维:西安,长安,渐次模糊的后花园……我也许不会来了,也许还要回来。这个我说不准,因为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又将是怎样的生活。我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我灵魂深处的后花园,是我永远如影随形的。”当飞机起飞时,宋隐乔感到了一种迷茫,他感到一种失落与惆怅,或许也有一种安慰,小说结尾透出一种浓重的感伤情绪。“《后花园》的浪漫和感伤,反映了一个优秀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巨大关注和对人类痛苦的深刻体验。”方英文通过长篇小说《后花园》探索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问题,人类精神家园并不是外在于人类心灵的乡村与都市,而在于人类心灵世界的和谐阳光与恬静从容,人应该永远与自己的后花园如影随形,人应该永远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西藏虽然被视为未被污染的一块净土,可以肯定的是,宋隐乔在那里也找不到他的灵魂栖息地。因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永远在远方,在彼岸,每个人都是一个“过客”,人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寻找,这样才能保持自己心灵的宁静。方英文通过这部小说探寻的是生命的意义之源和生命存在的价值,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方英文是一位具有中西文化视野的作家,他尤其喜爱鲁迅、茅盾、沈从文、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文学巨匠。文学大师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实践,深刻影响着方英文的精神气度和创作追求。方英文以其灿若舒锦的文采和终极关怀的风雅,行走在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路上。《后花园》的艺术超越及其成功,也许只是方英文文学创作生命步入另一段行程的开始。正如陈忠实所说:“从作家写作来说,方英文的创作已经进入自由叙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