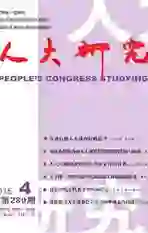有效行使人大质询权的思考
2015-10-28伊士国蔡玉龙
伊士国++蔡玉龙
人大质询权作为人大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大质询权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致使人大监督的功效尚未完全发挥。因而,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激活”人大质询权,保证人大质询权的有效行使。
一、人大质询权行使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季卫东教授曾指出:“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1]我国人大质询权正是陷入了这样一种“名归而实不至”的尴尬境地。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人大质询制度,明确赋予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权,且越来越规范化、程序化,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质询权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据有关媒体统计,近 30 年来有不少于 80%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没有行使过一次质询权。如果说我们过去还能列举几个经典的质询案例的话,如“1989 年 5 月,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就中央要求清理整顿公司提出质询案,最后以副省长杨汇泉被罢免而告终;2000 年 1 月,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起质询案,导致省环保局局长易人;2009 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部分直属机构违法收费和挪用财政资金行为提出质询案……”。那么,近几年来,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很少行使质询权,质询案例自然鲜有谈起。2010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其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曾燃起了人们无数希望。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跟进措施,到目前为止,人大质询权行使的次数依然非常少。对于这种情况,学者们将其称为质询权的“闲置”“虚置”“休眠”等。正如曹众教授指出:“‘质询被写入宪法和法律文本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如果把1954年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质问也算在内,那么这项权力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已存在50多年的历史。当前,又距离2010年委员长的‘提起两年多过去了,像询问那般,中央层面本应起到示范效应的质询案,至今却悄无声息。质询权依旧休眠……”[2]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大质询权出现了上述状况呢?是不是“一府两院”的工作中没有什么值得质询的问题呢?显然不是。正如王鸿任代表指出:“质询权的长期闲置,并不是各地‘一府两院的工作中没有值得质询的问题,而是规避刚性监督措施的惰性。”[3]
笔者认为,人大质询权被“虚置”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识上的误区。由于质询是人大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强制被监督对象回答代表或委员提出的问题,且代表或委员可以根据回答的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因而,质询权具有较强的“刚性”,与询问、审议、视察、检查等监督方式相比,“问责性”更浓一些。因而,许多对人大质询权不了解的人,特别是“一府两院”的领导人员,误认为人大从事质询工作,就是给自己“唱对台戏”,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甚至就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一些官员还误认为,一旦被人大质询,就要被罢官,即使不罢官,也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一府两院”一般不愿积极主动地配合人大的质询工作。而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基于上述理由,也怕得罪人,也不敢积极主动地行使人大质询权。第二,法律机制不健全。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人大质询制度,但该制度仍然存有不少缺陷,特别是规定比较原则、抽象,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如人大质询会如何组织、如何开展、如何处理等都无具体的细则规定,这样使得人大开展质询工作往往于法无据,无从下手,实践中操作难度也比较大。第三,实施门槛高。考虑到人大质询具有较强的问责意味,因而,我国法律规定了较高的实施门槛。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有利于避免质询权的滥用,但实施门槛偏高,也会阻碍人大质询权的正常行使。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才有权提出质询案。这就无形中增加了人大质询权行使的难度,因为如果某一质询案得不到法定人数的赞同,就根本无法提出。又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只能在各级人大会议或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提出质询案,其他时间则无权提出。因为各级人大会议一般每年才举行一次会议,各级人大常委会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且各级人大会议或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本来就非常多,这就导致人大质询工作无法经常性开展,难以做到常态化,等等。
二、“激活”人大质询权的对策
“严密监督政府的每项工作,并对所见到的一切进行议论,乃是代议机构的天职。”[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加强人大监督,要“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要“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5]。因而,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激活”人大质询权,以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具体说来:
第一,提高对人大质询权的认识。要排除妨碍人大质询权行使的错误认识,就必须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知识的教育和培训。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大质询权是宪法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之一,妨碍人大质询权的落实,将会损害我国人大的地位和权威;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大质询权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妨碍人大质询权的落实,就会妨碍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大质询权是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必然要求,妨碍人大质询权的落实,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可见,人大质询权的行使,决不是给某些机关或人员“唱对台戏”“没事找事”“找麻烦”,而是人大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当然,也要提高人大代表或委员对人大质询权的认识,并要加强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培训,使他们不仅要敢于质询,还要善于质询,提高人大质询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实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衔接。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人大质询权,但是两者的规定却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最突出的就是我国宪法没有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权,也没有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两院”的权力。如我国宪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而我国的监督法、地方组织法等却规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质询权。这样,就使得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质询权,以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两院”都缺乏宪法依据,都存在“违宪”的嫌疑。因而,我们应对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以实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衔接,为人大质询权的行使提供宪法保障。具体言之,可以将宪法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具体程序由法律规定。”此外,可以在宪法第三章第五节中增加关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权的规定,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提出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的具体程序由法律规定”。
第三,进一步完善人大质询制度。虽然我国质询制度不断发展,但仍然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言之,一是关于质询主体。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委员联名才能提出质询案,这无形中增加了质询权行使的难度。可以考虑修改相关法律,降低数量上的要求,以方便人大代表或委员提出质询案。二是关于质询对象。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质询对象范围仍然有点窄,不够全面,可以考虑将其扩大。“质询对象除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外,在人代会期间,还应增加同级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领导人,以实现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监督。同时明确规定司法质询的对象是‘作出生效行政行为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决定书等终局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6]三是关于质询时间。由于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会议次数少、时间短、议程多,因而,如果只在会议期间才允许人大代表或委员进行质询的话,显然难以保证质询的效果,也达不到人大质询的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地方组织法的相关条文,规定人大代表或委员在闭会期间也可以行使质询的权利,以做到人大质询工作的经常化。四是关于质询程序。目前人大质询工作尚缺乏一套具体细致的程序规定,使得人大质询权的行使缺乏程序保障。因此,应通过立法增加有关人大质询程序的内容,包括质询案的提交、质询案的审议、质询人的提问、被质询人的答复、质询的后果等。特别是应明确规定质询不满意的法律后果,否则,人大质询权就会形同虚设。可以考虑规定,如果“代表或委员对质询不满意时,可以要求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常委会将被质询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常委会全体会议讨论。若质询案根据一定程序被提交大会或常委会会议讨论后,下一步的结果可以是:或表示满意通过;或需进一步组织特定调查;或提出罢免、撤职案等,都由会议来决定”[7]。
注释:
[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曹众:《设计对实施的向往——对询问权、质询权的审视与反思》,载《法治与社会》2012年第7期。
[3]王鸿任:《从代表角度谈质询权的闲置》,载《人民代表报》2012年3月24日。
[4]【美】威尔逊著:《国会政体》,熊希龄、吕德本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7页。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 ht
m,2014-6-20.
[6]柯兰:《激活地方人大质询权需要顶层设计》,载《检察日报》2013年9月9日。
[7]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作者分别系河北大学人大制度与地方立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副教授,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