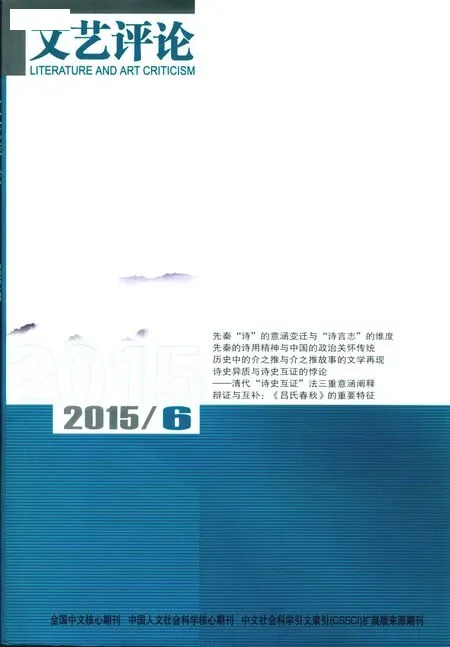桐城派与《庄子》考据学
2015-09-29李波
李波
桐城派与《庄子》考据学
李波
桐城派素以古文著称于世,但此派亦非常重视学养,强调学、文相济,以学济文,故兼有学派性质。方苞以礼学名世,姚范所著《援鹑堂笔记》曾为梁启超称道,姚鼎有《九经说》、《三传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传世,方东树、吴汝纶、马其昶等人皆学有所成。桐城派出入于经史子集,于先秦诸子尤重《庄子》,像姚鼎《庄子章义》、方潜《南华经解》、王先谦《庄子集解》、吴汝纶《庄子点勘》、马其昶《庄子故》、林纾《庄子浅说》等皆为今人熟悉。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普遍用力于考据,这似乎与桐城派宗法程朱、以义理为主的宋学主张大相径庭。其实不然,桐城派从方苞时引入经子互证的考据方法,之后姚范、姚鼐、方东树一直到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等人皆重考据,考据是桐城派治学的一大特色,只不过桐城派以古文名世,加之乾嘉学派盛极一时,故其学术成就被掩盖而鲜有人注意。那么桐城派《庄子》考据有何特点,与乾嘉学派相比有何不同?将此问题搞清楚,对于深入了解桐城派大有必要。本文即以桐城派晚期师徒二人吴汝纶《庄子点勘》、马其昶《庄子故》为例,对桐城派《庄子》考据作一深入探索,以期揭开桐城派治学真面貌,亦使世人对桐城派与乾嘉学派考据异同有一清晰的认识。
一
《庄子》在流传过程中经历秦火、兵燹、散佚、纂改等多种厄难,古本渐失真,而世传众版本文字出入较大。从唐陆德明、宋陈景元、元吴澄直到明人杨慎等皆利用相关版本进行了校勘比对,取得了一定成就。到了清代,《庄子》古文献散佚已相当严重,清代学者很难找到精审的版本进行校勘,在此种情况下,他们尝试在方法上突破前贤,另辟蹊径,于是将乾嘉经学考据方法引用到了《庄子》文本校勘中,引起了《庄子》校勘学上的一次革命。这方面的突出成果有卢文弨的《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的《庄子杂志》、孙诒让的《庄子札迻》、于鬯的《庄子校书》等。如卢文弨的《庄子音义考证》每从音义的角度对文字进行考订,并对通用字、正体字与俗字等加以辨别,视角独特,多有创获。王念孙的《庄子杂志》多从以音求义、文献互证、通假引申、研究古韵等方法对《庄子》文字进行校勘和句读,为世人所重。孙诒让的《庄子札迻》则将《庄子》文字与古文献如汉代碑文等互证,这是他人所不及的①。
在清代朴学风气影响下,桐城派也相当重视文本校勘工作。桐城派早期人物姚范《援鹑堂笔记》号称遍校群籍,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姚鼐《庄子章义》十分用力于文本校勘,其所用校勘方法主要有依古本校勘、依文意校勘、依韵校勘、文献互证等,但内容较为简单。桐城派后学更加重视《庄子》文本校勘工作,主要发挥了姚鼐所运用的文献互证、互校的方法,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文献材料较为广博。姚鼐对《庄子》文本的考证主要局限于一些《庄子》古本,而吴、马二人则大量地运用了一些重要的古代文献资料。试看吴汝纶的《庄子点勘》。如《逍遥游》篇“藐姑射之山”句“藐”下注:“《列子·黄帝》篇作‘列’。”《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句“刑”下注:“某案《文选·嵇康幽愤诗》注引司马注‘被褐怀玉,秽恶其身,以无陋于形也’,‘陋’字疑误,据此‘刑’当为‘形’,无近者遗之也。”又如解《天地》篇“时骋而要其宿,大小、长短、修远”句云:“姚云:‘此下有脱文。’某案‘大小、长短、修远’六字当为郭氏注文,郭注‘大小长短修远’:‘皆恣而任之,会其所极而已’,盖释‘时聘而要其宿之义’,今注文无上六字,夺入而正文也,又据《淮南·原道》作‘大小修短各有其具’云云,姚谓有缺文者是也。”②皆引证有据,虽然证据略示单薄,亦可备一说。而马其昶《庄子故》的校勘又比吴氏向前发展了一步。如《应帝王》篇“萌乎不震不止”句下注云:“‘止’,一作‘正’,今从崔本,成元英曰‘震,动也’。其昶案,《列子》亦作‘不止’,贾子‘萌’之为言‘盲’也,《汉书》‘民萌’注‘无知之貌’。”于“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句下注云:“其昶案:‘弟’,《列子》作‘茅’,卢重元注云:‘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淼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识也’。孙志祖曰:‘《埤雅》‘茅靡’言其转徒无定,一作‘弟靡’,‘弟’读如‘稊’,稊茅之始生也’,此可证无作‘弟’字之理。”③从所引证据来看,皆引用多重证据,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其二,十分重视利用《淮南子》中的资料从事文本校勘。《淮南子》是西汉黄老学思想的产物,里面保存了不少庄子语言,以此来校勘《庄子》,很有意义。吴汝纶、马其昶对此书较为重视,二人著作引用《淮南子》文本材料比比皆是。如吴汝纶解《德充符》篇“人莫鉴于流水”句云:“‘流’一作‘沫’。某案:‘沫水’当作‘流沫’。《淮南·俶真篇》正作‘流沫’。”解“彼且择日而登假”句云:“徐云:‘假音遐’,姚南青云:‘《大宗师》‘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与《列子》‘周穆王登假’同。’某案《淮南·精神》篇‘此精神之所以登假于道也’,高注:‘假,至也,或作虾,云气也。’此‘登假’当如高氏后说,谓乘云气而上遗世之义也。《大宗师》‘登假’当如高前说,谓进至于道也,又案《淮南·齐俗》篇‘乘云升假’,注云:‘假,上也。’”其重视《淮南子》程度可见一斑。马其昶继承其师做法,亦用《淮南子》互校。如解《天道》篇“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句云:“其昶案,不尽即有余也,《淮南》言‘周公殽臑不收于前’,文句与此同,无崖犹无形,谓其敛气于内,食物狼藉概不经怀也,老氏主清净故云。”以上可见,《淮南子》中的某些异文对于《庄子》文本校勘很有价值。虽然乾嘉学派也偶引用之,但像吴、马二人这样大量利用此书资料对《庄子》进行文本校勘,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其三,利用唐宋类书从事文本校勘。宋代王应麟曾利用唐宋时的类书辑出了大量《庄子》佚文,这些佚文对于校勘《庄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清代乾嘉学派对这些资料并没有充分运用,而大量利用这些类书从事文本校勘工作的,清代马其昶算是最突出的一个。马其昶利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白贴》等类书中有关《庄子》的资料,校出了不少《庄子》异文。如《逍遥游》篇“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句下注云:“其昶案:《御览》引作‘以其远而无所至极也’。”于《天地》篇“鸟形而无彰”句下注云:“其昶案,《艺文类聚》引作‘无迹是也’,食、迹为韵。”于《天运》篇“然乃愤吾心”句下注云:“其昶案,《释文》‘愤’又作‘愦’,《艺文类聚》亦作‘愦’。”于《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句下云:“其昶案,《白帖》引作‘灌注’。”对于类书中的这些异文,马氏并没有做判断取舍,而保持了一种存疑的科学态度,以备世人参考。后来的学者如刘文典等人,就对这种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
此外,二人继承了姚鼐的做法,有时依文意校勘,有时依韵校勘,虽然用得不多,足可说明桐城派前后文本校勘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从以上可以看出,桐城派的文本校勘并没有重复乾嘉学派的路子,而是另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
乾嘉学派最精通的莫过于小学训诂,他们在大量运用先秦诸子材料进行经学训诂之余,又转而将之运用于先秦诸子。清代考据家《庄子》训诂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发明因声求义的方法,征引经史子集文献资料,纠正了很多前人以讹传讹的错误注释,不仅疏通了文句,也使庄子本意得以还原。此外,俞樾《庄子评议》在借鉴、总结并改进王氏父子研究诸子的方法基础上,做了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等工作,特别在《庄子》文字考释方面创获殊多。他如孙诒让的《庄子札迻》、于鬯的《庄子校书》等亦多有新见。
桐城派前期姚鼐《庄子章义》拒绝汉学家的训诂方法,只作简单的字词训释。到曾国藩时则十分推崇汉学家的小学训诂工夫,“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曾文正公家训》“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在其影响下,桐城派学者开始用力于《庄子》文字训诂,作为曾门弟子的吴汝纶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而其弟子马其昶又与之一唱一和,师徒二人的《庄子》著作表现出了以下四个训诂特色。
其一,引用魏晋学者的治庄成果。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庄子学极为发达,出现了一批专门《庄子》研究著作,可惜后来大部分已经亡佚,但很多说法因《文选注》、《经典释文》以及一些类书而赖依保存,这些成果因为时代较早更接近古意而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吴、马二人在进行《庄子》字词训诂的过程中,即大量地引用了这些学术成果,特别是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庄子音义》部分所保存的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李颐、支遁、简文帝等人的材料,书中俯仰即拾。如吴汝纶解《齐物论》篇“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几句云:“司马云:‘枝,柱也;策,杖也;梧,琴也。’崔云:‘枝策,举杖以击节。’”解“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几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几句云:“崔云:‘齐物七章夫道未始有封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解《养生主》篇“而况大軱乎”云:“《释文》引《字林》云:‘肯,著骨肉也。’司马云:‘綮,犹结处也。’崔云:‘大軱,盘结骨。’”又如马其昶解《逍遥游》篇“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句云:“司马彪曰:‘搏飞而上也,上行风谓之扶摇’,《尔雅》‘失摇谓之飚’。”解“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句云:“崔譔曰:‘堂道谓之坳’,支遁曰:‘谓有坳垤形’。”马其昶亦十分推崇魏晋旧诂,他于《庄子故序目》中说:“前后为注者百数十家,独郭象注最显。陆氏《释文》多存唐以前旧诂,自象注及诸家益各用己意为说,本旨荒矣。”因此其在注文中大量采用魏晋旧诂。如仅注解《逍遥游》篇,就引用了支遁、陆德明、崔譔、司马彪、简文帝、郭象、李颐等人的治庄成果。如果对吴、马二人所引他人训诂成果材料作一统计,显然引用魏晋学者的成果比重是非常大的,这充分说明桐城派学者对魏晋旧诂的重视,这也成为了桐城派训诂方法的一大特色。
其二,引用乾嘉学派的成果。桐城派前期姚鼐与乾嘉学派可谓水火不容,以至拒绝引用汉学家的学术成果,而后期桐城派学者对汉学家的态度和姚鼐当年已绝然相反。从吴、马二人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大胆引用了不少清代汉学家的小学训诂成果。吴汝《庄子点勘》多引用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人的一些观点。解《人间世》“若能人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句云:“王怀祖云:‘《广雅》:樊也,边也,字通作藩,《大宗师》吾愿游乎其蕃’”,解“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句云:“俞荫父云:‘益’当为‘溢’,即上文溢美、溢恶之义。”解“名也者,相札也”句云:“王伯申云:‘礼与札形似而谓’,《淮南·说林》‘乌力胜日而服于鵻礼’,《广雅》‘鹪札’,《御览》‘譌为鹪礼’皆是。”吴氏对二王与俞樾成果的推崇程度可谓与曾国藩一脉相承。而马其昶《庄子故》引用汉学家的成果比其师范围大大扩大了,除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俞樾外,他如郝懿行、洪颐煊、卢文弨、洪亮吉、顾炎武、孙诒让、邵晋涵、段玉裁、阎若璩、朱骏声等人的说法也时有称引,这里不再举例。清代末期桐城派学者这种勇于打破汉宋界限,采取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
其三,引用桐城派学者的训诂成果。作为桐城籍桐城派学者,吴、马二人有着浓厚的家乡文化观念与乡土情怀,也带有较为鲜明的学派意识。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于《庄子故》中“《庄子》篇目”下说:“先公所校阅庄子数本,皆临写刘、姚各家圈识,未有自点定者,独曾文正公《杂钞》中所载《逍遥游》、《养生主》、《骈拇》、《马蹄》、《胠篋》、《达生》、《山木》七篇为己所点定,其《外物》、《秋水》二篇则未加墨,今迻录此七篇圈识于印本中,其余阙略各篇概以姚氏圈识补之,以便学者云。”足可见吴氏父子学派观念之强。因此他们的著作中理所当然地大量引用了桐城籍学者以及桐城派学者的训诂成果。吴汝纶于《庄子点勘》中主要引用的是前期桐城派学者如刘大櫆、姚范与姚鼐的训诂成果,尤以姚范成果最多。如解《人间世》篇“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句云:“姚南青云:‘名读甍,司马云:‘丽,小船也,又屋檼也。’”解《胠箧》篇“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句云:“姚南青云:‘不乃犹无乃也,与邪通’。”解《达生》篇“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句注云:“姚南青云:‘达生,务生,生本读性’。”而马其昶《庄子故》除了引用桐城籍学人像方以智、钱澄之等的成果外,还大量引用了桐城派学者像方苞、姚范、姚鼐、方潜、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姚永朴、姚永概等人的训诂成果。如解《逍遥游》篇“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句云:“方以智曰:迳庭犹霄壤,言迳路之与中庭偏正悬绝。”解《齐物论》篇“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句云:“吴汝纶曰:‘爱,隐也,障翳也。’”“故载之末年”句云:“姚永朴曰:‘小《尔雅》:载,行也,末年犹云终世。’”“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句云:“曾国藩曰:‘有待,景为形使也;又有待,形为气使也。’”解《人间世》篇“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句云:“郭嵩焘曰:‘蕉’与‘焦’通,即《诗》‘如惔如焚’之意。”“外合而内不訾”句云:“方苞曰:‘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省’”等等。除了引用桐城派训诂成果以外,吴、马二人还引用了此派义理阐释的不少成果,二者相加比例远远超过了所引乾嘉学派的比重,这说明桐城派学者始终坚持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汉宋兼采的治学主张。
其四,大量利用《淮南子》《周礼》等文献资料从事训诂。吴、马二人的《庄子》考据并非一味地引用他人的现有成果,也较注意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庄子》字词训诂作出自己的判断。综观二人训诂,一个突出特点是十分重视《淮南子》高诱注的文献价值,大量利用了其中的材料进行训诂。吴汝纶多引《淮南子》高诱注作为证据材料。如解《逍遥游》篇“南冥者,天池也”句云:“某案运,行也。《淮南·原道》篇‘天运地滞’,高诱注:‘运,行也。海运犹言海行,言是鸟之行于海也’”。解“而几向方矣”句云:“司马云:‘园,圆也’,某案《淮南·诠言》篇作‘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高注:‘方,道也。’”他在利用高诱注作引证时,有时还对高诱注进行了一些校证,如解“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几句云:“崔云:‘若有若无谓之葆光。’某案《淮南·本经》‘葆’作‘瑶’,高注:‘瑶光,北斗构弟七星也,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擿起阴阳以杀生万物也。一说瑶光和气之见者也。’某案:高注二说皆未是,《淮南》正文释之曰:‘瑶光者,资糧万物者也。’”受其师影响,马其昶也十分注意利用《淮南子》中的资料。如解《逍遥游》篇“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句云:“其昶案,照与炤灼同字,《说文》:‘灼,炙也。’《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即此所谓并炤也。葆光之道,天且宜然,若十日在上,虽蓬艾亦不能自存矣。”解《人间世》篇“皆求名实者也”句云:“其昶案,《淮南》‘名实不入’,注:实谓幣帛货财之实。”解“始乎谅,常卒乎鄙”句云:“其昶案,谅,明也。鄙,固陋也。《淮南》‘始乎都者常卒于鄙’,都鄙犹好丑也,义同”等等。马其昶或利用《淮南子》原文材料和《庄子》互训,或利用高诱注作引证材料,显然是对其师治学方法的进一步灵活发挥发挥。
此外,马其昶还十分重视运用《周礼》的资料对《庄子》作训诂考证。如解《庚桑楚》篇“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句云:“其昶案,《汉书集注》‘期,要也’,《礼》郑注:‘费犹惠也。’”解《徐无鬼》篇“下之质执饱而止”句云:“其昶案,《周礼》‘疏执取也。’”解“形固有伐,变固外战”句云:“其昶案,《礼记》郑注:‘成,善也,善则自伐,变则外战,争战之形,固皆心造。’”解“丘愿有喙三尺”句云:“其昶案,司马说三尺为剑是也,高纪提三尺,师古注三尺剑也。《左传》、《释文》‘喙,口也’,唯口与戎故以剑喻,犹言舌锋也,《礼记》‘不能有其身’,注:‘有,保也。’有喙三尺,即金人缄口之戒”等等。罗勉道曾在《南华真经循本释题》中说:“顾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时语,有非后世所能悉晓。然尚有可征者,如‘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乃《太射》有司正司获,见《仪礼》。”④马其昶正是在此种思路启发下,积极引用《周礼》中的资料来训释《庄子》字词,这种以经证子的方法,可谓是对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学习和发挥。
三
校勘和训诂是吴汝纶、马其昶《庄子》考据学的主要特点,此外还表现出了其他方面的一些考据特点,一是句读,二是名物考释,三是辨伪与辑佚。而这些特点在马其昶《庄子故》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1.句读。庄子难读世所公认,其中有些句子的句读历来有争议。作为古文流派,桐城派讲究因声求气,十分重视句读问题,故研究《庄子》亦颇用心于此。姚鼐《庄子章义》对此有所涉猎,到吴汝纶、马其昶时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如吴汝纶于《齐物论》篇“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下注云:“某案,王伯申说‘之’犹‘于’也,此‘溺之’当训‘溺于’,十二字为一句,五句为一事。”马其昶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最大,如解《大宗师》篇“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莫然”云:“吴汝纶曰:‘莫然属上读’。其昶案,《北堂书钞》引此,亦以‘有间’为句首。”解《人间世》篇“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句云:“其昶案,自有其美,故见恶于人。且德厚信矼,卅二字连读。”解《应帝王》篇“治外乎正而后行”句云:“其昶案,‘治外’七字为句,‘正’同‘政’,即经式仪度也。”解《达生》篇“不厌其天,不忽于人民”句云:“其昶案,‘民’字句绝,民真为韵。”解《天地》篇“治乱之率也”句云:“其昶案,‘治’字断句,《尔雅》‘率,自也’,《天运》篇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解《知北游》篇云:“以长得其用”句云:“其昶案,‘是用之者’十四字为句,《淮南》云:‘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解《列御寇》篇“不若人三者俱通达”句云:“其昶案,‘不若人’八字为句。”解《天下》篇“夫弃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句云:“其昶案,‘曰愈’属上读,与‘几矣’为对文,充一贵道,皆惠子之说,前辟其舛驳,此举其说之近理者。”这些观点较为新颖,值得参考。
2.名物考释。自唐代成玄英、宋代罗勉道以来,学者们开始对《庄子》中的某些名物制度有所考证,其间代不乏人,至清代俞樾撰《庄子名人考》而达到高潮。马其昶受此风影响,亦注意对《庄子》中的某些名物作考释。有时做地名考释。如解《逍遥游》篇“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句云:“其昶案,《御览》引《隋图经》曰:‘平山在平阳,一名壶口山,今名姑射山。’”有时对动物作考释。如解“子独不见狸狌乎”句云:“其昶案,正字通‘貍’,野猫善窃鸡鸭,《尔雅》注‘鼬啖鼠,江东呼为鼪。’狸同貍,狌同鼪。《秋水》篇‘捕鼠不如狸狌’。”有时对音乐知识作考释。如解《徐无鬼》篇“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句云:“其昶案,康熙《几暇格物编》云‘乐发于何音,止于何音,取琴瑟之类,置二器均调一律,鼓此器一弦,则彼器虚弦必应,推之八音之属皆然,所谓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韵律同也。’”像这样的名物考释不拘一格,较有意义。
3.辨伪。自苏轼《庄子祠堂记》指出《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伪作以来,学者承其说,从不同角度作了进一步阐释。桐城派亦接受了此种观点。姚鼐在《庄子章义》中本着考据的精神,进一步论证了《让王》等四篇为伪作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考证了《庄子》其他篇章中的伪作。如《秋水》篇“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句下解云:“此处语意极害教,然非庄子文也,盖所谓其子必且行劫者也。”《天道》篇“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句云:“素王,十二经是汉人语”等等。马其昶进一步发扬了姚氏辨伪之精神。他于《庄子故》序中说:“《释文》称内篇众家并同,自馀或有外无杂。余谓外、杂二篇皆以阐内七篇之义,其分篇次弟果出自庄生以否,殆不可考。其间皆不无羼益,以其传久,故一仍之。其《让王》以下四篇,旧次《列御寇》前。然自苏子瞻辈,皆断其伪,今观之犹信。太史公称其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世所好儒者,皆托为孔子之徒。今《胠箧》所言,不及孔子,第绌儒信老,是其义矣。若《盗跖》真诋訾孔子,是殆擬为之者,读史公语未审耳。且又乌睹所谓老子之术者哉!非史公所见之旧,其为赝决也。因从宣颖《南华经解》例,退其篇目附于后。又姚姬传先生谓:‘《汉志》庄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然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可决其非庄生所为者,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书而为象去之矣。’”反映了桐城派的实证精神。
4.辑佚。早在南宋王应麟就从唐宋类书、《文选注》等文献资料辑得大量庄子佚文而编成《庄子逸篇》,开《庄子》研究辑轶之先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关注。清代考据家十分热心于《庄子》的辑佚工作。清人万希槐、翁元圻分别对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作了笺注,对其中的《庄子》逸文作了集证和校补,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中辑录《庄子》佚文数则,茆泮林在王应麟工作基础上辑有《庄子逸篇》、《庄子逸语》等。马其昶对庄子逸文颇感兴趣,他不仅收录了前人所辑佚的一些成果,又亲自进行辑佚工作。其《庄子故》书末附有《庄子逸篇》部分,其中收录清人万希槐、翁元圻校补的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庄子逸文39条,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所辑8条,黄奭《逸庄子》7条,还有马氏自己从《太平御览》中辑得庄子逸文9条。于每一条下皆注明出处,有些条目还做了进一步考证,对于世人了解《庄子》古貌十分有益,亦体现了马其昶的求实精神。
四
桐城派主要作为一个古文流派,其实亦具有学派性质,他们的《庄子》考据研究虽然无法与乾嘉学派的精深相比,但自有其贡献,不应为世人忽视。现在有些学者过分贬低桐城派的学术成就,这是不科学的,也不客观。
首先,桐城派主张“义理、辞章、考据”三位一体,故考据只是其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像乾嘉学派那些走专门之路。我们知道,乾嘉学派重在经学文献整理,志在求精求深,故一人一生专攻一经,诚如梁启超所说:“乾嘉以后学者,皆各专一书以终身。……其分业愈精,共发明愈深。百年前之经学,其组织殆可称完备。”⑤由于六经皆古书,因此他们在研究中必须利用先秦诸子典籍资料来佐证儒家经典,沿流而讨源,无形中引起了子学的复活。“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通习经史相淬厉,其结果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⑥加之后辈由于经学悉为前辈所占,故转而考子。于是,考据学派在研究经学之余开始关注子学,认为“子为六经羽翼”,并将经学的考据方法应用到了子学中,使子学考据大盛。在这种情况下,《庄子》考据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桐城派《庄子》研究显然受到了此种风气的影响,注重对《庄子》的考证研究。但桐城派古文家的身份一方面,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达到乾嘉学者那样的学养;另一方面,他们的宋学立场又限制了他们的学术风格,故其《庄子》考据学基本上沿袭了南宋朱熹以来理学家的考据路子,偏重简炼、明了特色,不走繁复之路。从历史上来看,作为身兼理学家和文人身份的桐城派,如果抛开乾嘉学派不论,他们对《庄子》的考据研究已经算是比较系统,较为出色的了。
其次,桐城派《庄子》考据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桐城派《庄子》考据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桐城派前期以姚鼐《庄子章义》为代表,考据色彩并不浓厚,不管在考据方法上还是内容上都较为简单。桐城派中后期,由于曾国藩的倡导,考据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且明显突破了汉宋界限,最明显的例子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但郭氏桐城派背景并不强烈,只能算是个案。而作为桐城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马其昶,无疑是桐城派中后期最具代表色彩的人物。综观他们的《庄子》考据,表现出了个性化特色。首先,在文本校勘上,多利用《淮南子》以及大量类书进行文献互证、互校,有其积极意义。其次,注意利用前人训诂成果,不管是乾嘉学派,还是桐城派,亦或是魏晋时人成果,皆兼容并蓄,不拘一家,打破了学派界限,十分难得;在训诂方法上虽然没有乾嘉学派那样集淹博、精审、识断于一身,但大量利用像《淮南子》《周礼》这样的资料对《庄子》进行训诂,亦颇具工夫,不乏新见。再次,考据内容较为全面,在校勘、训诂、句读、名物考释、辑佚、辨伪等方面皆有所涉猎,基本涵盖了清代《庄子》考据的大部分内容。
研究桐城派与《庄子》考据学,为我们重新认识桐城派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桐城派应时而变,其对《庄子》考据的研究无疑向世人表明了一种学术姿态。而这种学术上的变化与其古文创作的关系则更值得玩味。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401331)】
①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15页。
②吴汝纶《庄子点勘》,清宣统二年衍星社排印《桐城吴先生点勘七子》本。文中所引吴氏资料皆出此本。
③马其昶《庄子故》,清光绪三十一年集虚草堂刻本。文中所引马氏资料皆出此本。
④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释题》,明正统《道藏》本。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评点史”(编号:12BZW063);中央专项配套资金青年人才培训与研究支持计划“桐城派《庄子》学”(编号:WXY201F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