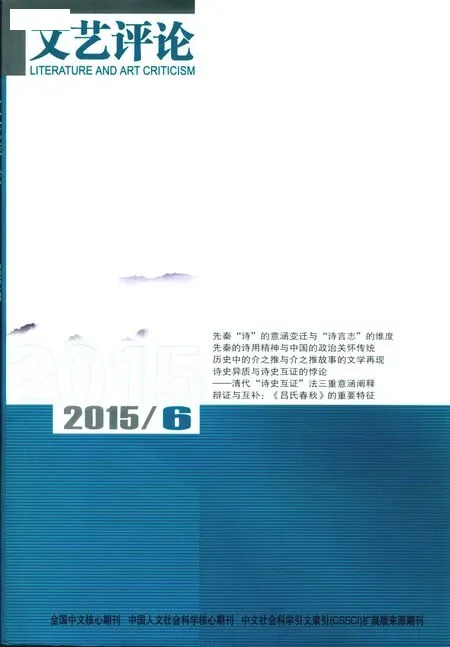张爱玲在“两岸三地”的文学接受比较
2015-09-29王千一
王千一
张爱玲在“两岸三地”的文学接受比较
王千一
提起张爱玲,人们仿佛回到了旧上海那喧嚣拥挤而封锁的租界,看到了破旧而空寂的洋房里弥漫着青蓝色的鸦片烟雾,闻到了灰尘腐朽的味道;又似乎回到了旧香港,回望着拥挤的沙龙里跳着华尔兹的女人,叹息着镜中的她们被岁月和物质消磨而蜕变……张爱玲把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城市凝聚在同一时间段,西洋与传统结合的作品让她的作品充盈着迷人的魅力,其文学的独特价值也注定着,在半个世纪里海内外研究学者的认同和关注。
一、海外的“张爱玲”传播
尽管最早正式对张爱玲的研究是40年代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的相关评论,但由于战争给学术环境带来的恶劣因素,并且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不被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所认同,所以傅雷的研究评论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太大的轰动。但是海外对张爱玲的阅读与认可却把张爱玲的文学研究推及到一个研究的风口,这不仅是张爱玲本人居住地域的特殊,同时还有深刻的政治因素在其背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美台反共气焰高涨,美国反共政治学家戴维拉参与《中国入门》的著述,而夏志清作为他的助手也参与其中。由于当时不同政治目的的角斗,1952年起夏志清得到反共的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开始编纂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夏志清开始对反共倾向的作品介绍多为热心①。正逢张爱玲带有反共意味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热销,又符合夏志清对于文本编辑的要求,所以夏志清将张爱玲定位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这使得她第一次被正式列入华人文学研究的视野。而从张爱玲自己本愿来说,对于美国支持下创作的《秧歌》颇为仓促,并非自发创作,对于远离政治的她来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似乎都不太满意。②
从创作内容上来说,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在1943-1945年,与创作背景相应的是上海沦陷和租界半殖民的状态,这个时候的上海处于现代化的进程阶段,传统与西洋的结合使老派和新派在相互对立的摩擦下充实着上海独特的文化。此时的香港则是在殖民的独特文化成熟下逐渐壮大,并以其特定的文化氛围将消费行为与意念,化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真正紧张的战场。半殖民文化与殖民文化下的城市文明渐渐形成了后殖民主义,它颠覆了欧洲中心论③,打破了白种人与其他有色人种二元对立的局面,人种间在相互排斥中交杂,恰如搭配着帝国殖民权力下的华洋文化的对比,有着不同殖民心理层次的表现。而由此又产生了殖民心理的女性主义研究探讨,诸如日本池上贞子的《张爱玲和日本》就探讨张爱玲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认为,张氏的作品揭露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女性歧视,新的自由恋爱对现代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等。
张爱玲透过扭曲而间接的方式探索个人自身的主体中心,个人欲望与自身相互压抑,传统与西洋文化相互排斥共同构成了“本外同体”的特质。对于隔岸观火的海外人士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炫魅和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殖民心理的多层多义性,让张爱玲的小说成为桥梁,建构着中国人视野中的“洋”文化,这是幽秘的、矛盾的,又是敞开的、明了的,中国文化之于海外殖民文明的交错中,张爱玲找到了话语立足点,书写着中国现代发展的颠簸。这满足了海外人士对中国殖民文化的偷窥欲望,继而将张学研究播散开来。
二、台港的“张爱玲”接受
美国和我国台湾的互动关系也影响着学术的交流和动态,夏志清60年代的文学史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由此也波及到了台湾。张爱玲的作品大部分写于汪伪政权时期,所以蒋方政权并不接纳她,因此50年代初张爱玲见台湾无处可留便转身香港。但由于《秧歌》、《赤地之恋》的反共倾向和张学在美国的广泛传播,并且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兴起开启了“文化寻根”,所以她的作品才能走入台湾并被研究者关注。其中,唐文标和水晶让张爱玲在台湾复活。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研读方面,台湾学者作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其中唐文标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尤其引人瞩目。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和《张爱玲卷》为对张爱玲的进一步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文标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他是张学在台湾新的开创者,对张爱玲的研究也是对中国文化新的探究。而水晶则对唐文标的研究得以补充,通过访问张爱玲提供了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起居鲜为人知的资料④,并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其文本进行文学结构的内在分析。此外,叶石诗在《台湾文学史纲》中把张爱玲放在“反共作家”姜贵之后,在台湾文学史上首次亮相。文学研究对张爱玲的关注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台湾一些作家甚至可以归于张派传人,诸如蒋晓云、萧丽红、施叔青、李昂、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与袁琼琼,甚至三毛等。特别是蒋晓云在1976—1978年连续获得《联合报》小说奖,评委正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朱西宁和夏志清。而王德威称张爱玲“祖师奶奶”的同时,甚至在《“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中为张派构建了文学族谱,勾连了张爱玲、女性主义、台湾女性小说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研究者必读论文⑤。从功利意义上讲,张派霸占着台湾的文坛注定了张爱玲在台湾巨大的声誉,由此有些评论家将张爱玲列为台湾作家。
张学研究阵地不单单是在台湾,在香港也是颇有影响的。由于张爱玲生活在香港十年,又有着丰富的香港生活经验,同时许多创作也都是在香港完成,并以香港为蓝本进行,所以香港学者都自觉地关注张爱玲。在殖民文化浓厚的香港,他们对张爱玲文本中的后殖民主义有着更深的理解和观照。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成为了张学研究的集中地。刘登翰先生的《香港文学史》就特别介绍了张爱玲的创作,将张学传播到文学专业读者中。
从张爱玲文学本身来看,她细腻地笔触,鲜明的都市特征,令台港研究者能够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她的悲剧性体现了她对社会的分析和关注。如夏志清所言,“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但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⑥夏志清先生对其价值的重新定位,恰恰弥补了大陆文学史的研究空缺。台港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越来越客观的研究张爱玲文学的内部建构,受到海外研究影响,他们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开始研究张氏小说人物的命运,这一阶段无论是在“量”还是“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很大的突破,从文化哲学和人类学的理里分析视角解读张氏小说的审美意义。这对大陆学者的批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大陆的“张爱玲”审视
傅雷在40年代发表评论后,谭正璧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张爱玲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批判,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对张爱玲予以高度评价并将其与鲁迅相提并论。随着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1956年移居美国,一直到80年代,她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大陆的文坛上。建国后,由于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严峻,对文学的创作内容和题材的局限性更加严格。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新兴发展的学科,其政治使命却是更加的艰巨。张爱玲的作品写于上海沦陷区,其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内容政治性的淡化,使得它难逃大陆将其封锁的宿命,如果张爱玲没有离开大陆,她或许无法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在1980年文学“去政治化”的思潮中,将政治狭隘的与“纯文学”相对立起来。有些人在呼救,让文学的归文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这一文学思想解放,将冰冻多年的作家作品重新挖掘,让更多的作品回归到人们视线并产生它新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赵园在1983年即有评《传奇》的论文,她着重阐发了张爱玲小说的意义⑦,并呼吁学术界关注这位被遗忘的作家。与张学传播到台湾的途径不同,大陆研究张学的出发点并不受他国的政治干预,在政治条件自我改良的基础上,将尘封多年的作家重新挖掘,也就是说大陆的研究初端是学术文化氛围的醒发并将其深化。尽管由于政治原因,大陆对张学深入研究的时间较海外和台港地区晚,但研究的程度并不亚于它们。
张爱玲的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上海,由于身世家族的显赫,她从小就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大陆这片土壤给予了张爱玲的“根”,这个“根”也恰恰是大陆人以其自身的文化经验对张爱玲的接受和认同。大陆以其研究的地域优势对传统的挖掘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在台港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哲学将研究的领域范围扩大。到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界迎来了思想革新的春天,“人”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被认识,大陆学界带着对新生的向往开始醒发。大陆的受众群体多,长期封闭让人们对文化的渴望程度加深,所以台港文学能迅速地被人们接受并得到认同,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大陆学者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并在台港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填补台港文学研究的空缺。1985年之后,大陆的研究少些急功近利和政治浮躁,心平气和地重拾张爱玲作品中的“情欲”文化,有的则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张作品中的“自抑”性。90年代后,文学评论则从心理分析到微化分析,诸如意象、服饰、建筑、语言、结构……研究的多样化和细微化令张学在大陆刮起了一阵热风。从专业学者的文学批评到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从书报到媒体传播无一不展现张学的新生。
“张爱玲风”在大陆于90年代中期刮起,而它的出现不单单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更迎合了大众消费的市场经济,其中“出版界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安徽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台海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都出过张爱玲的图书,总数超过50种”⑧。大众的消费促使着市场的推广,市场的推广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张爱玲文学又带给现代更为深刻的商业价值和意义。文学与市场相接使得大众在接受上有了新的突破,追求文学价值已不能够满足当代受众群体和文学界人士,如何利用文学,带动经济又使经济发展文学这是时代的新命题,张学接受开创了这一领域。而在新的时代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张学的批评接受,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问题。
四、“张爱玲”研究的新使命
张爱玲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一是她的文本内容及其文化意义融通中西:二是她生活的地域经验也将中西文化相勾连,至此她成为不可泯灭的中西方文化意义的新符号。张爱玲的绝大多数作品避免了政治化和功利化,文本的现代意义与时代有共同频率的律动。在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历史地位正名后,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重新审视,更有对作家这个群体本身的反思。从创作者来说,这是张爱玲对作家作品的创作意图的自省,作家是否承担历史使命?或者说作家的存在意义何在?如同蒋方舟所说,“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作家在反映时代和自身的文化意义时还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前瞻时代发展的趋向及困境。张爱玲之所以能够不掩埋在岁月的尘埃中,是她的独立思想,并非意味着她对时代和历史的抛弃,而是在犹如自言自语的描述中反映出对人类永恒的苦难和命运的思考。张学符号的新意义不单单令作家自省,同时对文学批评界的发展也有新的趋向。
大陆同台海政治经济的交流促进着文化的新发展。尽管张学研究的初端各有不同,但是发展趋向却是渐渐走向同一。张爱玲这个有着浓厚中国文化传统意蕴的作家,将台海“两岸三地”共同的中国文化的“根”连在一起,经过微观研究如今逐渐走向了宏观的研究发展之路,从对传统的挖掘再到对张学的批评之批评,这是第三代张学研究者的共同意向。“两岸三地”人民以更为深刻同一的文化体验为华人这一族群提供特殊的审美经验⑨,跨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呈现华人的心灵史,同根、同路将共同构建华人的新文学审美理论。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30024)】
①②③⑤张羽《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3期。
②④⑦灵真《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华文文学》,1996年第1期。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⑧李俊、李虹《张爱玲文学现象解读及其当代启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⑨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