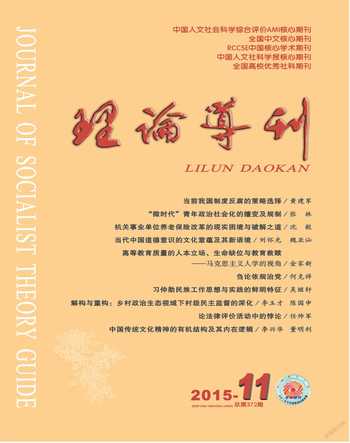美国新公共治理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15-09-10张西勇
张西勇
摘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范式由“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向“新公共治理”转变,其目的是不断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管理边界,实现三者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通过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组成的网络结构,公共事务管理者创新公共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为利益相关者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新的通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充分利用准立法程序和准司法程序,丰富拓展新公共治理实践,提升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和效能。考察美国新公共治理的实践和过程,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治理;美国;准立法治理;准司法治理;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1-0107-06
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各种系统和网络的日趋独立,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治理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弊端,以便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治理促进了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提升治理能力,除了需要行政机关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更需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督者、“消费者”——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此,只有创新多元化的治理规则和手段,畅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通道,才能广泛听取民意和集中民智,发挥集体智慧,进而提高公众满意度。而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新公共治理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新公共治理的兴起
治理的概念在许多学科领域得到探究,包括政治科学、公共行政、政策制定、规划设计、社会学等。尽管“治理”(governance)和“政府统治”(government)都崇尚目标导向活动,但二者并非同义术语。“政府统治”通常是指拥有法定的和正式的权威,并通过强制性力量来贯彻和执行政策;“治理”指的是基于公民和组织共享目标活动的创造、执行和贯彻,它们可能拥有也可能不拥有正式的权威和强制力。[4]4-5作为一种活动过程,治理寻求政策制定的权力共享,鼓励公民自治和独立,并提供公民参与公共物品提供的程序。
世纪之交,“治理”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认为,公共行政正朝向“合作理论、网络理论、治理理论、制度建构和维持理论”发展,以回应在“碎片化和脱节的”国家中,“司法权和公共管理间衰落的关系”。他强调制度主义、公共部门网络理论和治理理论与未来的公共行政研究有关,并对制度主义与公共部门网络主义进行了区分:制度主义是关于“规则、角色、标准、预期的社会建构,以约束个体和群体的选择和行为”;而公共部门网络理论是关于“相互依赖的结构”,它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联动机制,包括交换和互惠关系、公共利益、共享信念和专业展望的联系。治理理论发生在制度领域、组织或管理领域、科技或工作层面,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科层体制与程序流程,并深受行政法、委托一代理理论、交易成本分析、领导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影响。
凯特尔(Kettl)观察到,向治理转变的动力是“行政行为的扩张,行政伙伴的多元化,以及政治影响对政府外部系统的扩散”。他指出了提升谈判和协调技能的必要性:除了懂得使用科层制和权威外,行政官员还必须管理复杂的网络结构,更多地依赖人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过程,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和绩效管理技能,并增强过程的透明性。即根据谈判和协调技能建立人力资本,为公民参与提供通道,构建自下而上的公众问责机制。
网络理论清晰地表明了谈判技能的必要性。阿格拉诺夫(Agranoff)和麦奎尔(McGuire)证实了协同管理中网络结构的出现,他们将其界定为“在多元组织安排中参与和管理的过程,以处理单个组织不能或较易解决的问题”。他们对“协作”和“协同”进行了区分,尽管两者都主张一起工作来解决问题,但是“协作”还有有益性和善意的维度。可利用的协作机制非常丰富,基于组织结构和行政架构的考虑、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协作机制在处理城际关系中得以利用。并且,与协同相比,协作安排在实践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阿格拉诺夫认为,相比传统科层组织,由于网络结构更注重自我管理,其成员来自于不同的组织文化,且自愿性质较强,使得管理者在网络结构下的管理方式迥异,他们的决策过程从通过议程到付诸实施都有很大差异。但是“决策时的共享经历、充分的探讨等因素催生了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当决策产生胜利者和失利者、当出现零和博弈的情况时,会影响公众的参与和奉献。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由于共识是建立在双方协议的基础之上,因此,网络结构很少能制定核心决策”。
不同于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将治理界定为政策形成和执行的过程,萨拉蒙(Salamon)在《政府的工具:新治理导论》一书中,将治理界定为政府管理的工具和技术。新公共治理是一种架构,它承认“现代技术的协作特性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从事复杂网络管理的公私部门的行动者广泛使用的行为工具,满足不同类型公共管理所产生的需求,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者强调协作和实现而非等级和控制”。他认为,在公共管理中引入新公共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特定的技能,即谈判和说服、协作和实现,它们包括激活(activation)、流程(orchestration)、调节(modulation)。激活可以获得网络结构的参与,流程是劝说行动者进行协作,调节是提供足够的激励推动协作行为的完成。然而,工具制造者、使用者和公共管理者使用这些技能的过程并不清晰。
二、美国新公共治理的过程与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启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在这一改革的浪潮中,美国积极探索政府治理新模式,不管是公共服务社会化,还是“政府再造”,其目的是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在由“管制型”向“治理型”转变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创新公共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并通过法治程序鼓励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丰富了新公共治理的实践和过程。
1鼓励公民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新公共治理的实践。新公共管理倾向于把公民视为顾客,认为公众只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公共服务。并且,与作为整体的公众相比,个体公民直接参与治理过程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有关公众的一般理论以四个必要条件为基础:宪法;有道德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回应公众集体利益的制度和程序;仁慈和更好的公共服务。有道德的公民理解法律基础(宪法),相信美国体制的价值是天赋权利,愿意履行个体道德责任,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包括在交谈中注意忍耐和宽容。然而,尽管宪法文本并不考虑公民的直接参与,但是通过“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建立紧密联系”能够创造有智识的公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行政官员与公民之间回应与责任的双向机制”,能够提升公共事务管理的效能。
在新公共治理过程中,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日趋重要,参与的工具和方法日趋多样,公众的作用极大增强。在新公共治理过程中,行政官员的核心责任问题凸显。在治理的典型模式中,行政官员处于三权分立冲突的中心。由于代表制的缺陷,“授予公民独立话语权能够提升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改善政府的公信力和洞察力。”实际上,在政策制定、贯彻和执行方面,公共行政官员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为公民的参与提供直接的通道,其方式是通过“在官方和公众之间建立横向协作关系,寻求‘权力共享’而非‘权力控制’”。同时,公民的参与能够促进民主的健康发展,不管是作为一种手段还是目标,公民协商都将加强民主。因此,应该鼓励公民参与那些影响公众生活的决策。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治理机制,尤其是需要强化地方层面的治理,并简化公民参与的程序。因此,美国鼓励利益相关者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以此方式来倾听公众的呼声,且有利于他们履行民主义务和追求自身利益。
2探索公民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新公共治理的工具和方法。与科层组织决策相比,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组成的横向网络构成了治理的新结构。因此,必须更为关注公民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工具、方法和程序。在美国新公共治理实践中,为了提升治理的合法性,公共行政官员采取多样化的治理模式,在多个政策领域鼓励公民与利益相关者通过准立法(quasilegislative)和准司法(quasijudicial)的程序来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
(1)准立法程序在新公共治理中的运用。准立法程序包括协商民主、网络民主、公共对话、参与式预算、民事陪审团、学习小组、协同决策,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或公民之间其他形式的协商和对话。类似小组讨论、圆桌会议、市民大会、工作对话选择、协同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伙伴关系安排的情境下,也经常运用准立法新公共治理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根据涉及的公众数量、发生的公共空间、对真正协商的培养、对理性讨论的促进、政府的授权,以及实际后果等因素,来选择不同的模式。若涉及人员相对规模较小且非正式的情境,如公共对话或学习小组,可能更关注成员之间相互沟通和故事交流,以建立信任;而规模较大的公共事务治理可能会预先设定议程,并倾向于有逻辑的、理性的谈论,以建立联系和共识。这些治理过程以寻求协商作为终点,或者向政府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当然,与政策过程的联接点不同,这些组织的目标也迥异。例如,凯特琳国家事务论坛(Kettering′s National Issues Forum)模式有助于公民明晰他们的偏好,其方式是通过在小团体中对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所采取的具体行为选择进行协商。与此相反,协商民意测验能帮助胜选的决策者履行其代表功能,它可以通过代表性的样本提醒决策者:如果大众有充足的时间对某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的话,他们的政策偏好会是什么。在利用准立法过程进行协商时,参与者会考虑多元化的观点,批判性地思考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特定的情境下努力使集体决策满足公众的需求。大多数促进协商的方法需要公共空间、利益为基础的谈判、共识的建立、积极的聆听和冲突解决技巧,以成功实现协商的目标。解决冲突的技巧、实践和流程,有助于提升协商的质量,其方式是帮助参与者表达偏好和消除差异。
(2)准司法程序在新公共治理中的运用。在新公共治理中,准司法过程涵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如调解、简化程序、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团审判、实况调查、约束性或非约束性仲裁,这些程序对国际组织、国家组织和地方公共机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目的是解决存在于就业、教育、家庭、环境、法庭、刑事司法、社区环境等领域的冲突。就调解而言,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正的第三方机构,有助于冲突各方通过谈判方式达成自愿协议或解决方法。就简化程序而言,公正的第三方机构有助于利益团体之中或利益团体之间的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和协商达成一致。微型审判涉及到向争议双方的高层决策者呈现简短证据和进行辩论,然后高级决策者通过协商达成解决方案。实况调查也涉及到公正的第三方机构,它通过举行非正式的听证会,收集证据,然后根据证据做出决定。争议各方会在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判。仲裁的形式本质上和私人判决一致。所有这些过程为公民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行政机构的行为——如贯彻执行法律——提供了新的通道。
准立法过程和准司法程序共性明显,既体现在彼此之间,也体现在新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决策过程中的冲突是内在的,随着决策过程中参与者数量的增加,涉及到的职位、利益、价值和观点也在增多。在新公共治理实践中,运用准立法和准司法的程序提升了个体的话语权,授予公民和利益相关者不同于传统治理过程的权力,并聚焦利益而非权利。这些新公共治理的方法寻求吸引公民和利益相关者就利益冲突进行对话,并把公民和政策过程联接在一起,既包括政策的制定,也包括政策的执行。
准立法和准司法新公共治理过程在国际、国内、地方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贯穿于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中,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制度化的通道,为政策的制定、落实和执行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工具和重要的方法。
3通过完善法制为新公共治理提供法定框架。在《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PA)许可的范围内,美国的公共行政机构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不同的治理流程做出选择。对新公共治理的实践来说,宪法本身是静态的。然而,针对新公共治理过程的法定框架早已存在于联邦层面,并且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发展迅速。[23]
(1)联邦层面对新公共治理的法定支撑。联邦层面的法定框架有助于明晰治理过程之间的根本联系,它在特定情境下把准立法和准司法领域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在增强公众对联邦行政管理机构治理过程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方面,《行政程序法》有了重大突破,体现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行为。正式的组织行为采取规则制定和裁决的方式。在规则制定方面,行政管理机构制定适用于将来的总体规则。规则制定一般需要发布公告,并且需要公众进行评议。[24]在裁决层面,通过对证据和事实的回顾性检查,行政管理机构确定个体的权利。根据《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管理机构在依据正当性程序做出裁决前,要举行裁决听证会,如公告、盘问证人、呈现证据和辩论、接收书面判决理由等。非正式组织行为、规则制定和裁决在整个政策系统中规范了行政管理机构的行为,贯穿于政策制定、落实和执行的整个过程。行政管理机构的行为与政策系统的联系使得这些过程彼此联接,并和治理联接在一起。
《行政程序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民和利益相关者与行政管理机构在治理过程中的关系。公众的需求使政府的工作更加透明,通过规则制定中的政府公告和评议,公民能够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声音;通过判决,能够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免受政府的干扰和侵害。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并确保能够被行政管理机构所听到。然而,这些传统的治理过程也限制了个体、组织和群体参与的程度。如行政管理机构可能在已经对政策建议做出基本决定之后,才有选择性地举行听证会。[25]另外,行政判决可能会限制证人证词的内容,其原因是他们说的某些话不能被当作证据被采信。[26]
相对较近的《行政程序法》修正案在相当程度上扩展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机会。美国国会对《行政程序法》通过了两个修正案,并在1996年使其永久化,即《1996年协商制定规则法》(the 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 of 1996, NRA)和《1996年行政争议解决法》(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6, ADRA)。自从国会通过这两个法规后,联邦政府采用新公共治理程序的行为大幅度增长。[27]
“准立法(quasilegislative)”过程为行政管理机构的运行确立了标准、指标、预期,或者说规则和规制。[23]《协商规则制定法(NRA)》规定了在准立法新公共治理过程中对监管式谈判的应用。它要求行政管理机构要召开一个由25名或较少的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小组,对提议的草案规则、后续的公告和评论文本进行谈判。[28]然而,当授权行政管理机构使用备选争议解决方案时,《行政争议解决法(ADRA)》也考虑使用准立法过程。环境治理领域更多地使用准立法新公共治理过程,如在制定、落实和强制执行环境政策的过程中使用利益调解、简化程序、建立共识、协同决策等方式。[29]
准司法(quasijudicial)过程通常指回顾性的、客观的机构行为,它涉及到特定的公民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或义务,其范围囊括非正式的裁决方式和正式的裁决方式。非正式裁决的方式主要指学校教育对学生行为规则的塑造,而正式裁决则是《行政程序法》所鼓励的、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清晰规定的十项法定诉讼程序,包括公告、证据呈现权、对质和对证人的盘问、口头辩论、书面决定等。《行政争议解决法(ADRA)》规定,准司法新公共治理过程包括调解、程序简化、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团审判、实况调查、约束性或非约束性仲裁。[30]
几乎在所有公共决策、政策制定、贯彻落实、强制执行的过程中,都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通过消除利益集团的冲突以实现一致,这些新公共治理过程在多元化甚至相互竞争的参与者之间提供了协调和合作机制。其结果是,这些程序增强达成稳定共识的可能性,并且有助于增强参与者的公平感、公正感,以及制度的合法性。
(2)州和地方层面支撑新公共治理的法定框架。然而,由于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行政程序架构,因此类似于联邦层面《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创新并没有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出现。尽管州级行政程序法模式(the Model 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MSAPA)并没有出现在行政程序法和协商决策制定中,然而,州政府实际上已经采用了这些程序,行政官员也获得隐性授权来使用这些程序。另外,多数州政府已经采用州级行政程序模式,它们对一般案件进行非正式的解决和处理,允许行政机构成立咨询委员会,要求行政机构采用对公众有利的非正式规则。[31]所有这些规定为行政机关提供了非正式的、一致导向的过程,这些过程都具有新公共治理的特征。
由于明示权限的缺失,作为一种私人判决的形式,约束性仲裁会导致行政机构针对私人决策者的管制权力面临违宪授权的问题。然而,一般而言,其他有关新公共治理程序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对治理程序和约束性结果都预先达成了协议。另外,新的《统一调解法》(Uniform Mediation Act)在第二章第六节为政府使用调节方法提供了明确规定,许多州(如伊利诺斯州)已经开始采用这种统一法案。
要么根据《州行政程序法修正案》,要么通过行政命令(如马萨诸塞州),许多州都授权州行政管理机构使用新公共治理过程。有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和协商决策(negotiated rulemaking)的州立法范围广泛,既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也包括概要性的和具体的。例如,新墨西哥州只是笼统地要求行政机构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而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却通过了类似于联邦行政争议解决法(ADRA)和协商制定规则法(NRA)的法案。更为常见的是把一般性的授权作为《州行政程序法》的一部分。如印第安纳州授权州行政管理机关利用调解的方法,其条件是调解员必须像州级高等法院的调解员一样接受过专门的训练。总之,在州级层面,授权和鼓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新公共治理中使用准立法和准司法方式的过程增长迅速。
三、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进行“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作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并提出“加大社会治理创新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以便更有效地消除国家治理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32]在此背景下,美国新公共治理的过程与实践对促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尽快实现由“管制”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变。“传统政府管理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公共服务的政府垄断、集中管理和政府机构的直接生产等制度安排,更源于这一模式所衍生的思维定势和政治气候。”[33]在此背景下,政府的改革就是破除政府万能的神话,打破政府垄断性直接生产是唯一最佳模式的观念,为市场化改革破除思想藩篱,开拓发展空间。“市场化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展示了公共管理的新愿景,‘市场式政府’被视为未来政府治理的系统战略和可行模式之一。”[34]就美国而言,自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一直比较活跃,从公共服务社会化到政府再造,美国政府一直在探索政府治理新模式,构建合作共赢的公私伙伴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便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政府从其管不好、管不了的市场领域、社会领域逐渐退出的过程,通过明确界定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的权力边界,建构三者之间良性的互动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理理念不断得到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35]这意味着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职能根本有效转移,实现“管制”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变,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新型关系。“治理”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参与,结成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形成一个上下互动、双向度或者是多维度的管理过程,以实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2以创新制度安排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36]作为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集合,制度能通过对违规的惩戒来形塑人们的行为习惯,它“意味着权威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4]9因此,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的力量,它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路径。在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后,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必然。“在最近三十多年里,国家的权力和权威经历了重大的重新改造,治理已成为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多边的过程。为了实现意愿中的国内政治目标,推行重大的政策纲领,解决国内危机,政府越来越需要坐到谈判桌上,与公共的或私人的、国内的或国外的各种组织进行磋商。”[37]然而,尽管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但在日常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格局中,政府依然是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替代的最大的权威组织。而且,其他社会力量能够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必须是在政府提供的制度性许可的前提之下,它们不可能在多元化实践格局中摆脱国家或政府的引导、协调和规制或其他管理方式。换言之,当今公共事务治理的多元格局只是一种次格局,是政府治理格局的延伸,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新模式、新面貌、新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积极行使“规则制定者”的功能,发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应能力,通过制度安排为新公共治理提供法定框架,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通过修改《行政程序法》,制定《协商制定规则法》和《行政争议解决法》,在制度上提供了治理机制,规范了行政官员依法行政的程序,畅通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丰富了新公共治理的形式和方法,促进了新公共治理实践的发展。
3探索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方法。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生活、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对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一方面,信息技术进步和新传媒的发展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技术化基础,使公民获得公共事务治理和管理绩效信息的渠道更为便利和畅通。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与非营利组织的活跃成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组织基础。“第三部门的兴起使得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选择日趋多样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各类非营利组织,进入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并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承担一部分共同产出公共服务的责任。”面对公民需求多样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政府应主动求变,积极创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渠道和方法。其实,在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化的治理工具,根据政府治理目标设计来选择治理工具,是一种有目的的思考过程。“确定哪些治理工具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质上也是一种公共决策和制度变革。”[39]美国采用准立法和准司法的新公共治理过程,吸引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方式值得借鉴,这些方式包括在法定框架内使用谈判、调解、简化程序、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协商、合作以及建立共识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35]这就要求,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创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方式和方法,而且还要提升行政官员治理技能,包括召集会议、评估冲突、谈判、积极倾听、重构组织、简化程序,以及建立共识。“公共管理者应该通过支撑新公共治理过程的法定框架,为更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便利条件,以协调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主体的利益。”
[JY][XCL.TIF]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KG-*8]∶[KG-*2]7.[ZK)]
[2]沈荣华, 周义程.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J].理论探讨,2003,(5).[ZK)]
[3]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告[EB/0L].http:// www. people. com. cn / n / 2015 / 0305 / c34740726643598. html, 20150305.[ZK)]
[4][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张胜军,刘小林,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ZK)]
[5]Jun, J. S. 2002. New Governance in Civil Society Changing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Rethinking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Century, edited by Jong S. Jun, 289–307. Westport, CT: Praeger.[ZK)]
[6]Frederickson, H. George. 1999. The Repositioning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2(4): 702-705.[ZK)]
[7]Kettl, Donald 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ZK)]
[8]Agranoff, Robert, and Michael McGuire. 2003.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New Strateg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ZK)]
[9]Agranoff, Robert. 2003. Leveraging Networks: A Guide for Public Managers Working Across Organizations. Arlington, VA: IBM Endowment for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ZK)]
[10]Salamon, Lester, ed. 2002.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ZK)]
[11]Frederickson, H. George. 1991. Toward a Theory of the Public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22(4): 395–417.[ZK)]
[12]Stivers, Camilla. 1991. Some Tensions in the Notion of “The Public as Citizen”: Rejoinder to Frederickson.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22(4): 418–23.[ZK)]
[13]Wamsley, Gary L., Charles T. Goodsell, John A. Rohr, Camilla M. Stivers, Orion F. White, and James F. Wolf. 1990.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 In Refou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ited by Gary L. Wamsley, Robert N. Bacher, Charles T. Goodsell, Philip S. Kronenberg, John A. Rohr, Camilla M. Stivers, Orion F. White, and James F. Wolf, 31–51.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ZK)]
[14]Cooper, Terry L. 1984. Citizen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4(2): 143–49.[ZK)]
[15]Bingham, Lisa Blomgren, Tina Nabatchi, and Rosemary O’ Leary. 2005. The New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Process for Stakeholder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of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5): 547558.[ZK)]
[16]Fung, Archon. 2003a. Survey Article: Recipes for Public Spheres: Eight Institutional Design Choi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1(3): 338–67.[ZK)]
[17]Ryfe, David Michael. 2002.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Study of 16 Deliberative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3): 259–377.[ZK)]
[18]McAfee, Noelle. 2004. Three Models of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1): 4459.[ZK)]
[19][JP2]Ackerman, Bruce, and James Fishkin. 2004.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JP][ZK)]
[20]Moore, Christopher W. 2003. The Mediation Process: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Conflict. 3r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1]Schwarz, Roger. 2002. The Skilled Facilitator: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Consultants, Facilitators, Managers, Trainers, and Coach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ZK)]
[22]Bingham, Lisa B. 1997.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andbook of Public Law and Administration, edited by Phillip J. Cooper and Chester A. Newland 546–6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ZK)]
[23][JP2]Rosenbloom, David H. 2003. Administrative Law for Public Manager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JP][ZK)]
[24][JP2]Kerwin, Cornelius M.. 1999. Rulemaking: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Write Law and Make Policy. 2nd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JP][ZK)]
[25][JP2]Thomas, John Clayton. 1995.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New 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Public Manager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JP][ZK)]
[26]Cooper, Phillip J. 2000. Publi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3rd ed. Itasca, IL: F. E. Peacock.[ZK)]
[27]Senger, Jeffrey M. 2003. Federal Dispute Resolution: Using AD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ZK)]
[28]Kerwin, Cornelius M. 1997. Negotiated Rulemaking. In The Handbook of Publi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ited by Phillip J. Cooper and Chester A. Newland, 225–3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ZK)]
[29]Durant, Robert F., Daniel J. Fiorino, and Rosemary O’Leary, eds. 2004.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considered: Challenges, choices, Choices, and Opportun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ZK)]
[30]Bingham, Lisa B., and Charles R. Wise. 1996.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0: How Do We Evaluate Its Succes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6(3): 383–414.[ZK)]
[31]Carter, Lief, and Harrington, Christine. 1999.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ZK)]
[32]黄杰,朱正威.国家治理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义、实践和走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5,(4).[ZK)]
[33][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KG-*8]∶[KG-*2]38.[ZK)]
[34][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和私人市场[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KG-*8]∶[KG-*2]5.[ZK)]
[3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0L].http:// www. sn. xinhuanet. com / 201311/ 16/ c_118166672. htm. 20131116.[ZK)]
[36][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KG-*8]∶[KG-*2]3.[ZK)]
[37][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曹荣湘,龙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KG-*8]∶[KG-*2]12.[ZK)]
[38][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孙柏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KG-*8]∶[KG-*2]3.[ZK)]
[39]唐娟.政府治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KG-*8]∶[KG-*2]33.[ZK)]
【责任编辑: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