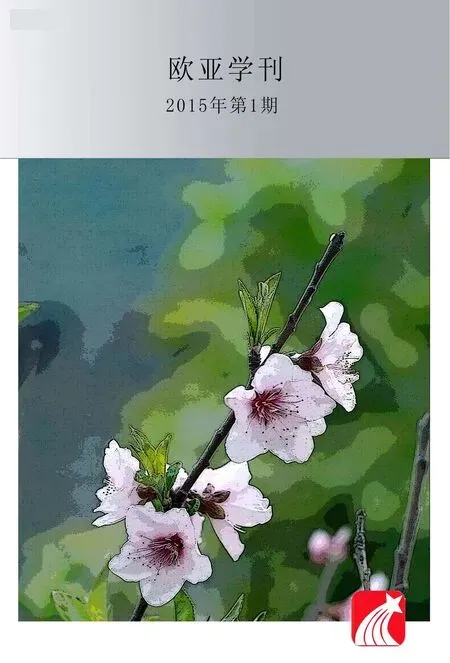寄多羅貴霜的若干問題
2015-09-04余太山
余太山
寄多羅貴霜的若干問題
余太山
一般認爲,《魏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國王“寄多羅”,應即中亞錢銘所見Kidāra Kushāna Shā[hi],茲就有關問題略述己見。
一
在各種有關寄多羅貴霜的記載中,漢文史料無疑最應受到重視。這就是《魏書·西域傳·大月氏條》: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
和《魏書·西域傳·小月氏條》: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這是僅存的記載寄多羅貴霜較有系統的文獻資料。
如所週知,魏收原著《魏書·西域傳》已於唐宋間亡軼。今天看到的《魏書·西域傳》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劉恕等人在整理殘缺的《魏書》時,取《北史·西域傳》補入的。而由於《北史·西域傳》除主要依據《魏書·西域傳》外,還摻雜了《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的內容,近人對考定《魏書·西域傳》原文下了不少工夫。但對於其中“大月氏條”和“小月氏條”,一般認爲均係魏收原文。
通過對上引傳文的研究,關於寄多羅貴霜,大致可以得到以下認識[1]:
1. 寄多羅政權被稱爲“月氏國”,表明寄多羅係貴霜王族之裔。蓋中國史籍一貫將貴霜王朝稱爲“月氏”。
2.傳文並未明言寄多羅王就是該政權之創始人,只知道《魏書·西域傳》所述“大月氏國”的全部事情均發生於寄多羅王在位期間。可以說,寄多羅王的活動構成了“大月氏國”的歷史。
3. 寄多羅王所都“盧監氏城”(或衍“盧”字),應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國都城“藍市”、《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都城“監氏”,亦即吐火羅斯坦首府Bactra。
4. 傳文稱寄多羅月氏國“北與蠕蠕接”。蠕蠕即柔然,早在其可汗社崙在位時(402-410),就有可能越過葱嶺,侵犯吐火羅斯坦。立國該地的寄多羅政權“數爲所侵”應是事實,但未必因此遷都。傳文所謂“西徙都薄羅城”也許是誤傳。“薄羅”,一說乃Bactra的又一譯稱。[2]
5. 寄多羅王立國吐火羅斯坦後,雖屢遭柔然侵擾,仍率兵南征,越過“大山”(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按之《魏書·西域傳》,“乾陁羅以北五國”應指渴槃陁之南五國:鉢和、波知、賒彌、烏萇和乾陁羅。
6. 寄多羅月氏國將版圖擴大至興都庫什山之南,卻不敵自北方入侵之“匈奴”,其王寄多羅因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而西徙。“匈奴”應即新興的遊牧部族嚈噠。
7. 寄多羅王西徙時,命其子留守北天竺的領土,即“乾陁羅以北五國”。《魏書》編者按照前史慣例將西遷寄多羅王所率部衆稱爲“大月氏”,將留守故土者稱爲“小月氏”。
8. 傳文描述寄多羅月氏風俗稱:“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中僅“以金銀錢爲貨”一句可以認爲是寄多羅月氏國的實際情況。“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云云,無非抄襲前史關於大小月氏的記載。而“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無非是因寄多羅王“西徙”聯想所致。
9.《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貴霜人全部活動年代之下限是437年。蓋有關記述主要依據北魏世祖太延年間董琬、高明關於西域的報告,而董、高西使歸國的年代是太延三年(437)十一月。換言之,截止這一年,不僅寄多羅王業已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很可能已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魏書·西域傳》可能包括董、高西使之後的資料,關於大小月氏的情報不應例外,但如果考慮到嚈噠西徙吐火羅斯坦的年代不遲於5世紀30年代末,則董、高報告中已含有關於寄多羅王西徙的信息也是可能的。
二
除中國史籍外,可注意者還有亞美尼亞史家埃里塞(Elišē)的記錄。據載:薩珊波斯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457年在位)卽位伊始,其祭師曾對這位國王說:
動員軍隊,召集士兵,去進攻貴霜人的國家,帶領全體人民居住到諸門那邊去吧!當他們完全屈服,遠方不友好的國家也被封鎖住的時候,您的計劃和期望就能實現了。您要統治貴霜人的帝國,正如我們要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宗教一樣,希臘人也不敢反抗您的力量。[3]
伊嗣俟二世接受了祭師的建議,對他的軍隊和盟國發出了動員令:
我們决定遠征東方,再次平定貴霜人的國家,願神保佑我們![你們]接到命令,就立卽徵集騎兵,隨我來阿巴爾(APar)州![4]
於是,“他突然侵入了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國家。戰鬬持續了二年,卻未能征服他們”[5]。上述事件發生在伊嗣俟二世卽位第一至四年(438-441)之間。[6]
對埃里塞上述記載,笔者理解如下:
1. 雖然沒有提及“寄多羅”,但這裏的“貴霜人”必定和《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月氏有關。
一則,如前所述,中國史籍一貫將貴霜稱爲“月氏國”。這“月氏國”便是埃里塞所謂“貴霜人的國家”。儘管其時吐火羅斯坦業已被嚈噠人佔領,但在伊嗣俟二世心目中,那裏還是貴霜人的領土。
二則,《魏書·西域傳》沒有交代被“匈奴”即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的大月氏國寄多羅王的下落,通過埃里塞的記載,我們才得以獲悉,西徙的寄多羅王西向衝擊了薩珊波斯的東部邊疆。埃里塞的記載和《魏書·西域傳》的記載在時間上是相銜接的。436/437年是寄多羅被逐西徙年代之下限,其明年伊嗣俟二世即位。
2. 埃里塞將“貴霜”與“匈人”聯稱,結合《魏書·西域傳》的記載似可得到確解。
一則,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的寄多羅貴霜人,很可能衝擊薩珊波斯的東境,剛剛登基的伊嗣俟二世纔不得不起而迎戰,爲根治邊患而試圖“平定貴霜人的國家”。東西兩種記載時間上的銜接證明了這一點。
二則,從伊嗣俟二世試圖“平定貴霜人的國家”來看,他戰勝了犯境的“貴霜人”。這似乎表明“貴霜人”的力量並不強大,並未蓄意侵略波斯。他們祇是西徙的寄多羅貴霜餘衆。
三則,伊嗣俟二世爲“統治貴霜人的帝國”,而侵入“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國家”。這表明波斯人的國王意圖統治的是原貴霜之領土,遭遇的卻是已經逐走寄多羅王、佔有吐火羅斯坦的“匈奴”。新興的“匈奴”即嚈噠人力量自然不是潰敗的寄多羅貴霜可比,因此,伊嗣俟二世入侵吐火羅斯坦的“戰鬬持續了二年”,未能奏功。
伊嗣俟二世最初遭遇者不僅僅是西徙的寄多羅貴霜餘衆,還有接踵而至的嚈噠人。波斯人或亞美尼亞人無從正確區分,產生了概念的混亂。“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客觀上就是來自貴霜領土之匈人或征服了貴霜之匈人。
3. 結合《魏書·西域傳》和埃里塞的記載,可以知道這些“貴霜人”均被伊嗣俟二世視爲敵人,其故土吐火羅斯坦也是伊嗣俟二世打算平定的地方。這似乎表明這些寄多羅月氏或“貴霜人”不可能是所謂貴霜—薩珊人。
三
除埃里塞外,拜占庭史家普里斯庫斯的有關記載也值得重視。這位史家多次提到波斯人與“Kidara匈人”()之間的戰爭(33,41,47,51)。[7]其中最詳細且可供討論的是第41章第3節的有關記載:465年,當拜占庭皇帝Leo一世(457-474年在位)的使者constantius抵達波斯時,波斯王卑路斯正駐蹕在與“寄多羅匈人鄰接的邊境上”。
戰爭隨之爆發,戰爭的原因是Huns收不到波斯人和帕提亞統治者此前一直繳納的貢金。這位君主的父親拒絕納貢,選擇了戰爭,其子連同王國一起繼承了戰爭。結果波斯人被這場戰爭拖垮,企圖用欺詐的手段結束與匈人的鬭爭。於是卑路斯(Perozes,當時波斯君主的名字)派人去見Huns的首領Kunchas,表示樂意言和,並希望締結盟約,將其姊妹許配給他,因爲他恰好非常年輕,還沒有生兒育女。可是,可汗接受了這些建議時,卻沒有娶到卑路斯的姊妹,娶到的是波斯國王派去的一個僞裝成公主的女人。卑路斯對她說:祇要她不揭穿這一詭計,就能享有王室的身份和優裕的生活,如果說出這一欺詐行爲,就會被處死,因爲Kidara人的統治者不會容忍娶一個婢女而不是一位貴族婦女爲妻。和約按照這些條件簽訂,卑路斯不久就從他對Huns統治者的背叛中得到了報應。由於該婦人害怕Huns統治者有一天會通過他人獲悉她的真實身份,處她以極刑,從而揭穿了欺詐行爲。Kunchas稱讚了她的誠實,繼續讓她做他的妻子。但爲了懲罰卑路斯使詐,他藉口與鄰邦交戰需要指揮戰事的將軍,而不是士兵(因爲他的士兵爲數衆多)。卑路斯派出了三百名一流的軍官。Kidara人的統治者殺死了其中若干人,而使其餘人致殘後返回卑路斯處,告訴卑路斯這就是他的背叛應得的懲罰。於是兩國間戰火重燃,戰況激烈。因此,卑路斯在Gorga亦卽波斯人駐軍的地點接見了constantinus……在這一節中,與卑路斯敵對的一方被稱爲“寄多羅匈人”,有時也稱爲“Kidara人的統治者”或“匈人的統治者”。對此,我的理解如下:
普里斯庫斯記載的Kidara這一名稱無疑可與見諸《魏書·西域傳》的“寄多羅”勘同。如果這裏Kidara便是《魏書·西域傳》的寄多羅王,那么說明這位貴霜王自437年前後西徙,直至457年卑路斯登基至少20年內一直在與薩珊波斯作鬥爭。而依據普里斯庫斯的記載,可以推測寄多羅王業已役屬“匈奴”,充當馬前卒,或和“匈人”結成某種形式的聯盟,與薩珊波斯進行了飜覆的鬬爭。不過,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
另一種可能性是:西徙的寄多羅王不久便在和薩珊波斯的鬬爭中,或者在同追逐他的“匈人”的鬬爭中陣亡。其部衆亦爲“匈人”或波斯人消滅。薩珊波斯因而面對“匈人”即嚈噠人的入侵,且因無法戰勝後者一度納貢求和,直至卑路斯即位後才重開戰端。準此,普里斯庫斯所謂“Kidara人的統治者”乃指統治Kidara人的“匈人”,而不是指寄多羅王本人。
目前,笔者比較傾向於後一種可能性,不過前一種可能性似乎也無法完全排除。但是,薩珊波斯國王卑路斯所面對的“寄多羅”似乎有別於伊嗣俟二世所遭遇的“貴霜”。不管寄多羅王與“匈人”的關係怎樣,卑路斯的主要敵人無疑是“匈人”,亦即新興的嚈噠人。其人早在5世紀30年代末就渡阿姆河南下,到卑路斯登上波斯王位時,無疑已經鞏固了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
普里斯庫斯提到一位“匈人的首領”名Kunchas,希臘原文爲Koύγχας,早已有人指出其實不是人名,而是Qun-Xan之訛傳。[8]這Qun-Xan顯然便是Hun-Xan,可譯爲“匈可汗”。貴霜或寄多羅貴霜人均不採用“可汗”這一尊號,這也表明這位首領是一位嚈噠可汗。[9]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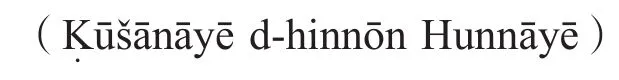
今案:卑路斯與之作戰的“貴霜匈奴”,無疑就是普里斯庫斯所謂的“Kidara人的統治者”。結合同爲拜占庭史家普洛科庇烏斯[11]的記載,可以進一步搞清楚這一名稱的內涵。蓋普洛科庇烏斯有與上引《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平行的記述如下:
後來,波斯國王卑路斯(Perozes)捲入了一場與嚈噠匈人──他們被稱爲白匈人──爭奪邊境的戰爭。他集結了一支威風凜凜的軍隊,進擊嚈噠。嚈噠人是名副其實的匈人血統,可是與已知的任何匈人不同。他們的領土旣不與其他匈人的鄰接,也不靠近,而是緊貼波斯的北境。而在波斯國界的對面,坐落着一座嚈噠人的城市Gorgo,該城因而成爲雙方頻繁的邊境衝突的中心……
由於嚈噠匈人佯敗,誘敵深入,波斯軍陷入重圍。卑路斯不得已與嚈噠匈人議和。(I, iii)
此後不久,他因急於向匈人報仇雪恥,不顧自己曾立下的誓約,迅速在波斯全境及其盟國徵兵,率之進攻嚈噠。
結果因再度中計而全軍覆沒,卑路斯陣亡。“從此,波斯就成了嚈噠的屬國,向嚈噠進貢,直到居和多(cabades)鞏固了他的政權,認爲無需再向嚈噠人繳納年貢時爲止。”(I, iv)普里斯庫斯的“Kidara人的統治者”和《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的“貴霜匈奴”在普洛科庇烏斯這裏成了“嚈噠匈人”。
又,《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提及:
居和多敗行枉法,波斯顯貴陰謀弑君。居和多獲悉,棄國逃往匈奴國,投奔匈奴王。他曾爲質子,成長於該國王庭。其弟ZāmāshP遂取代他統治波斯。居和多本人則在匈奴中娶其姊妹之女爲妻。其姊妹在其父喪生的那場戰爭中被俘去,因係公主,成了匈奴王之妻,匈奴王和她生有一女。居和多來奔,她就將此女許配居和多。因當了駙馬,居和多受到鼓勵,日日哭泣於匈奴王前,懇求軍援以誅叛復辟。匈奴王允其所請,給予大軍。當他踏上波斯國土時,其兄弟已聞風而逃,於是他如願以償,誅殺叛臣。(XXIII-XXIV)
普洛科庇烏斯的平行記述如下:“居和多偕同Seoses一起逃跑,居然未被看破行藏,最後投奔了嚈噠匈人(EPhthalitae Huns)。嚈噠國王將其女許配居和多。既爲駙馬,居和多遂率大軍討伐波斯,波斯人不願迎擊,迅速潰散”。居和多終於復辟。(I, vi)
要之,只要將《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書中有關“貴霜匈奴”或“匈奴”的記載和普洛科庇烏斯的相關記載進行對照,就不難發現上引埃里塞的也被稱爲貴霜人的匈人或普里斯庫斯的“Kidara人的統治者”均爲嚈噠人。
五
以上涉及的諸多事件中,比較明確的年代只有一個:437年。正是在這一年,董琬、高明西使歸國復命。這一年因而亦成爲《魏書·西域傳》記述的大、小月氏國事情發生時代之下限。換言之,正是在這一年或之前不久,寄多羅王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因而薩珊波斯王伊嗣俟二世即位伊始便不得不發動對“貴霜人”的戰爭,蓋西徙者不免衝擊薩珊波斯東境。不用說,“匈奴”即嚈噠人也就是在這一年佔領吐火羅斯坦的。
寄多羅王西徙時,令其子守富樓沙城(Purus·aPura),亦即乾陀羅。中國史籍稱這個偏安於都庫什山以南的貴霜政權爲“小月氏”,其存續時間較長。蓋《魏書》本紀有載:
太安五年(459)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高宗紀)
和平元年(460)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高宗紀)
太和元年(477)九月,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高祖紀上)
“居常”得視爲Kushan之對譯,而“車多羅”得視爲Kidara之對譯。或據以爲遲至477年這一政權依然存在[12]。或以爲上述資料表明嚈噠人勢力越過興都庫什山的時間不可能早於477年。
今案:嚈噠人入侵印度次大陸的時間另當別論[13],僅憑寄多羅後裔朝魏的記載就推斷這一年代則過於草率,因爲嚈噠人征服一個地區后未必消滅當地的統治者。有證據表明,嚈噠人慣於利用原有的政權統治征服地區,只要這些政權表示臣服,向嚈噠人納貢就行。換言之,不能排除在嚈噠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之後,乾陀羅的寄多羅貴霜政權在朝貢北魏的同時,也朝貢嚈噠的可能性。
《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紀》載雲等於正光元年(520)訪問乾陀羅時,發現該地已爲嚈噠所統,且“治國已來,已經二世”。這說明嚈噠勢力進入乾陀羅最早應在5世紀五六十年代,477年或者可以視爲嚈噠人直接統治該處年代之上限:
正始四年(507)十二月丁丑,“鉢崙……乾達諸國遣使朝貢”。(《魏書·世宗紀》)
永平四年(511)六月乙亥,“乾達……達舍……不流沙諸國並遣使朝獻”。(《魏書·世宗紀》)
十月丁丑,“……烏萇……乾達等諸國並使朝獻”。(《魏書·世宗紀》)
“乾達”應該就是《魏書·西域傳》所見乾陀國,在《魏書·本紀》所載乾達朝魏之年很可能已役屬嚈噠。《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紀》又載:
至正光元年(520)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噠所滅,遂立勅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持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鬭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噠”即“嚈噠”。《魏書·西域傳》有類似記載:
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鬭,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鬭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一說“業波羅”可能指“寄多羅”。[14]今案: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乾陀羅如此,曾爲寄多羅征服的乾陀羅以北諸國很可能在差不多同時落入嚈噠的勢力範圍。各處殘餘的寄多羅貴霜人應該有大致相同的遭遇,不是爲嚈噠所滅便是淪爲附庸。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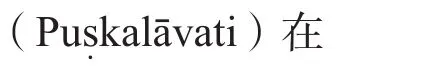
今案:此說成立與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鳩摩羅什所用“小月氏”這一概念。笔者認爲鳩摩羅什如此指稱至少有以下兩種可能性:
1. 鳩摩羅什稱“兜呿羅”(即吐火羅斯坦)爲“小月氏”是因爲在他的時代,領有吐火羅斯坦的是寄多羅貴霜人,而貴霜一直被稱爲“月氏”。寄多羅人既是貴霜之裔,被鳩摩羅什稱爲“月氏”毫不奇怪。至於著一“小”字,可能是爲了區別於此前的“大月氏”,亦卽曾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的大貴霜國。至於同一個鳩摩羅什又稱乾陀羅、Swāt河源頭爲“大月氏國”,則可能是因爲該地長期以來是貴霜王朝的最繁榮的地區,在某種意義上足以代表大貴霜國的緣故。
2. 如果考慮到中國史籍習慣上將被迫遷離故土、另謀發展的月氏大部稱爲“大月氏”,而將留守原地的月氏餘衆稱爲“小月氏”,鳩摩羅什亦遵循這一慣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則似乎上述指稱還可另作解釋:興起於吐火羅斯坦、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的貴霜政權,因故(如受薩珊波斯壓迫)不得不放棄吐火羅斯坦,南徙於乾陀羅一帶,是爲鳩摩羅什所謂“大月氏國”,而留在吐火羅斯坦之餘衆,則被鳩摩羅什稱爲“小月氏”。如果其時寄多羅王已經崛起,在鳩摩羅什心目中亦屬於“小月氏”之列。
《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王崛起於大部南遷後留在吐火羅斯坦的貴霜餘衆之中,本應屬於鳩摩羅什所謂“小月氏”範疇。但是,該王於吐火羅斯坦復國後,又興兵南下,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原貴霜之領土(乾陀羅以北五國),復因被“匈奴”所逐,不得不放棄吐火羅斯坦西徙,而使其子留守興都庫什山南之領土。因此,《魏書·西域傳》將該王所率西徙之貴霜人稱爲“大月氏”,將留守故土(乾陀羅一帶亦寄多羅月氏領土)者爲“小月氏”。
應強調指出的是,如果遵循上述中國史籍的慣例,鳩摩羅什不可能將勝利的進軍者稱爲“大月氏”,祇能將放棄吐火羅斯坦、南遷乾陀羅的貴霜人稱爲“大月氏”。同理,《魏書·西域傳》將寄多羅王之月氏國稱爲大月氏,祇能是因爲他被“匈奴”所逐西徙,而不是因爲他率月氏主力入侵西北印度。前一種情況纔與公元前177/前176年月氏大衆被匈奴逐出祁連、敦煌間故地西徙大夏可以類比。事實上,寄多羅王在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後必定回師吐火羅斯坦。這與月氏放棄敦煌、祁連間故地西徙和寄多羅王放棄吐火羅斯坦西徙大異其趣。
此外,鳩摩羅什在他所譯《馬鳴菩薩傳》中,稱馬鳴的保護者迦膩色迦王爲“北天竺小月氏國王”(或“月氏王”):
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經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有所求,當相給與,何足苦困人民久住此耶?答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舉此一國,無一億金,如何三億而可得耶?答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之,不能捨也。於是比丘爲王說法。其辭曰:夫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淵弘,義存兼救。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爲上。世教多難,故王化一國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爲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遠近,宜存遠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其言,即以與之月氏王,便還本國。[20]證之《大智度論》“北天竺月氏國”這一稱呼,所謂“北天竺小月氏王”很可能衍“小”字。此“北天竺小月氏王”在《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徑作“月支國王”[21],似可佐證。
不管怎樣,在鳩摩羅什迻譯《大智度論》的年代,或者說最晚到鳩摩羅什去世之年(413),《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王可能已崛起於吐火羅斯坦,但似乎尚未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
七
一說寄多羅人曾統治過克什米爾地區,有文獻和錢幣兩方面的證據。[22]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中國文獻的證據似乎表明寄多羅人並未統治克什米爾。《魏書·西域傳》並舉“大月氏國”、“小月氏國”與“罽賓國”,隻字未及月氏與罽賓之關係。
二則,據《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行紀》,乾陀羅之嚈噠王“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未能降服之。雖然按之年代,不妨將這位嚈噠王比定爲Mihirakula,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王此時的對手是寄多羅人。
三則,退一步說,即使嚈噠人是繼寄多羅人之後統治克什米爾的,其人也毫無必要通過摹倣後者之錢幣表示其合法性。或者說,嚈噠錢幣和寄多羅人的錢幣類似未必表明寄多羅人曾先於嚈噠人統治克什米爾。克什米爾的嚈噠人很可能摹倣其他地區的寄多羅人的錢幣,其目的也許僅僅是爲了便於流通。


要之,無論文獻和錢幣都沒有提供寄多羅人曾統治克什米爾的證據。因此,說者在此基礎上就其年代所作推論毋須再作探討。事實上,說者有關年代的推算也經不起推敲:作爲主要環節的迦膩色迦年代衆說紛紜,而克什米爾諸王治期之平均數亦無從確指,其結論自難令人信服。
八
本節之討論有關寄多羅人崛起和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之年代。
(一)法顯記弗樓沙國事情有云:
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餝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27]
說者指此處“月氏王”爲《魏書·西域傳》所傳寄多羅王。“大興兵衆”云云,即該王“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事。[28]不僅如此,若就佛鉢來源推敲之,其說似得以增強。蓋法顯又載:
法顯在此國(揵陀衛),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
據此,佛鉢本在毗舍離即中天竺,而據前引《馬鳴菩薩傳》,經“北天竺小月氏國王”強索,佛鉢乃自中天竺來到揵陀衛,與法顯所述,若合符契。
果然,則在法顯遊歷乾陀羅(402)之前,寄多羅王已南侵北天竺、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而“欲取佛鉢”歸吐火羅斯坦也。
遺憾的是此說若干處似欠妥帖:
1. 誠如說者所言,《法顯傳》有云:“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其時間無論下距法顯啓程之年弘始二年(399)、遊歷乾陀羅之年,抑或《法顯傳》脫稿之年義熙十年(414)[29],充其量二三十年,似可據以類推“昔月氏王”欲取佛鉢事去法顯西行之年亦不致太遠。但查《法顯傳》全書,冠以“昔”字之人事年代久遠者佔絕對多數。換言之,法顯於“月氏王”前著一“昔”字,暗示其年代久遠之可能性不能排除。
2. “北天竺小月氏國王”強索佛鉢事亦見《付法藏因緣傳》卷五:
月支國王威德熾盛,名曰栴檀罽昵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伐,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華氏城)。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持用奉獻罽昵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德如來所持,雞有慈心不飲蟲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爲納受之。即迴兵衆,還歸本國。[30]
蓋一般認爲罽昵吒即《馬鳴菩薩傳》所載小月氏國王。據此,佛鉢本在華氏城,非毗舍離,與法顯所聞天竺道人之言亦不一致。
3. “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云云,結合“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之類說法,神話色彩鮮明,傳說意味濃厚。很難相信法顯在這裏描述的是發生在十多年前的一幕。
4. 客觀上,並不是祇有寄多羅王一人纔有可能興兵伐弗樓沙國。因而歷來對法顯上述記錄有多種解讀,或指“月氏王”爲貴霜諸王之一,丘就卻或迦膩色迦等[31];或指爲貴霜崛起前之大月氏王[32]。諸說難分優劣,祇能存疑。說者爲證成己說,皆力證“欲取佛鉢”之月氏王爲佛徒。[33]其實國王“欲取佛鉢”與其信仰並無必然聯繫。
很可能月氏王與佛鉢有緣之傳說已深入人心。佛鉢逸失處,便稱爲月氏王索走,佛鉢所在處,則稱月氏王欲取不能。要在借月氏王擡高鉢之身價,如此而已。
(二)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有載:
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湼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賷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賷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卽其座,訖利多王驚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34]
說者又指其中呬摩呾羅王爲寄多羅王,並據同卷玄奘關於摩揭陀國無憂王(即阿育王)、犍陀羅國迦膩色迦王和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之年代,推出呬摩呾羅王滅迦濕彌羅訖利多種年代爲390年,以爲可與前引法顯之記述相呼應。[35]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據《大唐西域記》卷三,迦濕彌羅之呬摩呾羅王係釋種之裔[36],與月氏或貴霜毫不相干。
二則,呬摩呾羅不過玄奘所傳“覩貨邏國故地”之一,位於雪山即興都庫什北麓(“呬摩呾羅”意即“雪山下”),而寄多羅王都監氏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載縛喝所在地。兩者顯然不在一處。
三則,寄多羅王的業績是復興貴霜王朝,呬摩呾羅王僅僅是復辟呬摩呾羅王位而已,雖然都可以稱爲“光有疆土,嗣膺王業”,但其性質、規模不可同年而語。
據《魏書·西域傳》,寄多羅王興師遠征乾陀羅以北五國。據《大唐西域記》,呬摩呾羅王僅偷襲迦濕彌羅一處。迦濕彌羅在《魏書·西域傳》稱“罽賓國”,並非“乾陀羅北五國”之一。
五則,《大唐西域記》卷三稱迦濕彌羅國中摩揭陀國無憂王(即阿育王)的年代是“如來湼槃之後第一百年”[37],犍陀羅國迦膩色迦王的年代是“如來湼槃之後第四百年”[38],而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的年代則是“如來湼槃之後第六百年”。說者根據這些數據,加上今人考證所得迦膩色迦之絕對年代[39],推算出呬摩呾羅王“光有疆土,嗣膺王業”的年代爲390年。且不說佛滅之年衆說紛紜,所謂“湼槃之後”若干年亦皆籠統,難以落實,不可能從中推出可信之結論。
(三)說者以爲從4世紀80年代到5世紀20年代,漢文佛教文獻以“月氏國”指稱乾陀羅地區,正值寄多羅王朝佔領之時。說者指出這一點,也是爲了探究寄多羅王朝佔領乾陀羅年代之上限。有關考證可議處不少。
1. 《高僧傳·慧遠傳》卷六有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40]說者以爲這表明遲至慧遠聞佛影時,寄多羅已南侵西北印度,“月氏國”乃指犍陀羅以西那竭呵城(Nagarahra),亦即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九所載“大月氏西佛肉髻住處國”。[41]
今案:慧遠(334-416)聞佛影究竟何時,無從確定。即使慧遠以“月氏國”指稱寄多羅政權,亦無從由此推出寄多羅統治乾陀羅之年代。
2. 《水經注·河水二》:“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迹、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弗樓沙國。”[42]所謂“佛鉢在大月支國”,乃指弗樓沙。說者據以爲竺法維的年代當在僧表之前(439年以前),與法顯同時或稍後。
今案:竺法維,或以爲係“竺法雅”之訛。竺法雅,《高僧傳》卷四有傳,其事蹟亦見該書卷九《竺佛圖澄傳》,與道安、佛圖調爲同時人。另說竺法維應爲宋、齊間人,《高僧傳》卷二之末有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43]因此,竺法維應與僧表同時代。[44]即使如說者所言,竺法維之年代早於僧表,亦無從證明寄多羅早在四世紀末已佔領乾陀羅。[45]
3. 《藝文類聚》卷七三引支僧載《外國事》稱:“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娑[46]越國,是天子之都也。”支僧載年代有異說[47],說者力主其年代早於法顯,蓋所載和竺法維合。
今案:支僧載稱佛鉢所在大月氏國爲“天子之都”,表明此“大月氏國”應指貴霜王朝,因爲devaputra一號屢見於閻膏珍、迦膩色迦之銘文。換言之,即使支僧載年代如說者所言,亦很難指“大月氏國”爲寄多羅政權,因爲寄多羅王採用的尊號是Shāhi,而不是“天子”。
4. 俄藏敦煌文書Ф. 209號《聖地游記述》稱:佛伏天魔處有樹,而“彼國天子並以七寳莊嚴此樹”;又稱:佛鉢在奚吴曼地城東[醯]羅寺,“天子及王一切見今供養”。[48]說者亦指其中“天子”爲寄多羅貴霜統治者Kidara。
今案:既無證據表明《魏書·西域傳》所傳寄多羅王(包括可能存在的寄多羅貴霜王朝其他統治者)以“天子”作尊號,說明此文書提到的“天子”不是寄多羅統治者,或者說此文書描述的時代不是寄多羅貴霜統治乾陀羅的時代。說者考此文書絕對年代在412-433年間,果然,則表明在此文書撰寫之年寄多羅王尚未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北天竺。
其實,乾陀羅尚未被寄多羅佔領,僧侶們仍可能稱之爲“月氏”,蓋乾陀羅曾爲弘揚佛法的貴霜王迦膩色迦所都,而貴霜一直被稱爲“月氏”。降至支僧載時代,貴霜雖亡,僧侶們用業已滅亡的“月氏國”指稱佛鉢所在地乾陀羅不足爲奇,猶如今日中國人稱山東爲“齊魯”、稱江浙爲“吳越”一樣。強調“天子之都”,則有擡高佛鉢身價之用意在。
另說:法顯所載北天竺的情況與中天竺不同,後者在一個國王治下,前者則包括互不統屬的諸國。由此可見,遲至法顯遊歷北天竺之日,寄多羅人尚未統一興都庫什山南北。[49]
今案:其說未安。寄多羅王興兵越大山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後,這五國可能依舊存在,不過役屬寄多羅而已。換言之,法顯的記錄對於判定寄多羅崛起的年代意義不大。[50]
九
本節略述寄多羅貴霜的族屬問題。
西方學者多將寄多羅與匈人勘同,主要依據便是前引普里斯庫斯和《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的記載。但是,如前所述,只要將這些記載和普洛科庇烏斯的有關記載對照起來閱讀,便不難發現《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所述貴霜匈奴無疑便是普洛科庇烏斯所述嚈噠匈人。既然直到卑路斯去世之際嚈噠人仍然被稱爲“貴霜匈人”,也就不能否定埃里塞所載“貴霜匈人”乃至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不是西遷的寄多羅貴霜人,而是嚈噠人的可能性。毫無疑問,祇有伊嗣俟二世纔會遭遇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人。當然,也不排除其時被征服的寄多羅貴霜人充當嚈噠人進攻薩珊波斯前鋒的可能性。[51]
以寄多羅貴霜人也被稱爲Huns這一錯誤認識爲前提,說者或將寄多羅貴霜人與Ammianus Marcellinus[52]所載chionitae勘同。[53]而Ammianus Marcellinus僅僅記載:chionitae有王名Grumbates,隨沙普爾二世(ShāPūr II, 309—379)遠征拜占庭,其子戰死於Amida城(今土耳其Diyarbakir)下。(XIX, 1—2)除了chionitae一名可與Huns勘同外,別無其他證據。尤其可以指出的是,據Ammianus Marcellinus(XVI, 9—4),356年在東方入侵波斯的族群有二:chionitae和Euseni。據研究,Euseni係cuseni之譌,而cuseni即貴霜(Kushans)[54]。這就是說,在Ammianus Marcellinus,chionites和貴霜是明確區分的,不容混淆。
或以爲Kabul附近TePe Maranjan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金幣有βαγo κιδαρo字樣,這一窖藏入土於ShaPur三世在位時期(383—388)。[55]換言之,可以認爲寄多羅貴霜年代早於ShaPur三世的治期。於是,便消除了將chionitae和寄多羅人勘同的年代障礙。
今案:錢銘所見Kidaro字樣不無可疑之處。這些錢幣有可能屬於最後一位貴霜—薩珊王(Kay Wahram)。[56]至於這些錢幣的樣式和後來寄多羅王的錢幣式樣某些相似之處,可以理解爲寄多羅王摹倣貴霜—薩珊王錢幣的結果。[57]
或以爲寄多羅人錢幣的特點是在他們征服的地區採用當地的幣制,沒有自己獨立的錢幣系統。既然有一種早期索格底亞那錢幣,反面有一個弓箭手的形象,正面銘文中有“寄多羅”(kydr)一詞,這些錢幣便成了寄多羅人曾出現在索格底亞那的證據,儘管存世的2000多枚這類錢幣中,只有7枚有“寄多羅”的名字,表明寄多羅人在索格底亞那的統治是短暫的。換言之,雖然這些錢幣的年代不可能早於4世紀中葉——因此寄多羅人征服索格底亞那不可能早於這個年代。但只要寄多羅人有可能在沙普爾二世治期統治過索格底亞那,哪怕時間很短,指寄多羅人爲chionitae的合理性便大增。[58]
今案:此說亦有未安。寄多羅人在吐火羅斯坦以寄多羅王名義發行的金第納爾倣照貴霜-薩珊金幣的式樣,而在所佔印度土地上發行的金幣乃倣照晚期貴霜諸王金幣的式樣,似乎反映了上述寄多羅人鑄幣的特點。但是,寄多羅人並未佔領薩珊波斯領土,卻也在乾陀羅倣照薩珊錢幣式樣打鑄自己的錢幣。可見上述7枚錢銘有“寄多羅”字樣(即使所指正是《魏書·西域傳》所載“寄多羅王”)的索格底亞那型錢幣未必是其人佔領索格底亞那後打鑄的,當然也不能由此推論其崛起年代可以上推至4世紀中葉甚或更早。
既然Kabul附近TePe Maranjan窖藏中並不存在寄多羅貴霜人的錢幣,指弓箭手型錢幣爲寄多羅人錢幣又無確證,將寄多羅人的年代提前到沙普爾二世治期就失去了立足點。
順便說說,學界曾試圖依據寄多羅貴霜政權發行的錢幣推斷其年代,但顯然並不成功,蓋錢幣可以摹倣,而錢幣的發行者和其摹倣的對象時間上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59]現存寄多羅貴霜的錢幣既有摹倣沙普爾二世的,又有摹倣巴赫蘭五世(Bahrām V, 420-438年在位)和伊嗣俟二世的,既然沒有證據表明有一個以上以Kidāra爲名的貴霜王,也就至多據此推斷這些錢幣打鑄於伊嗣俟二世治期或其以後的年代。[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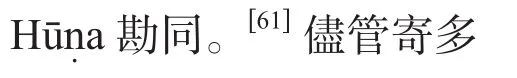
祇要考慮到嚈噠人自號“匈奴”,又來自一度處於貴霜或寄多羅貴霜統治之下的吐火羅斯坦,“貴霜匈人”或“寄多羅匈人”這些稱呼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而突厥佔領之後吐火羅斯坦的情況正可參證。蓋據《冊府元龜》卷九六六,“吐火羅國,唐永徽三年(652)列其地爲月氏府。以其葉護阿史那烏濕波爲都督。開元七年(719),其葉護曰支汗那;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咄祿頓達度爲葉護”。顯然,以阿史那烏濕波爲首的統治吐火羅斯坦的突厥人,也完全可以稱之爲“吐火羅人”或“吐火羅突厥人”。
十
要之,寄多羅貴霜人可能是貴霜之裔,其王寄多羅大概崛起於貴霜—薩珊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衰落之際,且一統吐火羅斯坦。這個政權雖然一再受到柔然的侵擾,其王寄多羅仍興師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
其後,由於嚈噠人入侵吐火羅斯坦,寄多羅王不敵,率部西徙,一度衝擊薩珊波斯東境。寄多羅王本人下落不明,既可能在與波斯人作戰過程中陣亡,也可能死於接踵而至的嚈噠人之手。
因此,寄多羅貴霜政權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結束的年代大致可以確定,亦即與嚈噠入侵吐火羅斯坦的年代基本相符。其始年則無法確知,祇能說也許在4世紀末至5世紀初。寄多羅王很可能就是這一王朝的第一代君主。
寄多羅王被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之際,其子留守興都庫什山南之地,史稱“車多羅”(Kidara)或“居常”(Kushan)。其人可能一度服屬於南下次大陸之嚈噠人,苟延殘喘至5世紀80年代末。
注釋
[1]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pp. 66 -75。
[3] R. W. Thomson, tr., Eishē, History of Vardan and the Armen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3.
[4] 注3所引R. W. Thomson書,p. 64。
[5] 注3所引R. W. Thomson書,p. 66。
[7] R. c. Blockley,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 PaPers and MonograPhs 10, Francis cairns, 1981-1983.
[8]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esP. 353.
[9] 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 70-74。
[10] W. Wright, The chronicle of Joshиa the Stylite, 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and Notes, cambridge,1882.
[11]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12] 說見注2所引榎一雄文。
[13] 關於嚈噠入侵印度次大陸,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 85-102。
[14] 說見注2所引榎一雄文。
[15] 《大智度論》卷一一:“譬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千那,到東方多刹陀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大正大藏經》T25, No. 1509, p. 141)
[16] 《大智度論》卷九:“(釋迦牟尼佛)有時暫來北天竺月氏國降阿波羅(APalāla)龍王,又至月氏西降女羅刹。”(《大正大藏經》T25, No. 1509, p. 126)
[17]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pp. 274-275。(《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2)
[18] 《大正大藏經》T25, No. 1509, p. 243。又,《翻梵語》卷八引《大智論》“第二十五卷”:“兜呿羅,譯曰小月氏也。”(《大正大藏經》T54, No. 2130. p. 8)
[19] 注2所引榎一雄文。
[20]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46,pp. 183-184。
[21]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58, p.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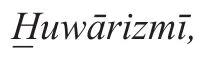
[24] H. W. Bailey, Rāma II, Bи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иdies 10 (1941) PP.559-598, esP. 583, note 2; Irano-Indica IV, Bи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иdies 13 (1951) PP. 920-938, esP. 921.
[25] 說者以爲這與榎一雄[K. Enoki, On the Date of the Kidar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иnko 27 (1969), PP. 1-26; 28 (1970), PP. 13-38.]的結論不謀而合。
[26] 注1所引余太山書,pp. 85-102。
[27]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pp. 39-40。(《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5, p. 858)
[28] 見萬翔:《寄多羅人年代與族屬考》,《歐亞學刊》第9輯,2009年,pp. 115-160。又,“大興兵衆”伐弗樓沙國之月氏曾被指爲嚈噠,見M. F. c. Martin,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shāns, Joи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3—2 (1937) = Nиmismatic SиPPlement, No. 47, PP. 23-50 with 5 Plates,這顯然是錯誤的。批判見注2所引榎一雄文。
[29] 注27所引章巽書,p.178。
[30]《大正大藏經》T50, No. 2058,p. 315。
[31] 參見注2所引榎一雄文,以及注27所引章巽書,p.44,等等。
[32] 章巽說,見注27所引書,p. 44。
[33] 諸如:在貴霜興起之前,大月氏王已接受佛教,證據見於《三國志·魏書》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見注27所引章巽書,pp. 44。
[34] 注17所引季羨林等書,pp. 338-339。(《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7)
[35] 注28所引萬翔文。
[36] 詳見《大唐西域記》卷六,注17所引季羨林等書,第516頁。(《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7, p. 901)
[37] 注17所引季羨林等書,pp. 327-328。(《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6)
[38] 注17所引季羨林等書,pp. 331-332。(《大正大藏經》T51, No. 2087, p. 886)

[40]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59, p. 358。
[41] 《大正大藏經》T25, No. 1509, p. 126。
[42] 見陳橋驛:《水經註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p. 35。
[43] 《大正大藏經》T50, No. 2059, p. 337。梁寶唱《名僧傳抄》抄《名僧傳》(第二十六)載僧表事稱:“僧表本姓高,凉洲人也,志力勇猛。聞弗樓沙國有佛鉢,鉢今在罽賓臺寺,恒有五百羅漢供養鉢。……乃至西踰蔥嶺,欲致誠禮,并至于罽賓國。值罽賓路梗,罽賓王寄表有張志模寫佛鉢與之。又問寧復有所願不?對曰:讚摩伽羅有寶勝像,外國相傳云,最似真相,願得供養。王即命工巧,營造金薄像,金光陜高一丈,以真舍利置于頂上。僧表接還凉州,知凉土將亡,欲反淮海。經蜀欣平縣,沙門道汪求停鉢、像供養,今在彼龍華寺。僧表入矣,禮敬石像。住二載,卒于寺。”(《卍新纂續藏經》第77册,p. 358)“凉土將亡”云云似指北凉故上述僧表事應在439年之前。
[44] 酈道元:《水經注》,森鹿三、日比野丈夫等譯注,《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1,東京:平凡社,1985年,pp. 138-139, n. 107。另參看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敍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87年,pp. 565-578,esp. 577。
[45]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иi-ching-chи, Serie Orientale Roma: 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P. 60, 以爲竺法維這段話暗示當時那竭國(今Jalālābād)是以弗樓沙爲都城的國家的一部分,這個國家即寄多羅貴霜王朝。今案: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竺法維訪問大月氏國的年代不清楚,無從據以推斷寄多羅征服乾陀羅的年代。
[46] 原文作“婆”,此據L. Petech說改,見L. Petech, Alcuni Dati di chih Sêng-Tsai Sull’India, In Selected PaPers on Asi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LX,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 P. 314。
[47] 注44所引向達文,esp. 577,以爲支僧載活動於5世紀初,與法顯同時。陳連慶《新輯本支僧載〈外國事〉序》,《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1期,pp. 19-21,以爲其年代約略相當於笈多王朝月護王(chandraguPta)、海護王(SamudraguPta)時期(320-380)。蓋海護王之子超日王(chandraguPta II, Vikramāditya,380-415年在位)時期,笈多王朝的首都從摩揭陀遷走,這與支僧載的記載不符,故其時代當早於法顯。
[48] 《聖地游記述》,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4,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p. 241-242。
[49] 見注2所引榎一雄文。
[50] 注25所引K. Enoki文引《出三藏記集》卷一四鳩摩羅什年十二“至月氏北山”之記載(《大正大藏經》T55, No. 2145, p. 100),證365年時乾陀羅已稱“月氏”。今案:其說非是。此“月氏”乃龜茲之別稱。
[51] 說詳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pp. 180-210。
[52] John c. Rolfe. tr., Ammianиs Marcellinи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39.
[53] R. Göbl, Dokиmente zи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иnnen in Baktrien иnd Indi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67, II, PP. 53-54. E. V. Zeimal, Politicheskaya istorya drevney Transoksiany Po numizmaticheskim dannym, Kиl'tиra Vostoka. Drevnost'i rannee srednevekov'e, Leningrad, 1978, PP. 192-214; E. V. Zeimal, The Kidarite Kingdom in central Asia, In B. A. Litvinskiy,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P. 119-128.
[54]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36, n. 5.
[55] 注53所引R. Göbl書, I, pp. 17-18。
[56] F. Grenet, Regional interac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India in the Kidarite and HePhthalite Periods, Indo-Iranian Langиages and PeoPles, 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11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03-224.
[57] A. D. H. Bivar, The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Kushano-Sasanian Governors in central Asia, In J. Harmatta, ed., Prolegomena, to the Soи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317-332.
[58] 注53所引E. V. Zeimal文,見B. A. Litvinskiy書, esp. 120, 129。案:迄今沒有發現寄多羅人曾領有索格底亞那的確鑿證據。有人試圖證明之,如: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English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5, PP. 107-112。其說未安,參看注28所引萬翔文。
[59] 例如:注28所引M. F. c. Martin文以爲寄多羅貴霜的年代在356-367/368年,有文獻和錢幣的證據。但其結論不可信從。批判見注2所引榎一雄文。
[60] A. cunningham, coins of the Tochari, Kushans, or Yue-ti, Nи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иrnal of the Nиmismatic Society, 1889, Pt. III, 3rd series, No. 35, PP. 268-311, 則認爲錢幣證據支持寄多羅貴霜年代的5世紀說。
[61] 見注53所引E. V. Zeimal文(載B. A. Litvinskiy書)。
[62] 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 85-102。
[63] J. F. Fleet,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corPиs InscriPtionиm Indicarиm, vol. 3, No. 13, calcutta, 1888.




Som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Kidarite Kushans
Yu Taishan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欧亚学刊的其它文章
- in the Religion of Light: A Study of the Popular Religious Manuscripts from Xiapu county, Fujian Province
-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BAIDAR FAMILY IN
- 明教中的那羅延佛―福建霞浦民間宗教文書研究
- NEW DATA ON THE HISTORIcAL TOPOGRAPHY OF MEDIEVAL SAMARQAND
- THE TURKIc cULTURE OF THE INNER TIANSHAN: THE LATEST INFORMATION
- 中國境內祆教相關遺存考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