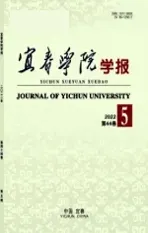论李东阳格调论诗学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2015-08-15张智炳
张智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李东阳是明诗学的转关者,也是格调论的开启者。所著《怀麓堂诗话》预揭格调论诸因素,继高棅《唐诗品汇》之后,具体探讨“辨体论”,并深化诗歌“声乐论”①,表明其崇唐黜宋元的宗唐旨趣。所不同者,高棅持“申正黜变”的“正变”观,更多批评韩诗之变;而李东阳则倾向“通变”,既把韩诗置于唐诗史中以见韩诗之变,更将其置于唐宋诗史的转捩点上,以明韩诗对推动诗史发展的诗学意义②。
一、明初格调论诗学的萌芽及基本内容
明初格调论诗学首先孕育于唐诗学中,远源于“由宋返唐” “宗唐得古”的元代唐诗学。杨士弘选《唐音》,主张“审其音律之正变” (《唐音姓氏并序》)及唐诗“始音” “正音” “余响”的三分法,直接启发了高棅《唐诗品汇》 “辩尽诸家,剖析毫芒”的“别体制之始终” (《唐诗品汇总序》)的辨体思想、初盛中晚“四唐”说及“正始”“正宗”“正变”等九品格局的形成;二选均崇盛唐,且辨体、审音、崇唐等皆预合格调论诸因素。明初格调论的宗唐理路与政治上的复古风习相互扭结,张少康先生说“格调说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和文学上的复古、摹拟思潮联系在一起的”[1](P168),永乐以还,则演化为“台阁体”润饰鸿业的富贵之气与点缀升平的雍容之态。对此,李东阳即主张以声、乐、调论诗以救弊,开启了格调论唐诗学。
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即是诗、乐统一的表征。即使后世的诗歌与音乐逐渐分离,成为案头文本,但其自身的音乐性并未完全消失,因其体制仍以音律节奏为先,从而构成抑扬顿挫的声调以讽咏,甚而直截入乐歌唱,此即为格调论之“调”。萧华荣先生说“'调'指诗中飞沉清浊抑扬高下的声调的运用、排列、组合在读者心中引起的音乐美”[2](P222),亦即张少康先生说的“由声律所形成的诗歌音乐美,以及由这种音乐美所产生的悠远之韵味”[1](P167);所谓“格”,张先生即认为“指诗的立意,亦即诗歌的审美意象之构想”[1](P167)。如高棅说唐诗讲求“声律、兴象、文辞、理致”[3](P8),即集“格”“调”言之。笔者认为,“格”不仅指诗的“立意”,更指向其作为诗的文体特征,所以格、调皆与诗歌风格论关系密切,而体现明诗学价值取向的“辨体”论就因而成为格调论的精彩部分之一,因为“体”在古典诗学中本身就包含着“体格”与“风格”的双重因素。格调论的根本任务在于辨析各时代最盛行之诗的体制与风格特征,从而给其时的诗学审美与诗歌创作提供卓绝的取法范本。这也是李东阳诗学辨体理论的动力之一,但他并未一味崇唐、复古,亦未走上摹拟而失故步的褊狭之路,反而具有宏通的眼光,观其对李、杜、韩、苏“诗格”于唐宋诗史发展的推动及对韩、欧、苏打破诗、文二体界限而兼长的赞誉便可见出,体现了“拟议以成其变化”(《周易·系辞上》)的精神实质。
二、李东阳的格调论诗学观
李东阳与其《怀麓堂诗话》论诗虽驳杂,抽绎其精粹者恰关乎崇唐黜宋元论;诗文辨体论;气运与风格关系,进而以诗歌音调为切口,分析二者间的交织面貌,即声乐论。他对韩诗的诸种论评即以此为理论根基。
(一)崇唐黜宋元论:绍继传统格调论
崇唐黜宋是元人对格调论的最初贡献,以宋诗为参照,体认、比较并确认唐宋诗风貌差异。李东阳虽亦如之,但对杰出宋诗人及唐宋诗之会通的肯定,自见其批评见地。他说:
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4](P181)
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4](P33)
李东阳无法对宋元诗视而不见, “各有兴致,但非本色”的话,稍作扬扢之后便出以批评,剖白其“宗唐得古”的心声溢于言表,“充分体现了李东阳宗主汉、魏、唐,而贬抑六朝、宋、元的诗学思想”[4](P183)。这与严羽“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的“向上一路”(《沧浪诗话·诗辨》)的取法路径别无二致。所云“兴致”“本色”与“深”“浅”等即是对宋元诗歌风格的表露,这是格调论比较中正的辨体思路。
(二)声乐论:探讨气运与风格之关系
李东阳引入“文章固关气运”[4](P116),意在考究时地的推移、变换造就的“气运”与诗歌的时代、地域风格之不同的深层关联,从而特地关注到体现风格最直接、最外在的诗歌音调特质的作用,并作为切入口而论析之。如: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哉?[4](P179)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邪?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4](P134)
这个切入口体现了风格最直接、最外在的诗歌音调特质上的差异,即“声调”与其进一步的“音殊调别”。对于一时无法解释的浑成诗体(体制与风格),即以律诗论,律之“规矩”易作而律之“调”难辨,李东阳只以“巧”体味之,并从感知诗歌的不同音调着手,进一步具体辨析构成诗歌音响性(音乐性)的音调声律(声调)的不同表现来体察人各一面的诗体。这一方法就是声乐论,也就是李氏格调论中的“以声论诗”,具体表现为“眼主格,耳主声”;其中, “音调”当与古诗联系更多,而“声律”与近体关系紧密。这是他不同于传统格调论者辨体的独特之处,因而郭绍虞先生说“由声乐之关系以论诗之音调,那便与沧浪不尽同。沧浪所论偏于诗之风格,而西涯所论,则重在诗之抑扬抗坠之处”[5](P378)。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4](P24)
李庆立先生释“具眼”为“具有鉴别事物的眼力”,释“格”为“主要指诗歌的风格而言”[4](P25)。如果“声”指声韵、声调而言,那么,“格”虽指风格,与立意有更多关系,但还应包括诗歌体裁才更具“看” (兼指“阅读” “辨别”)的内涵,因而“眼主格”才有较全的辨体意义,所以“眼主格,格指诗歌体格;耳主声,声指诗的声调,合而言之即为格调。以声论诗,是李东阳论诗的本旨”[6](P86)。李庆立先生更明确指出:“李东阳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认为诗必须具有自然之音韵,因而辨识诗的'时代格调',强调不但要用'眼'去'读',而且要用'耳'去'听',要具有辨别音韵的能力。”[4](P27)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不错。
(三)辨体论:严格但不失宏通的眼光
由前述可知,李东阳的声乐论是其辨体论的具体落实,但在恪守“以声论诗”辨体时没有胶柱鼓瑟,往往传达出较为通达的信息:
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4](P6)
古、律诗最显著的差异就在讲求声律的严格与否。概言之,唐近体诗之前的中国诗歌概称之“古诗”,包括乐府、歌行,其形制特点不拘平仄要求,不工于偶对,用韵自由,长短参差,更便于表达澎湃的情感,易于寄托古雅式的寓意;而律诗恰与之相对。所以古诗中杂有律法,就是变体;而律诗产生于唐,可以借助古声达到更为“古典”的创作预期。对此,查清华先生说“古诗唐人可以仿作,但古诗的声调是汉魏诗人情性的表现,是汉魏那个时代的'自然之声',因此,必须将它与近体诗严格区分。若求其次,'律犹可间出古意',因为古诗在先,律间出古尚可视为古意犹存,若古涉律调将使古体诗不伦不类”[7](P66)。李东阳的这句话对七子派的唐五古辨体理论似有所启发,李攀龙就在《唐诗选序》中引申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观点。这是似乎是“后出转精”的结果,但李氏本人还尚无如此偏执:
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侧长短、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4](P20)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4](P60)
笔者以为李东阳作《怀麓堂诗话》至此已经表露了将其诗论的关键部分都表露出来了,辨体是为了尊体,为了给诗坛提供一个既纯且优的范式,就是提倡“自然之声”,这或许不可厚非,但李东阳毕竟面对风格复杂、诗体多变的创作实际,似乎也有破体的要求,间接承认了破体的合理性,对“长篇节奏”主“有正有变”已可看出其倾向,他强调只要能“得于心而发之乎声”,抒发真性情,达到“音响与格律相称”,就能取得“不越乎法度之外”的效果。所以他肯定杜甫长篇的“变化不测,可骇可愕”,对杜诗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只要再琢磨“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的心理蕴含,就可发现李东阳把“唐调”与“杜学”对举,其肯定杜诗之变的意向是非常明显的。
在承认杜诗之变的重要意义之后,笔者就不难发现,后文他对杜、韩、苏于中国诗史演进的重大贡献的揭橥,就是暂时撇开格调说的严正之论,对唐宋诗史的演变有一个比较通变式的认识。李东阳继续把该思想具体地贯彻到他的“诗文辨体论”与“诗歌声乐论”中,对韩诗创作的“变异”之处作出了不失公允的评判。
三、李东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一)诗文辨体论中的韩诗观
诗文辨体理论是中国文体学发展成熟的表现。辨体就是对不同文体及其本体特征的认识,有利于文体朝着尊体的方向演进。它较有可能肇始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中,并体现在文章总集的编选上。汉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已初步区分了不同文类;至魏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专讨论文体;晋陆机《文赋》具体分文体为诗、赋等十类;六朝的文学创作讲究唯美,偏好偶对,骈文鹊起,文体表达甚为考究,萧统编集《文选》,辑录赋、诗、骚、诏等38 类,“反映了当时对文学作品的特色和范围认识日趋明确”[8](P1);刘勰《文心雕龙》深具古代文论之成,自《明诗》至《书记》亦以20 篇的容量专门讨论文体,使文体研究愈来愈具理论化向度④;唐代着重深化诗体演变,由古体到近体,由绝句到律诗;宋代则促成散文文体的再度勃兴。由于唐宋古文运动的持续深入,文体又渗入到诗歌当中,早在以杜、韩为代表的盛、中唐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倾向,诗、文两种相差较远的文体开始走向互渗,后世突出表现为宋人如陈师道、释惠洪等对杜甫“以诗为文”与韩愈“以文为诗”的争辩,既是对文体的细微辨析,也是有关唐宋诗之争的发端,表达了人们对唐宋诗创作特征的考察。
至明代则演化为举世探究诗学辨体的热烈局面,李东阳既主诗、文尊体,更有突破诗、文壁垒的意识,强调其融合与兼工。其《匏翁家藏集序》云:
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若《典谟》、 《训诰》、《誓命》、 《爻象》之谓文, 《风》、 《雅》、《颂》、赋、比、兴之为诗。[9]
区别“言之成章”与“文之成声”的不同,抓住“成声”的诗本体以区别于“文”,似乎透露了文先于诗的文体演变观点:诗是有组织的“文”“成声”后的复杂文体。他在《镜川先生诗集序》、《沧洲诗集序》分别说:
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后之文皆出诸经。而所谓诗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声韵,例以格式,名虽同而体尚亦各异。[9]
诗之体与文异,故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其难如此。……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风韵,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9]
李东阳进而抓住诗歌“兼比兴,协音律”、“声律风韵,能使人反复讽咏”着重强调了诗歌对于人的审美情感作用,所谓“畅达情思,感发志气”。他的诗文辨体仍与其声乐论紧密相连,以突出诗本体。笔者发现,李氏努力道出“诗限声韵,例以格式,名同而体异”,诗“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云,实际上又把诗细化为“长于记述”与“短于吟讽”两类, “长” “短”明显作为互文而言,即互有长短利弊,强调“终其身而不能变”的诗歌之用,已给下文的“诗文兼能”埋下了伏笔。他在序陆釴《春雨堂稿》时说“静逸先生尝谓诗与文各有体,而每病于不能相通,意若非予鲜可与言者”[9],故发表了诗文相通的意见:
近代之诗,李、杜为极,而用之于文,或有未备。韩、欧之文,亦可谓至矣,而诗之用,议者犹有憾焉,况其下者哉!后之作者,连篇累牍,……转盼旋踵,卒归于澌尽泯灭之地,……且今之科举,纯用经术,无事乎所谓古文歌诗,非有高识余力,不能专攻而独诣,而况于兼之者哉![9]
李东阳虽举出时人对李、杜之文“未备”,韩、欧之诗“有憾”的议论,但仅止于“诗之用”的层面,就是把诗作为科举经术的参照而言;从他所讥讽的“后之作者”与“今之科举者”之诗文在转盼旋踵间即卒归于澌尽泯灭来看,对韩、欧“以文为诗”流转至今之诗仍给予了心理上的赞许,至少暗自保留意见。随后他就肯定地抛出其所理解的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和及其诗史意义:
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而或者又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况未必似乎!……顾惟其异于文也,故虽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盖间世而始一见。韩昌黎之诗,或讥其为文;苏东坡之诗,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叹。今观其宏才远趣,拔时代而超人群也。[9]
由此看来,李东阳虽有较强的尊体意识,诗学取向归于唐诗,但他并未因此而堕入崇古摹拟的恶趣,故以韩、苏之诗“宏才远趣,拔时代而超人群”的磅礴才力,规劝并救正当时诗坛崇古摹拟而失故步的流弊,看中的正是韩、苏诗对诗歌题材的大胆开拓,是对韩、苏生当唐诗之后开辟诗歌创作之功的期许,赏誉韩诗“博学聚理”、 “取物广才”的包容性,即敢于向新的题材与体裁提出挑战;相反的,其辨体重在标举创作范式,重在“不因循”,能自立,他在《怀麓堂诗话》中就说过“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4](P49)。其文学史观较为宏通,并对当时的摹古之风提出批评,客观上窥视到一个通变的诗史。李东阳之所以对韩、苏之诗评以“拔时代而超人群”,是因为二者“能兼诗文之长”;同时,笔者也看到李东阳诗论自身已包含着变通的破体论。这为他进一步探讨韩诗艺术提供了理论先导。比如他说:
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4](P55)
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4](P205)
这印证了上文对韩诗创作特征的认识。与此相应的,是李东阳虽引入宋人对韩诗“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探讨,但没有接续诸如陈师道的话语⑤,而更可能接受了陈善“诗文相生”的观点⑥。一方面,针对“昔人未然”的“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特看中杜、韩之诗的“所得、所就”,即区别昔人创作的特异之处,亦即“偏长独到之处”,故对杜、韩诗偏于能开新称赞有之;另一方面,这种开拓主要得力于对诗“格”的突破,由汉魏的简古诗格到杜、韩、苏“可尽天下之情事”的“渐粗”诗格,客观上揭示了从汉魏到唐宋诗史发展的转关点,眼光不可谓不独具。如果李东阳说的“诗格渐粗”是偏于文学内部演变的话,杨国安先生则就外部的社会文化演进对韩愈诗格的变化予以文化学阐释:“由于内优外患的严重现实,由于士子生命道路的艰难,他们对于改变社会现状的企图,这一切都使盛唐诗歌中那种浓烈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衰颓暗淡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作风。另一方面,随着安史乱后经济、社会的急邃变化,中唐的学术风气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汉唐体系趋于崩溃,佛禅思想大为流行,新的儒学体系正在酝酿,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社会文化的整个底色都呈现出变化纷纭的面貌。”[10]有助于理解韩诗大变的内涵。而李东阳从接受者的角度特针对“台阁体”润饰鸿业与点缀升平的冗阘啴缓之弊,以及明初宗唐、视宋诗不顾的褊狭局面,以杜、韩、苏的创作提请文坛注意,以期改变偏执的摹拟风气。
综上,李东阳诗论虽恪守体格声调,但已具通变的潜质,如他还认为韩诗“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健,以别出一格”[4](P203), “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4](P114),是体格上的破“格”,也是声调上的“跑”调,使他的诗论更富生动的实践性。这便关联到其声乐论。
(二)诗歌声乐论中的韩诗观
李东阳诗学体系的另一核心是声乐论,强调诗与乐的紧密联系,以至视诗乐一体。声乐特质在古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涉歌唱性(声调)为多,在近体诗中则呈现为人为的格律,是诗歌审美与体制特征的浑融呈现。严格地说,声乐论也是辨体论的组成部分。《怀麓堂诗话》开篇就明确说: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4](P1)
李东阳实际重申了汉儒解《诗》的诗教论,况且他借用的“乐”在上古确曾被赋予过风化的职责,所以他说“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4](P43)。不过,他强调《诗》为“六艺中之乐”,“别是一教”,还是偏取诗歌的音乐特性、审美性,也就是“陶写情性”,其效果是“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将乐引入诗则意在强调诗歌在声调上的音乐属性,进而从声调、韵律上去辨析诗歌所具有的格调特征,从而分析诗歌的兴象风神,最终体味到诗人的性情,这才是李东阳诗论的归宿所在。但借诗乐一体以裨补于世、群聚人心、感发志意等是儒家诗论的客观延续,而非李东阳的刻意追求,所以他一方面注重诗乐之联系,另一方面注重诗、文声乐特质的不同,进而以之进行诗文辨体。这是其另一初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东阳论韩诗云: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4](P64)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李东阳以乐之“五声”(宫、商、角、徵、羽)来比附不同的诗歌风格。以宫音拟李、杜诗,出于宫音为五音之首, 《周礼》中已有“凡五声宫之所生”的记载[11], 《礼记》也说“宫为君”[12](P561),都说明宫声的宏大,富有主导性。宋陈旸也说“宫声感人,则其意欢和”[13],若说杜诗目睹安史变乱的苍生忧难,已染变调,但说李诗“欢合”却大致不错。相形之下,韩诗的“角声”就彻底属于变声,因为陈旸还说“角声感人,则其意奋厉”[13],一如周德清云“角调呜咽悠扬”[14]。如果抛开明格调派在辨体上主大历以后诗歌为变体的话,以陈、周的“角调论”观照韩诗,大致也是符合实际的。对此,《中国文学理论史》就分析说“宫声是我国古代音乐中最基本的调式,调性典雅沉重,所以说'最优'、'可以兼众声'。李、杜之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典范,风格壮阔而丰富,即正调,故比之为宫。韩愈之诗'横空盘硬语',走入奇险、高亢一路,故比之为角。这里已经表现出李东阳强调诗的格调,就是为了提倡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的那种宽宏而丰富的时代格调”[15](P40),所以即使韩愈诗歌声调正而有变,但他的客观成就仍使其诗歌得变中有正的特色,李东阳视野中的韩诗并非尽是“变调”,比如:
韩、苏诗,虽俱出入规格,而苏尤甚。盖韩得意时,自不失唐诗声调。如《永贞行》,固有杜意,而选者不之及,何也?[4](P242)
“出入规格”分明是偏义复指,指向“入规格”,而“规格”正是指李庆立先生所解释的“诗歌体裁、音韵等特点”[4](P243),韩诗的“角声”在李氏心中是“不失唐诗声调”的。但李东阳举出韩愈“不失唐调”的《永贞行》诗,很耐人寻味。《永贞行》是一首情感宣泄颇为直露的诗,甚至显得矫激,讽刺王伾、王叔文一干得意、偷柄篡国的“私党”,如果比之《诗经》,当属“变雅”作品,而李东阳说其“有杜意”,就把诗歌指向“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9]的“兴观群怨”说,因为杜甫在安史乱后的大部分描写山河板荡、生灵涂炭,讽刺唐廷穷兵黩武的诗篇几乎都出于他“奉儒守官”的儒家立场,表现了杜甫的仁爱与批判精神。可见,李东阳的格调论虽然宏通,但不全是“宽宏”的中和之声,再次印证了其格调论不离儒家文学思想的底色。但他也能正视韩诗的“变调”:
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韩退之亦有之。[4](P114)
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捷,以别出一格。回视纯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自后则韩退之、苏子瞻有之,故亦健于诸作。[4](P203)
李东阳着意分析韩诗声调“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独为矫捷”的“变调”特征,且其艺术效果实则“健于诸作”,是一种成功的创作。所以笔者认为,李东阳固然严辨诗文各有体的本色所在,但其格调论并非刻意崇唐媚古,往往散发着机动、变通的宏达气息。这得力于李氏本人的文学批评眼光,而杜、韩等人本身卓越多重的诗歌创作成就,则是他借以品评的最终渊源。
考察明代格调论唐诗学的流变,就可发现李东阳始终扮演着一个承先启后的关捩点角色,其诗论经前七子扬扢而成为有明中后期的主流诗学。所以,七子派后学胡应麟总结云“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俱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16](P345)。入清后,沈德潜反观明诗说“永乐以还,崇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应之,相习成风,靡然不觉。李宾之 (东阳)力挽颓澜,李(梦阳)、何继之,诗道复归于正”[17](P309)。李东阳对韩诗的种种评说,正是基于他的格调论;而嗣后的格调论者对韩愈的认识也与李论深有联系。格调论唐诗学的主题之一即辨体,其对韩愈五七言古诗的接受是在讨论唐古体诗的视阈下进行的,这一过程由李攀龙发端,经王世贞,尤其是胡应麟、许学夷等总其成,最后由胡震亨从唐诗整理的角度收尾。要之,韩诗在明代接受的动态正是与其诗学的演进脉络相始终,而格调论不仅是明诗学的主流,在韩诗接受上更彰显了主要作用。
结 语
李东阳生当明代由前期向中后期转变的节点,其所开启的格调论诗学亦具承上启下的品格。他在元人已初露端倪的格调说诸因素基础之上,绍继杨士弘《唐音》及高棅《唐诗品汇》宗盛唐的诗学思想,包括习染明初宗唐复古的政治风潮,其格调论也主崇唐黜宋、元诗的取法路径。所不同者,他把格调论落实为辨体论和声乐论,为格调论的具体展开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
在对韩诗的接受上,基于李东阳本人的诗学批评眼光,他对时世气运与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属意有之,并以格律声调为突破口试图探寻诗歌风格差异的文体因素,且引入“声乐论”的概念辅助其辨体论。他借由对汉魏“简古”诗格到经杜、韩、苏一衍再衍的“渐粗”诗格,不仅窥视到一个贯通的唐宋诗发展史,而且使其严辨诗、文二体之分别的尊体论具有变通的破体论色彩;并通过分析李、杜、韩诗的声调、韵律差异来甄别不同的格调特征,从而分析诗歌风格,最终体味到诗人的性情,使其格调论更具实践性品格。可以说,杜、韩、苏的诗歌创作成就是玉成李东阳格调论深具宏通品质的最终渊源,而李氏又以其诗学理论肯定了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通变”的质素,不同于高棅《唐诗品汇》的韩诗“正变”观。
注释:
①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申述承元杨士弘《唐音》“审音律之正变,别体制之始终”而深论之(见明高棅编选、王宗尼校订《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0 页)。
②本文“韩诗”非谓汉代《诗经》“三家诗”的韩婴之“韩诗”,而潜在地主要指韩愈古诗,且高棅、李东阳对韩诗的讨论亦主要针对其古诗。
③关于明诗学格调论及其中“格”的含义,可参看查清华《中国诗学的“格”论》(《人文杂志》2006 年第3 期)、邓新跃《明代前中期诗学辨体理论研究·绪论(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34 页)、王宏林《格调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内涵》(《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 期)。
④参考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代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 页。
⑤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引黄庭坚语说:“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303页)
⑥陈善在《扪虱新话》中云:“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见宋俞鼎孙、俞经辑刊《儒学警悟》,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657 页)
[1]张少康,刘三复.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萧华荣. 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高棅编选,汪宗尼校订. 唐诗品汇·总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 怀麓堂诗话校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6]袁震宇,刘明今. 明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查清华. 明代唐诗接受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明]李东阳. 怀麓堂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杨国安. 试论中唐两大诗派创作中的共同趋向[J]. 文学遗产,2007(4):28.
[11]郑玄注,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春官宗伯下·大司乐[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朱彬撰,饶钦农点校. 礼记训纂(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3]陈旸. 乐书·乐图论[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周德清,中原音韵[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成复旺,蔡钟翔,黄保真. 中国文学理论史(明代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胡应麟. 诗薮·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沈德潜撰,王宏林笺注. 说诗晬语笺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