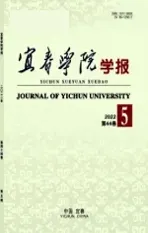论“仙婆”在当地中的文化隐喻——以广西平南县官成新新村为例
2015-08-15林业锦潘薇薇
林业锦,潘薇薇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在广西平南官成汉族人的日常生活中,民间信仰特别是“仙婆”之风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特色。“仙婆”即女巫,是旧时汉族客家人对女巫的称谓。其职能是请神问鬼,替人驱邪解厄。行术时于厅堂中置一桌,上放香炉烛台及敬祀物品,焚香烧纸后,即请鬼神降临,仙婆身体颤动,谓神灵已经附身。请神问鬼者,则可相对而谈。”[2]广西平南属汉族聚居区,随着时代的变迁,一部分汉族客家文化逐渐被非客家文化同化,但“仙婆”之风气仍然传承至今,但在程度上已逐渐被淡化。
一、平南官成“仙婆”法事的主要仪式
在平南县官成乡村民间,“仙婆”充当中介的法事仪式主要有“仙婆” “问米”、 “仙婆”庙会祈愿还愿、“仙婆”送鬼招魂三种。“仙婆” “问米”、“仙婆”庙会祈愿还愿、“仙婆”送鬼招魂等已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习俗和民风,影响着广大村民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模式。“旧时汉族的民间信仰风俗,信仰巫术的求神者,往往将巫师作为神灵的代理人”[3]比如王爷庙、观音庙、大王庙之类。“仙婆”在祈福和还福中充当着沟通人和神灵的中介作用。在当地,“仙婆”在整个祭祀活动中具有无上的神奇权威,架起了人神对话的桥梁。
(一)“仙婆”“问米”仪式
平南县官成的“仙婆”“问米”主要是就个人的问题向神灵请教。“问米”一般在“仙婆”家室内进行,“仙婆”家自设神坛,方便进行法事。一般来说,仙婆“问米” “问”的是“坟山”。 “坟山”是指已故者的墓地及其阴间生活,“问”坟山就是通过“仙婆”请神,仙婆神灵附体,将死者在阴间的生活状况及坟山的环境告之已故者家属。“问米”时,仙婆事先准备米盆1 个,里面放置1~2 斤大米,再放1 ~5 块钱,插上3 支点燃的香。接着,来“问米”家属及“仙婆”便围坐在神坛前,神坛上燃放2 根蜡烛,5 杯烧酒,3 杯清茶,在“问米”过程中,无需摆放鸡、肉、果、饼等供品。家属递交已故者生辰八字,示意“仙婆”问死者坟山,“仙婆”念了几句咒语,随即进入迷狂状态,其灵魂跟已故者交感,灵魂为已故者灵魂。随后,家属“问”已故者坟山状况,在阴曹地府生活境遇。“仙婆”均根据已故者的口吻一一复述。假若已故者答复过得很好,无需家人担心,则此“问米”法事可以结束,家人亦可放心;若已故者回答其在阴间境遇很糟,如坟山风水不行,过得不安宁,则需再请“仙婆”另做法事。 “仙婆”另做法事,须头绑红巾,左手执刀(5 寸见长的短刀),右手握剪,然后将之前盛装道具的米盆擎在头上。“仙婆”念咒文,请求神灵降临。站立于神桌前的“仙婆”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渐渐地动作越来越大,剧烈地晃动身体,并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尽管“仙婆”身体晃动厉害,但米盆依然稳当地顶在她头上。这时的“仙婆”如处仙境,“灵魂”已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身体,飞往神灵的世界,请神传话, “神灵附体”,降人阴间阎罗王处,下到地府查办何方妖孽作怪导致已故者坟山不安宁,待查办完迫害已故者的妖孽,“仙婆”扮演的神灵即告之家属应修缮或移迁坟地,多给阴间的已故者送去衣食住行之类的祭品,劝告已故者切莫回人间“作乱”。 “仙婆”如此“神灵附体”,传达给家属神灵的旨意。待“仙婆”恢复常态,对之前所作所为全然不知,这就加深了人们对其“神灵附体”能力的确信。
“仙婆”“问米”以幻想行为方式与神感应后为一般民众传输虚拟的神的旨意。“虚拟的神灵的旨意给求神者在从‘精神痛苦’向逐步摆脱痛苦的途中注入虚幻的心理慰藉,人们依赖、影响于装扮成神的人。”[4]这就是有“仙婆”作中介的“交感魔力”。
(二)“仙婆”庙会祈愿还愿仪式
“仙婆”庙会祈愿还愿的主要职责是帮别人祈福与还福。平南县官成的人们主要在比较有威望的庙宇里祈福,也叫“求神”。祈福时,需许下承诺,待愿望实现后,他日必须来还福,否则遭天谴。“仙婆”在做法事的过程中所用念唱的歌诀和咒语,由来已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乡民的道德文化意识。“在初民心目中,对这些咒语、歌诀的功用和灵力是确信无疑的,它们在心里上支撑着、强化着人们的信念。”[5]人们相信她是神的化身,神赐予其神秘的通达天人力量。认为仙婆是神灵在人间的使者。
若村民想到某“灵验”庙宇祈福与还福,需请来“仙婆”为其传递祭拜者信息以及下达神的“旨意”;若是有人生病或身体不适时,除了去医院或找大夫医治外,还会采用一些特殊的“仙婆巫术”仪式为病人“送病消灾”;家属为了表达对已故者的缅怀与关心,勿返人间“作乱”,以及告戒后辈要积善积德,特请“仙婆”请神下凡,通入阴间“查办”已故者状况,传达神的旨意如何“消灾驱邪”。
2010 年2 月2 日上午,淫雨霏霏,笔者、吴XQ、吴MN 和吴仙婆徒步爬山至平南县官成新坪村“勒封国王祖庙”祈福。胡仙婆嘱咐,进国王祖庙前必须洗手,以免玷污神灵。吴XQ、吴MN和吴仙婆带去的供品酒、茶、水果、糕点等一应俱全,不求数量多少,但求种类齐全。供桌上最靠近神像之处摆放一碗水,碗内放置艾草、柚子叶和柏枝。柏枝,意为“百子千孙”之意。紧接着的是盛放于特制祭祀用圆盘里的1 只全鸡和1 整块猪肉,均为制熟,再外面一排是饼干和桔子,最接近祭拜者处是5 杯茶水和3 杯酒。待吴XQ 点燃香和蜡烛,自报家门,向吴仙婆报上要祈求平安、财富、求子、文曲,吴仙婆就开始念唱了。
“香烟阵阵,酒肉满桌,今日我来到国王祖庙,诚请大王、二王、三王、土地、先锋皆主,请天兵天将下凡,为那林家LM 户啊,保佑佢LM 在广东求财,平安又顺利啊!”吴仙婆边舞唱边向神灵敬茶,腔调悠长怪异,吴XQ 和吴MN 在旁跪拜作揖,虔诚地祭拜众神。吴仙婆继续念唱,当中不时向神灵作揖,每次作揖都跪拜地上,往地上倒三分之一杯茶和1 杯酒。紧接下来吴仙婆继续为林LM 的4 个儿子祈愿。 “我二请天兵天将,来到那林家LM 户啊!保佑佢大仔林YC 啊!在中山求财,平安发大财啊!我三请天兵天将啊!保佑佢LM 二仔林YY 啊!在福建做生意啊!顺风又顺水啊!保佑佢出年成家,添丁又发财啊!”此时吴仙婆跪在地上,将茶杯里的茶下倒完,然后再倒一杯酒,站起来继续舞唱。“我三请天兵天将,天上的文曲星啊!来到那LM 户啊!保佑佢三仔林YJ,在大学读书啊,节节高升,毕业稳到好工作啊!”这时吴XQ 献上一匹红布,吴仙婆双手接过,边念唱边将供桌上的柚子叶沾碗里的艾草水浇到红布上,把红布的一边缠绕自己额头,再舞唱着爬上神坛,将红布披在五神肩上。然后继续念唱。“我再请天兵天将文曲星,保佑佢四仔林YC 啊!在梧州读书,学业进步啊!”念唱完毕,吴XQ 和吴MN 向五神捐钱,所捐之财物由胡仙婆代为收管。据吴仙婆称,香客所捐的钱物,会在功德榜上记录下来。
祈福的最后一步是求签。吴XQ 先为其二儿子求姻缘签,得上上签,吴XQ 大悦,认为3 位王、土地公和先锋显灵,她的积善积德开始应验,为儿子祈得一个好愿,承诺愿望实现后必来答谢。紧接着是吴MN 求签,所得是下签,吴MN 不悦。吴仙婆即问吴MN 是否平时没尽到积善积德,吴MN 若有所思,闪烁其词地回答的确有。于是吴仙婆告诫其日后要积善积德,方能化凶为吉。最后,燃放鞭炮,祈福仪式毕。最后,吴XQ 和吴MN 以及吴仙婆各取少许供品回家给家人吃,意为让神恩赐的平安幸福降临到每个人头上。这其中蕴涵了当地人心灵深处的平等意识与遭遇现实中的种种无奈。
在每次的民众祈福、完福活动中,只有仙婆才能恭请国王祖庙五神降临,使神像和自己充满神力,人神沟通才成为可能。神在接受敬拜的同时,亦将其力量投射在仙婆身上,仙婆成了一个精神符号。那么,人跟仙婆沟通,神的强大权力能给自己加上重重的砝码,这是一种民间巫风的遗存。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仅仅用虔诚的行为通过仙婆向神述说着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对神灵验的期许。人们亦相信五神会在另一世界倾听他们的倾诉与祈求。
(三)“仙婆”送鬼招魂仪式
在平南县官成乡村社会中,除了去医院找医生治疗外,人们还会采用一些特殊的“巫术”仪式为病人“送病招魂”。而这些“巫术”仪式的执行者,往往是病人的家属,一般是病人的奶奶。病人家属充当“仙婆”角色为病人“送病招魂”是平南官成乡村社会中非常普遍的方式。在有些笃信这种“巫术”神奇功效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稍有不适或头痛感冒等常见疾病也会采用此类“送病招魂”方式“治病”。病人家属往往根据病人病情及其得病前的行为又采取不同的送病方式,在此列举出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若某小孩白天外出像往常一样玩耍,傍晚回家后感到恶心、头晕等身体不适症状,当地人则认为是被故去的亲朋好友或其他恶鬼“念祚”,把小孩的魂招去了,于是其女性家长会充当“仙婆”为病人召回灵魂。其方法就是准备好白饭1 碗,些许炒好的黄豆,去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一般是岔路口(据说岔路口是各路野鬼交汇的地方,出现的频率较高)。女性家长充当的“仙婆”高喊三声得病小孩,“× × ×!返来咧!返来咧呜!”然后劝慰各路野鬼“吃饱了走你队的路去啦,别再来乱搞了!”说着将事先准备的白饭和炒黄豆撒向地上。“仙婆”归家后,忙说“× × ×返来了!”然后抱着得病小孩说“某怕某怕,耳儿在,耳儿在。”“仙婆”整个“送病招魂”仪式结束,随之是等待小孩的病愈。若小孩只是受到惊吓,不多久自然地病愈,人们便会将功劳强加在“仙婆”身上,是“仙婆”把小孩的灵魂“招”了回来;若小孩不见好转,便会借助科学医疗。村民深深的相信,不是“仙婆”“送病招魂”不力,而是野鬼太厉害,加上科学医疗定能将其制服。
二、“仙婆”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当然,广泛存在于乡村社会的仙婆巫术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从而导致很多人对“仙婆”巫术都所有一个偏颇的认识,认为其只不过是封建迷信的把戏,这正是我们所要批判的。然而,正如济群说的“信仰有助于净化人的心灵,找到人生的归宿,建立社会道德规范,引导人们继续古代圣贤探索真理的道路。”[6]“仙婆” “问米”、“仙婆”庙会祈愿还愿和“仙婆”送鬼招魂作为当地人的一种宗教信仰,也是我国宗教信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此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乡村“仙婆”文化,应该看到其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积极作用,不应一概将其看作是村民愚昧无知的表现和“仙婆”聚敛财富的手段,而是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挖掘其蕴涵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仙婆” “问米”、 “仙婆”庙会祈愿还愿和“仙婆”送鬼招魂三个仪式中,村民关心的是自己的祭拜能否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平安吉祥。村民对神的出身并不太在意,注意的是神明是否灵验,认为灵验与否是由乡民的积善积德心境决定的。对当地乡民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仙婆”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
广西平南官成的大部分“仙婆”法事行为所用的施法工具是日常生活用具、仪式也较为简单,职业化的“仙婆”在为人们送病消灾时的收费比较合理,生活也十分简朴,但“仙婆”假扮神所提供虚拟的神灵附体,“仙婆”法事所提供的心理观赏性,特别是人神共娱提供的“天人感应”的人神关系的神秘性,体现了我国古代巫文化的遗风。“仙婆”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地社会道德文化的进步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如通过“仙婆” “问米”、“仙婆”庙会祈愿还愿、“仙婆”送鬼招魂这三个仪式,时刻提醒村民要平日要多做善事,多积功德。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经济的冲击,当地“仙婆”巫风不断衰退。在祭祀的宗教与神圣色彩逐渐淡化的现代文化背景下,仙婆做巫时所展示的仪式演化为民间人情世故的表演,并进而积淀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二)当地人对“仙婆”文化的认识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跃发展,生产劳动的集约化。人们有时在面对天灾人祸或小私有的破产等情况产生绝望和恐惧心理。而内心冲突和不满情绪是每个人从来就有的。这就使人们似乎力求逃避现实,至少暂时忘却这一现实。更何况“宗教存在于人类社会有三种基本的功能,生存的功能,整合的功能与认知的功能。”[7]。笔者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除了它消极落后和迷信的本质主导作用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着积极的派生作用,特别是在宗教伦理道德方面,对民众起着积极的警示和教化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综观“仙婆”的法事活动,发现平南官成人以其个性化信仰方式彰显了本地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特质。在仪式的背后,隐藏的是乡民面对现实与理想而作出的适应性抉择。当地乡民固守其信仰阵地的现象,究其原因既有整个汉族的普遍文化背景,又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1. 当地人对善恶观念的认识。由于各种原因,鬼神观念在当地社会百姓的心目中依然存在,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生活在阴间。同时也认为人生前的生活行为和道德品性也决定其在“地府”的生活行为和道德品性。即生前作恶多端的人,在阴间也会变为恶鬼,时常来骚扰“阳间”善良的人们。同时在乡村社会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祖先崇拜”,他们认为亲人去世后,就会生活在“阴间”,可以看到阳间亲人或者子孙的生活状况及行为。当亲人在逢年过节时没有给他一定的祭品,他会来到阳间提醒他们或者惩罚他们。因此,只有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去攻击或“贿赂”才能祛除“鬼”对人造成的伤害。同时因“鬼”生前与自己的亲疏关系、生前的所作所为以及鬼出现的时间将其归为“善”或“恶”的不同类别,在“送病消灾”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果认定影响人们生活的“鬼”是自己的祖先或者是亲人,则采用比较友好的、给予祭品的方式送其回到阴间。如果认定“鬼”与自己生活没有关系或者是在阳间时常做恶的人,则一般采用刀、剪、尿液等具有攻击性或者污秽性的东西攻击。如果此“鬼”纠缠不休或者作恶多端,则采用更为复杂和严厉的“巫术”来惩罚。这就表现出了当地人对“家鬼”与“野鬼”、“善鬼”与“恶鬼”的区分与认识,也从另一个侧面警示人们平时要多做善事,多积功德。
中国人对天地人生的态度是现实的,这当中也包含一种来源于天地鬼神信仰的社会心理。当地人认为天行有常,顺应天命、天道,即无灾无殃。鬼神则聪明正直,把握着某种道德公理,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鬼神的监视。做人的正确与否,天地鬼神自有自由公断。这种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就是要讲究良心,待人处事要以“善”为标准。
2. 当地人对祖先观念的认识。“仙婆”“送病招魂”巫术在群体当中有广泛的信仰基础,当地大多数乡民相信其“神奇”的功效。这与当地汉族的祖先观念、鬼神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契合性是分不开的。“鬼”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说文解字》鬼部曰:“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贼害,从厶。”[8]一方面,“鬼”是祖先或亲人的灵魂,能给人带来保护。生者必须不停地通过各种“献祭”的仪式来祭奠,以此来沟通双方的情感。当因某种原因“鬼”不能享受祭奠时,就会以使人“得病”、“阳宅不安”等方式向生者“索取”祭品。另一方面,“鬼”是恶人或亲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灵魂,常常带有“恶性”,会经常“骚扰”或“攻击“与其无亲情的人。基于对这种鬼神观念的信仰,在较为封闭、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心目中,往往将得病的原因归结为“鬼”干预。
在平南县官成新新村,“送病消灾”巫术是当地民间文化和民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仙婆巫术“这类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其着调节器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平日单调生活辛苦劳作的调节器;另一方面,也是平日传统礼教束缚下人们被压抑心理的调节器。进一步看,这样一种调节器又起到了社会控制中的安全阀的作用。”[9]一方面,“仙婆”“送病消灾”可以增强人们抵御疾病和面对生活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人们对祖先的敬畏,提高故去亲人在群体心中的地位,加强故去亲人与生者之间的联络渠道。当村民对一些不可把握的事情而感到不知所措时, “仙婆”祭祀仪式正好提供了一整套人们与祖先灵魂沟通的一路媒介,以警示生者不仅要善对死者,应该在活着时善待每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安定“有福”的情况下得到“庇佑”。
总之,对现代迷信的根源,必须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分析,必须考虑与其相关的社会因素、认识因素和心理因素。对广西平南“仙婆”也应理性看待,既要看到其迷信成分,也要看到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1]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叶大兵,乌丙安. 中国风俗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3]季羡林,何立. 宗教词典[M]. 学院出版社,1999.
[4]张琪亚. 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2).
[5]李惠芳. 中国民间文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6]济群. 济群法师谈人生·当代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李亦园. 宗教与神话[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9]赵世瑜. 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