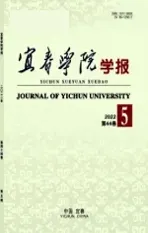默默无闻暗香在,“奇葩”亦当有春天——试论邵洵美的翻译思想
2015-08-15潘华凌刘弘玮
潘华凌,刘弘玮
(宜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近十年来,久被遗忘的邵洵美重新回到了学界的视野。随着研究的深入,邵洵美在中国新诗史、出版史上的功绩渐渐地“浮出历史地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①。然而,邵氏在翻译领域的实践和成就还鲜为认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翻译理论史上的地位还未得到应有的肯定。且不论国内几部近现代翻译史专著,如《中国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査明建、谢天振:2007)、《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郭延礼:1998)都对他只字未提,就连《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邹振环:2000)也只把邵洵美列为外国文学译著出版机构的创始人,而非“上海翻译出版界的‘当代英雄’②”。至于他独具特色的翻译思想及其中独到的翻译见解,在《中国理论史稿》 (陈福康:2000)、《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 (文军:2007)中更是踪迹全无③。对一生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④积极探讨翻译理论、撰写过大量译书书评的邵洵美来说,这样的待遇未免有失公允。
鉴于此,一些研究者开始对邵洵美的翻译活动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现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邵洵美的翻译实践上,如王京芳(2007)、易松明(2011)、刘弘玮(2012,2014a,2014b)列举了邵氏不同时期进行的译介活动,基本呈现了邵氏翻译实践的全景。而针对邵洵美的翻译思想和理论进行专题研究的只有杨晓斌、周永涛(2012)的《唯美的翻译 诗意的叙事——邵洵美翻译思想探析》一文⑤。该文从翻译定义、翻译态度、翻译技巧、翻译细节、翻译困难、诗人译诗等9 个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邵氏翻译思想的主要内容,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同时,该文局限于对邵氏关于翻译的诸多文献的呈现与解读,既无对邵氏翻译思想理论体系、翻译观的宏观评价,也少与同时期翻译家的翻译见解的微观比较,难以展示邵氏翻译思想的特色。
为此,笔者运用比较和对比的研究方法,探询邵氏翻译思想与同时期译家译论的异同,并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客观、全面地呈现邵洵美翻译思想的特色。从《谈翻译》展示的经验式和随感式翻译思想,邵氏“为艺术”的翻译观,邵氏独到的翻译见解等方面入手,凸显邵洵美翻译思想的独特性和超越性。
一、《谈翻译》展示的经验式和随感式翻译思想
从宏观的理论体系上来看,邵洵美的翻译思想主要是他从自身的翻译经验和对翻译的自我认知出发,对翻译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可以说经验漫谈有余而科学阐述不足,有些地方甚至有待商榷。他早期关于翻译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34 年发表在《人言周刊》上的译学论文《谈翻译》中,散见于他的译书序言、译书书评中。后者自然无需赘言,我们不妨观察一番《谈翻译》一文中关于翻译策略分类的情况。
文章多处显露出作者主观臆断的痕迹,对文学作品翻译的起始时间、“热闹”的划分标准未加以说明,全凭作者的感觉。此外,“我觉得”、“我总把”、“据我所知”、“在我个人意见”、“我相信”、“我确信”等类似短语充斥全篇。这种情形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者对翻译定义、翻译态度、翻译策略、译入语表达力等的看法属于他个人的主观判断。因缺乏科学的分析、阐述,文章有种“信不信由你”而非“信不信在理”的意味。
作者把当时译界对“意译”、 “直译”、 “硬译”翻译策略争论的原因归结为对翻译的不当定义,即“太把翻译当为是商业的或是政治的事业”。而只要把翻译“当成文学工作”,且对中西文字有“充分运用的才能”、“彻底了解的修养”,则“意译”、“直译”、“硬译”便根本不值得讨论了。诚然,对翻译的不同定义确实会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不管翻译定义如何,都改变不了其“运用两国文字”的本质。诚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任何“两国文字”都不可能在语言的意义、形式、风格上完全一致。因此,作者试图通过消除文学翻译中双语在表意、传神上的差异(“原作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的正确解释,力量与神韵”可以“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来解决对“意译”、“直译”、“硬译”的争论收效甚微。事实上,作者文章结尾处对翻译策略的三种分类同上述分类之间只是用词表达上的不同,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他对翻译策略的三种分类分别是:一是林琴南(林纾)的“要原作来迁就中文的文字能力的范围”的翻译。二是徐志摩和苏曼殊的“相信中文尽够有表现原作的能力”的翻译。三是朱维基的“觉得原有的中文不够丰富,要用一种新的中文结构去表现原作精神”的翻译。 (陈子善,2006:131)邵洵美对分类中的第一种持否定态度,这与“五四”以来中国译界对林琴南翻译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值得一提的是,文章根据译者对译入语的表现能力的不同看法来对翻译策略进行分类,这在整个翻译理论史上是很罕见的。鉴于当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徐志摩和苏曼殊的翻译应该属于“意译”,而“用一种新的中文结构去表现”的翻译则属于“直译”,甚至“硬译”。
不过,就邵洵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国译论传统而言,他在翻译理论上暴露出的缺乏逻辑严密性的缺陷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从形式上来说,《谈翻译》是一篇比较系统论述翻译问题的专题论文,在当时并不多见。况且,中国传统译论大都在“序跋文章⑥”中加以展示,至晚清时,才出现了“长篇论文和条陈、建议⑦”,民国时期的一些译论也多以“译书的序跋”形式呈现。虽说当时也有不少翻译专论,但多半也是译者从自我经验出发,对具体翻译问题,如意译、直译、翻译选材、译者要求、译诗方法等等的探讨。以文军(2007)在《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中统计的从1894-1934间的31 篇翻译论文为例,这类论文就有20 篇,其余的则涉及对具体翻译、译作的评论、翻译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邵洵美译论的理论性程度在同时代人的译论中是比较高的。
二、邵氏“为艺术”的翻译观
邵洵美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对翻译是“运用两国文字”译界没有争议,但对翻译是否是“文学工作”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邵氏的“文学工作”是针对“商业的或是政治的事业”来说的,矛头直指当时译界有人通过翻译途径来实现经济、政治诉求的社会现象。
邵氏的这种翻译观有深厚的自身原由。首先,他的翻译起源于他中学时代对教会学校学到的外国诗歌的翻译,并试图通过诗歌翻译来创作新诗⑧。他最早发表的新诗便是“半创”、“半译”的结果。因此,他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起就是“文学的工作”。其次,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名门望族,经济实力雄厚,足以支撑他对文学的嗜好。他在从事翻译工作时无需承受任何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一切翻译活动皆源自对原文的喜好、原文的美。最后,他留学欧洲期间,接触到了大批“追求形式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作家,进而接受了唯美主义文艺思潮⑨。他强烈反对文学(当然包括翻译文学)与政治的“合作”、 “联姻”。他在《自记笔记》中专门讨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与政治合作是“可耻”, “革命者把文学当革命的利器”会遭到“革命文学家的反对”,“文学家把文学来改良政治”会被“讥为天语”。他倡导“写文章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对文学本身的爱好”,“预备挨饿而写文章的作家”是“英雄”。 (陈子善,2006:126)他把翻译定位为“文学工作”,就是强调翻译也是为了文艺本身的美和价值,是“为了艺术”的“艺术”,从而彰显了他唯美主义的翻译观。
但是,不管邵氏认同与否,翻译文学与政治“合作”、“联姻”的翻译观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有其存在的理由与空间,且成为了当时译论的主流。20 世纪30 年代,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巨大内忧外患,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有识之士、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纷纷发挥自己的专长,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如此背景之下,一切文学活动,包括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进步翻译工作者以翻译作武器,参与社会改革是时代要求使然,不以个人喜好为转移。此外,这种翻译观也是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我国译论从晚清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有关翻译的现实功用的论述”,而这“确实是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特色”。 (陈福康,2000:195)20 世纪20 年代,以郑振铎、矛盾(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与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之间就翻译的功用与目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郑振铎强调“通过翻译介绍,为中国文学的第一步打基础”,又提出翻译介绍的“两层的作用”,即“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陈福康,2000:221)矛盾指出翻译的动机(目的)“除主观的强烈爱好心而外,还应该有‘适合一般人需要’、 ‘足救时弊’等观念”,而且“后者更是合理的”。 (陈福康,2000:233)他们批判当时郭沫若等人的唯美主义翻译观,因为后者“不赞成郑振铎、矛盾的翻译介绍‘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的意见,强烈反对文艺的‘功利主义’,认为这种意见是‘文艺的堕落’”。 (陈福康,2000:259)如果说20 世纪20年代人们对翻译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问题尚有争论的话,那么到了30 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为人生”的翻译观便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译论的主流观念,就连郭沫若后来也纠正了自己之前对翻译的看法。
邵氏此时提出“为艺术”的翻译观,显然不符合当时的译论主流和趋势,是“另类”,是“奇葩”,但却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为人生”的翻译观功在介绍社会变革急需的“现代的思想”,那邵氏的翻译观至少对当时译界为了经济、政治目的而盲目、胡乱的译介有所警示。在此观念指导下,邵氏大量的对唯美主义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的译介至少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
三、邵氏独到的翻译见解
邵洵美的上述观点致使其翻译思想长期受到译界的忽视和诟病。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把他的翻译观看作是缺点、瑕疵的话,那也是“瑕之有理”、“非瑕之瑕”。更何况瑕不掩瑜,无法掩盖其翻译思想中的闪光点。
(一)动态的翻译目的论
邵洵美在《谈翻译》中用了较大篇幅来讨论“须要先决的问题”,即“翻译的态度”,也就是翻译的动机或目的。他把翻译动机归纳为两种:“主观的或为己的”和“客观的或为人的”。邵氏的这一分类与矛盾(沈雁冰)关于翻译的动机的分类几乎如出一辙,但侧重点各不相同。后者重在论证文学翻译中“客观的动机”的合理合法性,前者侧重于翻译目的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效果之间的内在和动态的关联。出于前种目的,译者更多地关注自己的需要,“以一己的眼光为标准”,选择与“自己的性格相像”、与自己的创作“神韵吻合”的原文文本,翻译简直成了“创作”,翻译的标准是: “对原作、原著人、译者自己”负责,以致译作像是原作在译入语中的“重生”。而出于后一种目的,译者更多地是关注译文读者,以“人家”、“一般人”(即读者)的眼光去选材,翻译成了“散布的工作”,标准是“使读者读了译作和读了原作得到同样的效果”。(陈子善,2006:131)尽管当时翻译家,如罗家伦、傅斯年、矛盾、邹韬奋等对翻译目的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翻译选材之间的关系多有讨论,但都局限于对二元关系的探讨。而邵洵美展现的翻译多元因素间的内在、动态的关联无疑更为深刻、全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式的目的论”。我们认为,邵氏的这种独到的翻译见解,是他翻译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理应受到现代翻译理论史家的关注。
(二)辩证的诗歌可译观
邵洵美的一生都与诗歌翻译有缘,中学时期翻译外国诗歌,留学后翻译唯美主义诗歌,晚年翻译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他的诗歌译作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赞扬。秦瘦鸥指出,他翻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等的诗作都能达到“信、达、雅”三项要求。赵毅衡对他翻译雪莱的几部长诗的评介是“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准”,以致其“读原作反而没有那种战栗”。此外,邵洵美本身就是诗人,出版了3 部诗集和一部译诗集《一朵朵玫瑰》。作为诗人翻译家,邵洵美对诗歌可译性的见解可以说是权威而又独到。
邵氏认为,如果译者“自己不是个诗人,他便一定不能译诗”,因为即便他“对于某国文字是精通”、“对他本国文确是有根底的”,译作也确实在“文法上或字义上”没有“错译”,“在文法上也绝不会不通”,但那不一定是诗,因为“诗是神秘的”,其文字具有“唯有诗人方能会晤的神秘。”邵氏对非诗人不可译诗的观点表明,诗歌是可以翻译的,只不过诗歌的译者须具备诗人的气质与条件。这与郭沫若的“诗人译诗”是一脉相承的。邵氏总结的诗歌译法“以重音来计算音步”是对可译性的拓展。邵氏成功地翻译诸多诗歌的事实,以及诗歌翻译史上成功的案例,也是对诗歌可译性最好的证明⑩。
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承认有不可译的诗歌,即便可译,也必会有所损失。他在谈现代主义的诗时说到, “他们的技巧既全在文字”,以致“无法向不认识他们文字的人解释了。”在此,他要表明的是,翻译中双语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是部分诗歌不可译的原因。而他翻译莎茀的《爱神颂》时,无法顾及其中的韵格。翻译迦多罗斯著名的情诗时,只能将其大意以诗歌形式译出,并感叹“原诗音节缠绵,值得反复歌颂,可恨翻译是绝不能保存原诗的音节”。(陈子善,2006:78)在他看来,诗歌翻译的损失是必然的,或是韵格,或是音节,又或为音乐美。
由此可见,他对诗歌是否可译问题的看法是辩证的:既肯定诗歌的可译性,又能具体地看到译诗中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以及不可译的原因。这种诗歌翻译观是对矛盾关于诗歌可译性的悲观、抽象观点的超越,因为后者认为,“有可以译的,也有万对不可译的,而可以译的也是‘聊胜于无’”。(陈福康,2000:240)
(三)超前的文化翻译观
20 世纪30、40 年代,邵洵美是上海滩非常活跃的文化人,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主动同来到上海的外国文人进行交流,如美国著名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英国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裔美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 –1973)等等。他推荐西方文学作品,传递西方文坛的最新出版信息,努力培养热爱西方文艺的“文化班底”。他对外译介中国的文学作品,创办《声色画报》以展示中西双方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与碰撞,通过及《直言评论》对外通报中国文学和抗日战争的情况。邵洵美这种中西交流的经历和意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对翻译的看法,让他超前地从宏观的文化视角来看待翻译。
他在译书书评《评伍光建译<约瑟安特路传>》中,不仅指出了译文中的错误,而且阐明译者错译的原因:由于对小说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了解。我们据此可以知道,他对翻译的认识:翻译不只涉及对语言字的理解,还与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掌握有关。在他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译本的序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在翻译中对“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的重视。此外,邵洵美在译文后附加的原注、自己的加注,甚至还有译者自记、原作者的生平见解、译者小注等(可见于邵氏的译诗集《一朵朵玫瑰》)无一不说明了邵氏的文化解释学翻译观。
通过上述对邵洵美翻译思想所作的横向、纵向的比较与对比,我们看到:邵氏的翻译思想和他的文学观是一脉相承的,强调翻译与政治想脱离,艺术至上。这正是他的翻译思想不受当代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史家忽略的重要原因。但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邵氏的翻译思想自有其合理之处,且其对翻译的诸多独到的见解,毫无疑问具有理论史的价值。在当今倡导学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文艺领域,邵氏翻译思想这朵“奇葩”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注释:
①不过否定的观点仍然很尖锐,刘纪新博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连续发表了两篇以“邵洵美并不‘美’”为主题的文章:《邵洵美并不“美”——驳近年来关于邵洵美的翻案文章》(见《中国图书评论》,2013 年第8 期),《邵洵美并不“美”——应谨慎评价邵洵美的诗歌成就》(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8 期)。
②本书第七章专门有一节介绍了上海翻译出版界37 位“当代英雄”,其中包括了当年作为青年编辑经常登门拜访邵洵美的翻译家王科一和著名翻译家、诗人、莎士比亚研究大师方平,后者后来成了邵洵美的女婿。参见邹振环《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12 月)和盛佩玉《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 月)。
③更加令人感到诧异的是,由吴笛博士等编著的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之一的《浙江翻译文学史》(杭州出版社,2008 年1 月)和吴笛博士撰著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的《浙籍作家翻译艺术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4 月)二书均只字未提浙江余姚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和出版家邵洵美。
④罗莉芳曾撰《论邵洵美在上海的文学、文化活动》一文,系统介绍了邵氏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在上海期间的文学文化活动情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该文载2008年6 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0—369 页。
⑤刘弘玮在《邵洵美翻译面面观》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简述了邵氏的翻译思想,主要介绍邵洵美于1934 年发表在《人言周刊》上译学论文《谈翻译》中表述的思想和散见于其书评、发刊词、译后序、文集自序中的观点,内容涉及翻译的定义、翻译态度、翻译技巧、翻译目的、翻译评论、译文质量和译者素养等等。该文载于《宜春学院学报》2014 年第4 期,第103—106 页。
⑥最经典的莫过于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1896 年),其中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成为一百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邵洵美对严复提出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评价:“严氏论翻译所谓‘信、达、雅’三事;‘信’与‘达’人言甚是,惟对‘雅’字,每多怪论。此处‘雅’字不作‘高雅’、‘风雅’、‘古雅’解,严氏之意无非是‘文章好’而已。近人译文,以最上品而言,信则至多九十分,达则可有九十五分,文章好的却少得可怜。盖目前译文学作品者,未必皆文人也。”见盛佩玉《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第274 页。
⑦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书》(1894年)、梁启超的《论译书》(1897 年)、胡以鲁的《论译名》等。⑧本文关于邵洵美的生平资料主要参考了邵绡红的《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版。
⑨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是19 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一场组织松散的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1-1900)。唯美主义者主张人们应该热情地拥抱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并声称艺术与道德之间没有关联。唯美主义文艺思潮于20 世纪30 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坛颇有影响,“新月派”文人徐志摩的诗明显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
⑩诗歌翻译历来被看作是最具挑战性和最艰难的译事之一,而诗人译诗则是中外翻译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早在17 世纪,西方翻译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起了诗歌译者的身份问题,英国杰出诗人、翻译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曾指出:杰出的译诗者必须是杰出的诗人。因此,著名翻译理论家谭载喜认为:“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的翻译在质量上比不上散文翻译,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翻译家是学者而不是诗人,译诗却必须本人也是诗人”。中国诗歌翻译界也有众多译者和诗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学者、诗人、翻译家王佐良说过:“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诗人朱湘也指出:“惟有诗人才能了解诗人,惟有诗人才能解释诗人。他不单应该译诗,并且只有他才能译诗”。综观20 世纪中国诗歌翻译史,许多脍炙人口和影响深远的译著均出自著名诗人之手,如苏曼殊译拜伦的《哀希腊》、郭沫若的《鲁拜集》、梁宗岱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方平主译的诗歌体《莎士比亚全集》等。又如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诗歌的汉译,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译文或译本均出自徐志摩、朱湘、查良铮(穆旦)、朱维基、赵瑞蕻、屠岸等杰出诗人或具有诗歌创作背景的翻译家之手。参阅卢炜《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载2013 年7 月29日《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陈子善. 洵美文存[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3]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4]刘弘玮. 邵洵美的翻译成就[J]. 兰台世界,2012,(1):15-16.
[5]刘弘玮. 邵洵美翻译面面观[J]. 宜春学院学报,2014,a(4):103-106.
[6]刘弘玮. 邵洵美与翻译[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b(7).
[7]卢炜. 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J]. 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07-29.
[8]邵绡红. 我的爸爸邵洵美[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9]盛佩玉. 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王京芳. 邵洵美和他的出版事业[M]. 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7.
[11]文军. 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12]杨晓斌,周永涛. 唯美的翻译 诗意的叙事——邵洵美翻译思想探析[J]. 外国语文,2012,(3):94-97.
[13]易松明. 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翻译家邵洵美[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2):91-94.
[14]査明建,谢天振. 中国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15]邹振环.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