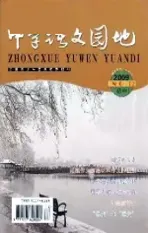这篇名作语病多
——《故都的秋》语病诊疗
2015-08-15罗献中
罗献中
[作者通联:河南固始县教师进修学校]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散文名作。该文脍炙人口,韵味悠长,历来深受读者喜爱。很多现当代散文选本都将该文编入其中。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白璧有瑕,这篇美文中竟然存在不少病句,经不起推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文的“美好形象”。毋庸置疑,作为文化传承者,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现代名家名作,不必为尊者讳,更不必掩饰其缺点和错误。基于此,我们现将这篇名作中的几处主要语病列举出来,并略作剖析,“以正视听”。
1.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
该句在副词“将近”与数词“余”的使用上明显存在抵牾,使该句在关于时间的表达上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将近”的含义是“(时间、数量等)快要接近”,含有“不足”之意;而“余”则表示“大数或度量单位等后面的零头”,含有“多出”之意。可见,“将近”与“余”恰好含义相反,两者岂能连用?所以,“将近十余年”这种表述前后矛盾,令人不知所云:究竟是十多年还是不足十年呢?消除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根据实情,将“将近”和“余”这两个“冤家对头”删除其一,保留其一。
2.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该句的主语“这秋蝉的嘶叫”和宾语“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搭配不当。句中的主语中心词是“嘶叫”,宾语中心词是“家虫”,这两个概念表示的事物属于不同类别,不能组成判断句,即“嘶叫”是(或不是)“家虫”说不通。根据句意,可将主语的中心词和修饰成分进行调整,改为“这嘶叫的秋蝉”,这样就可与“家虫”形成同类并组成判断了,即“秋蝉”是“家虫”,这才可以说通。
3.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
该句用错了连词。连词“但(但是)”连接的前后部分在逻辑上是转折关系。在该句中,连词“但”的前后两部分,在内容上相同(即“外国的诗人”与“中国的文人学士”一样,也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两者属于并列关系,并非转折关系。所以,该句中不能用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但”,而应该使用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而”。
4.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
该句存在动词“感到”和宾语“深情”搭配不当之错。“感到”一般以动词和形容词作为宾语,如“感到高兴(气愤、震撼、亲切)”等;而不能以名词作为宾语,否则说不通。而“深情”是名词,因而不能与“感到”形成正常搭配,即“感到深情”说不通(可以说“感受深情”之类)。另外,既然是“不能自已的深情”,即说明这个“深情”不是出自“秋天”,而是出自“囚犯”自身;不是囚犯从外界“感到”的,而是自身产生的。所以,根据句意,应保留“深情”,而把“感到”改为“生发”、“触发”、“产生”之类的动词。
5.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
该句弄错了短语“很普遍”所修饰的对象。由句意和逻辑可知,“很普遍”的事物其实是各种“读本”,而不是《秋声赋》与《赤壁赋》,因为它们只是两篇文章而已,并不能说是“很普遍”。因此,应调整“很普遍”在本句中的位置,使其与它本来要修饰的对象“读本”发生关系,联系起来(当然,字面上也要相应地略作变动)。具体而言,该句可以改成“……读本里又很普遍地有着欧阳子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
这些语病对这篇名作而言可谓不该出现的“硬伤”,是令人遗憾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作者在创作该文时一挥而就、未作仔细斟酌和修改之故。据作者之子郁飞回忆,本文是作者被当时北京某杂志编者到家中逼索出来的“急就之章”,随后即被拿去发表。(见郁飞《关于我父亲的〈故都的秋〉》)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将这一背景向学生作些适当说明,以解学生对本篇名作出现诸多语病的困惑。当然,瑕不掩瑜,这些病句在该文中毕竟只是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这篇名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