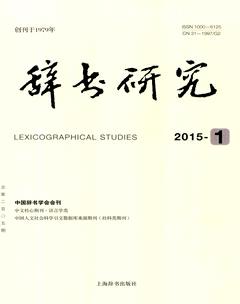《海篇直音》新考
2015-07-31韦乐韦一心
韦乐+韦一心
摘要《海篇直音》是对明成化本《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的“抄袭”之作,但却是中国第一部商业性字典。它的编撰和出版是书商和文人共同运作的一次成功的商业行为。它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明代弘治十二年(公元1498年)至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之间。作为一部在明清之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字书,它在中国字典编纂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海篇直音》《篇海》新考
《海篇直音》(全名《经史海篇直音》)是一部古代大型字书。全书所收字头数远远超过后来的《康熙字典》,达5万5千多个,总篇幅约50万字;其注音则统一采用直音,是中国第一部全直音字典。晚明时,它曾与明代最权威的官方韵书《洪武正韵》并列,成为皇帝的御用工具书,崇祯帝“凡经书有疑难字义、典故,即《洪武正韵》、《海篇直音》及《韵小补》等书,自搜查之。”
尽管它曾有过风光的历史,然而清初《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收录,近现代以来,若干重要的语文研究著作如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和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也未予提及。
这样一部巨型字典,就其现存最早版本——嘉靖二十三年刻《新校经史海篇直音》(本文所引《海篇直音》文献皆出于此)来看,其文本没有作者署名,没有成书时间标注,甚至没有序跋及任何文字介绍。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字书?在中国的字典发展史上,它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呢?
对《海篇直音》的研究,在国内是个冷门,除了西华师范大学杨正业的《〈海篇〉成书年代考》(《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和《语文词典编纂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有专门章节论述外,很难再看到相关的文章。而在邻国日本,对该书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深度。大阪大学的大岩本幸次的《关于明代海篇类字书群的几个问题》和《明代海篇类字书知见录》从版本学角度对《海篇直音》进行了介绍。
国内外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杨著认为《海篇直音》成书于南、北宋交替之时,最可能是金国人所作。对它极力推崇,称《海篇直音》“是汉语语文词典编纂史上第一个收字达五万以上的字典。它为尔后大型字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杨正业 2006:160),并且认为,在中国字典史上,《海篇直音》将大型词典的部首归并为444个,首创部首之下按笔画排序,444部首以“五音”“三十六母”为序的编排方式。而大岩本幸次则认为,《海篇直音》来自金代韩道昭《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又名《五音篇海》,以下简称《篇海》),对《篇海》进行了全面直音化改编。
真相究竟如何?笔者对《海篇直音》全书每一个字头及每一条注释进行了详细比勘和考证研究,可知杨著的结论是错误的(下文对此将有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将结合明代中晚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探讨。
一、《海篇直音》除将注音彻底直音化外,全面“抄袭”成化本《篇海》
在本文全面展开之前,很有必要首先消除一个误区——彼《海篇》非此《海篇》。
杨正业在《〈海篇〉成书年代考》中认为《海篇直音》(他简称为《海篇》)成书于南、北宋交替之时,此观点是从《篇海》和《海篇直音》中两个字头的释文中推演出来的:
1.《篇海·糸部》七画倒数第四字“”下引《馀文》曰:“,举禺切。《玉篇》元有,《海篇》脱,今增。”[1]但凡书籍引用,只有后世引用前世的,不可能颠倒。《篇海》既引《馀文》,而《馀文》又引《海篇》,由此,《海篇》便该是《篇海》的爷辈,成书应比金代的《篇海》早很多。
2.《海篇直音·金部》有这么一条:“,古文,音注,出《类篇》。”[2]据此,他推断《海篇直音》诞生于北宋《类篇》之后。
杨先生断定第一条材料中《篇海》提到的《海篇》就是《海篇直音》,于是凭借上述两点,推算《海篇直音》成书于南、北宋交替之时。
然而事实是:上述《篇海》中提到的《海篇》根本不是《海篇直音》。因为就在《海篇直音》里,在与《篇海》完全相同的位置上——糸部七画倒数第四个字——“”字赫然在目,它所标注的“音惧”,则与《篇海》所注“举禺切”完全对应。(上述《海篇直音》引《类篇》那一条,也同于《篇海》)
《海篇直音》明明有这个字,《篇海》却注“《海篇》脱,今增”,这充分说明此处的《海篇》与《海篇直音》根本不是同一本书。而查阅《篇海》的金刊崇庆本和元刊至元本,一切便真相大白——原来“”字及其注释根本就是成化年间文儒等人在修订《篇海》时加上去的。金、元本《篇海》在这个位置安放的是引自《奚韵》的“綄”字(《奚韵》的代号为黑圈●)。因“綄”字其实是个重收字(同笔画下第23个字即是),文儒等人“挖疮补肉”地删“綄”补“”,并在注音后加按语“《玉篇》原有,《海篇》脱,今增”。这个“”字是文儒等在宋本《玉篇》中见到而添上的,既不是《馀文》的字,也不是原本《篇海》的字。根据笔者的详细考证,文儒等人的按语所说的《海篇》,竟然是指韩道昭的原本《篇海》。在成化本《篇海》中,还有一处将《篇海》称作“《海篇》”的文字,即第五卷目录中“鬯部”的批注:“此鬯字原在穿母收之,《广韵》、《礼部》、《海韵》俱是丑亮切,《玉篇》、《海篇》是敕亮、敕向切。今将鬯部下七字移于彻母,永为后来检篇之便尔。”文儒等把“鬯部”从穿母挪到彻母,并添了这段批注,而对比金、元本《篇海》,原“鬯部”的确是在穿母收列,当然也没有这段批注。文儒等的批注完全符合金、元本《篇海》原况,其所述的“《海篇》”则正是指原本《篇海》。
对于成化本《篇海》中这两处称韩氏原本《篇海》为《海篇》的现象,如果不以金、元刊本《篇海》校勘,任何人都会因时空的颠倒而被弄糊涂。不过,成化本修订者们称韩氏《篇海》为“《海篇》”的行为在明代也并非孤例。弘治至正德间的释真空在其编撰的《篇韵贯珠集》中也将韩氏编《篇海》的行为叙述为“改并《玉篇》今成《海篇》”。(《四库存目丛书》第213册)
关于文儒等人修订原本《篇海》为成化本《篇海》的功过是非,笔者另撰文《〈篇海〉大揭秘》予以详细介绍,此不赘述。既然上述误区已解除,那么回到正题,来看看《海篇直音》是如何“抄袭”成化本《篇海》的:
1.部首雷同显现“抄袭”
《篇海》列444部首,所有部首按其读音依五音三十六声母排列次序,同声母下依平、上、去、入四声依次罗列,这是《篇海》的一个创举,其书名曰“五音类聚四声”也正是基于此。《海篇直音》没有相应交代,但其排部也同样如此,它与成化本《篇海》唯一的不同是在排列次序上将“马部”从部序第174位挪到了第190位,即从明母上声挪到明母入声结束之末,成为明母的最后一个部首。这个变动涉及范围并不大,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因为“马部”本属明母上声。《海篇直音》如此操作,显然有违声律体例。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木版雕刻之际出现一时遗漏,待发现时“木已成版”,无法改动,而扔掉重刻则成本太高,损失太大,于是只好在明母末尾补刻,好在并不太影响普通读者阅读。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成化本《篇海》已将金、元本《篇海》列于第十一卷中穿母之下(总序第282位)的“鬯部”改列在第五卷彻母之下(总序第116位)。对此,《海篇直音》完全照搬,所以它的“鬯部”位置也同于成化本而异于金、元本《篇海》。这成为它“抄袭”成化本的一个最有力证据。
2.两书所收字头数量雷同再现“抄袭”
成化本《篇海》444部首总收字数自身标注累计55479字,实际55521字。正德本《篇海》删去一些重复字,又补上四百多新字。《海篇直音》内不见正德本所补字,而更接近于成化本。《海篇直音》收字数自身标注累计55048字,实际54885字。这和成化本有几百字的差距,为什么还说二书收字数雷同呢?因为通过比勘,可知数字的差距主要源于《海篇直音》编者对成化本进行的加工及古代字典编撰过程中很难避免的脱漏。
就《海篇直音》对成化本的加工而言,它或是删去很多《篇海》的重收字,如“见部”在《篇海》中标注为“凡二百二十七字”,《海篇直音》则标注“凡二百二十四字”,经考查,《海篇直音》删去三个重收字:視、、;或是发现了《篇海》的脱漏而改正标注数,如“牛部”在《篇海》中标注为“凡三百二十九字”,但实际只有323字,《海篇直音》面对这实际存在的323字,又删去了它认为的一个重复字“”,自标为“凡三百二十二字”。因此,两书的收字数应是相同的。
《海篇直音》虽纠正了成化本《篇海》因脱漏而产生的标记数与实际数不吻合之误,自身却也犯着同样的毛病。仍以“见部”为例,《海篇直音》将《篇海》“凡二百二十七字”改为实际数“凡二百二十四字”,但在刻录时又漏刻“、、、、、”六字,故实际数仅218字。
如果承认《海篇直音》的自标数而忽略其刻印时的脱漏字不计,并且假定它删除重收字而不影响其雷同性,纯粹从理论上讲,《海篇直音》应该比成化本《篇海》多九个字。这是因为《篇海》有九个部首竟然忘了将部首字形自身列入字头。即:“亠部”漏列“亠”字、“歲部”漏列“歲”字、“章部”漏列“章”字、“卓部”漏列“卓”字、“興部”漏列“興”字、“學部”漏列“學”字、“部”漏列“”字、“羸部”漏列“羸”字、“令部”漏列“令”字。《海篇直音》全部予以补列,因此理论上多这九个字。
3.五万多字字序雷同率达97%以上
与成化本《篇海》比勘,《海篇直音》所收的五万多字头,除了“页部”有一二百字的次序有稍大挪动外,其余的443个部首中仅有个别字有前后挪动之差异。举两书的第一个部首“金部”为例,全部首1031个字头,次序全同的有1008字,另有22字是紧挨的上下邻字或左右邻行间挪了位,显然是刻录时疏忽所至;另有一个九画的“锻”字被挪到该部末尾,应仍是刻录时脱漏,校对发现后被补上的。再以一个小部首“巳部”为例,全部首26字,两书的次序完全相同。这样大的雷同是惊人的。
4.最重要的“抄袭”证据——《篇海》有上千处错讹被《海篇直音》复制甚至被延伸
《篇海》的错讹很多,有的是原本《篇海》的错,有的是成化本修订时产生的错。对此,《海篇直音》不仅全盘接收,甚至据错延伸。下面列举它延伸成化本《篇海》特有错讹的几个例子:
《海篇直音·气部》:“二音葵,天也,君也……”
此二字早在《集韵》中就被注明是“乾坤”的“乾”的异体字,但怎么会“音葵”呢?原来是成化本《篇海》反切注音将“渠焉切”误刻成了“渠爲切”。《海篇直音》按错误的反切音注直音“音葵”。金、元本《篇海》注音皆是“渠焉切”,连正德本《篇海》都是“渠焉切”。
《海篇直音·目部》:“音梨,自取。”
此字《群籍玉篇》和金、元本《篇海》引《川篇》皆注释为“音梨, 目”,成化本《篇海》误刻为“自”,《海篇直音》再错为“自取”。错误轨迹显而易见。
《海篇直音·宀部》:“音進,远也,函也。”
此字为“”的俗字,《群籍玉篇》和金、元本《篇海》皆注释:“疾葉切,远也,亟也……。”《海篇直音》错误注音“音進”和错误释义“函也”,完全来自成化本《篇海》的错误刻写:“疾禁切,远也,凾也……。”
《海篇直音·比部》:“音皮,人賫物状也。”
且不说《海篇直音》释文中“人賫物状”一语的晦涩难解,其实这个字头“”根本就是成化本《篇海》制造出的、在此之前从不曾有过的杂糅怪字。究其原因,那是因为古书竖列行文,“”和“毗”本是一组异体字。成化本《篇海》刻印时将两字完全挤成了一个字,在注释中又出现严重的脱漏和错字,由此引发出天下奇错。让我们看看事实真相:
成化本《篇海·比部》引《馀文》:“,房脂切。《说文》曰人色。今作毗……。”
《群籍玉篇》和金、元本《篇海》引《馀文》:“毗,二房脂切。《说文》曰人(脐)也。今作毗……。”
两相比较可知:成化本《篇海》释文中脱漏了极其重要的“二”字,又将“人(脐)也”误刻为“人色”。《海篇直音》肯定对“人色”感到费解,于是改为同样令人费解的“人賫物状”。因为其中“”字可能为“(賫)”字。《海篇直音》如此这般以讹传讹并延伸错讹,已经不须再多费笔墨去证实了。
5.不打自招——《海篇直音》书中不小心承认了“抄袭”事实
自成化本开始,明代各种版本《篇海》的书前“杂部”之后,都列有16个字的“拾遗”,它们是成化本修订者从《五音集韵》上摘出的,称为“《韵》有,旧《篇》元无。今且暂列于此,便于拣讨之易耳”。这16个字中,有两个字“ 、”其实在原《篇海》正文中已经存在,前一字位于目部第十五画,后一字在力部倒数第六字处。明代修订者或是粗心,或是对部首分设和字头归部不熟悉而未发现,误将这两个字列入“拾遗”。所以,“拾遗”中真正不被原《篇海》正文收录的是下列14个字头(各字头下本有注释,今略):
列于14个字末端的“慧”字被《海篇直音》归入“心部”第十一画,且在其本身音义注释结束后追加了一句“原系拾遗,今且列于此”——由此彻底暴露了它“抄袭”成化本《篇海》的事实——因为《篇海》有“拾遗”,正是从成化本开始的。
二、《海篇直音》是中国第一部“商业性字典”,它的编撰和出版,是明代书商的一次成功商业运作
明代以前,无论字书或韵书,中国古代字典的编撰和出版都不曾以赢利为目的。编撰大型字典耗时既久,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亦巨,故历来与牟利不沾边。用现代人的话表述,编撰大型字典的投入和产出从经济角度讲极不划算,十分的人财物投入往往只有一两分的经济回报。因此在中国的字典编撰史上,我们常常见到皇帝下旨编大字典,或是高官显贵、文化名人及高僧不求挣钱只求文化传承或扬名立万而编大字典,这类字典付梓时往往还伴有富豪资助。例如成化本《篇海》的万安序中就记载“适司设太监贾安、房懋来礼寺,睹兹成书,欣然捐赀绣梓”。但是到了明代,情况却有了变化。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业极盛的时代。自明初洪武起,统治者就重视和鼓励发展出版业,采取减免税收、放宽限禁等有利于出版业发展的政策。明中期以后,商业经济日益兴旺,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物质生产更加发达,印刷技术亦有很大进步,这些都推动着出版业走向空前的繁荣。而另一方面,明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受此影响,天下慕学向学之风愈发浓厚,所谓“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由此导致明代中后期知识阶层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全社会文化素质更加提高。在这些背景的综合作用下,彼时文化消费空前高涨,出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图书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在向市场索取其他书籍的同时,也一定在渴求字典这种工具性的书籍。
编书牟利此时已经成为可能和现实,而且正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明代出版业中滋生了许多不良现象。其中,“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叶德辉 1957:182),“意在变幻,以新耳目,冀其多售”(四库全书总目1997:1763)便是一种典型的恶习。就大型字典而言,运作者只要大大减少人力财力投入,大大缩短编撰出版时间,赢利就是可能的。但这样一来,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抄袭(也称改编)或盗版了。《海篇直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大字典。前文所述的它将“马部”放在明母末尾,以及将“金部”九画的“鍛”字补在该部末尾二十几画之后的做法,可谓是宁错也不返工,也正体现出书贾节约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海篇直音》不署作者名,也无序跋,这种做法正是当时书界改头换面、剽窃抄袭的典型表征。只不过,它“抄袭”得很巧妙:它将《篇海》的反切注音全转换为直音注音,释义也力求简洁,这使它看起来似乎比《篇海》更具有面向大众的实用性。而这种做法,找个内行高手,一年就可完成编撰,两年内就可上市。于是,一部由《篇海》改头换面而来的《海篇直音》就出炉了。
《海篇直音》的版式整齐美观,字头横竖对齐,再不像《篇海》那样字头只求竖正不讲横齐而使页面胀满显得杂乱,而且其简明扼要、通俗易查,收字繁富而篇幅不大。畅销书所应具备的条件它几乎都拥有,市场效果可想而知——据不完全统计,传世近五百年,《海篇直音》至少有十种版本存世,而失传的版本则不知还有多少。版本多证明印得多,印得多证明销得多,书商们在这个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自是不言而喻了。
综合考察中国字典发展历程之后,可以发现,《海篇直音》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商业性字典,而且它的成功运作显然已经打开了字典出版商业化的大门。到了明代晚期,题名中含有“海篇”或“海”字的大型字典竟然冒出二三十部,它们几乎都是《海篇直音》派生出的商业子孙,蔚为大观的它们俨然成为明末一种不可小觑的出版现象。对此,笔者将另文撰述,此不赘谈。
三、《海篇直音》成书时间
《海篇直音》全部文本中没有任何涉及其成书时间的文字。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就其所见到的北大图书馆所藏万历三年刻本《海篇直音》上的文字记载,推断《海篇直音》“当纂成于成化辛卯以后”,“万历三年以前”。
王先生推测的这个时间范围(1471—1575年)达一百多年,虽然正确但却不够精确,尚有较大的压缩空间。其实,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百川书志》上已经记载了《海篇直音》这一书名。而《百川书志》的编撰刻印出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故《海篇直音》的面世最晚可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而关于时间的上限,笔者认为早不过弘治十二年(1498年)。
弘治十一年,京都大慈仁寺高僧真空出版了《篇韵贯珠集》。该书内容主要是指导读者如何查阅使用韩道昭的《篇海》和《五音集韵》。真空在书中称《篇海》为“改并《玉篇》今成《海篇》”,还有另一句称《五音集韵》为“改并《广韵》成《海韵》”。(《四库存目丛书》213册三512页)一个《海篇》,一个《海韵》,真空形象地概括韩氏两书像海一样博大精深。而真空其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正德本《篇海》的修订者,《篇海类编》中就记载有他编的《等子韵》。中国古代小学家许多出自僧侣,如玄应和慧琳(编《一切经音义》)、可洪(编《随函录》)、行均(编《龙龛手鉴》)等。真空的成就与他们相比或许在伯仲之间。从真空绝非一孔之见的话推断,至少在弘治十一年时,“海篇”二字尚未成为《篇海》之外别的书的专用书名,也就是说《海篇直音》应该还没有面世。同时,笔者通过考察《海篇直音》中“”字的直音用字,可以推断《海篇直音》的编者参考了《篇韵贯珠集》,使用了《篇韵贯珠集》的“成果”:
《海篇直音·女部》:“,音随。”
这个“”字是个耐人寻味的会意字。从字形看,是“身体重在女子上面”,其读音在《篇海》“女部”中引《搜真玉镜》“音挼”。“挼”为多音字,主读音近ruo,很像表示男女性事的詈词。在中国不少方言区,俗称性交的字的读音即为ruo或ru或ri。这种字对于戒色的僧人来讲,应该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真空竟没有回避,他在《篇韵贯珠集》中根据“挼”字主音之外的另外读音,选择性地为“”另注了“素回切”的反切音。(《四库存目丛书》第213册)
《海篇直音》的编者应该读过《篇韵贯珠集》,并且似乎对“”有了新的解读——身边负重的女子,应该可以理解为“随附”或“紧随”,所以它刻意将《篇海》的“音挼”改为“音随”,与《篇韵贯珠集》所注“素回切”完全吻合。对于《篇海》全书30%左右的直音,《海篇直音》都是原文照搬,唯独“”字改动了直音用字,成为上万字中的特例。
由此推论,假如《海篇直音》编者在第一时间(即弘治十一年)就读到《篇韵贯珠集》,那么他们最快也要第二年(即弘治十二年)才能成书。因此《海篇直音》成书时间可以收缩为弘治十二年(1498年)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之间。
然而事实上,《篇韵贯珠集》是本小册子,很难引人注意。在明代信息传递并不畅达的情况下,《海篇直音》编撰者在第一时间读到该册子的可能性很小。而小册子在正德八年再次刻印,之后几年又随正德本《篇海》和《五音集韵》合刊出版。因此,笔者认为《海篇直音》编撰者更有可能是在正德年间读到《篇韵贯珠集》。由此,笔者推论《海篇直音》诞生于正德至嘉靖初的可能性最大。
四、《海篇直音》的价值和地位
作为一部“抄袭”的字典,《海篇直音》还谈得上价值和历史地位吗?答案却是肯定的。
尽管上文似乎对《海篇直音》批评多,肯定少,但其实笔者使用“抄袭”这个贬义词时,一直是加了引号的。因为笔者认为《海篇直音》编者的行为与当代常规意义的侵权抄袭有区别。
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的“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概念,后人修改、改编前人著作是常见的事。以字典编撰为例,唐人孙强修改《玉篇》、宋人陈彭年再次修改《玉篇》、陈彭年改《唐韵》为《广韵》、邢准和韩孝彦分别改编《类玉篇海》为《群籍玉篇》和《五音篇》、 文儒等修订《篇海》等等,都没有被学界认为是抄袭、侵权。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基于两点:其一,他们是公开改动,并且说明了来龙去脉,也确实根据相应的标准增减了很多内容;其二,许多案例在改动后仍然保留了原作者姓名。比如《玉篇》,无论唐本、宋本、元代本,无论增减多少内容,都署为南朝顾野王。
《海篇直音》与上述诸书不同,除去注音形式外,它和《篇海》的雷同率高得离谱,更使人不舒服的是它既不署名又未说明来龙去脉,感觉有些偷偷摸摸、瞒天过海的意图。但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并不应该全盘否定《海篇直音》,中国字典编纂史该为它留下一个位置。
第一,《海篇直音》是中国字典史上第一部全直音字典。
中国古代字典绝大部分采用反切注音,或反切音和直音混用。而全书注直音,《海篇直音》是第一部。比它早几十年有章黼的《直音篇》,虽名曰“直音”,却仍保留了个别反切注音,不能算是全直音字典。《篇海》收字5万5千以上,其中近70%采用反切注音,只有30%注直音。反切注音不够通俗,其中有很多读音特别是入声字读音很难准确拼读出来,而注直音则直观明了,大大方便了读者识读汉字。
《海篇直音》将《篇海》中原注反切音的近4万字全改注直音,应该说完成了一项大工程,为后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不仅如此,《海篇直音》所选择的直音用字,不少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很多是用本字(正体字)为异体字注音,给后世的文字研究者沟通异体字关系指明了方向。下面略举两例:
《海篇直音·辵部》:“,音逮。”此字为“逮”的异体字。(《篇海》原注释“徒亥切”)
《海篇直音·辵部》:“,音奩。”此字为“奩”的异体字。(《篇海》原注释“力兼切”)
第二,《海篇直音》是中国第一部商业性字典,忽略它不太光彩的产生过程,它为后世打造学术与市场价值俱佳的字典提供了借鉴。
文化产品,其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是一对很难统一的矛盾。或曲高和寡,或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大型字典更难做到既有高学术水平又是畅销书。但是,文化人既然有“文化”,他们就会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借鉴前人好的经验,借鉴别种文化商品的成功案例,最终打造出高品质的畅销字典。
明末清初,《海篇直音》在知识界肯定是一部人尽皆知的字典,类似于今天的《新华字典》。有几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1.《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科试考四》载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礼部郎中奏本弹劾科场舞弊,要求复核,其中对第十一名李鸿的指责便是其“《论语》篇腹中有一‘囡字,考之《海篇直音》,‘囡音匿,谓私取貌。询吴之人,土音以生女为囡,此其为关节明甚矣……”。
2.冯舒(此人为明诸生,入清不仕,钱谦益学生,著名诗人和诗论家)在评南宋陈师道诗时曾说:“全是形模,如村学蒙师着浆糊褶子,硬欲刺人,自谓矩步规行,人师风范,时读一字异人,其音亦正,然案头所有,《海篇直音》而已。”(傅璇琮 1978:899)
据此两例可知,《海篇直音》在当时文人笔下是信手可拈的工具书。同时,我们还可以在清代早期编成的《康熙字典》中见到该书多处引用《海篇》(即《海篇直音》)。由此看来,《海篇直音》客观上对明末清初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恐怕是该书的策划者和编撰者未料到的。
五、待解的谜团
1.《海篇直音》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未署编者,从而使编者是谁成为暂时抑或永远的谜。这个谜团是否是当时的书商刻意设置的?当时是否有人知晓?执笔人难道甘心让世人永远不得真相而未留下半点痕迹?
2.明万历司礼监制本《海篇直音》(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图书馆)中,有“万历三年四月十七日司礼监奉旨重刻”字样。这句话可能是真实记载,抑或是书商的广告用语。如果是真实记载,那么万历皇帝为何会为刊印一本无名氏的书下圣旨?另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有明天启元年刊《海篇直音》,记载有“天启元年二月吉日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实、高世明、沈荫、宋晋、魏进忠、刘克敬奏请重刊”的字样。如果这也是真的,那么《海篇直音》已是第二次沐浴皇恩了。尽管《海篇直音》是当时的一部知名畅销书,可是真的至于皇帝两次下旨刊印出版么?原因何在?另外也可以假想,既然有人启奏,奏书中总得讲清楚该书的来龙去脉吧?万历、天启年离《海篇直音》初始面市时间不算遥远,说不定奏书中就载有编者的姓名和成书时间。
笔者盼望了解该段时期明史档案的方家能查到当时的圣旨和太监们的奏折,或许能破解上述谜团。
附注
[1]韩道昭《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成化、正德、万历本皆此。
[2]《新校经史海篇直音》嘉靖二十三年金邑勉勤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231册。
参考文献
1.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8.
2.纪昀(清).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刘若愚(明).酌中志(卷之四).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4.杨正业.语文词典编纂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5.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
(韦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430073)
(韦一心成都市兴蓉街19号一栋二单元601室四川610041)
(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