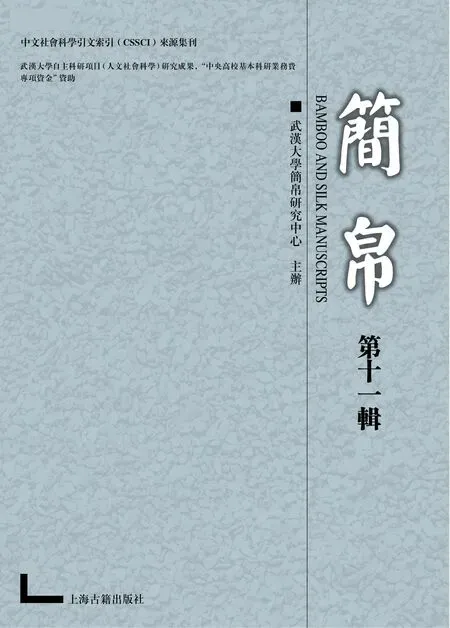漢簡“折傷兵物楬”試探*
——兼論漢邊塞折傷兵器的管理
2015-06-28樂游
樂 游
漢簡“折傷兵物楬”試探*
——兼論漢邊塞折傷兵器的管理
樂 游
西漢武帝時期,漢朝對匈奴主動戰略反擊,大啓封疆,從元狩到元鼎年間,在新獲的河西地區陸續設立郡縣。太初三年(前102)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漢書·匈奴傳》),逐步建立了河西走廊的烽燧亭鄣等邊塞防禦體系,是對抗匈奴、保障内地安全的屏障和基地。百餘年來,在河西漢代邊塞遺址,尤其是漢代居延、敦煌故地出土了數萬枚漢代簡牘,是當時河西行政、軍事、生活真實而生動的記録。漢塞爲軍事候望系統,許多漢簡反映了兵器管理制度和具體規程,頗能補史籍之闕。近年來,據漢簡研究兵器管理制度這一課題頗受學界關注,並已取得不少成果。*相關論著如黄今言: 《秦漢時期的武器生産及其管理制度》,《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第7—14頁;趙沛: 《居延漢簡所見〈兵簿〉〈被兵簿〉——兼論居延邊塞兵器配給》,《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第20—29頁;黄登茜: 《漢簡兵簿與漢代兵器論考》,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01年;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90—120頁;韓勇: 《漢簡所見邊塞兵器裝備及其管理制度》,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範大學2009年;范香立: 《漢代河西戍邊軍隊後勤保障考述》,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09年;趙寵亮: 《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54—263頁。我們擬在時賢的基礎上,通過一枚簽牌(正式名稱爲“楬”)上文字的改釋,劃分出一類新型簽牌,再勾稽相關簡牘,以求進一步完善對漢代西北邊塞折傷兵器管理規程的認識。

圖1
20世紀30年代出土的居延舊簡中編號爲266·14的木簡(圖1)出於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A8)。此簡保存完整,尺寸爲10.3× 0.9釐米,上端兩側各有一契口,用以繫繩,正面書13字,背面8字,字迹潦草。從形制和内容看,該簡是一枚簽牌(楬),但製作比較草率,可能屬倉促修治、臨時使用。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衹著録此簡背面照片,在《考釋之部》中亦僅録背面釋文。*勞榦: 《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研院史語所1957年初版,1992年影印一版,第317頁;勞榦: 《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研院史語所1997年影印五版,第109頁。社科院考古所編訂的《居延漢簡甲乙編》(以下簡稱《甲乙編》)中雖無正面照片,卻給出了正面釋文,並標明“失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册)》,中華書局1980年,第190頁。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自20世紀80年代末重新整理所藏居延舊簡,重拍此簡圖版並公佈於“漢代簡牘資料庫”中,學者始得見全貌。*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藏漢代簡牘資料庫(http: //ndweb.iis.sinica.edu.tw /woodslip_public /System /Main.htm)。我們先將晚出且質量較高的《中國簡牘集成》(以下簡稱《集成》)釋文移録於下:


西北邊塞漢簡中“豐”字有下列諸形:


漢代及以後的文字中豐、豊二字常混用,*林澐: 《豊豐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第181—186頁。但上舉諸字皆爲人名,古人名豐者甚多,而且出身下層的戍邊吏卒,也不至於以不常用字“豊”爲名,故皆應用爲“豐”。諸例字形依次趨於草化,程度較高的後三例下部與A似相近,但即使是在這三例草字中,也明確無誤的突出了上部“曲”形作爲特徵筆畫,與A的上部實不相類。是故釋A爲豐缺乏字形依據。





簡文正面“第十八”應是序數烽燧“第十八燧”的省稱,漢簡中多有烽燧名省去“燧”字之例,如:
(44·24)
(73·23)


(EPF22∶469A)


(敦煌1818A)

“完”即完好無損之意。據漢簡資料,當時箭矢在裝備時一般以五十枚爲單位裝入一“蘭”(籣),配備給單兵使用。*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93頁。另外,百矢爲一單位,與西周金文對箭矢的記載相合,可見一脈相承之制。在存放狀態下,則似乎習慣將兩個單位的箭矢,即百枚置於一處,加綴一枚簽牌。簡(1)雖是箭矢簽牌,但不管是從形制、内容、格式上還是從所標識的數量上,都與(5)~(7)一類大相徑庭,顯然不是存放箭矢的簽牌,而是一種新見類型,其用途、用法尚需討論。我們頗疑它與折傷箭矢的管理有關,是候官屬下各部烽燧所配屬的兵器發生折傷現象後,向候官上交時所加綴的説明情況的標籤。
漢代西北邊塞各烽燧配備的弓弩、箭矢、有方、盾等兵器一般由候官、都尉府等上級單位負責發放,如“第二燧三石具弩一,建昭二年受官”(326·4)、“第廿燧卒□丘定,有方一,刃生,右卒兵受居延”(311·2)是其證。*311·2 之“居延”或以爲指居延縣,如趙寵亮: 《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第261頁。按,應以理解爲同屬軍事系統的居延都尉府更合理,且甲渠第廿燧接近居延中心區域,在一定情況下由都尉府武庫提供兵器,是可能的。西北烽燧地處漢帝國邊防前哨,承擔着防禦外族入侵,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功能,故其所配兵器是否齊全完好,一直受到重視。候官下屬各部候長須逐月以“被兵簿”、“被兵名籍”等簿籍呈報所屬兵器狀況,*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93、101頁。如:

(EPT59∶48)
候官一級單位還要將相關資料按年度彙總存檔。對於破損折傷的兵器,各烽燧還要編制“兵完、折傷簿”等簿籍上報,由候官按月上報都尉府(EPT52∶453),並至少每季度歸檔一次(174·34),其形式大致如下:


六、完軍三。
(75·17)
(11) 稾矢七,羽幣(敝)
(45·14)

(EPS4T2∶76)



除了這種例行的檢查與呈報外,上級部門派出官吏“行塞”,巡視各部、燧時也會對烽燧的兵器狀況進行檢查,有時甚至還會有朝廷委派的官吏到邊塞“循邊兵”、“行邊兵”(如135·2、7·7A等所記)。這些過程中如發現問題,還會形成“舉書”以彰其過:


(EPT6∶67)
(15)爲文書簽牌,“卒兵舉”即關於吏卒兵器的“舉書”,(16)之“如舉”是“如舉書”之省。其既言“作治”,可能是對於某些缺損程度較輕的兵器先要責成部、燧戍卒就地修治,如:
(3·26)

(18) 元延二年八月乙卯,累虜候長敞敢言之。官檄曰: 累虜六石弩一,傷右橅。受降燧六石弩二,其一傷兩橅,一 傷右橅。遣吏持詣官,會月廿八日。謹遣驩喜隧長馮音持詣官,敢言之。
(170·5A)

(57·11)
由(18)知各燧兵器由所在的部統一上繳,而且明文規定須以吏而非戍卒致送,亦可見其較爲重視。(19)中的物品還要由候官送到更高一級的都尉府。各部、燧吏“詣官”上交折射兵器這一過程在漢簡中可以稱爲“還”,如下揭諸例:
(20) 隧長張嘉,休,還四月(?)兵物
(EPT17∶4)

(EPT52∶408)




圖2
由簡(1)的改釋我們發現了明確寫有“還”字的兵器簽牌,證明了漢代邊塞折傷兵器歸還過程中需要用到這種臨時的簽牌。有它作爲基準,我們可以對下面兩枚簡牘(圖2)的性質作出推定:
(145·16)

二年兵。
(EPT53∶78)
二簡均出甲渠候官,皆單面書寫,簡下端平齊,未見殘斷,前兩字之間的位置皆有契口。簡(23)尺寸爲10.5×1.1釐米,(24)爲 10.3×1.8釐米,都與簡(1)的長度近似,而稍短於漢尺的半尺,這樣的長度顯然是不適合編入漢代最常見的一漢尺規格爲主的簡册中的。再參照契口的形制和簡文内容,它們應當都是與交還折傷兵器有關的簽牌。另外,三簡寬度與漢簡中常見的 “札”(單行)或“兩行”簡大致相當,而長度約合大多數簡牘(1漢尺)的一半。類似的簽牌漢簡中較常見,多屬比較簡易者,可能不需要專門製作,而是取常用的一漢尺長的木簡從正中横斷後,再剜出契口即可。
次吞燧和第卅一燧都是甲渠候官所屬的基層部燧,分屬吞遠、鉼庭兩部候長統轄。簡(23)所謂“詣官”應即指遣人赴候官交還這五枚折傷的箭矢,與我們前面所描述的過程正可相應,箭矢數量上也合乎情理。簡(24)在描述弩的折傷情況後加注“二年兵”三字,在漢簡中是比較少見的,推考文義,“二年”所指應當是該弩發放的時間,即與書寫時間屬同一年號的某“二年”,故可以不必專門指出。這樣標注的目的或與交還折傷兵器時便於核對之前記載配發信息的簿録有關。這兩枚簽牌中(23)更可能在次吞燧上一級的吞遠部製作,(24)則不能排除在第卅一燧即製作完成的可能性,然後隨所標識的折傷兵器一起被送到更高級别的甲渠候官。值得注意的是,簡(1)、(23)、(24)同爲歸還折傷兵物時使用的簽牌,但它們的簡文内容除了皆標明兵器名稱及原屬信息外,似乎並無嚴格的書寫格式,而是隨具體情況有所變化,這可能與它們衹是起臨時標識作用,衹需讓經手人明白情況即可,故不必規定專門的程式有關。另外,河西屯戍漢簡中時見一些原屬某烽燧的實物簽牌,出土地卻在候官或其他烽燧遺址中,它们之中是否也有與折傷器物的交還有關者,是值得考慮的。而在通過所出漢簡比定烽燧的漢代名稱的研究中,這種因素也是應考慮在内的。*在比定漢塞遺址性質的研究中,封檢和簽牌所記録的燧名的重要性顯然要高於文書類的簡牘,但是有時也會産生一些問題,如居延舊簡中出於甲渠塞A6(可能是T11)遺址者有“第十六燧”的簽牌和封檢,而額濟納漢簡出土後,學者多認爲T9爲第十六燧。邢義田先生曾對類似情況提出疑問,説見邢義田: 《全球定位系統(GPS)、3D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以額濟納河烽燧與古城遺址爲例(增補稿)》,《地不愛寶: 漢代的簡牘》,中華書局2011年,第230—236頁。
要之,簡(1)、(23)、(24)這三枚簽牌是漢代邊塞折傷兵器交還過程中使用過的簽牌實物。它們的重新釋讀與歸類,不但深化了對“簽牌(楬)”這類特殊簡牘本身形制和用途的認識,也提供了新的材料,使我們對河西漢塞兵器管理中折傷兵器繳還的具體操作流程有了更加完整的把握,從而進一步加深對漢邊塞兵器管理制度的認識。
附記: 初稿寫成後曾蒙吴振武師、林澐先生及同窗胡永鵬兄審閲指正,謹致謝忱。
*本文寫作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牘學大辭典”(14ZDB027)、國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兩漢、吴、魏、晉簡牘文字的搜集與整理”(項目編號: 0610-1041BJNF2328 /07)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