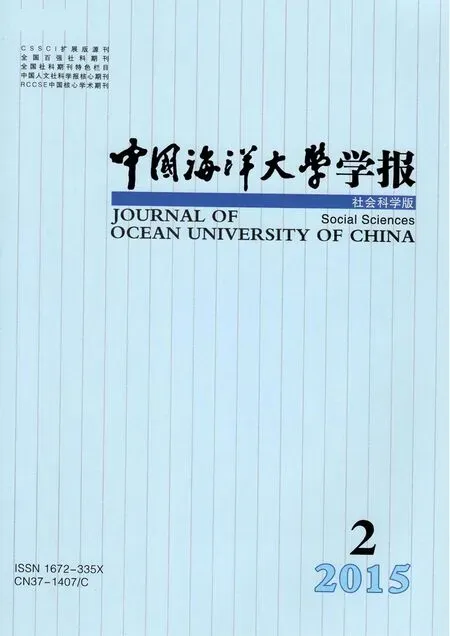短时记忆在国内二语习得中的研究述评*
2015-06-12徐方
徐 方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短时记忆在国内二语习得中的研究述评*
徐 方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短时记忆是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本文分析了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的关系、短时记忆的特点和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从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回顾了近15年来国内短时记忆教学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内短时记忆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和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短时记忆;工作记忆;二语习得;述评
一、引言
近年来,在二语习得方面涉及到心理过程的研究日益广泛。[1]在二语课堂和二语日常使用中,短时记忆牵涉到每天的语言运用,学生每天使用第二语言所做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短时记忆有关。
(一)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的关系
在20世纪60年代,短时记忆研究——在短暂的时间段在大脑中存储少量信息——构成了认知心理学发展的要素。人们在构建短时记忆信息处理模式的尝试方面产生了一些争议。遗憾的是,借助当时适用的方法无法清楚地解决这些争议,而这也导致了70年代大家对短时记忆研究兴趣的减弱,甚至随后宣告了该项研究的终结。[2]正当短时记忆这一旧观念逐渐失宠时,它被并入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工作记忆中了。工作记忆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对短时记忆系统特性的研究。工作记忆主张利用多成分系统取代单一储存体系,即通过大脑所储存的信息促进复杂的认知活动,诸如学习、理解和推理等,[3]Baddeley & Hitch的工作记忆模式不仅在认知心理学、而且在神经系统科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都极具影响力,1986年由Baddeley修改更新。到了80年代,人们对工作记忆的研究兴趣持续升温,尽管在大西洋两岸研究侧重点不一。90年代,得益于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成果,整个大西洋地区对工作记忆的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飞速发展,正是认知心理学和工作记忆神经心理学二者之间卓有成效的关系很好地助推了这一发展。
传统的短时记忆概念描述了一种几乎被动的短暂记忆储存,通过即时串行回忆信息来评定容量。[4]从时间上说,工作记忆的概念更时新一些,它描述的是一种更动态的体系,在认知活动中涉及到信息的短暂保留和转换。Baddeley等人的工作记忆模型分为三部分:视觉空间模板(Visual Spatial Sketchpad)、语音环(Phonogical Or Articulary Loop)和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 System)。工作记忆同时具有储存和加工两种功能,储存功能相当于短时记忆的功能,即在一定的时间内保存一定的信息;而加工的功能则和加工容量的概念有关。[5]工作记忆对语言学习(主要是母语学习)的诸多方面(如词汇习得、语言理解与语言表达、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6][7][8]从信息加工模式看,无论Broadbent提出的模型雏形,还是后来备受心理学家关注的Atkinson和Shiffrin的三级加工模型,[9][10]都强调短时记忆是信息加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并且短时记忆在功能上起着工作记忆的作用。由于巴德利提出,短时记忆是按照工作记忆的方式来活动的,所以,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工作记忆就是短时记忆概念的延伸,[11](P159)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来自相同起源。
(二)短时记忆的特点
1、练习效应(Effects of Rehearsal)
Atkinson和Shiffrin论述了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换信息的理论,强调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几项促进习得知识的控制处理策略:练习(Rehearsal)、编码(Coding)和意象(Imaging)(三种初始的学习方法)。[4][12]Atkinson和Shiffrin集中研究一种口头练习(Verbal Rehearsal)。口头练习被认为是一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form of rote learning),通过重复而不是通过理解记忆,因为这意味着反复练习信息直到我们认为已经学会。因此,学习抽象和无意义的材料鼓励使用练习。
Craik和Lockhart提出深层处理原则(Depth of Processing),认为重要的不是信息被练习多长时间,而是在多深的层次得到处理,强调死记硬背并不是行之有效的记忆方式,忘记开始于背诵停止的那一时刻,因此只有通过深层的有意义的记忆处理方式,才能更好地记忆。[13]相对来说,短时记忆中的忘记比较迅速,这是因为被记忆的项目是在一个相对浅的听觉(视觉)层次被分析。同样,记忆项目在长时记忆中的保持归因于深层处理,尤其是分析记忆项目的意义。我们越是把当前经历与以前储存的信息相结合,越容易记住他们。深层处理原理推翻了Atkinson和Shiffrin的口头练习转换到长时记忆的原理。
2、编码不同(Coding Differences)
Conrad、Baddeley、Kintsch和Buschke,Shulman、Conrad & Hull,Wickelgren和Wickens从不同角度进行试验,归纳出两种编码形式:听觉代码形式和语义代码形式。[14]
3、保留功能(Retention Function)
短时记忆保存信息时间短暂,如未得到复述,将会发生迅速遗忘,只要记忆项目的数量不变,识记材料性质的改变对短时记忆的遗忘进程没有多大影响。[15][16]因此应减少干扰(release from proactive interference),我们可以通过排列信息结构,即减少信息中的同类项来把干扰减小到最低程度。[17]
(三)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所谓信息提取,又称检索,指把储存在假定的记忆系统中的特定信息取出来以便使用。[18]它涉及许多问题,并且引出不同的假说,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
最早开展短时记忆信息提取研究的是Saul Sternberg。[19][20]他在研究中提出了相加因素法,认为短时记忆信息提取过程中做了系列搜索(Serial Search),而不是同时对所有元素进行检查(即平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因此Sternberg认为短时记忆信息提取是从头至尾的(Exhaustive)的系列扫描方式,而不是自我停止的(Self-Terminating)扫描。在这个过程中,识记项目与记忆集中的每个项目都会进行比较、匹配,然后作出是或否的选择判断。Sternberg的观点后来遭到Carballis、Theios,et al以及Townsend和Morin等人的反对。[21]
Wickelgren、Eysenck]提出直通模型(直接存取模型,Direct Access Model),[22][23]即提取不是通过比较或搜索,而是直接通往所要提取的项目在短时记忆中的位置,即直接提取。
Atkinson和Juola将搜索模型和直通模型结合起来,[24]提出了搜寻—直通混合模型。该模型认为,被试是基于探测词在主观熟悉量表上或高或低的值来作出反应的。
对作为信息加工最后阶段的信息提取的研究,无疑对揭示短时记忆的规律有重要作用。
二、国内短时记忆研究
根据从中国期刊网(CNKI)上搜索的相关学术期刊来看,语言输入方面的研究比语言输出相对多一些。研究者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探讨二语学习者的认知与心理过程,开始关注短时记忆/工作记忆的认知功能对二语学习过程的影响。同时他们还围绕短时记忆/工作记忆对语言输入(听力和阅读)、语言输出(口语和写作)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语言学习年限篇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语言输入听力1988-200421通过短时记忆提高听力理解理论介绍、教学经验总结为主的非实证性研究20023句法简化、短时记忆与听力调查实验;统计分析;实证研究20054抑制机制、可理解性输入、短时记忆和听力问卷调查与实验调查相结合;实证研究20063做笔记、听力和短时记忆访谈和学生内省;实证研究20083认知负荷理论、工作记忆、视听材料和听力教学问卷调查和访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20094听写、收听笔头记录、听力焦虑、听力动机与工作记忆/短时记忆理论分析;问卷调查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20102多种输入方式、工作记忆与听力理论介绍;实证研究20114图式、注意与工作记忆对听写的影响、信息结构与听力理论介绍;实证研究20122英汉互助记忆、语块、短时记忆与听力理论介绍;实证研究阅读1995-20055阅读速度、推理模型、图式、控制性阅读、预测与短时记忆理论介绍和教学经验总结为主的非实证性研究19981句法歧义与工作记忆实证研究2006、20072阅读技能迁移与工作记忆、词汇量与工作记忆实证研究2008、20092工作记忆障碍与阅读、课程资源开发与短时记忆理论介绍和教学经验总结为主的非实证性研究10-136工作记忆、句子处理与阅读实证研究语言输出口语2007-20123语调输入、语块教学、双语控制与工作记忆理论介绍和教学经验总结为主的非实证性研究20091工作记忆与口语流利性实证研究20122口语输出、语音回路与工作记忆实证研究20131口译的源语理解与记忆负荷实证研究写作20103策略构思、修改策略的个体差异、干预时机与工作记忆实证研究20122工作记忆超载、有效负荷与写作实证研究
从表中可以看出,语言输入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1998年在阅读方面有实证研究,2002年在听力方面开始实证研究;语言输出方面起步较晚,2009年在口语方面有实证研究,写作的实证研究开始于2010年。在这四个分水岭之前绝大部分研究属于思辨性的理论探讨和经验介绍,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强调短时记忆/工作记忆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方面。分水岭以后,逐渐从短时记忆/工作记忆的理论介绍和经验探讨走向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研究方法也逐步从描述性的思辨研究走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然而,由于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还有不少课题有待探讨:二语学习者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短时记忆/工作记忆进行学习?短时记忆的信息是如何提取的?与大量研究成年人工作记忆与语言理解之间联系的调查相比,在这方面针对儿童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短时记忆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来进一步论证短时记忆对二语学习的影响。吴潜龙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二语习得过程,提出一种以工作记忆为中心的模式。[25]桂诗春认为记忆在语言学习中占有中心地位,应通过增加可理解度以优化输入。[26]温植胜认为工作记忆为外语学能重要构成要素,对外语/二语学习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27][28]戴运财、蔡金亭引用Robinson的观点,提出工作记忆本身并不能等同于语言学能,因为学能综合体还包含其它的认知能力。[29]因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语言输入方面
通过阅读、听力或观看有标志的符号或图像,语言理解需要花费时间。为了理解说话者(或写作者)所表达的整体思想,听者(阅读者)首先要在一句话被表达完整之后记住句子开头的几个单词或词组,因此,这就是短时记忆的目的:在阅读和听力中提供持续性。[30]McCarthy和Warrington提出短时记忆的三种功能:语言理解、问题解决和通往长时记忆的途径。[31]
1、听力
在国外,从外语学习的角度研究短时记忆的实验为数不多,值得一提的两个实验中的一个是考尔的听力实验,考尔认为短时记忆是听力理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2]徐方复制考尔的实验运用到以英语为外语的中国学生,得出的结论是:短时记忆是听力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句法的短时记忆在提供可理解性输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33]国内对短时记忆在听力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陈吉棠可谓开国内短时记忆与听力研究的先河,1995-2005年发表短时记忆成为听力理解影响因素之一的论文4篇,1997-2012年发表短时记忆与听力理解关系的论文6篇,著名的六次“论记忆与听力理解”在国内掀起了短时记忆与听力理解研究的热潮,通过理论介绍、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了如何通过短时记忆来提高听力理解。[34][35][36][37][38][39]苏静认为句法简化促进听力理解,长句和复杂句对短时记忆带来太大负担,长句变成简单句后,短时记忆便能每次承受一个简单句的信息,使听力理解变得简单。姜维焕通过访谈和学生内省探讨了工作记忆与听力的关系,认为应通过大量言语感知和实践扩大长时记忆中的各种资源的容量,将受控过程变成自动过程。卢敏认为处在感觉储存阶段的信息保留时间相当短暂,只有受到注意时才能进入短时记忆,笔录是保障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转移到长时记忆的一种手段。王萌、谢小苑讨论了工作记忆由语言系统和图像系统两种认知系统组成。认为个体的记忆能力非常有限,但可以通过利用视觉和听觉相结合的方式输入信息将工作记忆的能力最大化,从而提高听力理解。王艳论证了工作记忆被用于理解过程中的信息储存和加工,遇到一个词就需要马上加工,而不是储存起来留作将来加工,工作记忆的有限容量和连接性推论方面的不足是产生解析阶段听力困难的主要原因。周罗梅综述国内外工作记忆与听力理解的相关研究,表明工作记忆与听力理解的显著相关。梁文霞论证工作记忆的直接影响一方面与工作记忆组成部分中的语音回路和中央执行系统的功能相关;另一方面与听力过程本身的特点也有关联。同时,听力考试焦虑程度越高,可用的工作记忆资源越少。杨学云论证了利用组块特点可克服短时记忆局限性,短时记忆理论是听写式语言输入的理论依据,听写式语言输入对听力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冯兰也通过实验以语块为单位进行记忆训练来提高听力理解。邱东林、李红叶运用工作记忆的心理模型,论证了应避免干扰工作记忆而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和信息遗漏,因此与语言输入无关的画面越少越好。在听力过程中,应以听为主,视为辅。王红阳论证了对于词汇量大的短文理解类听力,信息的解码和编码难度要比对话类听力高许多,这样会加重短时记忆的负荷,以信息结构为单位来区分新旧信息,强调信息中心,减少短时记忆的负荷对听力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教学指导作用。
2、阅读
作为一种有限容量的加工资源,工作记忆往往使个体能够在加工信息的同时存储信息,而这种基本认知能力往往与阅读等高级认知活动密切相关。[40][41]陈鸿标证明虽然阅读时的工作记忆容量与语言综合能力显著相关,但工作记忆容量的大小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理解句法歧义句并没有显著影响。吴诗玉、王同顺的研究发现工作记忆与心理表征建构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工作记忆还通过与抑制机制的关系间接地影响心理表征建构。工作记忆与抑制机制受到语言水平的直接影响的同时还在影响心理表征建构。闫嵘证明在语音信息加工过程中,听觉言语工作记忆、词汇量对篇章阅读理解有直接影响,需要以听觉言语工作记忆为中介。周明芳认为通过“组块识别”可以提高工作记忆的加工效率,工作记忆激活相应图式,原有图式得到证实或修正,理解得以生成。任虎林论证了高工作记忆力比低工作记忆力的中国学习者的阅读时间少,说明在阅读时间方面工作记忆起积极作用;但高工作记忆力比低工作记忆的学习者理解时间长,说明在理解方面工作记忆起消极作用。高工作记忆的中国学习者、本族英语学习者与低工作记忆的中国学习者在理解准确性方面几乎一致,说明工作记忆高低对理解准确度方面没有显著影响。马拯、王同顺证明外语学能和工作记忆呈明显相关,得出教学启示:教师应关注外语学能和工作记忆对不同阅读水平英语学习者的影响,提高工作记忆的容量。戴运财指出工作记忆容量大、中的学习者的关系从句习得效果明显比工作容量小的学习者好;工作记忆容量和教学方式都对关系从句习得有明显影响,但两者却没有发生相互作用。孙聪颖认为加工成分引起英语工作记忆的储存成分对英语阅读理解的作用部分;汉语工作记忆的加工成分以英语工作记忆的加工成分为中介间接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李晓媛运用实验和行动研究结合的方法证明教学辅助手段和不同的理解测试任务对二语阅读理解中的内部认知负荷产生不相同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受到学习者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和制约。
(二)语言输出方面
1、口语
工作记忆理论认为发音(Pronunciation)对语言处理和学习起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说出话语,我们的短时记忆广度(Span)将会受到限制并因此面临语言处理和储存语言到长时记忆的严重困难。近年来在语言教学中不强调发音重要性不仅阻碍了学生发音能力而且阻碍了他们处理和学习语言的基本能力。作为言语和理解的基础,发音应该受到重视。研究者证实了工作记忆的语音部分(PWM)涉及到言语处理。[42]尽管对成年人的研究显示工作记忆的语音部分不牵涉到有技能的语言处理,[43]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了儿童工作记忆的语音部分和语言技能之间的显著关联,事实上更多证据已证明工作记忆的语音部分在学习语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44]巫淑华论证了工作记忆容量大比容量小的学生的口语流利程度明显高,因此应重视工作记忆的影响,培养学习者语块意识,减少工作记忆处理信息的负担,从而提高口语的流利性。宋美盈论述了语言回路构成了工作记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功能是加工和存贮语音信息,证明了语言回路在二语词汇学习中对所有二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使用者都起作用,但其作用的大小依据学习者母语背景的差异而不同。金霞研究显示,工作记忆容量与二语口语流利度和准确度明显相关,但与口语复杂度并不显著相关,说明工作记忆容量是约束二语口语产出的重要认知机制;同时随着学生二语水平、口语产出编码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口语流利度的制约作用降低。赵晨实验证明词汇歧义和工作记忆负荷影响了读后口译的源语理解;通过对比高、低工作记忆容量学生在加工句首、句末音译词时的异同,论证了只有高容量学生在读后口译中阅读句末音译词的时间比控制词明显快得多。
2、写作
Abu-Rabia证实了工作记忆与二语写作之间显著的相关性。[45]张正厚认为策略构思和充分构思都可减少工作记忆的负荷,增加工作记忆可使用的空间,提高限时写作质量;充分构思还可增强学生对在线构思和监测的注意力。闫嵘证明了工作记忆对修改策略的显著影响:当时间限制修改任务并且提高对工作记忆负荷的要求时,工作记忆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强调对局部错误进行修正,而无法同时在表层和意义两个层面进行全面的更正;高工作记忆容量组意义修改得分和修改总分都比低工作记忆组明显高。王丹斌证明多稿法比修改法有效。因为修改时,学生可以节省出不少花费在写作内容和结构上的认知资源,减少短时记忆的认知负担,节约更多的资源空间去发现新错误,学生有机会使错误成为短时记忆通往长时记忆的桥梁,成功的作者能同时运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与读者进行双向的知识转换。蔡艳玲认为能否在二语写作中合理调配认知资源、有效地运用近似母语写作的认知策略尤其重要。语言技能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在作文意义建构中投入大量的认知资源,增大工作记忆信息处理量。易保树、罗少茜实验证明工作记忆容量对语言产出准确度有明显的影响,高容量组学习者语言产出准确度要比低容量组学习者高得多;工作记忆容量对书面语产出流利度和复杂度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三、国内短时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二语短时记忆教学研究的回顾及分析,可以预计,该领域的研究将会呈现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一)国内的研究都没有直接评估实时(在线)处理言语理解或言语产出过程中儿童工作记忆能力的个体差异的影响,因此评估儿童工作记忆技巧和他们在线(实时)理解和产出语言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今后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在研究内容上,短时记忆的研究会呈现跨学科与多学科综合的趋势,短时记忆研究的多层次和多方位趋势将更加突出。短时记忆教学研究已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叉融合,今后将与其他学科如神经科学、脑科学、神经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融合,其研究视角和思路将会进一步拓展。
(三)在研究方法上,多元化、规范化的趋势将更加突出。短时记忆的研究正逐步从以前的侧重理论性和经验性探讨的研究转向后来的注重教学实践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可以预测,借助于统计分析、认知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短时记忆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实践的研究将更为明确化和具体化。
[1] 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2] Crowder, R.G. 1982. The demise of short-term memory[J]. Acta Psychologica. 50: 291-323.
[3] Baddeley, A. D., & Hitch, G. J. 1974. Working memory[M]. In G.A.Bower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pp.47-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 Atkinson, R.C., & Shiffrin, R.M. 1968. Human memory: A proposed system and its control processes. In K.W. Spence & J. T. Spence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2, pp. 89-195). London: Academic Press.
[5] 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 Gathercole, S. & A. Baddeley. 1993. Working Memory and Language[M]. Hove,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7] Baddeley, A, S. Gathercole & C. Papagno. 1998. The phonological loop as a language learning devi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05(1): 158-173.
[8] Baddeley, A. D. 2003. Working memory and language: An overview[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36: 189-208.
[9] Atkinson, R. C., & Shiffrin, R. M. 1965.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memory and learning. Technical report 79.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al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10] Atkinson, R. C., & Shiffrin, R. M. 1969. Storage and retrieval processes in long-term memory [J]. Psychological Review, 76 (2): 179-193.
[11] 彭聃龄,张必隐.认知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12] Atkinson, R.C., & Shiffrin, R.M. 1971. The control of short-term memory[J]. Scientific American, 225: 82-90.
[13] Craik, F. I. M. & Lockhart, R. S. 1972. Levels of processing: A framework for memory research[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1: 671-684.
[14] 王甦.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5] Peterson, L.R., & Peterson, M. J. 1959. Short-term retention of individual verbal item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8: 193-198.
[16] Brown, J. 1958. Some tests of the decay theory of immediate memor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 12-21.
[17] Wickens, D. D., Born, D. G., & Allen, C. K. 1963. Proactive inhibition and item similarity in short-term memory[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2: 440-445.
[18] 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9] Sternberg, S. 1966. Science[M].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53.
[20] Sternberg, S. 1969. Memory-scanning: Mental processes revealed by reaction-time experiments[J]. American scientist, 4: 421-457.
[21] 杨治良.记忆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2] Wickelgren, W. A. 1973.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memor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 (6): 425-438.
[23] Eysenck, M. W. 1977. Human Memory[M]. Pergamon Press.
[24] Atkinson, R. C. & Juola, J. F. 1973.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V[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5] 吴潜龙.关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认知心理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4):290-295.
[26] 桂诗春.记忆和英语学习[J].外语界,2003,(3):2-8,
[27] 温植胜.对外语学能研究的重新思考[J].现代外语,2005,(4):383-392.
[28] 温植胜.外语学能研究新视角—工作记忆效应[J].现代外语,2007,(1): 87-95.
[29] Robinson, P. 2002.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aptitude and working memory on adult incidental SLA: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Reber, Walkenfeld and Hernstadt, 1991'. In Peter Robinson (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structed Language Learning (Chapter 10, pp. 211-26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0] Terry,W. Scott. 2009. Learning & Memory: Basic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Fourth Edition[M]. Pearson Education, Inc.
[31] McCarthy, Rosaleen A. & Warrington, Elizabeth K. 1990.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A clinical introduction[M]. Academic Press.
[32] 王初明.应用心理语言学[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33] 徐方.短时记忆、外语听力理解与输入假设[J].国外外语教学,2005,(1):28-35.
[34] 陈吉棠.记忆与听力理解[J].外语界,1997,(3):43-48.
[35] 陈吉棠.再论记忆与听力理解[J].外语界,2002,(3):36-40.
[36] 陈吉棠. 三论记忆与听力理解[J].外语界,2005,(2):38-44.
[37] 陈吉棠. 四论记忆与听力理解[J].外语电化教学,2009,(3):48-52.
[38] 陈吉棠.五论记忆与听力理解[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93-97.
[39] 陈吉棠.五论记忆与听力理解[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53-157.
[40] Graham. S. 1997. Executive control in the revising of students with writing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9: 223-234.
[41] Friedman, N. P. & A. Miyake. 2000. Differential roles for visuospatial and verbal working memory in situation model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9: 61-83.
[42] Adams, Anne-Marie & Willis, Catherine. 2001. In Jackie Andrade (Ed). Working Memory in Perspective (pp.80-81)[M]. Psychology Press Ltd.
[43] Shallice, T. 1988. From Neuropsychology to Mental Structur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 Baddeley, A., Gathercole, S. & Papagno, C. 1998. The phonological loop as a language learning devi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05(1): 158-173.
[45] Abu-Rabia, S. 2003. The influence of working memory on read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processes in a second languag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3(2): 209-222.
责任编辑:周延云
An Overview of Short-Term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in China
Xu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Short-term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has been a hot issu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nalyse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rt-term memory and working memory;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term memory; (3) the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 short-term memory. 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e studies of STM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in input and output in recent 15 years in China.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prediction of prospects for future short-term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in China.
short-term memory (STM); working memory;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review
2013-02-11
徐方(1970- ),女,山东海阳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
H314.9
A
1672-335X(2015)02-01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