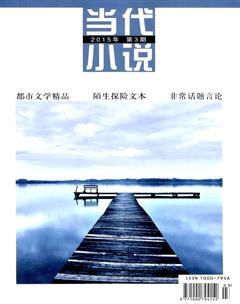三十(短篇小说)
2015-06-01玉荷
玉荷
1
年三十,贴对子。张增林老汉剁完肉馅,忙着刷锅,打糨糊,找笤帚,把集上买来的对子,从偏房的瓮盖上拿过来,一副一副摊在上房的床上,归置好,端着糨糊锅,搬着凳子,开始贴。刺啦刺啦,将上房门框上已经掉色、晒翘翘了边的旧对子撕掉,在右门框上刷上糨糊,拿一副上联,摁上,退出五六步瞅瞅,有点斜,正了正,好了,用笤帚唰唰几下压牢,啪啪啪拍拍,端起糨糊锅,到门左边,贴左门框。活不重,却挺费工夫。主要是张增林老汉年龄大了,七十有七了,腿脚不灵便了,他家大小六个门,要是以往,用不了一小时,现在,贴完院内的五个门,已经一小时多了。
端着糨糊锅,张增林老汉来到院外,贴院大门上的。
是个响晴的天。大街上向阳的地方,一片白花花的阳光。张增林老汉撕院大门上的旧对子。门是去年刚刷过的,黑黝黝的。对子的皱褶里,有的藏着灰尘,平时看不出来,现在一撕,竟噗噗地朝阳光里飞。张增林老汉朝后退了几步。
这座院落,是张增林老汉和老伴1962年的时候起的,五十一年了。盖房子用的土坯,全是他们一早一晚,自己打的。那时候他们年轻。老伴上土,穿着毛蓝褂,后面的大辫子一甩,一甩。张增林老汉提夯,穿着红背心。肩膀上的肉疙瘩一跳,一跳。石夯打在模子里的土上,咣咣咣,声音反到远处的山上,一声一声回响。先是上房起来了,然后偏房、灶房、猪圈、大门、院墙。那时候,这套院落,在村里基本属拔尖的。受到一村人羡慕。记得刚把整个院子归置好那一晚,张增林和老伴激动得一夜没睡,房间里,院子里,来回走,摸摸这门,瞧瞧那窗,说不出的熨帖。现在不行了。砖瓦的房子一套连着一套,噌噌的。宽敞,明亮,他这套房子就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了。俩儿子也曾想为张增林老汉起套新的,又不是没钱。他们一个在北海舰队,大校,一个在南海舰队,上校。两个儿媳也在部队上,两个孙子还在部队上,年轻轻的,就当上上尉和少尉了。张增林老汉说,都一大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的了,指不定哪天夜里,就睡过去,再也醒不来了,花那冤枉钱。就一直没再起。五十多年,有感情了。再说了,又不漏雨,也不透风,好好的,瞎折腾啥呢?
人,不能一走进新好里,就把以前的丢抛了。树没根不活,水无源干涸。
灰尘散了,张增林老汉朝右门上刷糨糊。时间长了,有点稠。张增林老汉把刷子在锅里搅一搅,尽量让刷到门上的糨糊均匀。退回来看上联正不正的时候,瞅见了右墙上的光荣牌子,红彤彤的,钉在那里。张增林老汉不由又想儿子、孙子了。大儿子、儿媳本来说好,年三十回来,陪他和老伴住一夜,初一回去的。昨天忽然来了电话,有任务,又回不来了。这年,只好又只有他跟老伴老两口过了。这些孩子,自从大了,出去了,一年一年的,就再也没一个好生在家呆过。真是孩大不由爹和娘啊。指望他们给拾掇拾掇,帮帮忙、干干活,怕得猴年马月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爹娘的,把他们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不就是希望他们能有出息,为国家干点事,替父老乡亲争光吗?何况,他和老伴身体又没啥大毛病,不缺吃,不少穿,村里、政府上也挺照顾的,昨天,镇长还带着政府的人,送来了花生油、肉鱼、米面。他们回不回来的吧。
其实,二儿子提前半个多月就来电话了,让张增林老汉和老伴到部队里过年,张增林老汉和老伴一商量,不去!那个南方的城市里,楼高得触着天,到处都是人和车,看着就眼晕,哪有村里好?再说了,儿子、儿媳、孙子都有任务去了,不还得剩老两口?算了吧!
呱嗒呱嗒!身后啥响?
正贴下联的张增林老汉,从凳子上回过身来,是巧巧在吃锅里的糨糊。去,去去,张增林老汉赶。巧巧一下退到大门内,钻进了独轮车下。张增林老汉看把巧巧吓着了,走到旁边,捡起块破瓦片,从锅里挖出些,放到巧巧的嘴旁,胡撸胡撸巧巧的头,别害怕,喜欢吃,吃吧!糨糊打了不老少,足够。巧巧看了看张增林老汉,伸出舌头,吃起来。
巧巧是条京巴,捡来的。春里,张增林老汉买化肥回来,京巴在路边的一道沟里,后腿像被压断了,拖着,一下一下朝前爬。四周又没人,肯定被遗弃了。怪可怜的!张增林老汉轻轻抱起,带回来了。养养,好了,除后腿有点瘸,挺不错的一条狗。老伴见狗挺懂事的,就叫它巧巧。秋天上,大孙子出差路过,回了趟家,说爷爷,这是条京巴。他们知道了这是城里人时兴养的宠物狗,就是不为看门,玩儿的。抱在怀里,孩子一样。
贴对子呀二大爷?是老茂祥家的大小子,在深圳打工,过年回来了。西装革履的,打着领带。
啊,回来啦?
回来啦!
过完年还去?
初六走。老板就给了八天的假。
现在村里进城的越来越多了,天南海北,盖大楼的,当保姆的,干保安的,送水的,摆小摊的,贴小广告的,做假文凭的,卖耗子药的,捡垃圾的,撬井盖子的,全有。过年,不管多远,基本都回来。喝喝酒,打打牌,串串门,热闹热闹,初五一过,陆续出村了,坐动车的,坐汽车的,留下老人、儿童。个别赚了大钱的,直接在城里买房子了,过年也不回来,把老人接到城里去。
张东贤就是。儿子在城里买房子了,一星期前,被儿子、儿媳接去过年了。张增林老汉想起张东贤,不由靠在右门框上,朝东瞅了瞅,他家和张东贤家在一条东西胡同上,一个路北,一个路南,中间隔着两户人家,路北一户,路南一户。张东贤家在东边。从张增林老汉这里,能看见张东贤家的大门口。朝张东贤家瞅完后,张增林老汉开始贴横批,不过此时精力有点不太集中,将两个字弄颠倒了,一念,不对劲,揭下来,湿呼啦的,重新进行调整,一个字的上部竟撕裂了,对正摁摁,用手胡拉着找补了找补,基本齐整,可还能看出来,左瞅右瞅,右瞅左瞅,寻思,算了,就这样吧。
收拾好糨糊锅、凳子,回家,归置了归置灶房里的柴火,顺了顺房檐下的镰刀、锄头、绳套,扫了扫院子,又摞影壁墙后的几块碎砖、水泥条,刷灶房大锅的锅盖。可张增林老汉手虽在不停地忙活,感觉上心里却总有个事在搁搁着,放不下去,到厕所里断断续续、滴滴答答地撒了泡长尿,抖抖,出来,系着裤腰带,望着上房的门口,自言自语地叨咕了几句,决定去偏房里推三轮车。
咋还推出三轮车来?老伴听到动静,挓挲着一双面手,在上房门口问。
到集上。
都晌午了,去集上干嘛?
再买副对子。
不都贴上了吗?
张增林一拧钥匙,三轮发动起来了,说了几句,没等老伴听清,突——走了。
不炸丸子了?老伴在后头喊。哪还有个影子?
2
张增林老汉出村口,奔西,朝方户集而去。按日子,今天是方户集。方户集逢阴历五和十。这也是张家营子附近,方圆十里八里的,年前最后的一个比较大的集。
以前,过年贴对子,村里没有人买。很多念过初中的,都能写。学校里有毛笔字课,叫写仿。每周安排一节,到有写仿课时,学生上学,提着墨汁,拿着毛笔。将写仿本打开一页没写的,底下垫一张老师写的字帖,蘸好墨,按照老师讲的握笔要领,屏声敛气,一笔一划,照着底下透过来的字帖的字迹,描。一点都不能马虎。讲究横轻竖重,点点如瓜子,撇撇如把刀。描得好的,老师在字旁划个红圈。不好的,老师会在旁边给写一个范字,让照着写两遍或几遍。现在,学校里基本没有写仿课了。以升学率论英雄,升高中考大学的又不考,谁还耽误那工夫。有空背几条定理,记几个单词了。
论起来,张家营子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有四个,小学校的赵老师,大队的张会计,村北的李大学问,代销点的三啊啊。就是张秋三,说话有点结巴,小时候落下的毛病。这四人,被称为赵楷张行,李隶三草。就是赵老师擅长楷书,张会计擅长行书,李大学问擅长隶书,三啊啊擅长草书,尤其赵老师的楷书,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的蝇头小楷,法度严谨,结字端庄,令人叫绝。抄写的《三国演义》和《水浒》,被英国的一家博物馆收藏。他写对子,从来都是自己现编词,切合每一家每一户的实际,没有重复的。对仗工整,讲究平仄,严格遵照云对雨,雪对风,暮鼓对晨钟那一套路数。写出来的对子好,过年找他写对子的排队。为过年增添了不少浓重的氛围。
如今,村里写对子不行了。小学校合到镇上去了,大队会计谁的,都年龄大了,手不拿东西都哆嗦得要命,还写对子来,天书差不多。其他能写点的,平时又不写,过年谁还值当地去买墨汁,买毛笔的。花那冤枉钱。直接买对子了。赶集时顺手的事,省钱省工夫。张家营子全村一百五十五户人家,大小二六一十二个胡同,五条街,自己写对子的,没有一家了。
到方户集,十多里,张增林老汉半小时到了。
正在散集。
归置没卖完的白菜、萝卜、生姜、大蒜的,将小米、绿豆、黄豆、黑豆袋子朝车上装的,数兜子里上午刚卖的钱的,擦卖肉的秤盘子的,朝马车里套骡子的,用摇把摇蹦蹦车发动机的,都有。
放好三轮,张增林老汉左躲右闪,朝里走,怕碰着散集的人。不时挂一下这个手里提的葱,碰一下那个肩上背的锅盖,打听着,找卖对子的摊位。砰!卖鞭炮的放的一个没响的鞭炮,在脚边响了。吓了一跳。现在这鞭炮,不像以前装黑药了,全是炸药,跟放雷管一样,吭吭的。特别是那些白书纸卷的,挑起来一放,炸得纷纷扬扬,如下雪花。要是年三十晚上点上,两军进入了激烈的交火一般,甭说看春晚了,站两米远说话都得喊。
卖对子的在大西头,还有卖年画的,卖灶王的,卖唱片光盘的,卖烧纸的,卖香的。张增林老汉找到那里时,全部卖对子的,八个已经卖完,收摊,走人了,另一个剩最后四副,刚被一个妇女买去。张增林老汉跟妇女商量,能不能匀给我一副?妇女说,家里正好,匀给你一副,那咋行?
张家营子这里有讲究,过年,门上必须贴对子。你到村里,如果发现哪家的门上没有对子,要么这家里有老人去世了,还未满三个年头。要么就是家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绝户了。为了图吉利,讨喜庆,现在,有的把粮食囤上、瓜棚上都贴上。过年走亲戚,冷不丁公路上迎面有一副对联唰唰过来,上联安全万里,下联日进斗金,千万不要以为是谁家吃饱了闲着没事,抬着门去串门,而是一辆拖拉机。年三十刚贴上的。呼呼的,从你身边开过去了。有时元宵节都过了,还能看到。
张增林老汉一看,跟妇女商量不成,就问卖对子的,不是可以现写吗?再写一副不就行了吗?卖对子的说,没红纸了,全写完了,你看!拿起写对子的案板下的纸箱,翻过来给张增林看。啪啪啪,还用手拍拍。张增林老汉说,那我去买张红纸?卖对子的说,都这天了,谁还开门营业呀?够呛!张增林老汉说,肯定有,你等我一会儿!卖对子的冲张增林老汉后背喊,顶多二十分钟哈,还回家过年呢!
3
方户集,是与张增林老汉所在的县相邻的一个县富江县方户镇的镇集,在方户镇镇政府西边,一处南北窄,东西长的空地上,前几年刚迁到这里的,原先在北面方户村的村子里,一条南北的街上,中间还有一个石拱桥,据说是北宋的时候修的,桥面的石板已被行人车马磨得十分光滑。2005年的时候,镇政府为了对桥进行保护,同时也便于对集市的管理,将集迁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还搭设了一排排铁皮棚子,砌了一道道的水泥平台。棚子上、平台上,用红油漆编了号。平时这里也有做买卖的,但主要是逢集时,人才最多,生意最红火。乌洋乌洋,人山人海。这集是要过年了,人少了。要是赶上平时的集,挤不动,抗不动。
与镇集紧邻着,北边就是一条商业街,店铺林立,卖水果的,卖文具的,卖服装的,卖杂品的,卖烟酒的,炸油条的,蒸包子的,灌香肠的,打豆浆的,扎花圈的,做衣服的,爆米花的,五花八门。平时这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现在却冷冷清清。拉了卷帘门的,门上锁了锁的,贴着过年歇业三天的。街边上,这里,那里,有几个卖鞭炮的摊子,摆着串鞭、二踢脚、摔炮、拉炮、大雷。摊主缩缩着脖,袖袖着手,站在摊子后面。不时喊一声,瞧一瞧了哈,一万头的响鞭,不响不要钱啦。旱天雷,二十七元了哈。
一家卖洗衣板、笤帚、铁锅等杂品的,女老板正在上门板。张增林老汉问,卖红纸吗?女老板头也没回,不卖。你去东边的文具店看看吧。张增林老汉上东,不远,来到文具店,关门了。朝东瞅了瞅,两边的店铺,好像没有一家卖的。又折回来,沿着大街朝西走。一家百货店开着门,张增林老汉走进去,里面都有电动车、摩托车,但与纸有关的,却除了稿纸、信纸,再就是烧纸。张增林老汉赶紧出来,东张西望的,继续搜寻。一个卖气球的,坐在街边的三轮车旁,车上系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气球,红红绿绿,随风舞动。张增林老汉问,兄弟,你知道这街上哪家卖红纸吗?我急用,想买一张写对子。卖气球的眨巴着眼,琢磨了琢磨,说,卖红纸的,嗯——卖红纸的,还真没注意哩。都这天了,卖的也关门了。前面那个胡同那朝北走,有一家卖土特产的,你看还开着门没有,他那里好像卖。张增林老汉说,谢谢你。去找那家土特产商店。还真有。张增林老汉买了一张。交上钱,卷吧卷吧,麻溜朝回走。
卖对子的已走了。来回一折腾,差不多四十分钟了,谁还在这里老等着呀?别说卖对子的了,整个集上都没几个人了。打扫卫生的都哗哗扫开了。
张增林老汉的三轮车,孤零零地放在东头那个空地上。旁边一堆卖甘蔗的削的甘蔗皮。
张增林老汉拿着红纸,站在三轮车边,寻思,咋办?跑这么远,不会就买了这张红纸吧?要是单买红纸,还用跑到这儿吗?那么,让谁写成对子呢?老伴的侄女女婿倒是写得不错,他在一个国有石化公司的工会工作,是国家级书法会员,写的作品到处参展,被香港、美国、日本等一些有钱的人争购,听老伴说,有一回,韩国的一个人让他给写了一幅字,一下子就给了二十万。还有两瓶叫人头马的洋酒。你说一个酒,叫啥不好?别扭!不过,那是人家外国的事,爱叫啥叫啥吧!家里就挂着他写的一幅字,是他给张增林老汉大儿子写的,两幅,大儿子带走了一幅,另一幅挂在了家里,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就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首,洋洋洒洒,看过的人都说好。不过,到他那儿太远了,得七八十公里。这要跑个来回,还不半夜个球的了。就他这个三轮,突突突的!
那么,找谁呢?
张增林想到了镇上的学校。对,到那里。虽说过年,放假了,肯定有值班护校的。大凡老师,基本都能耍两下子。离家也不远,七八里地。
4
镇学校很气派。现在的学校,除了深山里边的,穷困地区的,基本都很气派,一个中学,基本就跟早先时候的大学差不多。镇学校大门非常高大,外边镶着红色大理石,进门口,迎面是一个雕塑,汉白玉的,一个女学生,左手抱着书,右手高举起来,托着一颗科学之星。雕塑后面是一个喷水池。要不是冬天结冰了,水哗哗的。再往里走,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一栋连着一栋。最后面是操场,跑道是塑胶的,老远看着就禁不住想上去跑两步。
你找谁?门卫从传达室的窗户里探出头来,问张增林老汉。
噢!想找个老师,写副对子。张增林老汉说。麻烦你给帮帮忙。
门卫看着张增林老汉手里的红纸,今天值班的是教数学的曹老师,他在那个办公楼二楼,冲楼梯上去,右拐,第三个门。
曹老师正坐在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几个菜,放着几瓶啤酒。曹老师脸红红着。看来已喝得差不多了。写对子?这,这你得找马老师。曹老师打个酒嗝。嗝!毛笔这个东西,软不拉塌的,咱,咱不行。算个三十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求个一元一次方程,还,还可以。
那马老师在哪呀?
放假了,回家了。
他家,远吗?
不远。北边,商,商贺村。
噢!谢谢曹老师。张增林老汉说着,朝外走。镇学校到商贺村,五六里地。他要去找马老师。
到了楼下,又返回来,敲敲曹老师的门,曹老师,马老师叫什么呀?
马,马成玉。
谢谢!
三轮车的钥匙打不起火来了,拧了几次,吭吭吭吭,就是起不来。挺好的呀,二儿子前年花四千多块钱买来后,张增林老汉拉着老伴,赶集,下地,走亲戚,还拉小麦,运玉米,一直没出过问题。半夜三更的,都送村里的人紧急去县医院好几回,有张大攫柄、周四拐子、侯六的老伴。侯六的老伴那回多亏了张增林老汉的这个三轮,要不就完了。她跟侯六吵架,怀疑侯六有相好的,喝农药了。你说都五老六十的了。侯六光着一只脚,咣咣地砸门。张增林老汉赶紧穿上衣服,推出三轮来,加到最大油门,摸黑突突地去了县医院。一路风尘,三轮很给力。要说起来,就有那么一回,一次跑了八十多公里,没油了,停了。加上油,接着就好了。像一匹卧槽的马,突然后腿蹬地,前脚腾空,咴咴的,立成一个奋发与昂扬。
张增林老汉踩了踩油门,还是不行。下来,检查检查油路,活动活动两个把上的手柄,右脚踩到脚踏打火踏板上,用力一蹬,手转动油门,突——起来了。觉着就没啥毛病。
张增林老汉坐上,咔,挂上了挡。
5
商贺村叫是叫商贺村,但姓商的和姓贺的却没有几家,几乎都姓马,另外还有部分姓范,跟范仲淹一个姓。
马成玉老师家住村东,张增林老汉一问就问着了。把三轮停在门外,拿着红纸朝里走,马老师的爱人正在灶房里洗碗。刚吃完午饭。马老师在上房, 叽 叽剁馅子,准备包饺子,好晚上吃。请问马老师在吗?张增林老汉站在院子里问。马老师从凳子上站起来,挓挲着手,来到上房门口,和张增林老汉互相一愣。
怎么是你?
可不!咋这巧来?
进来吧!进来吧!马老师招呼。
张增林老汉进了上房。
马老师让了坐。敬烟,张增林老汉不抽。马老师把烟又插进烟盒里,集上等了你半个多小时,没来,急着回家吃饭,我就走了。
张增林老汉把红纸放桌上,是我买红纸耽误了。到处都关门了,一家一家的,费了半天工夫。
可不!都多咱天了?
这不,寻思到镇学校去找个老师写一写,值班的曹老师,把我介绍到这来了。没想到咱们还刚在集上见过。
缘呐!来!来来!赶紧写!
张增林老汉把红纸交给马老师。马老师展着红纸,就一张?张增林老汉说,就一张,对子老早就买了,上午贴着贴着,发现还差一副院大门上的。
马老师替张增林老汉割红纸。割完了,把墨汁倒进一个小瓷碟,提笔蘸满墨汁,面对红纸,思考着该写什么。抬头,对站在旁边的张增林老汉确认,院大门?嗯!张增林老汉答。马老师落了笔。
张增林老汉见自己闲着,洗洗手,替马老师剁馅子。马老师的爱人从灶房进来了,夺着刀,不让剁。张增林老汉说,忙惯了,闲着难受,你让我剁吧。马老师写对子,别的咱又帮不上。马老师的爱人只好依着张增林老汉,从茶桶里取出茶叶,泡上,跟张增林老汉聊牛,说棉花。问哪哪庄的谁谁谁认识不?
对子写好了,放在方桌上,晾着。马老师拧好墨汁瓶,涮涮毛笔。
墙上的表两点了。张增林老汉说,我得走。马老师找块海绵,把对子上没干的墨汁吸吸,垫上张报纸,卷起来。
张增林老汉要给钱,马老师坚决不收。张增林老汉只好又把钱放进兜里。
6
坡地里,这里那里,一伙一团的,提着篮子,扛着杆子,开始上坟,请祖先了。噼噼啪啪,东边西边,山前山后,坟圈子里不时响起鞭炮声。
往日车来车往的公路上,现在,只有一辆两辆的,偶尔从张增林老汉的三轮旁驶过。很着急的样子。肯定赶着回家吃团圆饭。
张家营子里,到处贴着红红的对子,有的大门上还挂上了红灯笼,红灯笼里扯上了电灯,单等日头一落,然后咔吧,把门庭照得流光溢彩,喜气洋洋。
菜香混合着酒香,在村子的上空弥漫。
张增林老汉一进家门,老伴就说,你个老东西,上哪去了,中午饭都不吃,咹?张增林老汉顾不上说话,停好三轮车,端上糨糊锅,匆匆朝门外走。老伴问,对子不是都贴了吗?咋?还要贴?张增林老汉答,张东贤家院大门的。
张东贤家院大门?老伴望着张增林老汉的背影,噢——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