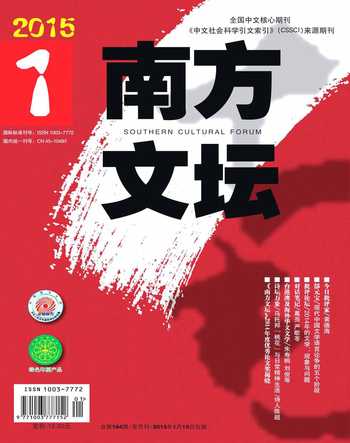理论动态
2015-05-31贺绍俊
●网络文学讨论
2014年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理论深化年,在这一年里,各类文学组织和报刊持续地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表现出试图建立起一套符合网络文学特质的理论体系、评价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趋势。
2014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共同举办了“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被认为“是一次多维度、高质量的理论研讨会,在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标杆性意义”。在年底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网络文学也成为重要的议题,年会就网络文学分别设置了“网络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和“新媒体文学与文化产业”两个讨论话题。不少报刊相继开辟了网络文学的专栏,如《人民日报》的“网络文学现认识”、《文学报》的“聚焦网络文学‘大神”等。
马识途专为网络文学写了一篇文章,一位百岁的老作家是如何看待网络这种新媒体的,这本身就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在马识途看来,“发展网络文学,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群众路线问题,是如何引导我们的下一代走上健康道路的问题。”马识途还建议纯文学的作家转向网络,他说:“我们有作家组织和众多的有创作经验及较高文化水平的作家,应该有意识地鼓励一批有志之士下决心转入网络文学创作队伍,写出好的网络文学作品,提高网络文学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平。”(见《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在如何建立起一套符合网络文学特质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上,有不少建设性的意见。陈福民认为,网络文学的勃兴是商业动机推动的结果,因此网络文学的种种问题“固然都由文学引发,但是很难在传统的文学范畴内予以讨论”,“以文学写作的商业动机合法性而论,网络文学所表征的各种现象,诸如写手签约、网站推介、盈利分成等等,都已不再是传统文学生产方式可以说明的,它还涉及更为复杂的资本运作、商业推广、利润分配等现代深度模式。因此,要理解这些新异因素对于未来文学的影响,除了一般的文学理解力之外,我們还更为迫切地需要建设一种文明理解力。”陈福民认为,在这种情景下,网络文学的批评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因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无法面对“浩如烟海规模宏巨的网络文学体量”,“也许,在未来以多媒体介质(电脑、平板、手机等)为主的阅读活动中,随意性和趣味性将以多元化的名义放逐了批评的系统性和严肃性。那时,人的终端的无限延展又是一个文明的新话题了。”(见《人民日报》2014年5月31日)何平认为,网络文学是老百姓文学,其核心价值观是草根文学伦理、江湖伦理,而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则是建立在五四以来的精英评价体系之上的,因此,传统评价体系很难适应网络文学研究。他希望批评家可以“去网络上批评”,“走向对话和协商”。邵燕君认为,网络文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性在网络时代的新生”。在媒介革命的视野下,如果网络文学的批评理论体系还是建立在传统批评体系之下,难免受制于精英本位的思维定式,应该跳出印刷文明的局限,引入新的尺度。李敬泽认为,要认清网络文学、类型小说与纯文学的不同。批评家在面对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等通过幻想的逆袭来应对现实,其中的幻想、梦想机制在网络文学中很重要,我们的文学理论却无法应对。因此,不能以纯文学的经典性强行要求网络文学。对网络文学来说,文学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网络文学表现的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它认识普通人内心的希望和梦想。(以上见《文艺报》2014年)
但黄平的观点代表了另一种思考路径,即不是强调网络文学异质于传统文学,从而需要为网络文学评价建立起另一套体系,而是认为网络文学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文学场,因此需要考虑的不是为它建立另一套体系,而是考虑如何使它进入到文学场。黄平认为小说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网络文学:“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发展、完善,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其中的哲学、宗教、经济、社会阶级、科学技术诸种因素都对小说的定型发挥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观念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推动小说的浮沉,今天讨论网络小说进入‘文学场,应该有这份历史的视野。”“网络文学要进入‘文学场,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观念的变化、知识分子的介入,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网络文学才能摆脱目前的文学地位,享有相匹配的成熟的评价体系。就现状而言,这两个条件还不成熟,无论是网络文学作家还是关注网络文学的批评家,都应该更耐心一些,现在谈论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场还为时尚早。目前我们的文学观念还无法接受网络文学的美学特征,知识分子的介入更是寥寥,网络文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还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文学圈,无法有效地进入文学场。我们讨论过往的历史可以弹指千年,但对于历史中的我们,这种改变是十分缓慢的。”(见《人民日报》2014年4月11日)白烨持相似的思路,因此他认为网络文学的问题是如何强化文学元素,“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似乎成为了支撑和推动网络文学的主要杠杆和重要力量。作为文学之一种来看,网络文学应有的另外的一些元素和力量好像在淡化,在隐退,在萎缩,比如说文学的质地、美学的素养、文化的意味、精神的含量。”而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传统的:“怎样结合网络文学的实际,培育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网络文学编辑,加强网络文学的评论,包括建立网络文学的评论队伍,构建评论标准与形成评论机制,让传统文学的经验、经典文学的营养、文艺美学的力量,不断影响和渗入进来,提升网络作家的艺术素养,保持网络写作的文学品质,制衡资本因素的无限扩大,都是十分必要和极其迫切的。”(见《太原日报》2014年6月9日)
网络文学的讨论更多的是理论和概念之争,容易停留在泛泛而论的阶段,而《文学报》的“聚焦网络文学‘大神”的栏目则是试图将讨论引入到对网络文学具体文本的讨论。在《唐家三少的“万年模式”》一文中,作者曹晋源对唐家三少的模式化写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唐家三少笔下的人物具有脸谱化的特征,其作品中“如山如海的人物基本皆是非黑即白,倒也适合网络小说吃快餐般的阅读方式”,“虽然人物尽是张张脸谱化般的出现,但三少从不吝啬对他们详细描绘的笔墨。”唐家三少小说的情节则是偏模式化,“基本都是屌丝逆袭、迎娶白富美的故事类型”,曹晋源将其称为“万年模式”,因为“这样的写法似乎大部分读者都不会觉得厌倦,有一些读者甚至越嚼越有劲,貌似写一万年都有人看”。但由于唐家三少写作思维的固定,这已经转换成了他的“职业瓶颈”。在《猫腻的“强大”与疲乏》一文中,作者孟德才剑指另一位网络文学“大神”猫腻。猫腻是近年来新崛起的网络文学作家,不同于唐家三少等网络作家,猫腻的小说不仅受到了来自网络读者的追捧,而且还赢得了文化界、学术界一些人士的赞赏。孟德才强调,猫腻的小说仍然是类型文学,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只有放在类型文学的理解框架中,方能得出客观、恰当的评价。他认为,猫腻“是网络文学界最有文青范儿、最能保证文学品格的一位作者。猫腻的意义,在于他开启了一种有别于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等小白文作者的小说风格。即那种富含‘剩余启蒙能量、具有社会现实思辨力度、洋溢着细腻温暖的文青情趣的小说风格”。但猫腻的写作已经露出疲态,猫腻的问题的出现“与当今网文写作机制密不可分,可以说是网络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高强度的写作任务、快节奏的更新机制,对于每一个网络文学写作者而言,都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以上两文均见《文学报·新批评》2014年11月6日)
●80后评说80后
80后是受到报刊重视的另一个议题。不少报刊围绕80后做文章,如《光明日报》开辟了“80后创作新观察”的栏目。而《西湖》的“80后观察”、《创作与评论》的“80后文学大展”、《名作欣赏》的“80后·新青年”、《百家评论》的“青春实力派”等则是一两年前就开设的,大多都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开辟的“青年作家研究”专栏也主要是以80后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在关于80后的讨论中,最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一批80后批评家的声音,我们不仅从中看到80后是如何评说80后的,而且也看到了一代批评新人的实力。
岳雯对80后的描述很有意思:“80后作家似乎个个都雄心勃勃,要在前辈们不曾涉足的荒野上开拓自己的疆域。然而,看似是一往无前的姿态,但方向却是朝后退的。这么说,是建立在与父兄辈的写作实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如果说50后试图介入社会政治,60后则回到了人性的领域;如果说70后的写作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楼阁之上,那么到了80后,他们将日常生活又推进了一下,也就是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被个人体验过了的现实,是精神现实。于是,现实呈现出更为精巧、幽微,也更为狭窄的图景。”“对于还在习得写作经验与技巧的80后来说,一个最方便的途径,是观察周围的人,或者就是自己,从他们身上提取写作素材。在他们笔下,不大见得到巴尔扎克、狄更斯式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素材。他们也无意于建构‘整体世界。鉴于年轻的写作者、阅读者大多是从文艺青年转化而来,于是,在他们的小说里,对文艺的追求和思考成了一个恒定的主题。”岳雯由此将80后的文学特质归结为“文艺”。她认为80后的创作都有文艺化的倾向,这使得他们的小说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比如对意象的偏爱。岳雯一方面认为文艺化并不见得是一桩好事,另一方面她又强调她喜爱阅读80后的创作。这样一种纠结也许正是同代人的特点。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对80后的成长和成熟抱有一种期待,期待他们不要太“文艺”,她用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她的这种期待,她期待80后能够明白:“在文学中寻找人生是一种活法,在人生中寻找文学是另外一种。”(见《光明日报》2014年11月4日)
《名作欣赏》2014年第9期做了一期80后文学的专号。编者为这一期专号选取了十二位80后作家的作品及创作谈,并邀请了十二位80后批评家对其进行评论。编者强调,参与本期专号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都是80后,显然他们是要强化80后的声音、眼光和立场。两位80后批评家也是专号的策划者金理和黄平的对话,表达了这期专号的宗旨,对话的标题就很醒目:“反思围绕‘80后的种种成见”。他们把这种成见归纳为四个方面:市场化、肤浅而匮乏经典意识、专业主义、无历史感或“反讽”的美学。他们分别对这四种成见进行了辩驳。关于市场化。他们并不否认80后与市场的关系,但他们认为如果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是很可笑的。“在今天面对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与其固守二元对立,还不如抛弃成见,尤其当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回旋余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去感知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与其去区分市场、文学,或者再把文学划分为雅、俗,还不如去关注各种块的缝隙间,是否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关于“肤浅而匮乏经典意识”。他们说:“一般人可能过于夸大青年作家将电影、美剧、动漫等元素编织入创作,却忽略了青年人同样在向经典致敬”,另外也得注意到,“‘80后作家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推动他们重构自身的写作资源。”关于专业主义。他们认为这一成见主要是针对80后批评家以及一部分传统文学体制中的80后作家。这种成见背后其实就是要“强调一个道德化的现实主义立场与宗教式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们辩解说,80后批评家确乎比较学院化,但学院化并不等于脱离现实,更不应该由此推论出西方文论本身就是空洞无物的,以及学院派批评都是封閉的知识循环。他们认为,一流的学院派批评一定是从彼时彼地的现实出发的。关于无历史感或“反讽”的美学。他们认为,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帖80后的理论框架中才可以发现。“对于‘80后无历史感的批评,其对历史感有隐含的限定,是指向阶级反抗的历史感,大致是一种‘左翼文学视野下的认识装置。”
具体进入到每一位80后批评家对80后文学作品的评说,仍能突出感觉到他们不一样的眼光,他们有意无意地为80后辩护的姿态。如在项静评论甫跃辉的创作的一文里,她首先强调了80后不一样的写作背景:“如果说‘50后‘60后逃避不了‘家国这个词汇的牵连,‘70后从个人身影出发,那么‘80后是从‘童年开始书写的。”她甚至感慨:“在‘80后作家上场之前,没有一个代际的作家如此繁复地因他们的出生年月而备受关注,转眼又被批评集体变老、暮气沉沉。”她同时也力图客观地理解80后评说80后的意义:“作为一个同龄人去评价作家的作品,往往带来同情之理解,也会单点放大我们自己的一隅之困。尽管有一个如何更好地以我们的眼睛认识世界,用我们的手心口更好地呈现世界的大前提,但把‘我们作为世界的中心,往往只是为了大声呼喊以引起他人注意。”
《名作欣赏》在这期专号里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他们编辑这期专号的思路。文章的标题是《请君评说:‘80后新青年》。“新青年”这个词让人眼睛一亮,稍有文学史知识的人马上会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就叫《新青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也许可以这样说,一场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思想革命就是从《新青年》开启的。《名作欣赏》的80后编辑也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联想中以“新青年”这个词语来命名今天的8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与社会转型期同步成长,在观念、情趣、行为方式等方面,是‘价值断裂的‘新青年,虽然不敢奢望与五四时代‘新青年比肩。”显然,他们也在借用《新青年》所蕴含的革命性的象征意义,他们期待80后能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革命性的突破。80后是在路上的“新青年”,也是需要我们不断评说的“新青年”。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