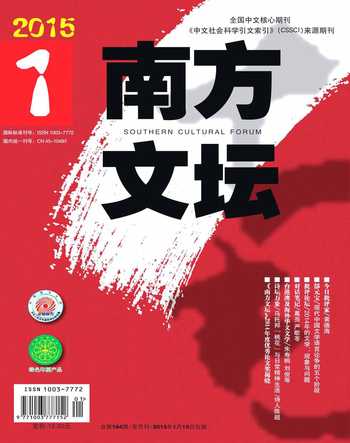庸常时光中的诗性消解
2015-05-31张晓雪
一
在叙事日渐普及的今天,曾经承担了主要叙事任务的小说开始面临新的困境。显然,小说已经不能仅仅把叙述完一个故事作为最终目标,而必须带给读者更多的、超出一般的新闻故事、新闻报道的东西。因为在讲述普通的故事方面,小说面对新闻故事、新闻报道有着天然的劣势——它是虚构的、不真实的话语。对于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强调从故事中认识社会人生的读者来说,真实意味着权威和生动。如何能让小说叙事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对当下小说写作至关重要。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小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泛叙事时代才有存在的理由。当然,这种现状对小说写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被称为现代小说的立法者的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就是要表现复杂的精神”①,强调小说就是要告诉读者,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但是,要实现这个写作目的,首先需要小说作者本身具有复杂的精神,能够超越一般读者把生活简单化、程式化划分的目光,用一种更复杂的目光打量生活,从中发掘出细微的矛盾甚至悖论,从而提供给读者。对于很多把描述生活中的一个小感悟作为写作动机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然,这个问题,对于汪淏来说,不是问题。作为一个非常自觉的作家,汪淏对小说题材的选择,对小说叙事技巧的把握,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汪淏是一个非常习惯于,或者说,强调描述生活中的“小”的人。他的小说,从来不关涉社会大事件,甚至也基本忽略小说叙事的叙事背景,所描述的事件,往往也都缺乏曲折性和复杂性,似乎就是一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交往故事。这些故事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元素,没有紧张刺激的情节刻画,就是那样的平平淡淡,似乎如生活本身一般寡淡无味。不过,掩卷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似乎极其平淡的小说却总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思考。《比翼飞》是汪淏的一个描述兄弟情感的小说,小说上半部分由倒叙完成,回忆了几个商校的学生在上学期间因为志趣相投,情同手足,毕业之后,兄弟几人虽然天各一方,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却始终互相挂念。在这一部分,小说描述了三兄弟毕业之后的两次相聚。虽然都是短暂的一夕相会,但是其中浓浓的兄弟情,跃然纸上。小说下半部分开始顺叙,描述三兄弟即将到来的这一次聚会,当然,先描述了叙述者对这次聚会的期盼。但是在进入具体的聚会之后,小说情节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一个三兄弟之外的当年的同学,以聚会“赞助者”的身份介入到三兄弟的聚会之中,而在这样外力的作用下,三兄弟之间的感情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到小说结束,虽然兄弟之间依然言笑晏晏,但是,我们似乎却对三兄弟的第四次聚会已经不抱有希望了。《叙事的艺术》讲述的是一对老情人重逢的故事。叙事者小说家陶然曾经有一个情人,叫夏雪。他们认识的时候,夏雪是一个尚未婚配的天真美丽的情感类文章作者,而陶然则正处于一段无趣的婚姻当中。这两人因为互相欣赏而在一起,成为情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只是互相欣赏,而没有向对方索求更多的东西。虽然夏雪似乎也有幻想和陶然结婚,但是她并没有提出要求。后来因为夏雪的结婚,两人的关系宣告结束。再次见面已经是多年以后,这时陶然和夏雪都已经离婚,应该说具有了结合的可能性。但是,此时的夏雪不但在外形上已经和当年的清纯的夏雪相距甚远,而且便是在思想上,也有更多的功利的要求。夏雪的心机在她重逢之后向陶然谈自己的婚姻的方式中集中体现出来,而陶然面对这个夏雪,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诗情画意,他巧妙地消解了夏雪布下的语言圈套。虽然小说最后这对当年的老情人再次同床共枕,但是,他们没有做爱,没有浓情,也没有诗意。《多年以前,多年以后》这部小说也讲述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感情故事。做戏曲研究的余梁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和一个宾馆总台的服务员李霞认识,并且发展到情人关系。李霞有一个不幸福的家庭,而余梁未婚。李霞在和余梁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幻想,加速了和丈夫离婚的步伐。但是余梁拒绝了李霞的幻想,告诉她,他们之间只是爱情的关系,只能成为情人,不能进入婚姻。之后两人再无交集。多年之后两人再次相遇,李霞仍然在努力地离婚,而余梁则已经完成了一次结婚一次离婚的全部过程。但是多年以后的这次相见也没有了多年以前的诗意,此时相见的李霞,主要目的是向余梁推销保险……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汪淏的这些小说中,他主动剔除了起承转合、曲折动人的故事性元素,似乎就是对生活的一次淡淡的回忆,或者说简单的叙述,但是这些叙述却能带给我们很多曲折动人的故事所无法带给我们的思考,带给我们感情的撞击。比如说,《比翼飞》中关于兄弟感情的描述,以及随着时光流逝,这种感情温度的消失,《叙事的艺术》中一对老情人重新相见,却从当年的诗情画意变得寡淡无趣且充满心机,以及《多年以前,多年以后》中以利益为主导的当年老情人的重逢,都会超出我们的阅读预期,呈现出生活的某种复杂性,从而带给我们深思的契机。藏策曾经提出一个超隐喻理论,我以为用来分析汪淏这些小说带给我们的思考颇为合适。藏策指出,“‘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超隐喻是一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编码,同时‘超隐喻也是一种‘俗套,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俗套。其往往是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隱喻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变为了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②藏策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之中,存在着一种惰性的、专制的思维方式。或者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驯化,或者是出自所有个体的思维惰性,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很多社会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指向。这些意识形态指向被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反过来也导致这些意识形态具有了专制性和权威性,一方面,会带来个体的思维的盲区,就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辨析这些意识形态是否合理,质疑这些意识形态的能力,另一方面,很多这种专制性的意识形态也被赋予了不可侵犯性,如果违反这种意识形态,就会受到社会群体的嘲弄、鄙视。事实上,在我看来,作为小说家,在当下这样一个现代传媒影响无远弗届的年代中,很大的一个价值可能就在于能够有能力认识到某些社会思维、话语中潜藏的超隐喻,并将之揭示出来,从而引起读者对这些思维、话语的重新思考。现代传媒是无法承载这种功能的,作为标榜真实、客观,并且强调承担社会正面责任的现代传媒,它只能去强化已经存在的超隐喻思维模式,而不可能质疑它们。这种超隐喻思维的普遍存在,只会带来社会思想的僵化,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人性的解放。汪淏的小说之所以叙述平淡而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这些小说在很多侧面,不同程度地触碰到了超隐喻,并对之进行反思,或者颠覆。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兄弟情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概念。“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段话借助《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传统叙事中,描述这种兄弟情的作品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对兄弟情义的极度尊重,关羽甚至在民间被神话成了神灵。可是这种兄弟情义在汪淏的《比翼飞》中得到了消解。我们毫不怀疑三兄弟在商校读书时的感情,这种感情如此深厚,甚至在几年以后,老大老二两人在郑州进修的时候,又专门跑到老三的家乡,徒步跑到乡下,只为了和老三一起相聚一晚。但是在小说的下半部,当我联系好老二秉德一起去找老大迟荣盛的时候,老大的身边却多了一个蹊跷的现在是百万富翁的当年同学胡敬东,而且也正是这个胡敬东为他们的同学会全程买单。从小说叙事来看,显然这个胡敬东的出现是老大迟荣盛有意安排的,因为他可以出资为兄弟几个的聚会买单,而胡敬东之所以愿意加入他们这次聚会,显然也是因为有求于小说中的叙事者马牧。也就是说,这次兄弟聚会充满了其他功利性的诉求。这样,在小说前半部被作者大力渲染的兄弟情在后半部就毫不留情地被这次本该是兄弟情谊一次升华的聚会消解掉了。
关于男女两性关系,在中国语境中,特别强调合乎社会伦理。那些不合乎社会伦理的两性关系在中国语境中天然就是耻辱、丑陋,甚至可以说是罪恶。但是在《叙事的艺术》中,汪淏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和抗议。小说中的小说家陶然在和夏雪一见钟情,并且发展成情人关系的时候,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按照传统中国伦理道德,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健康的,是丑陋的。但是小说中两人的关系却在这个时候是最美好的。两人对他们的交往都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诉求,内心充满诗情画意。而小说结尾,当陶然和夏雪再次见面的时候,按照传统伦理价值,他们都是单身,他们的交往和结合是合乎规范的,可是小说中的两人现在却再也难以走到一起了。在这里,汪淏显然质疑了传统伦理对于男女两性的规约,指出在评价两性的时候,是否互相喜欢、欣赏,是否彼此没有功利性的诉求才是最重要的特质。
能够构成超隐喻的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隐蔽性。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空间中的人很难有能力去辨识这些并非自明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的非权威性,而现代传媒则更是对这种超隐喻式的意识形态进行不断强化宣传,这就很容易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思想凝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在于贡献思想,贡献新的观看社会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汪淏是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一个作家,他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表面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背后的乖谬指出,并将之表现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们不能说汪淏表达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至少,通过这些小说,汪淏对一些似乎不容置疑的正统意识形态提出了自己质疑,带给读者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毫无疑问,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小说到底是写“小”还是写“大”,这在当下中国小说界似乎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有人强调小说一定要写“大”,即便题材不大,但是至少要微言大义,“‘小与‘大是中国小说的纠结所在,无论小说家还是批评家,常常是烹小鲜如治大国,在‘小里不能分明地看出一个‘大便寝食难安。”③另一方面,又有不少的作家、评论家不断强调小说要往“小”里写,强调小说就应该是“小”说。其实,在我看来,小说究竟是要写“小”还是要写“大”,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小说是不应该先天限制必须写“小”题材,或者“大”题材的,或者说,这并不重要。说小说就应该是“小”说,不过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语言游戏而已,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小说题材而言,重要的是,无论是处理“大”题材,还是“小”题材,小说家能否提供独特的视角才是最重要的。作家能否有独特的觀察事物的方式,并且利用恰当的语境把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呈现出来,对于他的小说写作至关重要。好的作家都是按照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塑造他的世界的。正如卡佛所说的,“作家不用太聪明,但他要有伫视平常事物而被惊得目瞪口呆的能力。哪怕可能因此受人嘲笑。”④如果作家有了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观察事物的方式,不管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在这个作家笔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正如卡佛笔下的日常生活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日常生活,奥康纳《好人难寻》中的杀人也不同于其他小说中的杀人一样。毫无疑问,汪淏是强调写“小”生活的,但是我并不以为汪淏小说的价值是因为他选择了“小”题材而具有的。他小说的价值在于,他描述出了自己眼中的独特的、别人没有观察到或者注意到的“小”生活,表现了对某些中国式超隐喻的质疑,呈现了生活中的悖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汪淏小说中的悖论是借助时间的自然延展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这种表达方式,正符合了其小说表现“小”生活的特质,也让其表达充分表现了表面平静的日常生活下面的惊心动魄。
汪淏很多小说都表达了他对生活中悖论的认知。我们不能说生活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充满悖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汪淏提醒我们注意可能存在的一种生活。《比翼飞》中充满了关于友情的悖论。从小说一开始表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会以为,《比翼飞》这个题目是用来形容三兄弟志趣相投的,但是小说最后点题,是我和老大,以及三兄弟当年的同学,现在的百万富翁胡敬东三人合影,然后在照片上题的字。事实上,即便是在当年同学的时候,我和胡敬东就谈不上是朋友,更谈不上“比翼飞”。这个照片的题字固然有少年孟浪的成分在内,但是志不同道不合的三个同学合影,并且在照片上题字“比翼飞”,则毋庸置疑已经带有了某种反讽的色彩。而小说最后,当三兄弟中的老大为了招待老二和老三,把胡敬东拉过来全程买单的时候,三兄弟的比翼飞似乎也已经到头,和当年题字为“比翼飞”照片上的三个人的关系也差不多了。三兄弟似乎都很注重感情,这几十年来又都似乎在互相挂念,但是见面之后却呈现出这样尴尬的局面。这只能证明,要么这感情是假的,要么这感情已经悄然变质,但是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对“比翼飞”三字的讽刺。所以,小说最后虽然四个当年的同学在山上高唱当年的校歌,但是,他们的心已经永远回不到少年时代,回不到这次聚会之前的状态。
《叙事的艺术》是关于两性关系的悖论。《叙事的艺术》中,夏雪原本是一个情感女作家,但是具有讽刺性的是,她却没有能够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这是这个小说的一重悖论。另外一重悖论在于,夏雪原本对小说家陶然是极为仰慕的,仰慕他的才华,他的小说写作水平,但是在小说中,在告诉陶然自己离婚的过程中,她却给小说家玩了一个叙事的艺术,在叙事中充满了语言的圈套,而这个叙事的艺术重心居然不是普通的叙事,而是带有功利心的托付自己的下半生。两人是因为写作而结缘,但是毫无疑问也会在夏雪的叙事的艺术中把两人的关系终结。
在这些小说中,悖论的走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从小说叙事来看,似乎当事人都并不想让这样的悖论发生,或者说,这些悖论的发生,都是违背着小说中人物的意愿的。虽然我们说汪淏的小说写的都是“小”事儿,可是即便是小事儿,也都是毫无疑问的悲剧。或者我们可以说,汪淏展示的是生活中不露声色的悲剧,是没有流血的伤痕。而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悲剧的发生,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小说中的人物既没有体察到这种悖论的出现,也没有能力阻止这悲剧的发生。一切都是在无休无止静静流淌的时间中自然完成的。不设置剧烈变动的故事情节,让悖论在时间的自然流淌中发生,显然更增加了汪淏小说的悲剧性。
合理利用时间的自然延展是现代小说的特质。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的开始部分谈到,小说打破了运用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的较早的文学传统。“小说的情节也因其把过去的经验用作现时行动的原因,使其与绝大多数先前的虚构故事区别开来。通过用时间取代过去的叙事文学对乔妆和巧合的依赖,一种因果关系发生了作用,这种倾向使小说具有了一个更为严谨的结构。”⑤也就是说,在小说这里,时间的顺序前行不仅仅是在遵循我们传统的物理时间,而且事实上这种物理顺序时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就是暗合因果原则,利用时间的自然延伸,使小说情节自然伸展。里蒙·凯南干脆就把故事的时间顺序视为一种因果关系的产物,“时间顺序原则,即‘后来怎么怎么的原则,常常和因果关系原则,即‘原因就在于此或‘因此什么什么的原则结合在一起。”⑥现代小说的这种特质在汪淏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的小说中没有巧合,没有乔妆,没有戏剧性的场景,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时间的自然流淌中自然完成的,时间就是汪淏小说中所有可能结果的唯一原因。汪淏小说特别强调时间的自然延展,在他的小说中,重要的时间段是叙事中物理时间的开头和结尾,这个物理时间的中段反而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一般叙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这种叙事模式对汪淏的小说并不适用。汪淏小说重要的就是小说中物理时间的开始和物理时间的结束这两个时间节点,就是在这两个节点上,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比如《比翼飞》中物理时间开端的青春情怀、梦想与友情与物理时间结束时青春诗意的破败、友谊的破败零落构成巨大的对立;《叙事的艺术》《多年以前,多年以后》中物理时间开端的男女没有任何功利的两情相悦与物理时间结束时男女两性之间的互相提防、把情感利益化构成醒目的反差。至于说为什么从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开头走向那样一个破败不堪的结局,汪淏并不注重在小说中物理时间的中段进行描绘或者暗示,甚至很多小说中这样的中段都是空缺的。就像《比翼飞》中的兄弟三人是隔了很多年才聚在一起,《多年以前,多年以后》中多年以后的李霞突然出现在余梁的面前,《叙事的艺术》中的夏雪突然在离婚之后出现在陶然面前一样,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事情就是突然从一开始的诗情画意转向了故事结束时的凋零不堪。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叙事虽然显得更加的不动声色,没有戏剧性,但是,却具有了更大的悲剧性。如果你能发现生活中的某些变化,你不愿意发生的变化,你还可以去阻止这个你不愿意发生的变化出现。即便你失败,即便是一个悲剧,至少当事人可以说自己已经努力了,或者说,至少他曾经发现了某个地方出问题了。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任何意外事件出现,就是在时间的自然流淌中,人就走了形了,事情、感情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比如说,《比翼飞》中的老大迟荣盛曾经痴迷文学,但是后来却为了钱而受到警告处分;老二秉德,在学校时书法就颇有功力,而且原本也梦想成为书法家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日渐消磨成一个普通平庸的中年男人,一个痴迷于麻将的小领导,而三兄弟的关系也在时间的静静流淌中,在似乎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悄然变形。《叙事的艺术》中的夏雪,一个曾经多么美丽、纯真、骄傲的女孩子,在生活的磨炼下,却成了一个世俗而颇有机心且身材走形的中年妇女。《多年以前,多年以后》中的李霞,多年以前曾经多么痴迷于爱情,多么的真诚,多年以后却为了卖保险来找多年以前的情人,曾经的情谊在这里成了谋取利益的手段。小说中所有的这些变化的发生都构成了一种叙事的悖论,而这一系列叙事的悖论呈现给我们的是,生活中到处都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无声的悲剧。汪淏的“小”的特别就在于,他把生活中被我们忽视的细节毫不留情地放大了,从而让这些普通的细节呈现出了惊心动魄的悲剧感。
汪淏喜欢描述“小”生活,而且能在庸常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生活的独特意蕴。面对这个被无数人美化的世界和生活,汪淏在尽力刻画日常生活之“小”的过程中,放大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从而在呈现生活悖论,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中的一些超隐喻的同时,把生活的悲剧性形象地表现出来,带给我们关于生命,关于自己更多的思考。
【注释】
①[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19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②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李敬泽:《2012:我的笔记》,载《南方周末》2013年4月1日。
④[美]雷蒙德·卡佛:《论写作》,见《需要时,就给我电话》,于晓丹 廖世奇译,85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⑤[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16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⑥[以]里蒙·凱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30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张晓雪,《莽原》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