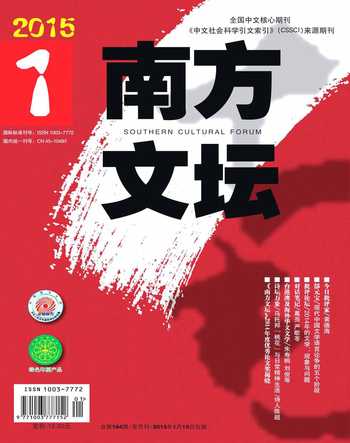怨,还是刺:红日近作略论
2015-05-31张柱林
红日是个喜欢谑笑的人,在基层工作久了,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发而为文,既生动有趣,又言之有物,比许多下笔千言空洞汗漫不知所云的所谓名家名作,对人生和文学有益得多。读他的小说,时常碰到隽言妙语,佳处令人解颐,有些刻画入微的细节,也足资捧腹喷饭。这绝不意味着,红日的作品只有消遣放松之用,很多时候,其题材和主题是让人沉重的,甚至有沮丧和苦涩的味道。这涉及幽默和讽刺在文艺作品中的功效问题,非常复杂,大体而言,我们可以略加分别,高蹈者故作滑稽突梯,仿佛看破红尘,嘲弄万事万物,其实常常是掩盖失败,逃避现实,如后现代主义的陷入犬儒;低下者常常又堕入另一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甚至流于挟怨报复、人身攻击。红日的嘲谑调笑,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两种情况,其原理却并不高深,无他,就是敢于自嘲而已。其近作,如“文联三部曲”《报废》《报销》《报道》,写的是文联的事,而长篇《述职报告》,叙述者兼主人公玖和平,其最后一个官方职务,也是文联主席,正是红日写作这些小说时和现在正担任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作品中,作者是在自指自况自涉,在这个僵化而脆弱的时代,颇要些雅量肚量。
细绎“文联三部曲”,觉得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各有侧重,《报销》涉及文联的工作性质与处境,《报废》主要写文联的地位与待遇,而《报道》写在文联任职的个人对自己的社会价值的思考。文联这样的单位,在中国还有几个,按名义来说是类似行业协会的民间组织,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准官僚机构,红日这三篇小说写的文联,也处处强调自己是处级单位,但却没有实权实惠,所以成了残疾人和失意干部的收容所,或解决官员级别的地方。红日作为文联主席当然深知这一点,他巧妙地将自身感受化为文学资源。《报销》一篇用第三人称,便于全面观察与描绘文联的处境,即名义上肩负领导一个地方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与创作实践,但其实根本无力开展活动,因为没有钱。甚至连制作一条横幅的支出都没法报销。文联主席章富有想了种种方法,都不奏效,最后还是一位权贵老乡帮他渡过了难关。《报废》以一个行将退休的文联老干部为叙述者,故事主体与《报销》接近,但其旨趣却要深曲许多。新任文联主席其实并不深谙文艺,但精于找钱,这与章富有正好相反。他和文联所有人一样,想换一辆新车,钱也找来了,但按规定他们原来的旧车还不能报废,所以新车自己不能用。小说的关键是一位坚持原则的闭副科长,但到关键时刻她也放弃了原则,同意报废文联的旧车。她丈夫担任导游,租用文联的旧车时违法违规,司机小黄如果将其告上法庭会导致他身败名裂。当然,那辆旧车在她丈夫租用时因性能老化出了事故,小黄的小腿报废,而她丈夫的脊椎与生殖器也报废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将其解决居然需要这么多的牺牲,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相较之下,《报道》一篇的基调就庄严许多。小说中也有嘲谑调笑,叙述者自称“文丕”,轻易让人联想到“文痞”,主人公之一外号叫“老跛”,因偷情被打瘸了腿。作品写城里的干部下乡扶贫,这是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各部门和单位都要去的,文联也不例外。文联找不到钱支持当地,想从业务上帮助农民也无能为力,文丕是从报社调过来的,自然想到了用自己的笔反映村里农民们的困难,引起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注意,从而间接帮助老跛他们。他的报道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只是开了个头,像我们这里的许多事情一样,虎头蛇尾。在农民们自力更生的过程中,他的报道有时也起到反作用,如为了修路无钱买炸药时,农民自制炸药,属于违法行为,外界知道后引来很大的麻烦。从“报道”对农民命运前途的影响方面说,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其双重作用。当然纯粹从技术角度看,作品的情节设计有点刻意。小说着力刻画的老跛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勇于自我牺牲是其主要特征。老跛与村民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修通了公路,可事情往往发展到最后出人意料,老跛牺牲后,领导认为他是扶贫攻坚的先进典型,于是为了塑造英雄,村民们又要不停地接待各级各种机关的来人,非常麻烦。村里的干部们认为,这也是“我”的一篇记述老跛的文章导致的。所以,“我”想用报道的形式帮助村民,体现自己的价值,恐怕也得一分为二来看。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叙述者对自己的角色并非只是肯定。文联前来扶贫的前两位,写剧本的老黄和画画的老章,就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而在老跛牺牲后,老章画了一本关于老跛的连环画,老黄则以老跛的事迹为蓝本写作电影剧本,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真正拍成电影的,当然,这是市里的电影。《报道》表面上报道老跛和“我”的各种因缘际会,而实际上再现的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总是化悲痛为力量,变坏事为好事。老跛不牺牲,将一事无成且默默无闻,而他一死,不但公路修通,还成了英雄,并成就了许多其他人。
虽说“文联三部曲”充满自嘲与讽世的双重意蕴,但到目前为止,红日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长篇小说《述职报告》。作品虽有意描绘当今中国中低層的官场百态,读者却会被主人公玖和平的命运吸引。他是一位富于牺牲精神的人,讲义气,重情谊,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他并不深爱自己父母收养的玖雪雁,但母亲决定让他们成亲,他就接受了这个“礼物”;他考上了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本可以像他的两位哥哥一样,出国深造,由于母亲病重,他就义无反顾地回乡工作,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他刚履新,一家工厂出现安全事故,本与他无任何关系,他却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致原已成定局的提拔也泡汤了。同时,他是一位工作认真负责、能力很强、方法巧妙得宜的人。小说一开始就写到这样一个情节,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玖和平,本可以安心在家休息,却闲不住,正好碰到一支因拆迁问题没解决抬棺材上访的队伍,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他无所顾忌地睡到棺材里面去;而为了阻止周志超上访,他费尽心思与其周旋,直到醉倒。作品为了让他完成一些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也就赋予了他一些别人没有的能力。如库区拆迁,一个叫阿三的拳师死活不拆,玖和平靠一身功夫折服了他;最后县政府要改大门征地,也碰到一个软硬不吃的钉子户,玖和平超群的乒乓球技术又发挥了作用。更难得的,是这样一个水平高能力强的“超人”从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不买官卖官,不恃强凌弱,唯一的一次出轨还是因为俩人真心相爱且女方主动,唯一一次私藏毒品是为了让临死前受恶疾折磨的母亲止痛。可惜的是,这个近乎完人的形象并没有完美的人生,他的所有理想几乎都破灭了。他与玖雪雁奉母命成婚,没有谈过恋爱,结婚一起睡在床上一年后才脱下衣服成了真正的夫妻。他与周小芳的爱情怎么看怎么别扭,叙述者的遮遮掩掩总有一种欲盖弥彰的味道,周小芳的一往情深仿佛是其扭曲的婚姻生活的补偿,而非源于生命的激情。他想做一个孝子,但依作品的叙述,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其意义被悬置了。而他工作的价值,无论他怎么定义,很显然并不依自己的理解而决定,只能由他的位置决定,也就是在一个官僚系统中被认可的程度。在这点上,他也完全失败了。整个作品,就是由他等待提拔开始的,到作品结尾,我们知道,他不但没有被提拔,还连公职都丢掉了。当然他丢掉公职完全是自己的责任,他因购买海洛因给母亲注射被判刑。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彻底失去了提拔的希望,因为打乒乓球时赢了新来的县长,他被调整到文联任主席,县文联就他一个人,办公室在哪里都不知道。一个理想的人与一个失败的人生,构成了作品的基本矛盾。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作品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小说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小说的结尾。玖和平当时从省城回来处理遗留问题,他与河边县政府已经没有关系了,可是縣长却请他去处理一件棘手的事。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县长也知道,在河边有些事只有玖和平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但这并不妨碍他一手断送玖和平的仕途。于是就发生了令人笑不出来的可笑一幕:早已不在其位的玖和平冒充河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宣读任命文件,以挽救一个因无职务安排想跳楼的职工。其实,那张纸是玖和平等人的法院判决书。那么,作品意在揭露干部任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似乎也没有那么简单。玖和平通过作品表达这样的认识:“有些事我明知道是错误的也要坚持,因为我不甘心;有些人我明知道是爱的,最后还是要放弃,因为没有结局;有时候我明知没有退路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其实,在这个世间,我们总有一些我们无法完成的事情,一些无法靠近的人,无法占有的感情,一些无法抵达的港湾,无法修复的遗憾。这一切的一切,大概都是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认了。”这段自相矛盾的话也许是一个刚被判完刑从看守所出来的前干部的思想冲突与思维混乱的反映,也可以视为叙述者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判断自己的人生。既然如此,你怎么能保证组织上就应该准确地判断他、合理地任用他呢?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作品所采取的第一人称所导致的。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时代的第三人称作品,叙述者表面上看去是一个旁观者,作品基本保持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对人物和事件的评判大致已由作品的叙述做出。而第一人称不然,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处理。很多时候与第三人称并无太多不同,只是“他”变成了“我”。复杂的是,“我”讲关于“我”的故事,在生活中必然是充满或自夸或自怜或隐瞒的情形的,在小说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换句话说,在第一人称叙述中,作家必然与叙述者构成或近或远的距离,在讽刺性的作品中,作家甚至是带着一种冷眼在观察与认识叙述者“我”。在技巧娴熟的作家笔下,这即形成一种微妙的反讽。读者会带着疑问重审叙述者的叙述,看他强调些什么,又遗漏了什么。对《述职报告》,同样疑云重重。玖和平真的那么完美吗?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做牺牲?这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叙述者的自恋的想象?以他修改增加县政府会议纪要内容为例,他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保护自己的顶头上司,其实质是伪造公文包庇职务犯罪。分明是犯罪行为,叙述者却心安理得地完成了它,那么,这种不计后果的“英雄”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感激上司的知遇之恩?为了讨好上司?还是抓住上司的把柄谋取私利?还是为了某种彼此心照不宣的义气?作品后来的情节可以视为叙述者对自己的辩解。父亲听说儿子被检察院的人带走,心里不安,就提出让玖和平将其他人来医院探视其母亲时送的礼金如数退回,玖和平拒绝这样做,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人际来往,退礼会“伤害朋友兄弟的心”,仿佛将友谊置于党纪国法与个人安危之上。姚德曙与之正好形成对比,作品暗示他被抓后供认出了上级的黎书记,将其形容为“软蛋”。
作品由此展现出“我”的两个重要侧面,一方面他被环境操纵扭曲,另一方面他将这种操纵扭曲视为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他用“认命”加以概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并未加以批判性的审视。他对自己的命运与使命没有一种自觉。小说中玖和平所处理的事件,多数与拆迁有关,在当今中国,特别是地方财政,以土地收益作为支柱的情形下,这是一道最具政治意味的主题。玖和平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洋洋得意之情。英勇地睡棺材、用武力和功夫威胁、用欺骗手段、用个人魅力、用师生关系,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里面,抗争与不合作的一方,要么是没有充分理解官方的好心和苦心,要么是缺乏与开发商的有效沟通,要么是想刁难一下乘机捞取一点好处,而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强买强卖、贱买贵卖、与民争利、故意拖欠款项等,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进行淡化。显然,叙述者抑扬之间,取舍别具匠心。所以,这就构成了主人公的性格的一种矛盾,一方面他违心地曲从环境,放弃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主动地承担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采取一些他不做别人也无法指责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有此能力的措施,而这些行为他不但不能从中获益,甚至会危及他的前途。这样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源于何处呢?叙述者这样塑造自己,图的是什么?作品表现的,仿佛是玖和平的一种本能。当然,叙述者叙述中的不自觉,并不意味着作者的不自觉,读者有时能感觉到作者对叙述者的批判与嘲笑,如小说结尾的黑色幽默。
叙述者在叙述中美化自己或为自己辩解,利用不可靠叙述提供错误的信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高大上”的形象,可以理解为人之常情。相较之下,其与现实的关系,就显得更加复杂微妙。在阅读《述职报告》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并不是叙述者对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而是他对现实的判断与描述。他认可现存的事实吗?很显然,他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其实相当不满,围绕着提拔一事,他告诉我们,有人因为上级领导的关照而得到好处;有人靠拉关系收买人心;有人逃避责任却不降反升;有人明显有问题可上级照样重用。而玖和平的存在,证明干部任用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像“我”这样有水平、有能力、有责任心、道德标准高的人竟然到四十五岁都没提拔到处级领导职位上!愤懑怨恨之情不言而喻。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小说对玖和平的前任盛主任的描绘,他已经内定要提拔,却选择了离职去读博士研究生。他是一个清醒的人,明确说姚德曙很危险。意味深长的是,小说写他很快被查出罹患了致命的癌症。难道这是印证俗谚“好人命不长”?成了一个反面教材?“我”当然想提拔,但遵守基本规则。这就注定了处境艰难。令人困惑的是,叙述中的怨恨并非否定现实,而是自己在现实中的尴尬位置。那些调侃促狭,就成了叙述者的自我贬损或自我宽慰,消解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从根本上说,《述职报告》的叙述者玖和平,确实并不是一个生命的自觉者,他的叙述中满是感伤与不平的怨,而不是批判与反思的刺。
为什么这样说?玖和平的案子一宣判,也就宣布了他的仕途的终结。这之后,他的叙述充满矛盾,时而慨叹感伤,时而顾影自怜。虽然他宣称自己内心坦然安宁,无怨无悔,却又心有不甘。他表示自己以后要遵守看守所陆所长的指引,“只想当作家,要聚精会神搞创作,一心一意谋发表”。可是,这部分明是面向读者的文学创作,却被他命名为“述职报告”,里面还有“我向组织保证”之类的词句。唯一的解释是,习惯成自然。他念念在兹的,并非抒情叙事,而是向“组织”“报告”,仿佛那才是正“职”。言下之意很清楚: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红日那几篇描写文联生活的小说,出自同样的机杼。几位文联主席,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是如何组织文艺工作者,不是如何发展文艺,而是如何解决经费开支,是如何维护自己处级干部的体面。当我们说红日是自嘲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那里面不光有无奈,也有自我批判。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