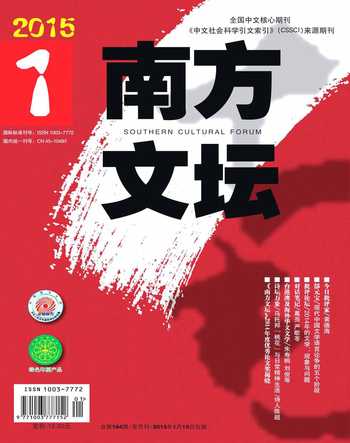如何讲述“王进喜”的故事
2015-05-31陈泉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热播并引起相当讨论,相对来说,工业建设题材电视剧较少,而2010年播出的《奠基者》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二十八集的篇幅展现了新中国动员一切力量从勘探到开采石油的壮阔画面,尤其是集中叙述了大庆石油会战中党的干部、知识分子专家、石油工人在外部国际环境紧张,内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在石油会战中出现的英雄人物“铁人”王进喜成为那一史诗年代的缩影,“王进喜”这个名字召唤起对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的记忆和想象。而“两个三十年”如何讲述“王进喜”的故事则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参照,将1974年的《创业》与2010年的《奠基者》并置讨论,是想通过两个文本对“王进喜”故事的不同讲法的对读,尝试思考两个时代之间的延续和断裂,同时也试图反思我们今天的文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从形式上说,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内,是一个无法区分彼此的整体,看电影是一种集体行动,而电视的观众则被区隔在家庭私产的客厅内,是居家式的更为个人化的形式,形式的因素作为一个隐喻,也有可能成为思考这两个文本之间关系的起点。
1.新人与铁人的辩证法
以王进喜为原型的电影《创业》主人公周挺杉是社会主义激进文化的产物,以典型化作为创作原则,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是由现实主义虚构出来的人物。周挺杉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身份是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油田上牵骆驼的年轻工人“十斤娃”。在影片一开始,叙述的是十斤娃的父亲老周掩护地下党员和为了保护油矿牺牲的故事,十斤娃在父亲那里继承了“带血的袖标”,在新中国成为一名石油工人,并获得了他原来的名字——周挺杉。十斤娃到周挺杉之间的过渡,是一个翻身的过程。这段翻身的历史成为《创业》中王进喜的前史。新人的故事一定要从起源讲起,新人在历史中形成,并与旧的历史决裂。而电视剧《奠基者》中,王进喜的首次亮相是作为钻井队长出现在新疆石油会战的誓师大会上,时间已经开始,而时间开始之前的时间被忽略了。在电视剧中的王进喜也许更贴近真实的王进喜,更接近真人真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现实主义对“真实”不同的看法。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出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周挺杉,还有另一个或许是讽刺性的名字——“高大全”,这里不打算检讨“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这一创作方法的成败得失。我们看到在影片中,周挺杉确实几乎完美。艰苦创业,高度政治化,在路线斗争上与党的官僚针锋相对,教育年轻工人,阅读列宁著作,学习“两论”,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代替工程师在地质勘探图上“划圈圈”。周挺杉之所以可以完美,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个人”,他与社会主义共同体之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周挺杉背后是一个阶级的成长,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主体的诞生,周挺杉是这一理想类型的符号化的化身。在电影《创业》中并没有出现“铁人”这个称号,在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创业,以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身躯投入到新中国的工业建设,这样的“铁人”被吸纳到“新人”的整体性中,成为并不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而“铁人”的创业与电影标题“创业”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将在下文再论及。
而经过《奠基者》的重新生產后,新人周挺杉被拆解成余秋里、康世恩(承担政治参与功能)、杨光羽(承担生产参与功能),还有——王进喜(承担“铁人功能”)。在剧中石油会战的初期,没有吊车装卸钻井设备的情况下,王进喜动员队员们说,“咱三十七个人就是三十七台吊车,是拖拉机,是大卡车,咱们就是三十七头牲口。”这是对“铁人”精神的生动的描绘,艰苦创业,自我奉献。但是这样的“铁人”,无法面对另外的一种质疑,在剧中有一个场景,年轻工人抱怨,“工人阶级也是人啊,拿人不当人,比地主还狠。”如果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只是征用工人们“牲口”的动物性功能,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甚至与地主老爷统治的社会有何区别呢?工人只有不只是作为劳动力而同时在实践中作为国家的主人、生产的主人,才是社会主义走向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电影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镜头,油田总指挥华程与工人一起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干部既是生产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劳动的参与者,这不仅仅是激发工人热情的策略,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克服的内在追求。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又成为克服现实困难的催化剂。正如一位日本学者在观察大庆油田建设时所叙述的那样,“如果研究室与现场之间有一剁厚实的墙壁,两者之间存在对立,相生相克,或利益第一主义的话,要取得成功是极为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干部参加劳动是很有成效的。”①而电视剧中党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工人批评说服工作,则很容易被解释成意识形态的骗局。从这个角度看,只有电影《创业》中的工人叙述才能克服电视剧《奠基者》叙事所面临的危机。
同时,《奠基者》并不是一部彻底去政治化的作品,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去政治去历史的“更真实”的故事应该如何讲述,一个“真实”的英雄,更突出个人欲望,有诸种缺陷,有儿女情长,比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等等,这当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有关。而《奠基者》的叙述重点虽然在“铁人”,但是仍然有新人的“残余”,所谓回到真实的历史,是“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并不是像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叙述的那样存在森严的区隔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所曾经创造的共同体的有机性,抑制了个人主体的生产壮大。电视剧中没有多讲王进喜“个人”的故事,王进喜的口头禅“咱们是谁?”突出的是“咱们”这样一个集体性的概念,“铁人”他毕竟不是一个“赤裸”的人,而是一个新的有机体的一分子,尽管他身上的政治性被剥离殆尽。
2.“王进喜”和他的“敌人”
故事总是内含冲突。在《创业》中故事在周挺杉与一系列“敌人”的斗争中展开,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容易动摇的知识分子专家、受自发势力影响的年轻工人,甚至是背信弃义的苏联,在这些斗争中形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在两个文本中都出现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在石油会战前线学习“两论”的情节。在《创业》中,周挺杉抓住的主要矛盾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而《奠基者》中王进喜抓住的主要矛盾是“国家没油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矛盾”,很难说是哪个故事更符合历史真实,但是可以指出的是,前者容纳后者,而后者则取消了前者。《创业》中周挺杉的主要“敌人”是会战副总指挥冯超,冯在会战初期提出“先生活,后生产”的“人性化”方案,钻井还没开动,先设计起石油城和街心花园(苏联道路),在遭到否决之后,又挑动容易动摇的总工程师章易之,提出“油田的主人是谁”的问题。最后有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冯劝周挺杉追随他,并说“我是最关心人,一切为了人。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党也就应该给你应得的地位、荣誉和幸福”,而周挺杉报之以怒斥,“我想要工人阶级的地位,中国人民的荣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幸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与“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是由冯所规定的“人”(个人、私人)的排斥性所形成的,“阶级”和“人民”则成为防御性的壁垒,这个壁垒所要保卫的正是千千万万现实的“人”。而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是,这种斗争既是政治的,同时也是伦理的、情感的,最后冯超被揭露出来是解放前出卖老周(周挺杉的父亲)的“旧社会小职员”。冯所代表的个人私利不仅是反政治的,同时也是反伦理的,社会主义所规定的集体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又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它的政治敌人同时也是伦理敌人。值得一提的是,冯作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敌人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外部,事实上回避了社会主义自身在内部生产出自己敌人的可能,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当年电影受到了“文革”激进派的批判。
而《奠基者》中,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石油部的高级干部(从前的革命者)在纠正“极左”的错误,当然,高级干部也承担了批评官僚技术人员脱离一线,脱离工人群众,批评后勤衙门县老爷作风。电视剧中反映出来的革命者与官僚的冲突,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殊性切开了一个视角,但是同时也遮蔽了王进喜等工人群众的主体性位置。在苏联(修正主义,另一个敌人)撕毁条约撤走专家之后,《创业》的石油会战总部把情况告诉周挺杉们,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也是油田的主人!”而在电视剧的叙述中,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们只关心劳动竞赛拿冠军,中苏分裂和苏联撤走专家的事件似乎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石油部领导们所忧心的内容。
《奠基者》中,王进喜的“敌人”是艰苦的创业条件,自然灾害和饥饿的狼,剧中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王进喜和另一位钻井队长马厚生的劳动竞赛中,由“斗争”变为“竞争”。电视剧中,王进喜仅有的一次消沉,是在马厚生发明了“钻机自走”而赢得比赛胜利的时候。劳动竞赛不仅有奖状、锦旗,还有物质奖励,所谓“搞出大名堂的给大猪,小名堂给小猪,没有名堂不给猪”。当政治斗争被取消后,工人阶级也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重新包裹它的将是经济性场域,从而劳动也将趋向于受商品关系的制约,不管对于劳动的意识形态修辞是多么美好,最终的结局将回到卢卡奇所说,“目标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脱离社会的行动,变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形式。”②电视剧力图将“物质奖励”放在极其不显眼的位置,不可否认《奠基者》试图要讲的是一个精神激扬的年代,及其对那个年代轻利益重奉献的美好想象。但是取消了政治,取消了王进喜与他的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仅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或许也可以被原谅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实践。而王进喜和马厚生的“竞争”,冯副指挥口中的“我是最关心人,一切为了人”的那个“人”,就成为从“真实”历史中走出来的自然与必然,成为后三十年关于“人”的想象的起点。
3.从“创业者”到“奠基者”
如前言所述,电影《创业》与电视剧《奠基者》的观看方式、场域也很不一样,这种接受机制与叙事结构之间同样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创业》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由各级放映队在工厂、公社组织群众观看,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凭借这一种技术和手段进行传播。从广场上的电影放映到家居客厅内电视剧的播放,既是技术手段的变化(不仅是纯粹工具性的变化,也包括电视商业模式、穿插广告等),也是生活方式的變迁。新的文化形式也内在地寻求新的文化内容,比如电视剧《奠基者》王进喜和马厚生戏剧性的冲突,于是井队之间“打擂台”就成为重头戏,技术员小卢和小王的恋爱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情节。这些娱乐功能在电视剧中是自然而然的,正如电影《创业》的教育功能对当时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同样也是自然而然的。今天偶尔人们聚集在一个小广场观看室外电影放映,只是作为一个怀旧的行动,同样当我们在电视机、家庭影院、电脑上播放电影《创业》时也许会有偶尔的感动,但更多的或许是乏味。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的“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也成为我们思考历史与当下的一个维度。
诚然,人民共和国在继承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历史同时,也继承了“市场范畴的残余”。这就直接涉及围绕社会主义工人在生产劳动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所谓“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的问题。曼德尔在研究过渡社会理论时指出,“从宏观经济出发,有规律地提高生产者的生活水平是‘物质刺激,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否认这一点只能说是陷入唯意志论,并为前进道路造成严重困难。”③《创业》事实上回避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奠基者》直接继承了这一回避,同样没有正面面对工人个体的物质感觉。但是后者的叙述修辞是,在总体性地回避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同时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意识地将那一个时代包装为纯粹精神性的乌托邦,这与它同时强调的物质性“奠基”之间事实上构成强烈的矛盾。因为精神成为没有真正来源的存在,“如果群众不参加讨论和决定事情,那么‘精神鼓励就慢慢变为一种受人控制的,对发展生产很少起作用的手段。”④恰恰是唯意志论最容易向唯物质论变质,从而《奠基者》的理想主义视角在完成与全面物质化时代之间连接时,只需要一个轻轻的跳跃。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创业》到《奠基者》再到我们今天的历史现实有一条延续性的逻辑在起作用。不断地克服这一逻辑与不断地受挫就成为人民共和国艰难的历程。
在如何讲述“王进喜”的故事中,创业者与奠基者是对于王进喜的两种不同的规定性,《创业》中的“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包含了阶级斗争和工业建设的统一,创业是一种进行时,未完成的,它通向了不断革命。而《奠基者》是对新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奠基者的赞歌,与创业相比,奠基是过去式,似乎意味一种历史终结的自我意识。于是就有了创业者王进喜和奠基者王进喜的两种不同的讲法,这种不同的讲法又来源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意识形态与情感结构。人物形象的变迁背后是时代的变迁,既有延续也有断裂,后三十年通过对前三十年的叙述来建立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它重新生产王进喜们,赞美铁人精神,自诩工业成就,将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而铁人精神固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但是难道不也为资产者所喜闻乐见吗?王进喜式的好员工不正是资本主义精神所需要召唤的吗?如果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为今天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扭曲)奠定了基础,是成为近代工业国家历史合理展开的一个环节,那么今天的重述历史事实上是承担了取消历史的功能,同时也造成了人民共和国合法性的危机。
【注释】
①[日]菊地昌典:《我所体验的社会主义》,谭美华译,1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116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④[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过渡社会的理论》,王绍兰等译,19、2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陈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