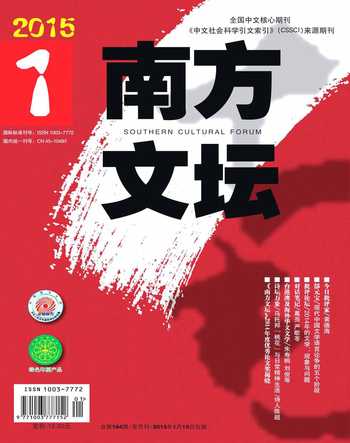异域的位置
2015-05-31颜敏
近现代以来,中国作家已经积累了不少如何叙述“异域”的文学经验,从晚清的官员日记开始,实录精神、反思意识替代了海客谈瀛的神话思维,异域的风物制度、人物事件、文化心理等以各种方式进入文本之中,在拓展中国文学表现领域的同时,对作家的审美思维和文本的美学品格等都产生了影响。但我们或是将这类作品简单归类为异域风情小说,或是从非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其异域叙述的意义,很少从创作角度去总结异域叙述的审美意义。在我看来,“探讨一个作家如何定位异域、怎样和为何叙述异域”等问题不但有利于真正发现异域题材小说的价值,也将从深层面上敞开异之于文学创作的意义。
陈谦是旅美华裔作家中的后起之秀,凭借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她已确立了在当代华文文坛的地位。她的小说,无疑具有地理疆域和文化心理上的游移性,很难鉴定其文本中异域和本土的绝对界限,但其笔下人物的自我意识和空间意识极為清晰,其创作也较为自觉地反思了异域之于自我建构及创作的意义。因此,本文尝试细读陈谦的几部小说,通过梳理其异域叙述的脉络以探寻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并呈现新一代海外华文创作在表现异域时可能达成的新境界。
异域的抽象指涉:别处的生活
所谓异域,是相对本土或故乡而言的,在具体层面,它可以指向某个特定地理疆域的风景人事;在抽象层面,则可以赋予各种寓意和象征。在陈谦的作品里,具体层面的异域在其文本中已经朝两个方向延展,一是美国,一是中国。若从陈谦小说的叙事主体来看,异域首先指向美国。借助那些在中国度过青春岁月再移居美国的华人,文本反复追问美国经验对这一代旅美华人的意义,追问诸如“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在美国又是否真正摆脱了生存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一类华人而言,故乡永远是中国的某个地方,而美国则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时空和处境,是异域。从早期《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苏菊、《覆水》里的依群、《望断南飞雁》里南雁、沛宁、王镭到晚近《莲露》里的莲露,都是在美国哪怕飞得再高,中国的故土经验也无法抹去的人群。而陈谦小说中另一些人物眼里的异域,则又变回中国。2002年发表的《覆水》中,老派的美国人老德和新一代的知识精英艾伦都将从中国来的依群作为遥远中国的投影和化身。2013年发表的《繁枝》和《莲露》中,在重回中国创业的旅美华人志达、朱老师眼里,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成为具有诱惑力和未知数的异域,再次改变了其人生轨迹和生活信念。不过,陈谦小说中,无论关于美国还是中国的具体指涉都非常有限,所涉及的地点、风景和人事虽然也有具体的空间线索可寻,却不以事无巨细的客观再现见长。这种具体层面的异域呈现方式,既无法与专注再现的现实主义传统比美,也无法与近现代集观看、体验、反思于一体的风土记、游记文学匹类。
事实上,与其说陈谦是从具体层面展现我们通常所谓的“异域”,不如说她已经从抽象层面对之重新定位与命名。早在《覆水》中,陈谦借助女主人公依群在困境中的两次突围,提出了“生活在别处”的命题并对之作了反思。如依群一样,人们在遭遇困难时,总将希望寄托在远方,希望通过出走来实现人生的转变,然而,当别处变成了此处时,我们一样跌落生活的繁尘之中,一样遭遇人生的诸多挫折。那么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在别处还是在此处呢?此处的生活与别处的生活真的大相径庭吗?这一连串的问题由陈谦在《覆水》中提出并尝试回答,但此时陈谦对异域意义的探索还刚开始,立场尚未坚定。一方面,她让依群喊出“生活在此处”的口号,告诫人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另一方面,依群又处在无法回头的宿命之中,只能再次踏上未知的追寻之路。在后来的小说中,陈谦的天平已经倾向于选择“别处”,“去远方”变成了她笔下人物的共同抉择。《望断南飞雁》中,南雁离开安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去更远的南方完成学业,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莲露》中,莲露为了摆脱心灵的痛苦和记忆的伤痕,朝海的尽头奔去。《繁枝》中的锦芯选择了自我放逐,飘然于熟悉的人群之外。虽然出走是现代人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衍生的基本生活方式,但陈谦却将之看成是人的宿命,在别处寻求生命新的可能,成了必然选择。由此可知,当她将异域定位成“别处的生活”并赋予其体现生命内在价值的意义时,实际是将异域抽象成了具有普遍性内涵的所指——人在现实困境中寻求的希望之境。
这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异域观,远远超越了近现代风土记和游记的异域定位,也超越了1960年代到1990年代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中的异域观。近现代以来的风土记和游记中,往往呈现具体而微的异域空间,未能对其进行抽象的思考。而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中,异域作为与中国对立的异质空间,常常象征着政治霸权等否定性的固化意象。上述文学创作中,其异域思维模式都建立在中西二元对立的语境之上,从而使得一些有关华人移民的虚构性文本不自觉地陷入了民族寓言的审美模式:“文化冲突成为基本的叙事动力,个人的悲欢离合被放大成民族国家的整体遭遇。”新世纪以来,一些海外华文创作慢慢远离了这种旧俗的审美模式,做出新的探索,陈谦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对于陈谦来说,中国经验和美国经验都是异常重要的创作资源,其小说叙事几乎无法避免呈现本土与异域、故乡和异乡这样的空间结构;但通过赋予异域更为宽泛灵活的普遍指涉,陈谦将自己的创作从民族寓言的审美模式中释放出来。当异域指向的是“别处的生活”时而不是特定国家民族的投影时,叙事的视角也更容易从“文化空间(包括民族属性、国籍身份等)的变动在个体生活中的投影”转化为“个体在变动的生活空间里之心路历程”,宏大的空间叙事就变成入微的心灵叙事,由此,涉及本土和异域双重空间结构的小说就成为探索个人心灵之旅的场域,不再被国家民族的先验性叙事框架所局限。
关于陈谦小说“向内看”的特质,旅美学者陈瑞琳有专文论述,她认为陈谦小说是以女性作为载体找到了通向灵魂的艺术通道①。我想对她这一表述加以补充。其实陈谦选择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故事,而是一个个辗转异国他乡、寻找自我的女性的故事。如果陈谦意在表现“人”这个命题,必然如陈瑞林所言去“呈现灵魂的痛苦挣扎”②及在痛苦中自我的成长;那么,她让人物在新的生存空间遭遇新的挑战,让生命的韧性和人性的复杂程度在变动的生活空间里得以呈现,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艺术策略,更是一个旅居国外的华裔作家的自然选择,因为这些女性所能具有的灵魂重量,是在她的经验范围之内的。陈谦曾经说过,“在海外遇到的女性,去国离家,走过万水千山,每个人都走过很难的路,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异国他乡。所以我身边的女生都很厉害,没有那种很强的意志力,是走不远,也无法存活的。”③严格地说,陈谦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在她笔下,无论男女,在新的生存空间中都有着同样的困惑,同样体现了追寻的勇气。如《望断南飞雁》中,无论是沛宁还是南雁,都将美国作为实现自己梦想的空间,在美国数年的奋斗历程中,他们都面临着莫大的压力,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耐性和干劲。对移民来说,异域都是比故乡更重要的成长空间,《望断南飞雁》中,正是在美国,沛宁和南雁才各自成为自己。
如果出走是人的宿命,那么,对以创作来思考生命奥秘的作家而言,将异域作为追寻者自我设定的乌托邦就是合理的叙事策略。正因此,“主人公离开熟悉的此在,奔向未知的异在”成为陈谦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呈现“在异域中生命的挣扎”也成为陈谦小说探索生命意义的重要审美手段。可以说,由于赋予了“追寻”以本然的意义,“异域”在陈谦小说中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崇高感。当然,作家不是直接使用这一词语,而是将之重新命名与诠释,并使之内化在小说叙事之中,它的位置是稳固的。
异域的淡笔描摹:再现的简化
异域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笔下,主要以几种方式呈现。一是随意化,作家无意中将自己所熟知的某种异域元素散落在其文本中,还谈不上对异域进行自觉再现与概括;二是景观化,作家将所见所闻或如实记录或略加选择,呈现人类学式的日志或浪漫主义的奇观;三是生活化,作家在文本中主要呈现异域生活的日常层面,风景退居其后,人事变成了主体。陈谦的异域呈现方式接近第三种方式,又有自己的特色。
陈谦小说中异域呈现方式的独特性在于,她所呈现的生活空间看似具有纪实性,实际是一种再现的简化,具体而言,是她以选择性的点染笔法提供一种接近生活常态的空间感觉,但在看似现实主义的风格后隐藏着象征化的现代主义思维。她说:“我并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对现实时空的组合方式,像那种魔幻现实,那种重构的A城、B城那种,不是我的个人的风格能所亲近的。每个作家的选择不同,我就喜欢一种很清晰的,有个人标记的东西,各人的来历才搞得清楚,我是这样想的。”④在她笔下,的确没有出现纯粹虚构的地点和扭曲的空间想象,出现的都是旧金山、硅谷、广西北海、广州之类的真实地点;活跃其中的人也接近生活常态,缺乏传奇色彩。这看似与写实传统的再现方式一致,其实不然,在陈谦小说中,像巴尔扎克式精雕细刻的场景建构和风俗人物描写是找不到的。事实上,异域的元素,无论是风景还是人事,在她的小说中都以服从叙事需要的白描笔法来简约呈现,以一种随主人公情感流动的方式来安放运转,淡笔描摹的场景和人事都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具有象征性和仪式性,符合的是现代主义的隐喻原则。如《覆水》中,提及依群和母亲旅行经过美国西部最大的哥伦比亚河时,并无这河景致的一字描写,而仅将之作为连接父亲投江自尽的节点,以这浩浩汤汤的河引发了母女俩对难以捉摸的生命归宿的哀叹之情。就是在描写美国景致较多的《望断南飞雁》里,渲染那场冰天动地的尤金城的大雪、那绵绵不绝的旧金山的寒雨,都只为映衬主人公沛宁此时的心境,少见客观的笔墨。一些海外华文小说里浓墨重彩呈现的异域生活场景和异族情人,在陈谦的笔下也不过寥寥几笔、色调淡雅。如《覆水》中的美国工程师老德、职业规划师艾伦、《莲露》中的风险投资家吉米·辛普森,都是以气质、精神人格取胜,少见精细的再现式描写。试看:“那个叫辛普森的老头齐刷刷的灰白短发,着深黑紧身运动衫,身板笔直地站在一艘神气的帆船前端,正抬手摘取架在头顶的太阳镜,一脸由衷开心的笑容,顺着脸上那些因常年户外运动晒出的深纹四下散开,让他的脸相显得立体有力,跟我在沙沙里多水边撞见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⑤
必须指出的是,陈谦小说有关异域的元素虽以淡笔描摹,可不乏力度,其审美效果恰如中国画里的铁线描,力透纸背。如《望断南飞雁》里的那场大雪和大雪中驾车独自行驶在路上的南雁,水乳交融,精彩地呈现了一个在异域环境中独自跋涉的女子之精神境界。《覆水》里写中国女孩依群初次见到美国工程师老德时,只有以下两句:“老德足有一米九的个子,正值壮年,身子骨十分硬朗”⑥,此时只突出他身体的健壮,而不涉及其他特征,显然是经过选择的。因为当时犯有心脏病的女主人公依群所向往的只是健康而无其他,故她只看到异族男人壮硕的身体;但后来正是老德的年老力衰造成了两人婚姻的困境,这一描摹又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伏笔。在陈谦小说中,这种颇见功力的描摹方式处处可见,使得其异域叙述的细部与小说的整体诉求十分协调,可以承载丰富的内涵。
以“再现的简化“方式来呈现异域,无疑是陈谦追求简约的审美风格的体现,在她看来,简化反而有利于确立一种真实感。她说:“为了使小说看起来更‘真,我必须去掉真实生活里更为复杂的戏剧性元素,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遵循‘忠实于生活的老话,善良的读者甚至可能拒绝小说的‘真实。”⑦的确,点染式的白描笔法,去掉了那些带有偶然性的、难以赋予意义的元素,突出了那些能够凸显主题的细节,从而可以确立起一种审美的主体性。
但这种异域呈现方式,与陈谦异域经验的性质不无关系。一般而言,对于刚刚踏入异域的移民而言,他们容易感受到来自差异空间的琐碎景观,产生的感情体验也往往比较极端,异域在其创作中容易被前景化,成为推动叙事、改变人物命运的突出因素。如《芝加哥之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等作品中,异域都是叙事的焦点,是处在舞台中心的形象。这种对异域的审美设定,往往催生戏剧化的情节结构、呈现片面肤浅的异域经验。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主题歌如此唱到:“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⑧将纽约安置在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极端,将之作为主要人物命运极速沉浮的隐喻,体现了被前景化的异域和戏剧化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但这种过于粗暴的异域呈现方式,逐渐被成熟的移民作家所舍弃,尤其是对那些深入其中,安稳下来的移民作家,他们的异域定位、观察方式及表达方式都在发生变化。陈谦从事小说创作时,已人近中年。在中国度过了最难忘的青春岁月,对“文革”也存有模糊的記忆;在美国也走过了留学打工的最初阶段,进入技术精英荟萃的美国硅谷当上了工程师,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她都有了更为全局深入的把握,因此,在她对有关异域的抽象化认定中,两者都可以是反思回望中的异度空间,但两者都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戏剧化场景,而是意味深长的生活世界。
陈谦的异域呈现方式,还可从写作目的的更高层面寻求理解。她的写作,可视为一种宗教性写作。每一篇小说,都在呈现灵魂的苦痛、寻找生命可能的救赎之途;恰如面向神父、也面向天父的忏悔祷告,在为迷失的人们招魂。这种忏悔祷告式的意义构造,决定了其文本的外在形式。小说往往采取特定人物的单一视角来展现情节、结构全文,在该人物的回望追忆中,不同时空中的诸多细节被连缀成整体以构建探幽人性迷宫的生活空间。这种近乎意识流的时空组合方式,使得为表征人性复杂性而出现的异域也成了点染式的背景。实际上,因为陈谦小说的聚焦点是呈现“某种人生的困局与生命的困惑”,文本的诸多元素包括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是淡出的背景,更遑论异域因素。但是,既然小说试图呈现人性的幽微挣扎,那么作为考验、表征人性的背景而出现的异域并非可有可无。一方面,如前所述,人的苦难总是在变动的环境中得以呈现,异域作为对人性考验的实际存在意义非凡;另一方面,宗教性写作需要依赖特定文化空间才得以存在,就好比忏悔祈祷中的教堂,作为仪式性的背景确保了心灵的声音畅通无阻。无论是《望断南飞雁》里沛宁茫然若失的忏悔录,还是《特蕾莎的流氓犯》里红梅杂乱无章的心灵呓语,都只有依托基督教文化的异域背景才具有了铺展的可能性。
当然,在资讯、交通极度便捷的时代,各种空间元素的水乳交融、不同国家族群的人流交汇已成常态,文学中出现异域景观已是极为自然的现象,根本无须戏剧化、前景化。如此看来,陈谦的异域表达方式也折射了时代的感觉结构。
异域感:一种审美
距离和观察视角的根源
我们已明白,文学不需也不能作为认知异域的主要方式;如果对异域的再现复制不是目的,那么对它的想象和借用将给文学带来什么呢?现在,我们从陈谦的创作入手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总结。
如前所述,一方面,陈谦小说中的异域是以点染笔法勾勒出具有抽象指涉的背景,在这一具体指涉漂浮不定的背景之上,文本重在探索有关人和人性的种种疑惑与思考。另一方面,其小说中本土与异域的空间结构是稳定的,异域虽不是聚焦点,也不是目的,但却内化在其叙事结构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何理解陈谦小说中异域叙述的矛盾性?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的价值,除了依附作家个人的写作才华之外,也会与思想立场、观察视角等有关联。某种程度上,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能以审美的方式提供与众不同的观察方式和思想立场。而海外华文作家的独特性在于,在本土和异域的空间构造中,他们将自己放在游移不定的中间位置,以自身为聚焦点,不但可以更换本土与异域的位置,更能确立了一种有利于审美观照的疏离感,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与本土作家迥异的观察视角,很多海外华文创作的审美价值正是从这一中间性位置生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与其说这些作家要再现某个具体的异域空间,不如说他们要借此确立一种异域感,进而形成独特的观察视角乃至表达方式。陈谦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在这一视野之中;理解陈谦小说中异域叙述的矛盾性也要从此开始。
从陈若曦的《尹县长》开始,海外华文创作就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思想立场深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当下反思之中,显现了以凸显人性的复杂幽深为宗旨的趋势⑨。陈谦的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莲露》等也被归属其中。如宋炳辉认为《特蕾莎的流氓犯》的叙事特色正是“借助异文化场域来反顾本土历史与文化”⑩。但是,陈谦文本中的异文化场其实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游动,恰恰是在对两种生存空间的双重审视与批判中,其小说从自我存在的角度呈现“人无家可归”的悲剧性。我想,这正是陈谦小说具备感人至深之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小说《覆水》中,陈谦尝试以文化差异来构造人生困境,敞开灵魂的苦痛和挣扎过程。华裔女子依群和美国男人老德的婚姻因生理的不和谐而名存实亡,但他们都在苦苦支撑着这一局面。如果说依群是受了知恩必报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约束,老德则是为了信守当年与依群姨妈相伴一生的约定,无论是报恩的中国传统人伦还是西方的婚姻契约,都给两个人带来了伤痛和孤独。依群和另一位美国男子艾伦的邂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故事,敞开了另一种异域生存困境——文化沟壑造成的情感交流滞碍。职业规划师艾伦带着专业主义的兴趣,走进硅谷丽人依群的生活,但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无形的文化阻力,表面意气相投、实则无法深入交流。当依群明了他们关系的症结所在时,选择了退回原位,原本躁动的心也变得更加脆弱焦虑。《特蕾莎的流氓犯》中,陈谦的技法和思考更加成熟,文化空间的印记及其与个人命运的纠葛都透过人物内心的瞬息变化被聚焦。在女主人公红梅(特蕾莎)的黑暗之心中,中国“文革”时年少的她犯下的诬告罪和在美国接受基督教洗礼后的忏悔意识相互纠缠,使她一直处在罪与罚的阴影之中,不得安宁。她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向受害者道歉,得到对方谅解就可以获得新生。但说出来又怎样?当她向中国来的王旭东诉说了一切时,心中的怪兽仍呼啸而来,心灵仍在荒漠之中。另一悔过者王旭东费尽周折得来的“文革”纪实,尽管真实动人却无法抚慰自己、更不用说抚慰他人。无论是中国式的立此存照主义还是基督教的忏悔精神,在陈谦笔下,都未必让沉重的心灵得以解脱。
在稍后的《繁枝》和《莲露》中,陈谦对技术理性主义主宰的美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进行更为清晰的双重审视和批判。她笔下的美国硅谷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世界,人们在狂热地投入技术革新、创造财富的世代潮流之时却丧失了生活的激情。改革开放的中国则是没有底线的花花世界,将人的灵魂抛入无底深渊。《繁枝》中女主人公锦芯的丈夫志达,在美国硅谷依靠个人奋斗拥有了不菲的财富、完整的家庭,可依然找不到归宿感;随着海归潮到中国创业,抱着重新来过的劲头,全力投入到一场婚外恋中,美国的精英教育、夫妻的患难经历、几个儿女全被抛在脑后,剩下的只有被解放的欲望。《莲露》中,女主人公莲露的丈夫朱老师,借助美国文化氛围摆脱了处女情结,与妻子和谐共处了几十年,但一回到中国就旧病复发,在伤害妻子的同时,自己也走上堕落之路。而原本可以让莲露打开心结的华裔心理医生,严格遵守不与病人产生任何私人联系的治疗准则,在她即将走上康复的半途中将之抛给无常的命运。这一小说,作者或许本意在试图呈现人无法战胜自我的困境,但客观上却也批判了中国可笑的处女情结、反思了西方的理性原则,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们联手毁掉了一个原本可能璀璨的生命。
如果个体就算游走于中西之间也无法摆脱困境、如果出走或回归都无法获得心灵的平静,那么,我们的灵魂之所究竟在哪里?当陈谦认识到“人无路可走”的结局后,她有关人的探索还能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呢?她的创作会舍弃本土与异域的空间结构吗?《下楼》是陈谦酝酿中的长篇小说的序曲,其中依然存在中国和美国的双重空间结构,中心情节是:一个女人在爱人坠楼死后再也不下楼,困守在静止的空间里,直到老死。由此看来,陈谦依然在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里思考人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变动的生存空间给予人的影响,是陈谦写作的原动力。她说,“没有去美国,我不会写作,没有这种环境的变换,人的存在不会有如此大的冲击。在美国的经历,打开人的眼界,开放人的心灵,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震撼和感慨之后的思考,是我写作的原动力。”11
我认为,异域感的存在,的确是一个移民作家特有的资源,有才华的作家,会充分挖掘这一来自自身经验的宝库。但对不同作家而言,异域在其创作的位置会有所偏差,对其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在陈谦的写作中,异域恰似一个能剧表演者的面具,已成为一种艺术得以成为艺术的框架,内在于其创作思维之中。其内在性在于,它与叙述主体自我建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借助异域所具有的投射性和他者性,叙述主体才得以不断自我确认、自我反思。因此,这个异域面具就算镌刻出真实时空的某些印记,我们也不可将之作为复制再现的范本,而只能作为渗透着叙述主体印记的心理影像。异域一旦成为作家的表征符号,就像表演者的自我不可能脱离面具而存在一样,两者相互叠合,催生了新的主体形象。这样,异域叙述就成为某些海外华文写作的重要标签,其表述方式则可以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然,对于作家而言,带上这一异域面具之后,自我的位置也变得模糊歧义,他可能需要不断重构和反思自己的异域经验来确认自我及其写作的位置。对于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而言,只要处在异域和本土的张力空间,这种自我探寻的忏悔祷告式写作就不会停止,我们期待的只能是另一种异域表述方式的出现。
小结
在陈谦笔下,作为再现的简化,异域不只是现实主义的布景与现代主义的符号,而是一种类似面具标示的生活成分和身份要素。与其说作家要再现某个异域空间,不如说她要借此确立一种异域感。异域感的存在,确保了作家对其所书写的双重文化空间形成具有疏离感的审美距离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异域感的存在,也使得创作主体的身份处在模糊不清的边界,需要不断重构和反思异域经验以确认自我及写作的位置。由此,陈谦的小说获得了一种越界性的美学特质:心灵世界在空间的斗转星移中出现令人眩晕的复杂性,古典的叙事方式获得了一种后现代的精神质地。在以追寻自我、反思人性为主旨的宗教性写作中,陈谦小说远离了民族寓言的审美模式,开辟了海外华文文学书写异域的新境界。
【注释】
①②[美]陈瑞琳:《向“内”看的灵魂———陈谦小说新论》,载《华文文学》2013年第2期。
③11江少川:《从美国硅谷走出来的女作家———陈谦女士访谈录》,载《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④黄伟林、陈谦:《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海外华人作家陈谦访谈录之一》,载《东方丛刊》2010年第2期。
⑤⑥陈谦:《覆水》,见《望断南飞雁》,1、137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⑦陈谦:《〈莲露〉写作后记》,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6期。
⑧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28页,朝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⑨⑩宋炳辉:《陈谦小说的叙事特点与想象力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颜敏,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暨史料整理”研究成果,项目号:13CZW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