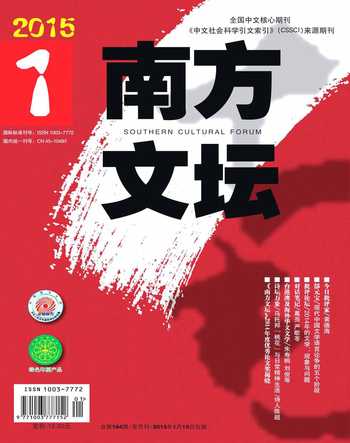母语分娩时的阵痛
2015-05-31胡国平
关于翻译,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中曾经有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在原作中,内容与形式就像果肉与果皮一样紧密贴合、浑然天成,而在译作中,包裹着内容的形式就像一件遍布褶皱的黄袍,拥有独一无二的纹理。这衣服上的褶皱正是译者在劳作过程中所留下的心血。本雅明使用这个比喻并非为了贬低译文,恰恰是为了颠覆我们对于翻译的传统观念。尤其在汉语世界,“信、达、雅”一直左右着翻译思想的主流,汉语世界一直在追求一种可信、流畅、优雅的译文,然而事实上,这些真的是翻译最内在的要求和召唤?这三者真的可以毫无龃龉地共存?其实,我们见到的往往是一些意义凝固、平滑顺畅、充满文学辞藻却毫无生命力的译文,这样的译作犹如一堆失去根基而被华丽展示的枯树,成为了曼德尔施塔姆所批评过的“现成意义的承办商”。尤其对于诗歌,这类译文恰恰构成了对语言的贬损。因为诗歌语言本身要求克服专制性的和怠惰的摹拟和大众消费的流畅,译文语言的褶皱必定来自对原作语言棱角和沟壑的谨慎的勾勒而不是毫无原则的抹平,甚至是对当下读者约定俗成的语言结构的挑战。
本雅明的质问令人意外:“译作是为了不懂原作的读者而存在的吗?”他心目中的优秀的翻译是为了传达“人的存在和本质”(Dasein und Wesen des Menschen),而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或传递信息。他首先关注的是作品的可译性。一部可译的作品必定会与生命发生联系,它言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命或一个时刻”,这样的作品主动召唤翻译,也就是说,它向翻译敞开,而拙劣的作品则拒绝翻译,因为后者迷失在了意义和形式的贫乏漩涡之中。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以信息或知识的交换为目的的翻译往往遮蔽了原作的内在生命,沦落为“非本质内容的不准确传达”。洞悉了人的存在和本质的作品必定会向语言形式提出别样要求,它拷问语言,与语言进行激烈的搏斗,将语言推向意义深渊的边沿,在它上面敲出缝隙或挤压出皱褶;那么,优秀的译作也需要同样的品质,这并非意味着译作可以随意对待原作,恰恰相反,正是在创造性的转化中,译作揭示出了原作的内在生命,甚至更新了原作的生命,从而实现了对原作的最大限度的忠诚。然而这已是另一种忠诚和精确,它是高难度的,它激活了原作并对语言自身提出了挑战。当我读到王家新的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时,我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译文。
另一方面,一门语言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尤其是现代性诞生以后,伴随着历史的急剧变化,语言也持续地更新着自己。那么,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译,翻译本身就成了一种刷新,为一门语言带来别样的呼吸,为这门语言的神秘之物输入新的血液。正如本雅明所说的,“翻译远不是两种僵死语言之间的毫无生机的等式,在一切文学形式中,翻译被赋予特殊的使命,即凝视外语词汇的成熟过程以及自身母语分娩时的阵痛(Wehen)。”这也是王家新这本译诗集的另一个激动人心之处,他的译文自觉地保留原文特殊的语法、用词的难度,在汉语努力发明出别样的句法、节奏和气息。他并没有刻意用陈旧的表达去抹平原文陌生的纹理,这使他的译文胜人一筹。他的翻译实现了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忠诚,这种忠诚听命于语言自身成熟过程的呻吟声因而跃入了对于语言和生命的深沉的爱。
汉语世界的诗歌读者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王家新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歌,正是他使策兰在汉语中成为一种深刻而又强有力的“在场”。许多年前,我还读到过茨维塔耶娃的《约会》,译者也是王家新。我惊异于茨维塔耶娃在汉语中呈现出如此充满张力的语言形态和如此激烈的生命体验,词语之间相互较量,而迸发出的火花是如此炫目:
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
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是的,我将被攫夺
在春天,而你赋予的希望也太高了。
我将带着这种苦痛行走,年复一年
穿过群山,或与之相等的广场、城镇,
(奥菲尼娅不曾畏缩于后悔!)我将行走
在灵魂和双手之上,勿需颤栗。
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
带着血,在每一道河湾、每一片灌木丛里;
甚至奧菲尼娅的脸仍在等待
在每一道溪流与伸向它的青草之间。
她吞咽着爱,充填她的嘴
以淤泥。一把金属之上的光的斧柄!
我赋予我的爱于你:它太高了。
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
这是一个在汉语世界里还很陌生的茨维塔耶娃,王家新的翻译赋予她的诗歌以我期待已久的语言形式。也许是我们误解了诗歌的音乐性,许多汉语译者总是希望让诗歌译文变得朗朗上口,反而极大地削弱了诗歌语言的独特张力。然而,王家新的译文偏偏不去追求这种庸俗的音乐性,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在他的译文中获得了一种缓慢攀升的力量,词语之间充满不经意的摩擦,声音在词语的停顿、牵引和对抗中形成隐忍的节奏。这样的译文正体现了本雅明所谓的母语分娩时的阵痛,它不只是内容的传达,更是语言获得生命的过程,词语的身上携带着与世界进行初遇时的血迹,最终的一切为了“赋予我的爱于你”。有了这一切,“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这样的诗句才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和任性。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地读着这首诗,它一再地唤醒我对诗歌语言的尖锐的感受力。现在,我也理解了王家新为什么会把他这首二十年前的译作作为这部译诗集的开篇:这是他最初的相遇,也是一场永恒的回归。
再后来,我又读到他翻译的奥登诗歌《爱的更多的一个》,这首译诗最初出现在他纪念余虹的文章里:
仰望那些星辰,我很清楚
为了它们的眷顾,我可以走向地狱,
但在这冷漠的大地上
我们不得不对人或兽怀着恐惧。
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
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
如果爱不能相等,
让我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
这样的译文浸透了语言的质询和对生命的洞察力。也许,翻译就是努力在两种语言中去成为“爱的更多的一个”,而只有当译者带着坚忍的爱去经受两种语言所带给他的冲击和考验,其译文才能征服读者的心灵。换作曼德尔施塔姆的说法,内容是从形式中榨取的,犹如海水从海绵中挤出。如果海绵是干的,就挤不出任何水分。贫瘠的形式根本不可能榨出丰盈的内容,更不可能承担起探测存在的任务。作为引文,这首诗,那时我在王家新的文章中只看到前两段,总是令我眷念着剩下的后两段,如今终于在这部译诗集中读到了:
我想我正是那些毫不在意的
星辰的爱慕者,
我不能,此刻看着它们,说
我整天都在思念一个人。
如果所有的星辰都消失或死去,
我得学会去看一个空洞的天空
并感受它绝对黑暗的庄严,
尽管这得使我先适应一会儿。
这样的译文,让人感到奥登的母语几乎就是汉语,或者说是译者在替他在汉语中写诗,并且具有对经验的无与伦比的提炼和呈现能力。本雅明在评论荷尔德林时说过,“诗人越是试图毫无转化地把生活变成艺术,他就越是无能之辈。”译者的情形不也一样吗?王家新的诗歌翻译展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语言才华,而且也是对汉语自身转化能力的探寻、发掘和催促。他的翻译总是浸润着精神力量,总有一种富于张力的呼吸,在语感上不同于其他任何译者,语言和节奏凝练而柔韧,或者说兼具了沉重与轻盈——一种能飞翔的沉重。
这部《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是他诗歌翻译的一次最炫目的集结。那些曾经零星流传、令人爱不释手的译文都被收录了进来。对我个人而言,这本译诗集还是曾经的阅读记忆的容器。这里有他译于1993年的那首《约会》,译于1996年的一批叶芝诗歌(曾经收入《叶芝文集》第一卷),还有近年来在《保罗·策兰诗文选》(2002)之外新译的策兰后期诗选,以及他新近大量翻译的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扎加耶夫斯基、阿米亥、夏尔等,以及零散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沃尔科特、奥登、威廉斯、斯特兰德、默温、洛尔加等。这些“光辉的情人”(王家新译夏尔诗句),仅仅看到他们的名字,就足以吸引我。更让人振奋的是,他的译文具有清晰的内在声音,具有稳定的富有张力的节奏,词语之间相互质询并试图达成和解的质感,以及命运那促迫心灵的回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比如他所译的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地写的一首无题诗:
环形的海湾敞开,卵石,深蓝,
缓慢的帆如云团一样继续移动——
我刚刚知道你的价值,就要离开。
比管风琴的赋格悠长,苦涩如缠绕的海藻,
那长期契约的谎言的味道。
我的头微醉,因为铁的温柔
和铁锈在倾斜海岸上的轻轻啃咬……
为何另一片沙滩会在我的头下铺展?
你——深喉音的乌拉尔,多肌肉的伏尔加,
这赤裸的平原——是我所有的权利——
而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肺来呼吸你们。
“铁的温柔”的确是用来形容王家新译文质地的绝好短语。用曼德尔施塔姆的另外一句诗来说,在这样的译文中,“词语可锻打和燃烧”,铁的温柔正来源于这样的工作。另外就是诗歌的最后一句,“而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肺來呼吸你们”。这是多么有力的表达!这样的译文使我再一次相信诗歌是对混乱现实的抵抗和穿透,是生命本身的呼吸结晶。策兰认为诗歌是一种“换气”,王家新在一个地方指出这也正透出“翻译的秘密”,而他的翻译,就是让曼德尔施塔姆来到汉语中“换气”:为了生命的延续,或者说,给出新的生命。
可以说,正是以这样的翻译,王家新恢复了诗歌翻译的尊严和魅力。他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的长诗《无论谁发现马蹄铁》,被人赞叹为“语言的天籁、翻译的天籁”(王东东语)。他所译的都是他精心挑选的诗人和诗作,并用了全部生命的激情去翻译。他捡拾起了一个俄语天才诗人在历史暴力下的语言废墟中所遗留的“马蹄铁”,用汉语来擦拭那最终的坚硬核心,使石头重新发出了歌唱。弗罗斯特在谈到真正的诗时说过,“读它一百次,它绝不会丧失它曾经为原有的惊异所揭示的意义。”“它始终愉悦,它倾向于冲动,它第一行写下来即有其方向,它在一系列幸运的事件上奔跑,然后终结于生命的澄清状态——不一定就是一种伟大的澄清,例如教派或崇拜,而是有那么一刻消除了混乱。”(转引自希尼《舌头的管辖》,黄灿然译。)读王家新的译文,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体验,它们在汉语中也是真正的诗。在他的译文中,那种语言的共振鲜明地留下了痕迹,每一首诗都具有清晰可辨的强劲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还不断被带向一些意外的瞬间——在那样的瞬间中,如王家新自己爱引用的本雅明的一句话:原作的本质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诗歌的力量不正是来自生命所诉求的语言的意外吗?语言中意外的声音、句法和节奏包孕着爱、希望和诺言,由此诗歌赢得了令人惊异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语言的意外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姿势,来自对生命的内在渴望所要求的语言难度,来自对常规的打破,而绝不是对时尚趣味的迎合。翻译也是一种对于意义钝化和流逝的永不妥协的抗争。尽管,王家新翻译过的许多诗歌在汉语里早已有过不止一个译本,他人的译文也是各有千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对自身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原作也就不断地需要新的译本去更新自己的生命。王家新的译文满足的正是我们对于作品生命的新的期待。他在翻译中凝注了他个人的语言敏感和极大的功力,也体现了当代汉语诗歌所取得的技艺成就,正如他所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致安娜·阿赫玛托娃》中的诗句所写,他的工作是“挑选可以站立的词”,让一首译作在汉语中永久“站住”。借此,他加入并推进了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王佐良、陈敬容等等构筑的一个“诗人译诗”的传统。
这还不是秘密的全部。他精心挑选翻译的诗歌还承载着另一种历史、经验和记忆。这部译文集中附录有一篇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三种历史》,文中这位波兰诗人列举了三种历史:武力的历史、美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现实的情形是,只有前两种历史被编撰和记录,苦难的历史却是哑默的。这就是为什么奥斯威辛的本质变得难以理解。苦难的历史只能交给文学和艺术去言说,然而“艺术史家们也对奥斯威辛不感兴趣。烂泥,简陋的营房,低沉的天空。雾和四棵枯瘦难看的杨树。奥尔菲斯不会朝这里漫步。奥菲妮娅也不会选择在这里跳河自尽”。在王家新的翻译和他的全部写作中,正浸透着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沉痛感。然而,“苦难与希望同时存在,这才是我们的生存图景。”(本雅明)富有勇气和良知的写作正是对苦难的揭示从而召唤出了希望。王家新所拣选的这些诗人,如策兰,如那几位俄罗斯伟大诗人,都承受了历史的沉重苦难,并通过语言的转化记录在了他们的诗歌中,他们的诗歌是苦难的见证,历史的哀歌,“是一个被推抵到灾难的核心的人才可以写出的诗。”(见译诗集附录:《〈在流放地:1935—1937〉译后记》)而王家新为什么要满怀感情地翻译这些诗人,正如他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一首箴言式的短诗所说:
对你,俄语有点不够,
而在所有其他语言中你最想
知道的,是上升与下降如何急转,
以及我们会为恐惧,还有良心
付出多少代价。
王家新最负盛名的翻译是策兰的诗。他翻译的策兰携带着语言在“去诗意化”过程中所凝聚起来的质感,充满历史的疼痛和存在的幽深。在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浩劫与苦难的汉语世界翻译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策兰,这一行为本身即是两种历史之间的深刻呼应。事实上,这正是作为诗人的王家新无论在写作还是在翻译中所呈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面目,他的翻译饱含着对历史的痛苦体验和对表达困境的独特揭示。的确,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翻译是创造形式的渴望。不过,这种形式首先来自一种抵抗,抵抗在残酷的历史中生命及其记忆的逐步流失和被剥夺。如同诗人,译者也是用语言进行测量和建造的人,是深深卷入语言命运、持续揭示生命苦难并召唤希望的人。并且如同写作,真正的翻译也是对语言困境和可能性的呈露,它知难而进,抵抗着磨损、遗忘和同质化,重新释放出语言的和人性的资源。这样看来,翻译犹如写作,是秘密记录命运的黑匣子,是席卷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深渊里的风暴。王家新的翻译就是这样一股强劲的風暴,它必将深入而持久地影响汉语诗歌的气候。
2014年7月
(胡国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