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散文
2015-05-30刘文飞
刘文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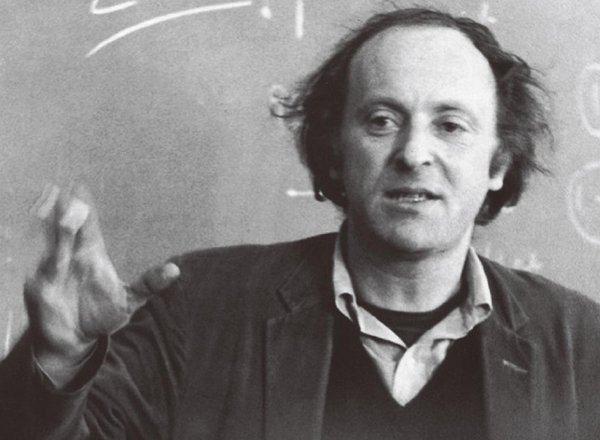

《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不仅是关于诗的散文,它们也是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
布罗茨基在评说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指出:“在她所有的散文中,在她的日记、文学论文和具有小说味的回忆录中,我们都能遇到这样的情形: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文体,诗歌发展成了散文。茨维塔耶娃的句式构造遵循的不是谓语接主语的原则,而是借助了诗歌独有的技巧,如声响联想,根韵,语义移行等等。也就是说,读者自始至终所接触的不是线性的(分析的)发展,而是思想之结晶式的(综合的)生长。”布罗茨基这里提到的诗性的散文写作手法,这里所言的“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文体,诗歌发展成了散文”之现象,我们反过来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中也随处可见。
首先,《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都具有显见的情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据说,布罗茨基性情孤傲,为人刻薄,他的诗歌就整体而言也是清冽冷峻的,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较之于诗人的“悲伤”情感,他向来更推崇诗歌中的“理智”元素。无论写诗还是作文,布罗茨基往往都板起一副面孔,不动声色,但将他的诗歌和散文作比,我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布罗茨基在散文中似乎比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抒情。与文集《小于一》的结构一模一样,布罗茨基也在《悲伤与理智》的首尾两处分别放置了两篇抒情色彩最为浓厚的散文。在《小于一》一书中,首篇《小于一》和尾篇《在一间半房间里》(In a Room and a Half)都是作者关于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的深情回忆;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第一篇《战利品》是作者关于其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细腻回忆,而最后一篇则是对于其诗人好友斯蒂芬·斯彭德的深情悼念。作者特意将这两篇抒情性最为浓重的散文置于全书的首尾,仿佛给整部文集镶嵌上一个抒情框架。在《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中,他深情地将斯彭德以及奥登和麦克尼斯称为“我的精神家庭”(my mental family),他这样叙述他与斯彭德的最后告别:“我吻了吻他的额头,说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请向威斯坦和我的父母问好。永别了。我记得他的双腿,在医院里,从病号服里伸出老长,腿上青筋纵横,与我父亲的腿一模一样,我父亲比斯蒂芬大六岁。”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他在《在一间半房子里》的一段描写:“在我海德雷住处的后院里有两只乌鸦。这两只乌鸦很大,近乎渡鸦,我每次开车离家或回来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它俩不是同时出现的;第一只出现在两年之前,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第二只是去年出现的,当时我的父亲刚刚去世。”身在异国他乡的布罗茨基,觉得这两只乌鸦就是父母灵魂的化身。布罗茨基在大学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哈代的诗歌,他一本正经,不紧不慢,可在谈到哈代《身后》一诗中“冬天的星星”的意象时,他却突然说道:“在这一切的背后自然隐藏着那个古老的比喻,即逝者的灵魂居住在星星上。而且,这一修辞方式具有闪闪发光的视觉效果。显而易见,当你们仰望冬日的天空,你们也就看到了托马斯·哈代。”我猜想,布罗茨基这里的最后一句话甚或是出乎他自己意料的,说完这句话,他也许会昂起头,作仰望星空状,同时也为了不让学生们看见他眼角的泪花。在布罗茨基冷静、矜持的散文叙述中,常常会突然出现此类感伤的插笔。布罗茨基以《悲伤与理智》为题分析弗罗斯特的诗,又将这个题目用作此书的书名,他在说明“悲伤与理智”就是弗罗斯特诗歌、乃至一切诗歌的永恒主题的同时,似乎也在暗示我们,“悲伤”和“理智”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情感元素,无论在诗歌还是散文中都有可能相互共存。他的散文写法甚至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般说来,诗是“悲伤的”,而散文则是“理智的”,可布罗茨基又似乎在将两者的位置进行互换,在刻意地写作“理智的”诗和“悲伤的”散文,换句话说,他有意无意之间似乎在追求诗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诗性。这种独特的叙述调性使得他的散文别具一格,它们与其说是客观的叙述不如说是主观的感受,与其说是具体的描写不如说是抒情的独白。“所有这些文本,都是作者的内心独白,是他激情洋溢的沉思,这些独白和沉思大体上是印象式的,无限主观的,但是,依据布罗茨基在其俄语诗作中高超运用过的那些诗歌手法,它们却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文本。”(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中译文第298页)
其次,《悲伤与理智》一书以及书中每篇散文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节奏都是典型的诗歌手法。关于布罗茨基的散文结构特征,研究者们曾有过多种归纳。洛谢夫发现,布罗茨基的散文结构和他的诗作一样,“有着镜子般绝对对称的结构”,洛谢夫以布罗茨基的俄文诗作《威尼斯诗章》和英文散文《水印》为例,在这一诗一文中均找出了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水印》共五十一节,以其中的第二十六节为核心,文本的前后两半完全对称。前文提及布罗茨基两部散文集均以两篇自传性抒情散文作为首尾,也是这种“镜子原则”之体现。这一结构原则还会令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创作中的俄国时期和美国时期所构成的镜像对称关系。伊戈尔·苏希赫在对布罗茨基的散文《伊斯坦布尔旅行记》的诗学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出了布罗茨基散文结构的“地毯原则”,即他的散文犹如东方的地毯图案,既繁复细腻,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也高度规整,充满和谐的韵律感。帕鲁希娜在考察布罗茨基散文的结构时,除“镜子原则”和“地毯原则”外还使用了另外两种说法,即“‘原子风格结构”和“音乐—诗歌叙事策略”。温茨洛瓦在对布罗茨基的散文《伊斯坦布尔旅行记》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布罗茨基的散文由两种文体构成,即“叙述”和“插笔”:“这种外表平静(但内心紧张)的叙述时常被一些另一种性质的小章节所打断。这些小章节可称之为抒情插笔(为布罗茨基钟爱的哀歌体),可称之为插图和尾花。……如果说叙述部分充满名称、数据和事实,在抒情部分占优势的则是隐喻和代词,苦涩的玩笑和直截了当的呼号。”(温茨洛瓦:《从彼得堡到伊斯坦布尔旅行记》,见其俄文版论文集《筵席谈伴》第179页)无论“镜子原则”还是“地毯原则”,无论“原子结构”还是“音乐结构”,无论“叙述”还是“插笔”,这些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观察到了布羅茨基散文一个突出的结构特征:随性自如却又严谨细密,一泻而下却又字斟句酌,形散而神聚。
与这一结构原则相呼应的,是布罗茨基散文独特的章法、句法乃至词法。《悲伤与理智》中的二十一篇散文,每一篇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均由若干段落或曰片断组合而成,这些段落或标明序号,或由空行隔开。即便是演讲稿,布罗茨基在正式发表时也一定要将其分割成若干段落。一篇散文中的章节少则五六段,多则四五十段;这些段落少则三五句话,多则十来页。这些章节和段落其实就相当于诗歌中的诗节或曰阙,每一个段落集中于某一话题,各段落间却往往并无清晰的起承转合或严密的逻辑递进,它们似乎各自为政,却又在从不同的侧面诉诸某一总的主题。这种结构方式是典型的诗歌、更确切地说是长诗或长篇抒情诗的结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蒙太奇”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布罗茨基多次声称,发明“蒙太奇”手法的并非爱森斯坦而是诗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布罗茨基是用诗的结构方式为他的散文谋篇布局的。《悲伤与理智》中的句式也别具一格,这里有复杂的主从句组合,也有只有一个单词的短句,长短句的交替和转换,与他的篇章结构相呼应,构成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布罗茨基喜欢使用句子和词的排比和复沓。他在《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一文中这样写道:“其结果与其说是一份大杂烩,不如说是一幅合成影像:如果你是一位画家,这便是一棵绿树;如果你是唐璜,这便是一位女士;如果你是一位暴君,这便是一份牺牲;如果你是一位游客,这便是一座城市。”排比句式和形象对比相互叠加,产生出一种很有压迫感的节奏。《致贺拉斯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对于他而言,一副躯体,尤其是一个姑娘的躯体,可以成为,不,曾经是一块石头,一条河流,一只鸟,一棵树,一个响声,一颗星星。你猜一猜,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一个披散着长发奔跑的姑娘,其侧影就像一条河流?或者,躺在卧榻上入睡的她就像一块石头?或者,她伸开双手,就像一棵树或一只鸟?或者,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从理论上说便是无处不在,就像一个响声?她或明或暗,或远或近,就像一颗星星?”布羅茨基钟爱的排比设问,在这里使他的散文能像诗的语言一样流动起来。在这封“信”中,布罗茨基还不止一次坦承他在用“格律”写“信”:“无论如何,我常常对你做出回应,尤其在我使用三音步抑扬格的时候。此刻,我在这封信中也在继续使用这一格律。”“我一直在用你的格律写作,尤其是在这封信中。”帕鲁希娜曾对《水印》中单词甚至字母的“声响复沓”(phonic reiteration)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找出大量由多音字、同音字乃至单词内部某个构成头韵或脚韵、阴韵或阳韵的字母所产生的声响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罗茨基在他的散文中使用了除移行(enjambment)外的一切诗歌修辞手法。
最后,使得《悲伤与理智》一书中的散文呈现出强烈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布罗茨基在文中使用了大量奇妙新颖的比喻。布罗茨基向来被视为一位杰出的“隐喻诗人”,他诗歌中的各类比喻之丰富,竟使得有学者编出了一部厚厚的《布罗茨基比喻词典》。帕鲁希娜曾对布罗茨基诗中的隐喻进行详尽分析,并归纳出“添加隐喻”、“比较隐喻”、“等同隐喻”和“替代隐喻”等四种主要隐喻方式。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隐喻”(metaphor)一词出现不下数十次。在布罗茨基的散文中,各类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比喻更是俯拾皆是。这是他的写景:“几条你青春记忆中的林荫道,它们一直延伸至淡紫色的落日;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尖顶,或是一座方尖碑的尖顶,这碑尖将它的海洛因注射进云朵的肌肉。”(《一个像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他说:“显而易见,一首爱情诗就是一个人被启动了的灵魂。”(《第二自我》)
这里所引的最后一个例子,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布罗茨基散文中比喻手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即他善于拉长某个隐喻,或将某个隐喻分解成若干小的部分,用若干分支隐喻来共同组合成一个总体隐喻,笔者拟将这一手法命名为“组合隐喻”或“贯穿隐喻”。
其实,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原本就无太多严格清晰的界线,一位既写散文也作诗的作者自然也会让两种体裁因素相互渗透,只不过在布罗茨基这里,在《悲伤与理智》中,诗性元素对散文的渗透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他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和洞见,灵感和意象,结构和语法,甚至具体的警句式诗行,均纷纷被引入其散文;只不过在布罗茨基这里,他借鉴诗歌元素进行的散文创作,“用诗歌的花粉为其散文授精”(帕鲁希娜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或许,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将《悲伤与理智》一书的文体定义为“诗散文”。《悲伤与理智》中的二十一篇散文均以诗为主题,均用诗的手法写成,均洋溢着浓烈的诗兴和诗意,它们的确是诗性的散文,但若仅把它们视为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以另一种体裁形式的继续,这或许是对布罗茨基散文的主题和体裁独特性的低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贬低”。布罗茨基的确将大量诗的因素引入了其散文,可与此同时他也未必没将散文的因素引入其诗歌,也就是说,在布罗茨基的整个创作中,诗和散文这两大体裁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两者间似乎并无分明的主次地位或清晰的从属关系。以《悲伤与理智》一书为代表的布罗茨基散文创作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所赢得的巨大成功,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布罗茨基的散文不仅是其诗歌的“继续”,更是一种“发展”,甚至已构成一种具有其独特风格和自在意义的“存在”。
与诗歌一样,散文也成为布罗茨基表达其诗性情感和诗歌美学的主要方式之一。布罗茨基通过其不懈的诗性散文写作,已经跨越了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间的分野甚或对峙;布罗茨基借助《悲伤与理智》一书的写作和出版,已经让诗人和散文家的名分在他身上合二为一。布罗茨基的散文无疑是堪与他的诗歌媲美的又一高峰,两者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构成了布罗茨基文学创作的有机统一体。
本文截选自《悲伤与理智》一书的译者序(第三章节),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