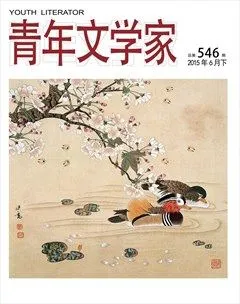反抗与妥协之间
2015-05-09赵盈盈
赵盈盈
摘 要:加缪《局外人》中的默而索是具有荒诞意味的文学典型,在面对死亡真相与人之为人的张力时有着一系列的反抗心理。本文试图沿着默而索成为局外人的轨迹,探讨他因为阳光而杀人的举动,从“精神上的危险分子”沦为“行为上的危险分子”的自我意识觉醒过程,并进一步探究其试图融入局内又游离于局外的“荒诞人与孤独者”形象背后的深层意义。
关键词:《局外人》;反抗;妥协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8-0-02
一、局内人
(一)妥协与渴望
《局外人》的法文书名是L?tranger ,?tranger译为“陌生人”时虽涉及人与社会的疏离关系,但更强调个人性情方面的怪异。考虑到文本采用的零度写作手法对情感的自然淡化,笔者会对默而索性格上的怪异抱以更加宽容的态度。
立足现实,默而索无疑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员。但适应社会规则却有悖其真诚的天性。可他却在困乏时主动找门房说话以提神,而非漠视众人直接入睡;在妈妈遗体前对抽烟有所犹豫,而非以自己的烟瘾为先。这都说明他妥协于社会中人们所遵从的道德原则。
事实上,除开妥协的成分,默而索也渴望融入社会。当妈妈的朋友来为妈妈守灵时,默而索选择相信他们不自然地点头是在跟他打招呼,也隐约承认了老人流露出的沉痛感是真实的。这意味着默而索并不排斥所谓表达悲痛的形式。默而索还默默关注着母亲生前的“未婚夫”贝莱兹先生,虽然初次见面时认为他“态度做作”,[1]10但在送葬母亲的时候,默而索却受感于老贝莱兹对母亲的那份执着之情,多次不自觉地关注瘸腿的贝莱兹跟随灵车的脚程。应该说,默而索对老人们的关注和言语表达上的木讷相对比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或许是默而索因爱而亲近这个世界的表现。
(二)局内人的局外意识
在葬母的整个过程中,默尔索都是一种向世界靠拢的姿态,这个世界里生活着广大的同他母亲一样善良的底层人民。然而世界里还生活着养老院院长、老板、警察等代表这个世界真正掌权者的人。如果说,默而索对前者有主动亲近之意,那对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麻木的被动和妥协。
在操办妈妈葬礼这件事上,养老院院长以掌权者姿态操控了全局,使得默而索从发丧报到送葬都处于被动的位置而无力反抗。但事实上,默而索对这种强迫感到了疲惫和厌烦。这种不满在院长私自决定为默而索妈妈举行宗教仪式的葬礼时达到了新的层次。因为此时一直以来都无所在乎的默而索在内心提出了质疑:“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1]5这是默而索首次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反对外来者附加给他的意志。如果说默而索反感所谓的决定了社会形态的社会掌权者,那么他一直以来怪异的行为就得到了解释,正因他看透了现存不公正的社会机制,相比于少数统治者而言,他才成了“局外人”。而较之于多数被统治者而言,默而索意识到了统治者所许诺的自由意志是无效的奢侈品这一痛苦现实后又成了局外人的“局外人”。当然,此时默而索的“局外”意识还很模糊,甚至当他杀人时都充斥着一种被强迫的意味。然而默而索毕竟开始萌生了局外意识。
二、对阳光的叛逆
(一)不孝之否定
当默而索萌生了反抗局内的意识后,精神的苦闷开始体现在行为上。他在妈妈葬礼后的第二天就去游泳、看喜剧、和女人做爱,这种将葬礼的肃穆感和死亡的沉重感抛之脑后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这看似不孝的行为该如何解释?
一开始,默而索对多出的两天自由时间无所适从,但他对时间的概念和意识也算初露端倪。然而为了遵循原先平凡刻板的生活步调,默而索去了海滨浴场游泳,并遇见了玛丽。他与玛丽亲密调情,这里或许掺杂了情欲的成分,但结合文本,他安睡在玛丽肚子上的行为更像是孩子寻求母亲安慰的举动。可见,游泳本身与玛丽带给默而索的安全感共同缓解了他精神与身体上的疲惫。关于做爱的描写,小说只隐晦用了两句话表达了一种可能性。之后,默而索在枕头上寻找玛丽头发留下的盐味的这一细节却表现出他对女性的天然依恋,玛丽作为小说中仅次于妈妈的女性,此时无疑缓解了妈妈死去后默而索内心的孤獨与寂寞。因此,检察官对默而索“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的谴责意味也大大减淡了。那么,问题就归结到了默而索对死亡的看法与态度。
(二)死亡与荒诞
小说的死亡事件有三起,母亲的死,阿拉伯人的死,默而索的死。默而索面对妈妈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其实是对死亡本身的淡漠。在默而索的思想里,死亡可以摆脱荒谬,得到解脱。然而,这或许出于自我的麻痹意识。将对死亡的恐惧封闭,麻木地生活就是默而索之前的生活状态。直到妈妈死了,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不甘压迫的反抗意识得以显现出来。于是他告诉律师:“我能够肯定地说的,就是我更希望妈妈不死。”[1]41小说中有句话,“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出现了两次,较典型地代表了默而索对于死亡和人生的观点。在默而索看来,世界的秩序和规则都是不合理的,人的选择是两难的。死亡也使得人的生命没有出路,因此世界是荒诞的。所以,他找不到生活的确切意义,而有限时间所赋予的有限的自由倒成了荒诞感的诱因。然而,默而索意识里的荒诞与自我的情感在妈妈死后产生了冲突,他明知“活着没有任何价值”却肯定地表明“更希望妈妈不死”,这也就意味着他萌生了对生命的渴望,他的自我意识变得强化了,对荒诞的感受也更明确了,这使得他逐渐脱离局内,走向局外。
(三)杀人与反抗
如果说,小说第一部里的主人公只萌生了荒诞意识却还未改变,那在第二部里,他对荒诞的认识与反抗就变得明朗了。因此起着过渡作用的杀人本身的意义非常值得深究。自始至终,杀人过程都显得隐晦不明,杀人动机则被包含在默而索的意识流动里。因太阳而杀人显然是一种象征。
有学者认为“阳光代表着打破了某种和谐后人所产生的焦灼感。”[3]确切地说是对生活意义探知无解的一种焦灼感。也有学者将这种焦灼感理解成为默而索因对母亲怀有负罪感而进行的自我惩罚。[2]176所以随着太阳所带来的负罪感的加剧,摆脱负罪感的死亡成了缓解其精神重负的途径,小说中隐晦表达的默而索杀人时产生的巨大快感也就与之相呼应了。两种说法都意味着默而索自我意识的失控,而这种失控正以暴力的杀人形式表现出来。于是默而索成了行为上的危险者。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默而索因为阳光杀人的行为是反抗荒诞的行为,从而大大消解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审判意味。[3]而学者倪伟从历史内容的政治批评角度出发,提出“黑脚”①和阿拉伯人之间对“海滩,大海,阳光,泉水”所象征的资源的争夺才是默而索枪杀阿拉伯人的隐喻意义。[2]180于是,默而索的杀人和阿拉伯人的被杀都成了无法逃脱的残酷历史宿命。虽然这两种说法都合理解释了默而索的杀人行为,但都忽视了“杀人”本身是犯罪。默而索杀了人就意味着他丢掉了为人的底线。这种人性堕落的快感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他从现实里脱离局内人的根本原因。当然,阿拉伯人的死亡也使默而索的自我意识走向了一个节点,他开始感觉苦难,却未意识到这苦难通向死亡。直到默而索被判处死刑,他对死亡的正视才彻底显现出来。这种正视兼含着反抗与妥协的意味。
三、禁锢中的反思
(一)对正义的诉求与失落
小说第二部里对默而索自我意识的觉醒有了更为清晰的表现,默而索被捕后开始接触法律社会中的掌权者,这种身份、阶级、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令默而索开始对法律、正义、友爱和自我进行反思。
默而索的案子一开始无人问津,直到一位预审推事的出现。推事对默而索亲切得甚至让他产生了想与之握手的冲动。然而,默而索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杀人犯身份的尴尬,从而变得清醒。事实上,推事曾直言感兴趣的是默而索这个人,而对死亡与杀人并不十分关注。由此可见,推事对案件的关注里少了基本的人文关怀,审问源于其卑劣的猎奇心理,正如默而索初见推事时所以为的“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因此默而索对法律程序的漠视就变得情有可原了。但是法律本身却代表着正义,默而索对此也毫不怀疑,所以他才会在律师气愤无法令他说谎以求胜诉时辩解:“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得到合乎人性的辩护。”[1]41然而,无论是漠视死亡的推事,只求胜诉的律师,还是歪曲事实的检察官,都使得法律维护正义与人性的本意失落了,默而索所感觉到的只剩下了身份与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与隔膜。“和他们都是自家人”成为了一种可笑的感觉。[1]44这时候的默而索自绝于世的局外意识又更近了一步。然而,虽然默而索对主流意识里的法律感到失望,却在莱蒙、赛莱斯特等人那里收获了难以言说的理解和友爱,也因此更加贴近了生命与人性。
(二)对荒诞的正视与反抗
法庭上的默而索词不达意的语言缺陷;检察官审判时的贵族优越感;律师无视当事人,只求胜诉的小丑姿态,都使默而索“局外人”的形象变得清晰无比。于是他终于意识到无法掌控命运的荒诞,这也成了他最终放弃上诉,选择死亡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这“接受死亡”的决定中还有着一层大义凛然地反抗荒诞的意味存在。这就是西绪福斯式的英雄主义②。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必须是世界的主宰。但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人类整体的人都无法用理性和科学穷尽世界,于是“人是世界的主宰”与“人无法掌握世界”之间的张力就使人变得可怜又可笑。小说中的默而索面临的即是如此的境况:被荒诞取代了主体位置的命运。因此,加缪为默而索设定了第三种结局以鼓励人珍视现世生活,即成为“反抗荒诞的英雄”。这种反抗荒诞的勇气起于默而索自我意识的全面觉醒。
在小说第二部的首章中,默而索还处于“失去了回想的习惯”的状态。而在第二章中却“学会了回忆”。甚至在回忆里将自己的生活重新过了一遍。此外,他还在入狱满五个月的晚上第一次主动对着铁碗看了看自己,也在那时“第一次清楚地听见了自己说话的声音”。这种对自己影像和声音的追寻意味着默而索的自我认知。此时的默而索虽然意识到世界是荒诞的,却并未陷入虚无,而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清晰回忆昂然赴死,宣示生命的意义。默而索接受了死,也就意味着面对死,既向死亡妥协又充斥着反抗的意味。因此,他与西绪福斯一样,既服从了“神”的惩罚又蔑视惩罚。而赴死的行径也使得他高于自己的命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
注释:
[1]转引自毛尖《巨大灵魂的战栗》,“黑脚”(pied-noir),指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法国人。
[2]古希腊神话中,神判处西绪福斯在地狱中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西绪福斯不肯向神低头,不断重复这种明知无意义的推石行为。加缪认为,西绪福斯“不肯向神低头”是反抗命运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法)阿尔贝·加缪,郭宏安译.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毛尖.巨大灵魂的战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3]Fletcher D. Camus between yes and no: A fresh look at the murder in l'?tranger[J]. Neophilologus, 1977, 61(4): 523-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