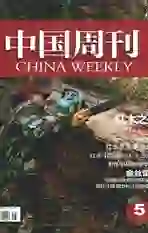思想的弧度与分裂
2015-04-29陈蔚文
陈蔚文,女,1974年7月生。籍贯浙江金华。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女友》杂志上海发稿中心主任、首席编辑,现供职文学刊物。
发表小说及散文随笔数百万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天涯》《小说月报》《大家》《钟山》等报刊,被收录多种年度选本。获“人民文学新人奖”等奖项。
出版小说集《雨水正白》(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随笔集《见字如晤》(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得浮生一日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未有期》(浙江文艺出版社)、《叠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诚也勿扰》(广东新世纪出版社)、《蓝》(上海远东出版社)等十本。
人类有许多关于第一创造者的纪录,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人,第一个发明麻醉剂的人,第一个发现X光射线的人,第一个研制避孕药的人,第一个发明镜子的人……可谁是第一个疯子呢?当然,这种猜想或许本身就不正常。
我想说的是,可能正是世上第一个疯子拉开了文明的帷幕!在神经元的某种紧张对抗中,一种脑部内的板块运动开始了,它不再是一个平整的大陆,而有了思想的弧度与分裂,像那句话,“裂痕是为了方便光的照进”,于是,文明与艺术之光才真正照进了人类。
每周三晚上,送孩子上课路上,我都会在一个公交车站碰到一中年女疯子,她衣着齐整,面色红润,正喋喋地向空气发表着演说,叙事完整,因果井然,以致我头回听见以为她在使用耳机讲电话。当发现她是疯子后,我特意在公交站台停留了下,装作等车,以满足窥听欲。她絮叨的都是些家事,那些存在于无数家庭中的纠结……一个日常的疯子,琐事的牵扯使她的神经发生了短路。
另一些疯子,是高于日常生活的,或者说他们的血液中藏有引线,遇上“疯”的火石,便会燃烧,产生宝贵的能效——艺术地界内,疯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原创资源,是点睛之笔!比如凡高,他的癫狂派生了阿尔金光四射的向日葵。还有挪威画家蒙克,他的精神分裂症((他父亲与妹妹也患有精神病,父亲常向孩子们灌输他对地狱的根深蒂固的恐惧)为美术史贡献了著名画作《呐喊》。蒙克曾说,“病魔、疯狂和死亡是围绕我摇篮的天使并且他们伴随我一生。”看看他的画名吧,《病室里的死亡》《绝望》《吸血鬼》《焦躁》《灰烬》——人类的精神黑洞在蒙克的画笔下无处遁身……
与他同类的画家有生于1973年的日本画家石田彻也,他的画作是另种风格的“变形记”,以超现实手法描绘日常生活,作品中人物全都眼神空洞,好似生产线上的产品,充满扭曲和压抑。31岁时,这位年轻画家“因火车事故身亡”,也有说是跳轨,我倾向后者答案。这些画作本身就像黑色谶语。
人类字典中对疯子的释义是“行为古怪的人,可能做出疯狂或放肆行为的人,也指一些思想不符合大众口味,但个性分明,叛逆,受少部分激进者支持的人”。从某种意义来说,神经太粗大或健康的人是不适合从事艺术的。甚至可说,疯狂程度与其作品的创造力与艺术价值成正比(装疯的不算),比如作曲家韩德尔就是在燥狂症发作最厉害的24天内完成了著名作品《弥塞亚》。
艺术与疯癫的关系,正如艺术与抑郁症的关系(“一份躁郁性精神病患者的名单有时看去像一流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名人录”)。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也说过:“所有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
就在前阵子,海子的遗书被公布,这使多年前他的死亡有了水落石出的解释:他死于迫害妄想,是“疯”将他直接领上了山海关的铁轨。
“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还有写给诗人骆一禾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
这两封信都写于自杀前夜,常远是他一个朋友,据常远说,两人并无过节,关系还不错。事实上是海子精神已错乱,“常远”只是他迫害妄想症的假想主角。
再来看海子诗歌便有了一种析照,那伏在诗歌背后的精神源流:跳跃的,癫狂的,泛灵的,他们使海子诗歌有了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向度,飞舞在另个时空,贯通着历史与未来的特殊语言节奏以及寓言式奇诡想像力。
按异次元空间理论,真实世界不止三维或四维,它是多维的,与宇宙时空并行的另外时空,坐标与时间轴可任意变化。癫狂,正是这么种时空转移。它从日常生活缓滞而沉重的引力中脱颖而出,在异时空中获得了崭新的艺术压强!
异次元理论还反映出人类多数派的傲慢。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不疯癫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可事实是,我们总是通过他人的“疯”确认自己神志健全,像电影《革命之路》中的数学家的母亲,房地产经纪人吉温斯太太不停为儿子的“疯言”辩解,“他有病,他有病”——然而这个疯儿子异乎清醒地连串发问倒令人反思:到底谁才有病?
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疯子”形象是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弥漫着污浊空气的第六病室,与其说是病房,不如说是监狱。关在其内的病人多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受侮辱与欺凌的人们。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向往智慧与正直的叶菲梅奇医生后来也被当作疯子,政府派了个来考查他的智能委员会。
他的朋友,邮政局长来看他。“我亲爱的朋友。医学守则要求医生向您隐瞒真相,而我作为军人只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真的,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过几天我去请假,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道走!仍旧照往日那样一道走。”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叶菲梅奇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他还是和局长上路了。局长一路上慷慨激昂,高声谈笑,无休止的唠叨,叶菲梅奇感到厌倦,“我们两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有趣因而不让人安静的利己主义者呢?”
但他没有办法自证,所有人,都认定他疯了。
“我的病只在于二十年来我在这个城市里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病,我只是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已经无所谓,我作好了一切准备。”
他在象征疯人的第六病室里脑溢血死去。
人类总视异己为天敌。天敌在左,疯子在右,这二者有时是同义词。
门罗的小说《梅那瑟东》中也有位被视作疯子的女诗人,一个活在自我灵魂小阁楼中的女人,小说并没指明她“疯”的症状,却借用当地报纸的一段评论,在肯定她丰富了本地文学生活之后说,“不幸的是,这位杰出人士在晚年神志变得有点不清,其行为也因此有点鲁莽,与众不同……她有着众人皆知的怪癖,成了一个笑柄。”
一个笑柄,是的,女诗人拒绝了邻居,一位盐商的可能示爱,她关闭了外部的通道,幽闭自己伴随诗歌直到死。在人们看来,这当然是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症状是写诗和拒绝一个收入不错的丈夫人选。但她同样像许多疯子一样,令我感动!一个诚实于自我内心的女人,她的“怪癖”就是绝不苟且,宁肯与孤独终生为伍,也不向一墙之外的世俗服低。
对“疯”这种状态我既害怕又有点向往,像对毒品。也许因为基因或骨殖里缺乏疯的勇气,我永没有“疯”的机会,但我尊重每一位疯者。
这些“疯子”,他们也许还可有另个称谓,“心灵捕手”,就像《哈利波特》魁地奇比赛中骑着飞帚的魔法高人,追逐着那颗飞舞不定的精神小球!在他们的体内,“精神”这种物质的波动尤为强烈,而在另一些“正常人”那里,这种走线始终平稳,平稳得就像一个死者的心电图。
多年来,“疯”在世人眼中都是一种由病理波及道德的重大缺陷,人们谈论“疯子”时像谈论某种怪异的转基因物种。然而一个没有疯子的世界又是多么地可怕啊!整齐有时也是种病毒,就像1906年沙皇俄国的军队迈着雄纠纠,气昂昂的一致步伐,通过彼得堡封塔河上的爱纪毕特桥时,桥身突然断裂——集体的过份整齐导致了灾难!从这个意义,让我们向疯癫致敬,忧伤而傲慢的疯癫啊——正是在那其中裂变出了奇幻的艺术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