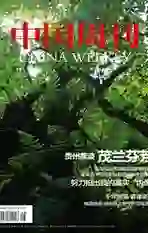千年湖笔 暮途坚守
2015-04-29雷虎
湖州,这座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曾经孕育了曹不兴、赵孟頫、吴昌硕、沈尹默等一批书画大家,书画文脉代代相传,“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并非浪得虚名。除了这些,能让湖州有如此底气将自身置于同是水墨重镇的苏扬二州之上,还因一件承载了中国文化无尽艺术魅力的物件:毛笔。
因为这杆笔,中国书画才成就了她的灵动、朴拙、空静、清雄……而湖笔,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所谓“毛颖之技甲天下”。
蒙公祠上湖笔厂

坐在去湖州的高铁上,窗外弥天的雾霾让人看不清方向,只能埋头看书。“去湖州?”正当我刚刚坐定准备开读时,临座开始和我搭讪。才一个照面就被陌生人猜出了旅行的目的地,让我既惊又喜。“你怎么知道?”临座笑而不答,指了指书扉页。我合书一看,哑然失笑,扉页上赫然写着《中国古代毛笔研究》,原来“此地无银”的招牌插在这里。
为访湖笔,我事先拜访了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研究中国毛笔的行家朱友舟先生。和朱先生聊得兴起,次日就带了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毛笔研究》启程湖州。这位陌生朋友的发问让我对湖笔兴趣更浓,湖笔只是文化人才关注的非主流,这种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人的固有观念此刻已摇摇欲坠,显然湖笔已经融入到国人血脉里。可惜,临时抱佛脚没有得逞,才看完序言和目录就已到湖州。
钻出火车,钻进雾霾。眼前的城市没有让我与湖笔产生半点联系,我知道,要想寻得湖笔,还要再往东南走四十公里,才能到达湖笔的正源善琏古镇。
一路上手机地图显示出一个个熟悉的水乡名子:织里、南浔、乌镇、双林。但视野里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和烟囱,这完全不是陆文夫小说的意境、陈逸飞油画的气场。正当我要把这些水乡贴上“名不副实”的标签时,出租车司机的话给了我无尽的想象:“这就到善琏了,要换是以前,从湖州城过来,只能走水路,一路要在船上折腾好几天!”
车走进善琏镇后,司机在鳞次栉比的招牌中不断停车问路。“湖笔厂?这里到处都是湖笔厂!”“善琏湖笔厂?这里都是善琏湖笔厂啊!”好不容易看到一座上有“善琏湖笔厂——沙孟海题”几个大字的牌坊,“就是这?我来过好多次啊!以前这门前不是一条河么?河边还有个码头,有好多人往船上装毛笔的啊?”拨云见日之时,司机的错乱感也到达顶峰。

我们走进牌坊,里面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院中心一个十平米见方的花坛,中间立着一块巨石。我凑近观摩,出人意料地发现碑文乃是字迹俊秀的《蒙公祭》,从中我读到了湖笔厂的历史——原来这个院子的前身就是毛笔始祖蒙恬的祠堂。古时,笔工们对于自己的授业祖师爷都怀有无比敬意,因而有笔工处就有蒙公祠。
善琏的蒙公祠始建于元代,那正是湖笔取代宣笔,夺得中国毛笔帅印的年代。每年农历三月十六蒙恬生日、农历九月十六笔祖娘娘生日时,笔工们就从各地赶来蒙公祠祭拜。这个传统随着湖笔的兴盛而慢慢融入到每个善琏人的血液,成为了善琏镇的民间习俗,祭祀蒙公的日子,也就成为了古时制笔业的“年会”。1943年,在一次日军的空袭中,整个善琏庙桥弄被一颗炸弹夷平,蒙公祠也未能幸免。1955年,随着公私合营如火如荼的开展,在善琏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前店后坊的各大小笔庄被统一收编。1959年,在原蒙公祠废墟上建立了善琏湖笔厂,从此,善琏只见笔工,不祭蒙公。
正当我看着碑文神游时,一位魁梧的中年人把我拉回了人间,接过他递过来的名片",“庙桥弄6号!庙桥?”看着名片上的地址,我想起了刚才司机的话。“这庙桥,是延续以前的老地名。直到前几年,我们湖笔厂前还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石桥叫庙桥,所以这一带就称为庙桥弄。无论是蒙公祠时期,蒙公祭时各地的笔工;还是改湖笔厂后,南来北往的笔贩,都是坐船而来,在庙桥上岸!”这位善琏湖笔厂的副厂长说到蒙公的前世、湖笔厂的今生就如同名门世家在数家谱,言语中有说不出的自豪。
沿着院子四周修建有平房一栋,小楼二三。“湖笔厂兴盛时期,这里曾经有七百多号人。那是择料车间,这栋负责水盆,那栋里边专门制笔杆!”站在蒙公石前,老厂长指着空荡荡的厂房感慨万千。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开始萌动,大小笔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曾经汇聚百家笔工的湖笔厂就变成了湖笔界的“黄埔军校。”
千万毛中拣一毫

文房四宝中,向来有“笔墨纸砚”之序。笔排在首位,并不是因为价值居首,正好相反。相对于已挤身于藏品行列的墨、纸、砚,千百年来,毛笔快速消耗品的属性一直没有改变。以价值来说,笔一直处于文房四宝的末端。之所以把笔放在首位,皆因制笔太难。
黄庭坚说:“然砚得一,可以了一生;墨得一,可以了一岁;纸则麻楮藤竹,随其地产所宜,皆有良工。唯笔工最难,其择毫如郭泰之论士……”因为,对每个笔工来说,都有要严格遵守的“三义四德”。所谓“三义”,是制作工匠秉承“精、纯、美”的准则;所谓“四德”,是指生产出的成品湖笔“尖、齐、圆、健”四德齐备。
“善琏毛笔一直到现在都是由纯手工制作,湖笔虽小,但制笔却是一个系统工程。每支湖笔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都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择笔、刻字等十二道大工序,而每个大工序,又可被分解为少则二三道,多至二三十道小工序。”在一楼的湖笔博物馆里,厂长机关枪一般说出了一堆专业术语。看到我的迷惑,厂长把我领进一栋三层的大楼观摩湖笔制造工序。看着“参观由里走”的指示牌,我明白,湖笔厂已经完全“沦陷”了,这儿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生产湖笔的地方,而是成了一个书画道场。
对于笔工来说,制笔可能是平凡普通的工作,但是在外人眼里,这却是一个书画艺术混沌初开的地方。在带了无数寻笔者到制笔车间参观后,最终湖笔厂决定顺水推舟,把制笔变成旅游试点项目。让参观者在漫游湖笔一百二十道工序中,体会“一只湖笔的诞生”。
我们在参观指示牌的引导下走上二楼,首先映入视野的二楼阳台把我唬住了:阳台上几十个竹栏棚一字拍开,每个栏棚里都晒满白色的笔头,或立或躺,或大或小,摄影师惊呼:“好多水饺!”房间里瞬间哄堂大笑。我赶紧拍了一张照片发上微博。萝卜头、干鱼?小伙伴们开始自由想象。没等我公布答案,已经有位文化达人试探着问我是不是到了湖州厂。
推开门,只见笔工每人左手拿一团整齐湿润的羊毛,右手不断用指甲从羊毛中抽选。虽然他们大多年近花甲,但手法却十分敏捷,每秒能重复二三次抽毛的动作。“这道工序,叫水盆,也叫水作工。任务就是将浸在水盆中的笔毛理顺,带湿剔除不适合做笔的杂毛、绒毛、无锋之毛,然后把毛理顺整理成半成品笔头。”
善琏有句俗语:“毛笔一把毛,神仙摸不着。”而湖笔笔工做的就是“神仙摸不着”的理毛工作。想把自由生长的狼毫、兔毫、羊毛做成蓄墨、聚锋的湖笔,难度可想而知。一个看似简单的水盆工艺,却“千万毛中拣一毫”,真正要做好,少则三年,多则十载。好在湖州笔工们从来对自己的工作都是“从一而终”。无论是水盆、择笔,还是刻字,要么不干,要干就是一辈子。
正是因为一辈子只做一样事情,培养了笔工们高超的技艺。有这群笔工在,“湖颖之技甲天下”就有了根基。
湖笔,一个正在没落的传说
从湖笔厂出来后已是下午两点钟。湖笔厂的笔工建议我去湖笔街转转,因为要了解真正的湖笔,就得拜访湖笔街那些民营的笔庄,他们才是湖笔真正的生存状态。听从了笔工的建议,我决定在湖笔街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很快就发现整个湖笔街大多时候都是空无一人,仿如一条“鬼街”。
下午三点太阳当头,这条长约一百多米的仿古街“阴森”依旧,街两边鳞次栉比的笔庄门面,有三分之二都闭门谢客,另外三分之一则门可罗雀。好不容易看到一位清洁工,立马凑上前去:“师傅,请问松鹤笔庄在哪?”清洁工指了指前方十余米处的一家店铺:“看到那家门前有一对毛笔灯的笔庄没?那就是。”之所以要找松鹤笔庄,是因为朱友舟和湖笔厂笔工一致推荐,理由只有一个:笔庄的老板章小华。
十五年前,出身江西进贤制笔世家的章小华,因为仰慕湖笔的声名,背井离乡来到湖州。十五年后,一个来“朝圣”的外地笔工,竟成了湖笔的招牌人物。从那对“毛笔灯”间往门里看,只见一位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在伏案整理笔头。
我报过家门后,中年人把手上的活儿一放,说他就是章小华。
章小华和毛笔的故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人文”——他出生在江西进贤一个毛笔世家,对毛笔的情愫来源于父亲。“我从小和毛笔特别亲,不是因为毛笔能写字作画,而是毛笔能换化肥!”章小华的父亲曾经是进贤毛笔厂厂长,但是父亲任职厂长时,却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日子。“全国都在破‘四旧’,毛笔厂当然也处于半停工状态了。但是公社又不敢完全把毛笔厂关了,因为那时的进贤,就毛笔还有点名气,每当工社没钱买农药化肥时,工社书记就来找我父亲,要毛笔厂开工制笔换农药。”父亲是个传统的老笔工,对毛笔心存无限敬意,认为用毛笔换农药是对毛笔的侮辱,却又不得不为之。但正因如此,毛笔工厂在那个非常年代还能断续开工。章小华自小就在毛笔作坊的摸爬滚打中爱上了毛笔。
上世纪90年代,章小华很快在进贤毛笔界闯出了名声。他想出外走走,看看自己做的毛笔究竟有几斤几两。章小华把自己最满意的几只笔带到了荣宝斋,荣宝斋的专家给了他一句评语:“真看不出,进贤也能制出这样的毛笔,竟然有几分湖笔的味道了!”这句话改变了章小华的命运,他决定到湖州看看真正的湖笔是怎么做的。
坐着乌篷船从南浔上船,一路沿着曲折的水道南行,狭窄的水道上来回都是天南海北的笔商,场景就就如鲁迅先生的散文《社戏》中描绘的一般。“就是这儿,我十五年前,就是从这儿下船的。船夫把缆绳往岸边的柱子上这么一绕就喝酒去了。”当年,从码头上岸,章小华感觉到的是诗画江南。但如今,当年笔商们坐着船儿往来的纵横水道已经被填平,鳞次栉比的湖笔庄还在,但是已经旧貌换新颜。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五年前,章小华离开进贤来善琏朝圣,十五年后,当他成为湖笔界“顶尖高手”后,整个毛笔界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湖笔大有被进贤毛笔赶超的趋势。
“湖州地区,因为人力成本,原材料等原因,近几年毛笔生产已经大不如前。”说到湖州制笔业的衰落,章小华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又到善琏周边的一个村子里收购羊毛。老远就看到羊倌正在“杀猪”,我纳闷了,问羊倌,你宰了这么多年的羊怎么突然改杀猪了。羊倌反问,你用过这么多年羊毛,羊没穿马甲你就不认识了?我定睛一看,好家伙,眼前的这只,长着羊的外表,却有着猪一般的体型。”我也乐得前俯后仰,但眼前的这位笔工却是一脸苦笑。讲起了“羊变猪”的原因。
最开始,羊毛衫走俏,于是人们就让羊少长羊毛,多长绒毛;后来,羊肉更好卖,于是羊就净长肉不长毛了。善琏地处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农户养殖的羊、兔的各项生理属性等都紧跟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动。以前,制笔人从来没为羊毛操过心,因为善琏附近的村庄,随便就能找到上好的山羊毛、兔毫。后来,附近的羊基因变异,笔工们只能去浙南的深山中寻羊;再后来,大环境变迁,让深山中的羊也不能幸免,笔工们只能去内蒙、新疆寻羊。如今的羊毛、兔毫的质量,相较以前已经是云泥之别了。湖州虽然有延续千年的制笔传统、技艺精湛的笔工。但如今制笔正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处境。
“现在,即使能寻找到适合制湖笔的羊毛,羊毛质量也大不如前。再加上制毛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江浙地区的经济大环境!你看湖笔街上,虽然笔庄林立,但是很多笔庄只有个空壳。偌大的湖笔一条街,除了举办湖笔节时能热闹几天,平时几乎都见不到人,很多笔庄都不再从事湖笔生产,甚至直接从进贤进货。如果这样的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湖州在不久的将来,将可能让出一千多年来中国毛笔业殿堂的位置!”说到这,章小华语气中有不尽的感伤。
“如果湖笔真的衰落了,我还可以回进贤老家,起码进贤的毛笔还欣欣向荣。”看到笔者听到他的话也开始伤感后,章小华反过来给我打气。但是进贤的制笔业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兴旺么?我想,我有必要去进贤看看。
深夜,走在湖笔街灯火通明却不见人影的街道上,笔庄窗户中漏出的光打在街道上,就如同船家的灯火映在水面。我走在街上幻想自己是那个朝圣的笔工,坐着乌篷在江南水乡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