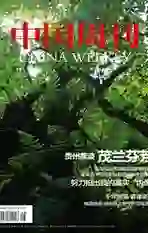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踌躇与彷徨
2015-04-29刘晗
《浮生六记》既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回忆录,同时也被视为中国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绘本。
苏州吴江地域的古典园林大多依水而建,曲径通幽,如吴侬软语和评弹民歌那般婉转悠扬、回味无穷。沈复将精美巧工的扬州园林看作浓妆艳抹的佳人,正是由于在建筑工艺中人工的成分大过自然所致,但他也未完全否决人工在园林艺术中的应用,人工雕琢多于自然未必使园林失去本真之美,山水之间的层峦叠嶂赋予人宛若自然去雕饰之感,从人工的雕琢中脱胎而出的不仅是形象上像自然的自然,也是在绚烂之后归于本色的自然的这样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重建园林即是建立理想的家园,一个微型私密乌托邦的诞生,将对社会的美好设想付诸文字—和谐有序的纸上城邦。蜿蜒曲折、若隐若现的朦胧景观既是封建社会家庭等级制度的再现,也是以沈复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欲求躲避世俗心态的外显。
通过《浮生六记》可以发现,他们在社会和官场的地位常遭到外力的阻碍和干扰,另一方面又有挑战世俗的心态。沈复游至虞山,虽不设登山路径,但他不顾他人阻拦,一意孤行勇攀险峰。游至函谷关,以身试险,体验自然景观的“绝处逢生”,从市集的喧嚣处行至人迹罕至之地,这源于文人的猎奇心理,以及对世事居安思危的身体力行。由此可以划出一条他在此地波澜起伏的心理曲线,由“静”至“动”,再从“动”反观自身当下冷落的“静”。这是其所观所延续到语言和行为的直接表现,而在园林建筑上则体现为层峦叠嶂式的亭台设计。将光影之虚实化用于亭园的构造之中,搭建起“立于世”、“远于世”,甚至“高于世”的空中楼阁,呈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矛盾心态。
如果说“秀”在目之所能及的亭台,那么“隐”就在光影流连、乐曲四起之处。沈复夫妇于临水的窗前赏月,窗作为自然的动态取景器,光与气穿梭于其中,就此打开了书斋中的人与自然的接触。窗与文人做学问有着紧密的联系,文人在窗前多是追忆年少时与夜、与书本为伴的孤寂;另外,窗作为遥寄思量的中介而存在,正如陈芸所言:“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沈复曾作“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其中,“吞”和“弹”点明了沈复之意:一扫白日之俗虑,星空点缀出爽然与顿释的情怀,在云、日、月、星的流转中尽显动态美。沈复卸下行走于沧浪之水中的惆怅、挥毫泼墨时灵感的闭塞以及生活之途遥遥无期的焦灼,先有心之澄明之境,万物方可在心上映出本真状态。
沈复与众友人于放鹤亭登高赏月,又是另一番情境。亭的构建归于虚空,置身于其中远眺,“气”贯穿着来自八方之景致聚于此,乐曲化解了凝固的建筑流入心中,仰望彩云追月,俯观情绪之驿动,此刻,情、景、乐从不同视角交融使物我合一,飘飘欲仙的真实与虚幻的博弈中得以再现。沈复将水陆上升起的层峦叠嶂和光影变幻复归于全感官享受,从有限的景观通达至无限的人生哲理,自然被赋予人格化的意蕴,与此同时,中国古典园林的建构恰恰契合了文人士大夫矛盾心态的构型,似乎只有欲说还休的隐秀写意之美,方能诠释他们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踌躇与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