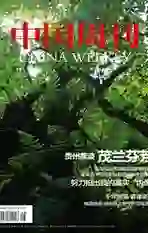崔国泰:冷酷的热度
2015-04-29梁爽
“一个艺术家,看到大工业时代在自己家乡的衰颓过程,
他能够抓住这样重大的社会题材,并且投入巨大的情感和精力去创作,
这在当代艺术中是非常可贵,也是非常重要的。”

崔国泰,曾先后毕业于东北师大美术系、中央美院油画系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2001年,还在清华美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油画个展,画展中一幅名为《体内的疯子》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崔国泰,全程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等很多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历史时期,历史因素、情感因素,造就了他强有力的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在历史的再现性与艺术的表现性之间,崔国泰一直在试图打破标准化审美模式对于艺术视觉深度的禁锢,以便最大程度地还原内心的真实历史。
基于看待社会的热度,他的工业系列肖像,既有怀旧的真实情感,又有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
2005年,在陈丹青为崔国泰策划的“伟大的残骸”展览开幕式上,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如是说:“一个艺术家,看到大工业时代在自己家乡的衰颓过程,他能够抓住这样重大的社会题材,并且投入巨大的情感和精力去创作,这在当代艺术中是非常可贵,也是非常重要的。”

崔国泰的家乡在沈阳,曾是新中国工业摇篮的东北,其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规模巨大的厂房、钢炉、重型机械,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巍然耸立,不断书写着辉煌,那种豪气干云的壮志永留记忆。
2000年前后,崔国泰从北京回到沈阳,在那里,时代的车轮正在碾过,重型工业体正在被集体肢解与捣毁,残存的厂房人去楼空,烟囱默默耸立,等待被分崩离析的一天。这些都引发了崔国泰巨大的情感触动。

两年后的2002,那时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厂房画室被拆,他画了那间大画室作为祭奠,工厂系列就这样有了一个“正式”的开始。
2002年、2003年也正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期,大量企业倒闭、整合。以沈阳为核心的这片老工业基地所承受的打击也是空前的,但因体系复杂、摊子过大,“拯救”过程的后遗症也着实棘手,数以万计的工人被买断工龄、冶炼工人的肺病无法接受继续疗养,整个地区的经济都陷入低谷。
对故土的眷恋,对行将消失时代的苍凉回眸,和对自己心灵伤痛的抚慰在崔国泰的心中交织,促使一批深刻触及中国大工业时代脉搏的“纪念碑”式的作品陆续问世,并且影响广泛。
崔国泰的这类作品画幅巨大,描绘主体也都被拉入近景,营造置身咫尺之感。在火车头、铁路和钢铁的世界中,因为有了切实的生活体验,所以有了温情的味道。近作《大工厂》就是这样一幅近距离面对曾经辉煌记忆的作品。工业厂房、黑黝黝的粉尘落满的玻璃窗和铁窗棱、一条条水平延伸的昔日里冒着蒸汽的管道……真实被层叠的颜料塑造着,时而锋利时而模糊;那流淌下的颜料时而提醒着观者,这里的大生产已经和我们拉开了时间上的距离,那激昂挥洒的大笔触,又让观者体会到这里曾经有过的民族热忱。
崔国泰擅用黑白两色,上世纪90年代时他就尝试将中国传统书画的精髓渗透到自己的抽象绘画实践中去,试图在中国画大写意和草书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图景。在这种“私密”和“酣畅淋漓”的绘画体验中,在长时间的运用和把控中,黑与白这两种极纯的颜色越发显现出质地感,恰如其分地诉说着钢铁时代的硬度和光感。黑白两极的中间地带里,又有变化丰富的褐色、红色、蓝色、黄色……调和着画面的温度,使作品有些许色彩倾向,但黑白两色带来的冷静思考是艺术家一如既往的执着。这是一种朴素的克制,如黑白摄影,浮现出社会的底色。
2014年,崔国泰的《童年河畔的小路》是他为数不多的有梦幻色彩感的作品,如火似焰的乡间荒草完全脱离了记忆的再现,在表现主义的手法中腾腾跳动,直入感官。正如崔国泰自己所言,他不愿意画甜腻的东西,更不愿绚丽的色彩消解了灵魂层面的力量。
随着东北老工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崔国泰也转向了军事题材。

对于中国近代战争史,崔国泰熟稔于心,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现代化装备战争都是他的兴趣点。而对于现代和当下中国、乃至全球军事关系的关注,则给他的战备和军事怀旧系列作品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来源。
崔国泰这个系列的作品,是从工业大生产现场向国家尖端科技成果转移的过程。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提高,工业振兴为民族自信提供了强大后力。和大多数20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崔国泰也有着苏联情结,他梳理过苏联援建项目的资料,也研究过如苏-27、歼-11——在空战中的作用和更新换代发展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建设三峡、哈飞、黎明等军工厂、上海宝钢,辽宁鞍钢,哈尔滨的三大动力等不少地方,崔都走访过。
不同于作为宣传手段的政治军事绘画,崔国泰画笔下的军事题材并没有偏离艺术的航道。在避免意识形态侵入艺术创作的初衷下,他通过图像背后互相支撑的逻辑关系,以最简洁的语言,最大强度地表达了精神性。2006年创作的《解放号机车》和《U2飞机残骸》、2007年的《大飞机》、2008年的《废弃的机场》等等,都是这个系列的代表作品。曾快速奔跑的机车静止在原地、云层中杀敌的飞机虎落平川。
2012年,崔国泰受中国航天五院邀请,到西昌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考察并创作了《枕戈待旦》。这幅五米五乘五米五米的巨大作品中,火箭发射器顶天立地地伫立着,即将冲入于浩瀚宇宙中的它,更对比出人的渺小。这依旧并非政治任务,艺术家带着对神力的敬仰将其完成。笔者并未将崔国泰定义成怀旧的艺术家,原因即是他的作品中仍有太多对当下的讲述及对未来的展望。
政治风景是崔国泰又一以并行不悖的视角展开的系列。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对工业时代的留恋,和工业时代的人对农业时代的留恋是一样的。2008、2009年他创作了《北大荒》组画。卡车上微展的旗帜,两三个人在车上挥手的动作,在既有印象中演化成为集体性告别。肥沃油亮的土地被翻起来,春播秋拾,陷进去的车辙如历史残迹般留在那里,甚至有人把生命安葬在了那里。让人不能忍受的除了天寒地冻,还有的侵入人心的荒凉,白日在肥沃的黑土上劳作,黑夜在寂静和思乡中度过。《北大荒》中,浓厚的荒原气息刺激着广袤的大地;开荒,这一特定时期的伟大的“行为艺术”,提供了一种时代聚焦的视角?还是反观了那代青年人的热忱和豪情?
2012的《边境》和2013年的《鸭绿江大桥》也是此视角中的作品。边境的寥寥杂草和巍然矗立的国界桥,含义深邃。这个题材,与崔国泰的工业题材不同,除了有冷酷,更怀有温情,这是一种纯然骨子里的关切。
笔者曾有幸在崔国泰的工作室见到他做画的过程,不是挥毫、爽朗等词可以概括。艳阳从天顶斜射进画室,未完成的几件作品挂在墙壁,典型河姆渡时期的陶罐队形整齐,黑色皮质沙发、轮廓简单的果盘被丰盛的水果覆盖,物出自然。黑胶碟旋转出铿锵有力的节奏,和着颜料掷地有声的挥洒和大笔触的勾勒,大面积的涂抹颇有些中国画写意的味道。在巨幅的画布面前,崔的作画过程颇像波洛克的行动绘画——虽然在政治取向上并不相同。
随着《征服天堂》、《旅途的末日》等悲壮乐曲时疾时缓地进行着,将近几个小时,一幅两米乘三米的飞机残骸已经完成了初稿的六七成。
崔国泰不断地激活日常所积淀的感情和历史线索。这些掺杂着政治的、军事的、经济发展的物质遗留和事件,混合着个人经验,转化成有纪念碑性质的图像,这些图像有着图像背后的力量。笔触间的宏大叙事,带有深沉的感情和历史重量感。让原本庞大冰冷的实物,远离了今日消费社会的语境,指向国家历史的更深处,在嘈杂喧哗人人逐利的病态社会中,凝聚着它清醒的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