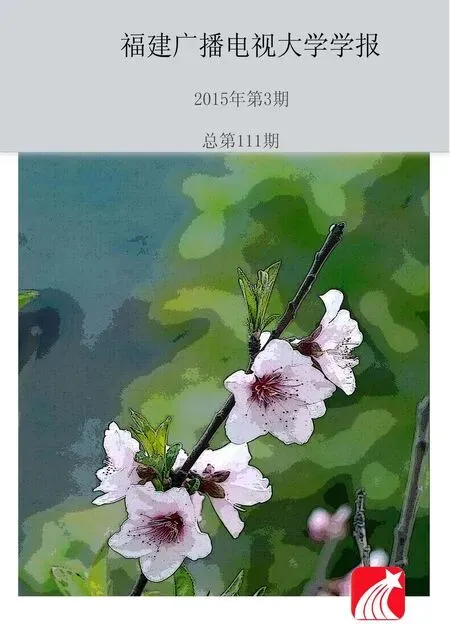渐变式的过渡
——建国初期的电影传播
2015-04-18颜纯钧
颜纯钧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
渐变式的过渡
——建国初期的电影传播
颜纯钧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的基本态势当然不是在一夜之间即得到根本改变的。无论是就必要性还是就可能性而言,新生的革命政权都把全面掌握电影传播的控制权稍稍往后拖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就表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渐进的状态。在新旧电影之间、公私电影之间、美苏电影之间,以一种消长之势进而去完成根本的转换。
中国电影;建国初期;电影传播
一百余年的中国现当代历史,政治的变动确实构成最基本的脉络;但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受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因果关系,恰恰不可能在瞬间同步完成,相反的表现出某种滞后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的基本态势当然不是在一夜之间即得到根本改变的。
一方面,作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共和国在建国之初要完成的仍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是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必要;与此同时,对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迟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正式开始。
另一方面,由于尚处于从无到有的草创时期,新中国电影也未充分具备物质、设备、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基础性条件,在短时间里完全取代旧中国电影;尤其是在上海、北京等少数大城市,旧时代的电影业已建构起成熟的传播网络,更不可能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即刻分崩离析。尽管如此,革命的电影事业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变电影传播的现状,则是从东北解放区时期,为全国解放做准备时就开始了的。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局面的根本改观、公众舆论和民众心理的倾向性变化,而且随着新生政权开始行使政治权力,国营电影更是很快确立起电影事业发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就表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渐进的状态,并且通过电影传播在几个不同方面的消长之势来完成根本的转换。
一、新旧电影之间
建国以后,中国电影的传播语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以1949年10月1日为绝对界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渐变的时期。应该说,以东北电影公司为代表的新中国电影,在建国前后还是以一种突飞猛进的姿态向前发展的,但其所生产的影片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从1949年3月到12月,在东北共发行的总计382部影片中,东影所占的数量仍是极少的一部分。除了大量的苏联影片之外,所谓“港沪片”(指港沪两地私营电影机构生产的影片)也占颇大数量。由于新电影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建国前后的几年时间里,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都不得不容忍一些带有落后意识的旧影片继续放映。也因此,1949年3月,袁牧之在东影为他去北京而召开的欢送大会上就说过:“大家知道,有些旧片子还在放映,……我们要拿出自己的作品和有毒的旧片子斗争,我们的影片要像大炮一样,到处开花,在质和量上都打败旧片子,我们才算完成了任务。”[1]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中,中国电影的传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过渡状态。在新旧影片之间,显示出此长彼消的演变过程。
这里,有几个原因:
其一,建国后电影观众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众多的城乡放映队的组建,电影观众逐步从几个大城市扩展到全国,工农兵观众的比例开始超过市民和小资产阶级。有资料表明:“工农观众激增,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八亿两千两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即占70%以上。”[2]观众成分的变化在当时显然具有关键的作用。在翻身做主人的意识支配下,普通百姓潜藏着的革命激情对电影的表情达意提出了新的吁求。而同一部影片在大城市和乡村中受欢迎程度绝然不同的情况也不时出现。
其二,新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电影的传播施加了强大的影响。政府相关机构的建立、各种有利于新电影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的出台、舆论宣传上一边倒的支持等,比之观众的情绪更起作用。一方面,是成立全国性的发行机构中国影片经理公司,“采用了‘集中编映’的发行方法让国产的故事片和长纪录片(含国营、私营)及译制的苏联片占据电影院的放映空间。”[3]另一方面,则成立电影审查机构,对以往上映的旧影片和外国影片进行审查、清理。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新旧影片在传播中此消彼长的态势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文化局1951年1-6月份的统计,全市上半年共上映影片节目467部,其中国营厂、私营厂的出品以及苏联、东欧影片占64%,其映出场次占总场次25531场的85%,观众占总观众数1125万的85%。值得说明的是,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出品,在节目数量上只有18部,仅占节目总数的3.8%,但其映出场次占18.6%,观众占22%。”[3]
其三,一部分带有所谓旧观念、旧意识的影片遭到了有组织地批评乃至批判,比如《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万家灯火》、《我这一辈子》等。在今天看来,这几部在当时被批判的影片,从艺术上看仍然是比较成熟、比较优秀的,但因为观念上的陈旧,照样不被新生的革命政权所接受。
一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进步电影人的艺术家,在刚解放的几年里发现自己竟然渐渐地被逼向了边缘。反过来那些来自解放区的、在艺术上刚刚起步的年轻电影工作者却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当时,革命电影的领导人秉持的观念就是:“对于编导干部之培养要‘大胆放手’。艺术干部中只要他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就鼓励他着手试拍小片或先搞纪录片,或先当一二次演员,从中熟悉整个制作过程和摸索电影表现技巧,往后就试行单独导演。”[4]当那些在艺术上可称为小弟弟小妹妹的解放区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后纷纷站上领导岗位,担当重要的艺术创作任务,拍摄出风格崭新的革命影片,受到领袖、大众传媒和观众的赞扬之时,身处上海的旧阵营中的电影人,心理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同时也抑制了他们的创作激情、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在精神上遭受前所未有的“矮化”。
于是,来自东北解放区的电影人成为新电影的代表,而尚处于上海私营电影机构中的电影人则成为旧电影的代表,这个新旧电影阵营的划分由于新政权旗帜鲜明的态度而益发显得对比强烈。
新旧电影的差别,其实就是工农兵电影和市民电影的差别。从延安解放区电影到东北解放区电影,再到新中国电影,革命新电影一直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创作方向和思想指针的。工农兵不仅成为电影的主人公,而且成了电影观众的主体。于是,革命意志、阶级感情、英雄品格、牺牲精神成了最被推崇和歌颂的方面。就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出《桥》、《钢铁战士》、《白毛女》、《赵一曼》等歌颂工农兵的影片之同时,以上海为基地的私营电影机构却在文艺为谁服务的观念上有不同的主张。昆仑影业公司的艺委会主任陈鲤庭等就曾提出:“今日电影还是以小市民为主要的城市居民为观众对象”,“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思想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影片(指国营影片)不能适应城市居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因此尚不能获得广大的观众。”[5]有关工农兵电影和市民电影的分岐,后来还引起《文汇报》在1949年8、9月间一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工农兵电影的新口号,并不仅仅涉及电影的题材内容,更成了划分阵营的一个标志。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袁牧之就认为在整个进步片内部,要保证工农兵电影主导。他“明确把‘工农兵电影’作为党掌握政权后进入新时期的无产阶级电影的标志,并把解放前党所领导的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以来所摄制的进步影片统统归诸为革命小资产阶级的”。[6]显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当时掌管全国电影工作的袁牧之那里,被演绎成制定电影方针与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于是,那些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上海电影人——这其中大部分是当时的左翼电影人和思想进步的电影人,却在建国后成为所谓“旧电影”的代表。他们仍然秉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仍然以城市的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作为预期的观众。小资情调、市民趣味、都市景观、类型情节等,仍然是影片运作的基本模式。西方学者保罗·皮克威兹认为中国的左翼电影是“经典通俗剧和初级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而通俗剧的传统则可以从“修辞的过度、夸张的表演和道德上的强调”等方面看出来。[7]从这批上海出品的影片中,不难看出《马路天使》、《桃李劫》和《十安街头》的影子。
即使是像《关连长》这样以解放军基层干部为主人公的电影,也难以避免采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去加以诠释。本意上是积极去呼应和追随新时代的潮流,效果却非但未必如此,甚至还遭遇当头棒喝——这真是始料未及的。在《武训传》遭受批判之后,孙瑜就曾这样发问:“在批判的当时,曾有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曾在中国解放前起过相当影响的一个进步‘电影公司’,一个一贯拍摄‘反帝反封建’电影的昆仑影业公司竟会在解放后拍摄出一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鼓吹‘向封建统治者投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武训传》来呢?会有这种可能吗?”[8]
而对那些来自解放区的电影人来说,尽管他们比上海的电影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实际上只不过比上海的电影人早几年加入革命队伍,他们经受的革命洗礼仍然十分有限,对工农兵还根本谈不上深入了解和深刻体验。表现工农兵只是出于命令的服从和态度的体现,于是主题拔高、表现夸张、思想大于形象等在后来愈演愈烈的创作倾向,在解放初期就已埋下了祸根。
二、公私电影之间
建国初期,还短暂地存在过一个国营电影和私营电影并存的传播局面。从国营这方面看,除了东北解放区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之外,在上海仍有一部分私营电影机构在解放后保留了下来。较有影响的有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大中华、大光明、黎明、兰心、中企、嘉年等。[9]这其中,昆仑早在解放前就一直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文华的主持人也倾向进步,不少编导长期和地下党有过联系。此外,尚有一家在初期的混乱中成为公私合营的长江影业公司。[10]
在今天看来,建国初期电影国营与私营并存的局面有它的合理性。首先,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仍然立足未稳,团结广大人民,尤其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社会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合乎时宜的。其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团结对象,对“私”改造的问题此时还没有提上议事的日程,一直迟至1955年才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的社会运动。再则,建国初期,由于体制上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剧本荒”。从1951年起,东影的编剧都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东影的剧本改由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提供。这对东影来说,是管理体制和制片厂权限的重大变化。“剧本荒”所带来的是严重的“片荒”。为了填补市场的空缺,也需要调动私营电影机构的积极性,利用其原有的人力、财力、器材和设备等制作更多的影片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建国后中央政府对私营影业持一种扶助与合作的态度,先后出台了《电影业注册登记》、《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旧片清理》等五个暂行办法。同时,“电影局自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年上半年止,已向私营制片业举办了五十六亿二千余万元的发行供求贷款,并借给胶片等原料以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困难。”[11]
建国前,在电影生产基地上海,“电影发行总的情况是民营公司,基本自理;敌伪机构,强行垄断;官办企业,控制垄断;美英的9大影片公司在上海均设立自己的发行机构。”[12]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接管国民党的公营电影制片机构,当时的中央电影局也十分重视组建自己的电影发行与放映网络。这其中,除了原来的东北影片经理公司之外,又在1949年12月设立了中南、西北、西南三个影片经理公司,随后于1951年2月1日成立负责发行影片的总机构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并继续设立另外的两个大行政区的影片经理公司。[13]全国性电影发行网络的建立保证了国营电影对市场的占领。凭借着执政的优势地位和全国性的发行网络,私营的电影制片机构制作的影片不得不借助于它来扩大发行;私营的电影院也需要通过它去获得更为广大观众欢迎的进步片来放映。国营和私营的电影传播阵地呈现出一个犬牙交错的状态。随着时日的推移,国营的电影发行与放映网络日渐健全,私营方面却益发地举步维艰。当国营和私营共同采取了统一协商排片的办法之后,实际上国营的电影发行与放映已经把私营的那部分吸附过来,统领过来了。
建国后公私营电影之间的消长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
从新中国历史上看,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全国性的对私改造体现为一个渐进的、相对平缓的过程。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中,提到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4]而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对私改造却一直到1955年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意思的是,对电影业来说,有关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历史任务,早在建国初期就基本完成了。“按照中共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1950年初,长江电影制片厂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9月,昆仑影业公司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与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合并,厂名仍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15]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影业在当时会比其他行业更快实行公私合营?除了社会的政治气候和民众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外,也和电影业对技术、设备、人才、资金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当时身处国营和私营的电影人心理上的优劣势已显示出较大的落差;另一方面,国营厂起步维艰,尚处于弱势地位,也需要极力吸引私营电影机构的人才参加进来。资金方面更是有天壤之别。国营厂凭借政府拨款,相对而言虽然也未见得“财大气粗”,但却具有基本的保证,私营机构则主要依靠票房收入来维持。因为资金困难、职工人心浮动、民众对国营与私营的不同心理偏好……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在经营上显现出不同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厂无论如何也很难再支持下去了。摄影师许琦曾回忆道:“一些小公司的员工开始向往国营厂,因为那时的生活有保障啊,一些人到处托关系、走门子,想进国营厂去,就连老板也希望把厂子缴给国家。这样的话,他们至少可以拿到一笔赎金,在经济上甩掉沉重的包袱。……上面领导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决定提前对私营电影公司进行公私合营。”[16]
第二个问题:电影业的对私改造之所以进行得比较早,也比较顺利,也并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是由共产党政府的强制政策所造成。这和几年后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运动展开的“对私改造”有着不同的态势。事实上,当时无论是中央电影局或者地方政府,对私营影业还是持扶助态度的。
根据汪洋的回忆:“当时在上海,一些私营的电影厂有些困难,主要是胶片、机器设备上的困难,我们党支援了他们。另外剧本也有困难,在上海专门为它们成立了一个电影文学研究所,请了一些作家为他们写剧本。他们缺少钱,政府给了他们大量的贷款,还准备成立一个银团来支援他们,因为在解放初期,私营的力量对中国电影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17]比如昆仑厂拟拍摄的《武训传》,就是从当时的中央文教委员会取得贷款,剧本也是经当时的中宣部审查认为没有问题,才顺利开拍的。[18]当然,无形的心理压力还是存在的。社会舆论一边倒的传播生态,几部私营制片机构拍摄的影片如《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等相继受到批判,国营厂拍摄的《桥》、《赵一曼》、《钢铁战士》等却受到党中央、政府部门和媒体界的大力追捧,并举办“新片展览月”来广加宣传……这对于私营影业的发展还是影响颇大的。尤其是当时尚处身私营电影机构的电影人,绝大部分都是左派或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长期以来就倾向进步、支持革命,所以急于融入新中国电影的阵营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这对于私营电影机构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当时的新中国在人民的心目中正如一轮红日磅礴出海;风行全国的主流价值观不是发财致富,而是‘参加革命’,人人以此为荣,人人以此作为人生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样,私营厂并入国家办的电影制片厂,也就是顺乎潮流、合乎人心的事了。”[19]从1951年9月到1953年2月,经过一连串的合并程序,存在48年之久的中国私营影业在形势逼迫之下,不得不以主动代替被动,就此寿终正寝。
三、美苏电影之间
建国初期外国影片输入情况,同样存在着一个消长之势。这主要体现在当时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代表美国和苏联之间——当然也包括相对立的其他国家。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高相关性,旧中国的外国影片输入无疑是绝对倾向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
据资料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4年内上海就进口了1896部美国片(其中长故事片1083部)。作为鲜明对照,此后27年间(1950年-1977年)在中国仅上映过1部从第三国进口的美国进步影片《社会中坚》(上海电影译制厂1959年译制)……”[20]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再进口好莱坞影片了,但基于革命的新电影尚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前几年已经进口的影片却仍闲置于片库,而观众欣赏口味的改变确也需要假以时日,所以当时的电影主管部门仍继续在安排发行和放映美国影片——当然从总体上看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8月,以好莱坞影片为主的西片市场,在上海从142部、占64.6%下降到63部、占36%。[21]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冷战格局基本形成,新政权在东北解放区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进口和译制苏联影片。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影片的译制和放映开始以一种国家电影政策的面目出现,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进口苏联影片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苏联影片的倾向性态度上。
在1950年一年里就发行苏联影片52部,在总计90部(包括国产“进步片”36部)中占据了一半多。[19]除此之外,新中国政府还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苏联电影。
从1949年10月开始,《人民日报》就连续刊发文章介绍苏联电影事业,大量译介苏联电影理论的著作,如《论苏联电影》、《银幕上的苏军》等。1951年11月6日,为庆祝苏联社会主义革命34周年,自11月6日起,新中国在20个大城市举办“苏联影片展览”,为期9天。1952年11月7日,为了庆祝苏联社会主义革命35周年,新中国再次举办“苏联彩色影片展览月”,规模扩大到66个城市的321家影院,同时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也在展览月期间访问中国。[22]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年看苏联电影的观众已达五千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从一月到六月的半年间,观众的数字已跃增到近四千万人,而且此后必将与日俱增。”[23]
在一个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国家性质的改变、政治阵营的重新选择,势必要带来一系列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化。新中国一成立,对美苏电影的好恶态度很快通过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舆论的一边倒、观众心理的明显倾向等方面反映出来。比如苏联影片的票价就定得比美国影片低,大众传媒上连篇累牍都是有关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还有的单位集体观看苏联影片等……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美苏电影的消长之势也许还要延续更长的一段时间,就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由党和政府控制的各种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入宣传,党的基层组织和受其影响的群众组织、民主党派都卷入到这个建国初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了流行口号,种种形式不同的反美活动不仅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而且也教育和动员了广大群众,形成了反美亲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举国上下,到处在开展消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生态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国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放映美片的惯例益发显得刺眼和不合时宜了。1950年11月10日,上海的巴黎大戏院最早在影院门口张榜大幅标语:“拒映美片”,并公开向社会呼吁。在强大的反美氛围中,此举立即引起连锁反应,各影院皆表示了“拒映美片”的决心。
很快的,全市40多家影院经理在广大影院职工及其代表的敦促之下,于11月14日以上海电影院同业公会名义作出决议,宣告“全市40多家电影院的劳资双方一致协议,接受广大群众的正义要求,爱国不分先后,自1950年11月14日起,全市影院停映美片”。与此同时,在美英资本的影片公司工作的127位职工,也不顾个人可能招致“失业”的危机,宣告即日起停止排映(发行)美片。上海各大报纸也联合发表声明“即日起停登美国影片的广告”。[12]自此,在政府的默许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在中国的放映活动基本终止,而苏联影片则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直至中苏关系骤然冷淡的60年代。
美苏电影之间的传播消长之势对新中国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化了中国电影创作者对苏联电影中表现蒙太奇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使后来的中国电影在表情达意上的强制贯输日益走向变本加厉;
其二,好莱坞电影在商业类型片上的各种叙事法则和运作经验逐渐被淡忘,更是阻碍了中国电影后来对商业电影的进一步探索,最终导致上世纪末期的陷入低谷;
其三,一代又一代的电影观众的欣赏口味在苏联电影和新中国电影的频繁接受中被加以培养,反过来又以一种正反馈的效应把欣赏的需求加诸于电影之上,一批“文革”电影的出笼和观众不正常的欣赏心理之间同样不无关系。
[1]程季华.首任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片断[J].当代电影,1995,(5):29.
[2]胡菊彬.“会师”之后[J].当代电影,1995,(2):32.
[3]沈芸.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始末[J].当代电影,2005,(4):39.
[4]陈波儿.故事片从无到有中的编导工作[N].文艺报,1950-02-01:3.
[5]文化部档案.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文艺整风学习总结报告[C]//吴迪.“人民电影”探讨:十七年中的第一波“非主流”.电影艺术,2007,(2):81.
[6]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C]//顾茜.建国初私营影业转轨之概观.电影艺术,2004,(4):43.
[7]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7.
[8]孙瑜.影片《武训传》的前前后后[J].新华文摘,1987,(2):164.
[9]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69.
[10]顾茜.建国初私营影业转轨之概观[J].电影艺术,2004,(4):44-45.
[11]沈雁冰.中央文化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节录)[C]//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上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7.
[12]《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电影志》第六编第一章[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13]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25-126.
[14]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C]//《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8.
[15]《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电影志》第一章第四节[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16]石川.访摄影师许琦[J].电影艺术,2005,(4):72.
[17]汪洋.十七年时期的新中国电影[J].当代电影:1999,(4):74.
[18]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C]//张兆龙.中国电影年鉴1995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250.
[19]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20]卢燕,李亦中.隔洋观景:好莱坞镜像纵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21]顾仲彝.加紧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C]//李道新.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360.
[22]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82.
[23]蔡楚生.苏联电影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影响和帮助[C]//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上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229.
[责任编辑:姚青群]
J905
A
1008-7346(2015)03-0001-07
2015-04-30
颜纯钧,男,福建晋江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