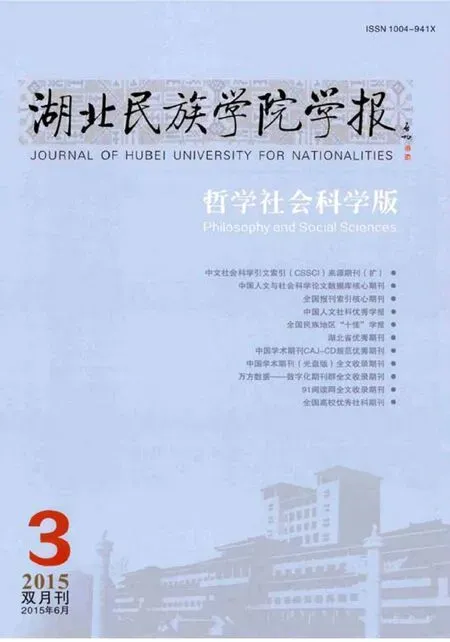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叙事主体分析
2015-04-17龚新琼
龚新琼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新媒体语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叙事主体分析
龚新琼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新媒体深度参与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改写了突发性群体事件传统的叙事格局。在新媒体语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出现了三大叙事主体:以“自利理性”为主导的当事方、“社会围观心理”主导的大众和“社会理性”主导的媒体。这三大类叙事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复杂的关系状态。
新媒体;突发性群体事件;叙事主体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此过程中,由于利益分配、观念转变、制度缺失、行为失范等,必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有可能在某些特殊时期、个别领域或局部地区出现社会矛盾尖锐化。
2009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态势,并出现了一种“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1]。非阶层性是说参与事件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不同的层面,无直接利益是指参加者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传播范围、影响力、参与面与知晓度主要取决于组织化的信息传播机构——媒体的传播容量、范围、立场态度与传播技巧和策略,从而使得相关事件的传播带有强烈的媒体主导的色彩,因而也具有高度的可控性,无论是从信息传播的时机上还是从信息的选择、组合与再结构化上都体现出一种“控制、管理”此类事件的惯性思维。但是新媒体在社会普及率的提高,人们知晓权与传播权等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整个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带来社会图景重构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传播领域的新气象。从新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格局重构的层面来观照此类事件则会发现,在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扩散与积聚、影响的传递与累积、受众的接受与参与,这些信息传播的要素与效果均呈现出较之于传统媒介环境下迥异的特质与规律。
尤其是对于“非阶层性、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而言,有三大类叙事主体在参与事件的话语表达与立场建构,这些姿态各异的叙事主体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状态,其分别受制于不同力量在信息场域进行着事件表达与重构。
“自利理性”主导的叙事主体——当事方
有关研究指出,群体性事件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2]。群众主要提出的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诉求,并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换句话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多为利益受损的个体或群体与相关组织发生的一种冲突事件。因而在有关此类事件的传播中,当事双方就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一极,扮演着诸如信息来源的重要角色。当事方既包括“相对强势”的组织,也包括利益受损、“相对弱势”的个人或群体。这一类主体更多基于“自利理性”来进行信息传播与话语表达。“自利理性”本是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考虑其他个体或组织的利益[3]。此处借用过来,指当事方更多从维护个体或群体、组织利益的角度,而非社会或公众利益的角度所进行的信息传递与叙事表达。
有研究者指出,有关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信息传播,信息博弈中重要的一方即是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传播主体。这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结构的行为主体, 其危机传播的表现形式是组织传播, 也就是与群体性危机事件利益相关的、直接涉及到的利益集团行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在危机事件时向社会发布信息的行为。[4]
作为“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是近来西方危机传播理论中的一个新的概念。大意是应对危机传播时,要注意考虑和危机事件相关联的各方利益,动员各个利益相关方一起来应对危机事件。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库姆斯在其“情景式危机传播”理论中提出来的。的组织,既是行为主体,又是传播主体和叙事主体,这种双重身份的叠加与重合,一方面,使其作为信源在整个信息传播链条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整个信息传播过程对之可能的依赖性,亦能赋予其信息较强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又带来信息传播链条其他环节对其叙事角度与立场过于主观性的怀疑与猜忌。这种既拥有话语传播的主导权,又受制于当事人身份的角色矛盾使得组织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出现缺位与错位。具体表现为或者沉默不语,作为当事方三缄其口;或者用简单的贴标签的方式来对事件进行定性,如常见的“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有组织、有预谋”等表达式,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组织叙事语态的简单化,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无组织化和无序化。
从组织一方来说,这种基于“自利理性”的缺位或错位表现,不仅使其作为信源的传播优势彻底消解,甚至还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组织与群众对立的虚假印象。从整个信息传播链条的完整与信息传播格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组织的缺位与错位,即是作为重要的叙事主体的角色扮演失范,不仅导致了信息源头上的权威信息缺失,在贻误最宝贵的事件处置时机的过程中也丧失了其话语主导和引领舆论的主动权。
同样是基于“自利理性”,与“相对强势”的、机构化的组织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缺位与错位不同,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在事件的信息传播则以一种活跃主动、积极把握传播机会的立场和姿态参与事件叙述。因为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媒体基本垄断了专业化和机构化的传播渠道,作为当事方的个人或群体既然丧失渠道优势,有关事件的话语表达和利益诉求就无法被更大范围公众倾听与关注。而新媒体在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打破专业机构的渠道垄断局面的同时,更赋予其强大的话语动员与舆论集结的力量。当事的个人或群体不仅可以发声,更可以利用新媒体来进行舆论动员,唤起普通公众的同情与关注,并经由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呈裂变式扩散,迅速积聚社会关注度。
从积极的层面来说,作为当事个人或群体以重要的信息来源身份参与话语表达,丰富了叙事的内容和角度,打破了当事组织和媒体垄断信息的局面;从消极的层面来说,此类大众可能由于“自利理性”驱动而制造谎言、谣言以迎合其他大众来提高事件的知晓度和关注度,以期实现预期目的。
“社会围观心理”主导的叙事主体——大众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组织与媒体拥有着较强的话语控制权,普通大众参与事件的信息传播相对滞后与缺失,相对于有着严密组织结构的行为主体,其信息传播的机会、渠道与能力都相距甚远。但是,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既有的传播格局。无论是“全民皆记者”,还是“人人都有麦克风”,抑或是“围观改变中国”,都形象地说明了普通大众全面、深度参与信息传播和话语表达的事实。所谓社会围观状态,即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的一种自觉化、普遍化的传播参与状态。正是此种普遍化的、自觉性的社会围观亦即传播参与行为,极大地扩散了事件的传递范围,增强了事件的影响力与辐射面。
在传统媒体宰制传播格局的情形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传播初期,信息主要以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在与事件利益相关的、直接受到损害的人或群体,以及与事件价值取向相同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流通和扩散[4]。这是一种点对点的效力较低的传播状态,形成的是基于利益攸关程度的相对封闭的人际传播圈。由于新媒体的普及,尤其是自媒体、qq群等即时社交通讯工具彻底颠覆了过去点对点的低效传播状态。首先是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对象和范围:从特定的目标群体到非特定的目标群体,从小范围的固定人群到较大范围的不固定人群传播,从直接利益关系群体到非直接利益关系群体。其次,信息内容更具多样性(也更多想象和猜测):从传统媒体影响人们想什么和怎么想到人们自己决定想不想、想什么和怎么想。如果说传播范围的拓展带来了对象数量的提升,那么其与传播内容的多样化之结合,则引发了最具变革性的传播图景更迭:传→受单向链条的断裂、媒体中心的消解、大众话语权籍由多种传播平台的放大等等。
有研究者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分析后发现,除极少数蓄意破坏分子外,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以直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逐渐扩大到一些存在类似情况的间接利益相关群体,以及心境相通、情感上持同情态度的部分群众[5]。与之相关的是,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信息传播与叙事活动的大众大都为非特定、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和群体。这类大众参与信息传播活动,一方面是新媒体赋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治理理念变更与民众参与意识复苏的一种必然要求。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因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积累的矛盾和“制度性受损”聚拢的社会不满群体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参与者[5],而某一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就会成为激发和宣泄不满情绪的导火索,迅速引起非当事大众的关注和传播。
技术层面的可能性与社会层面的必然性之结合造就的是一种全新的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状态:组织、大众与媒体各执一词、甚至针锋相对;群体极化现象严重[6];质疑心态的培养与蔓延。仅从湖北石首事件的发展过程就可窥见,对于非特定、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一类大众来说,其参与话语表达从主观上来说可能是对利益受损方的一种舆论声援与话语支持,从客观上也营造了一种话语场域开放、多样观点交流争论的生动舆论局面;但同时,对于非特定、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大众来说,其与事件的非直接相关性使其在信息的来源上更倚赖非官方、非主流的渠道,信息的加工上更具主观随意性和想象性,信息的传递上更多情感宣泄和情绪感染,从而造成信息的臆测、揣度多于信息的客观、真实之信息传播局面。
在诸如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中,“社会围观”心理映射的是民众籍由信息参与所获得的替代性补偿满足。或者说,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通过传统媒体、手机、网络等了解信息、关注事态、传播观点立场,与其说是出于直接的功利目的,不如说是其参与社会改造、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表达与立场宣言。
“社会理性”主导的叙事主体——媒体
媒体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传播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较之于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组织,和当事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或群体,其具有无可比拟的客观、公正、均衡的职业素养与职业形象;较之于非特定的、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和群体,其拥有更制度化、机构化的专业生产优势。因而媒体在对突发性群体事件进行聚焦、关注、解读和评析的过程中就拥有良好的信息整合主动权。“社会理性”本是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体以整个社会或群体的利益为目标,具有使社会或群体的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倾向和思维动力[3]。此处借用过来指媒体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争取维护公众知情权、媒介传播权的思路与做法。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新闻媒介在表面上与群体性事件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但是从根源上分析,媒介的“利益关联”却最为直接。因为群体性事件是因社会“协商”断裂、彼此不信任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此时新闻媒介的介入就承担着重要的将社会重新整合的功能与责任,甚至可以说,社会利益也就是新闻媒介自己的利益,因而,新闻媒介与群体性事件就具有了直接的“利益关联”[4]。由是观之,此时媒体与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关联”乃是基于媒体之“社会公器”、“公共领域”、“公共论坛”的角色与定位使然。
媒体“社会公器”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不偏不倚的原则立场和基于社会利益与集体理性的价值选择,但这仅仅为一种最理想状态的假定。事实上,有研究者在对石首事件中《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三家媒体的报道时机、报道量、报道视角等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面对同一群体性事件,三家媒体的解读却有明显不同。对于《湖北日报》和《楚天都市报》来说,发生在本地的事件,限于各种现实因素,没能及时、准确、全面的传播信息;《南方都市报》作为异地报纸媒体,其相对客观的报道起到了异地监督的作用,对地方保护主义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使得社会矛盾暴露出来,促进了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的全局稳定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7]
突发性群体事件多为区域性事件,因而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就可区分出本地媒体与异地媒体两类叙事主体。突发性群体事件多为冲突性事件和所谓“负面新闻”,本地媒体囿于地方保护主义或“信息封锁”、“家丑不可外扬”的老旧思维模式,或沉默失语,或语焉不详。事实上,大量有关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及其演变阶段的研究都表明,事件初期官方信息、主流声音的缺席是导致流言盛行、谣言蔓延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与本地媒体的失语和无为有关。如果说本地媒体在有关群体性事件中叙事话语权的丢失是一种被迫放弃的话,那么异地媒体则应当仁不让地担当话语主动权,否则整个媒介话语系统的集体失声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以社会冲突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冲突乃是当今社会结构的一种常态。当社会冲突发生时,社会的有关信息需求增强,并带来整个社会信息流量的随之增加。此时,专业化、机构化、制度化的话语表达和信息传播如果缺位,必然导致非专业化、非制度化、非机构化的话语表达与信息传播占领信息流通渠道,而一旦此种局面形成,组织、媒体,以至于整个社会所要付出的社会协调、关系修复成本将更高,最后的效果则相当有限。
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三大叙事主体所形成的话语布局中,作为当事方的组织和特定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或群体是重要的叙事主体之一,其作为信息来源和利益攸关方的角色赋予其话语主动权和“自利理性”——如果能将“自利理性”转向“社会理性”将极大增强此类叙事主体话语的可信度与舆论引导力度。作为公共话语平台和社会舆论机关的媒体,尽管有本地媒体和异地媒体之分,其在群体性事件中理应担当起社会整合、协商与对话的职责,自觉以“社会理性”为主导,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满足公众和社会的信息需求。作为“非特定阶层的、无直接利益”的普通大众来说,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应尽可能规避在“社会围观”心理主导下的集体非理性和对集群规范的否定与破坏。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叙事主体的关系模式图
突发性群体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利益受损方通过极端方式进行的一种利益诉求和表达,其目的在于利益的达成与实现。
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媒介依赖的强弱主要由两个变量决定,一个是媒介功能实现的程度,另一个即是社会冲突的程度[8]。可以这么说,个体或社会对媒介依赖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媒介信息传递的数量和质量也即媒介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冲突的程度。社会冲突越激烈,媒介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越多,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就越深,整个社会对媒介的依赖也就越深。反之亦然。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媒体应充分发挥专业生产权威、客观、深入、全面的信息传播优势,实现舆论的引导和社会的整合与协调。
[1] 中国社科院.2009年群体性事件多发 源于民怨太深[EB/OL].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12/21/content_19106337.htm.
[2] 李保臣.我国近五年群体性事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3] 胡石清,乌家培.关于信任的博弈分析[J].当代财经,2009(3).
[4] 伍新明,许皓.新媒体条件下群体性事件中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J].贵州社会科学,2010(10).
[5] 许海,唐远清.群体性事件本质、成因及防治的舆论学解析[J].当代传播,2011(4).
[6] 欧阳小婷.网民群体极化倾向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J].现代视听,2009(1).
[7] 于晓霞.群体事件传播中我国媒体角色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8] 龚新琼.关系·冲突·整合——理解媒介依赖理论的三个维度[J].当代传播,2011(6).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5-03-28
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信息传播与嬗变”(课题编号:2012Y055);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叙事模式分析”(课题编号:2015Z288);湖北师范学院文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和湖北省重点学科湖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资助。
龚新琼(1978- ),女,湖北公安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
G206
A
1004-941(2015)03-01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