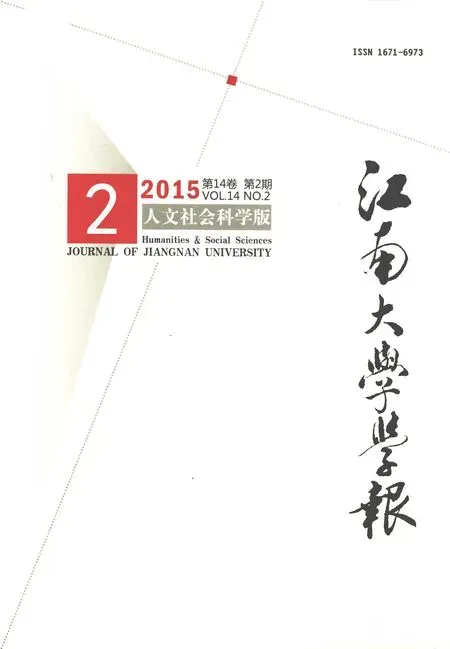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盛述论
2015-04-15陈晖莉
陈晖莉
(福建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盛述论
陈晖莉
(福建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晚明社会,文人大规模、大范围的佛寺旅游活动,可分为仕宦型寺庙游历之游、布衣型寺庙修学之旅、山林式心灵修行之旅和城镇式庙会娱乐之旅,呈现其清雅的文化性、世俗的娱乐性和科学的考察性等特征,是晚明社会特殊政治背景下文人失意心境的无奈寄托;是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文人休闲娱乐生活的表现;也是晚明佛教龙象复兴,士僧互动社会新风的表现。
[关键词]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盛
晚明时代上可追溯嘉靖后期,以万历到天启年间为主体期,下迄崇祯时期。万历年间,社会历史进入一个大变动时期,是一个动荡与繁荣、死亡与新生并存又先后交替的历史时期。在这动荡的时代,文人生活呈现斑驳陆离的时代特征,其中旅游生活表现突出。周振鹤先生指出:“这是前所未有后所罕见的现象。在唐虽有游人,而多数留连光景,作为诗料;在宋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在清代几乎萎缩到只有极少数人才热爱山水。而晚明却是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1]“明朝中后期那样如醉如痴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更为历史上所罕见”[2],旅游甚至成为晚明人“开门新七件事”之一*晚明人笑言新七件事:旅游、谈谐、听曲、博奕、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以区别“旧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此,学界也围绕晚明文人好游风潮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明代社会史学者陈宝良先生*陈宝良:《从旅游观念看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市民文化的演绎:晚明旅游风尚的文化动因》。《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明代的商贸旅游》,《中州学刊》,2007,(5);《明代的宗教旅游》,《中州学刊》,2006,(5).对晚明士大夫的闲暇生活、节日旅游、商贸旅游、宗教旅游等专题发表一系列文章。滕新才先生[2]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撞击下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转变研究晚明全国性的旅游热潮。周振鹤先生[1]从地理学角度论证了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过程。陈建勤先生在明清江南文人旅游研究领域可谓成果卓著,专题研究明清江南炽胜的游风及其社会意义[3]。先后发表多篇文章阐述明清江南地区的旅游消费专题[3]与明清文士的旅游观*陈建勤:《论游道——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一》,《旅游学刊》,2000,(4);《议景观——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7);《明清文士的景观观念》,《华夏文化》,2002,(3).。宋立中先生对明清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游船业经营、旅馆业发展及江南消费时尚化现象等作出深刻分析*宋立中:《论明清江南消费时尚化现象及其社会学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1); 宋立中:《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宋立中:《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社会科学版),2010,(2).。 魏向东、李蓓[4]引进量化研究方法解析晚明文人旅游者的基本特征与旅游行为特征并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把握文人群体的旅游行为规律。学者的研究丰富了晚明社会旅游风潮的研究,尤其是江南地区文人旅游消费现象和文人旅游观的研究拓展了晚明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其研究内涵。
然而,值得关注到是,在这股晚明文人旅游风潮中文人的佛寺旅游活动表现尤为突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寺丰富的景观资源,如以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佛教绘画、佛教饮食等为主的佛教物质文化;以佛教音乐、佛教伦理、佛教礼仪等为主的佛教精神文化和以佛教节日、节庆活动为主的佛教社会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文人前往领略自然秀美的风光,欣赏佛寺文化的艺术性和文化性,体验佛教神秘而清心的宗教氛围并参与佛事活动。然而,与学界对江南地区文人旅游消费研究成果相比,晚明文人宗教旅游研究相对冷门与薄弱。中国旅游史的研究专家如范能船、章采烈、王元海、许晓光、沈祖祥等*范能船:《中国佛教旅游》,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章采烈:《中国宗教特色旅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元海:《旅游宗教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许晓光:《旅游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沈祖祥:《中国宗教旅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多从宗教角度阐述三大宗教文化特色、宗教名胜及其与旅游的密切联系,但未能专题关注晚明文人阶层的宗教旅游风潮。陈宝良先生虽对关注到明代特殊的宗教旅游现象,但缺少对“文人”群体的专项考察。
为何文人多喜好选择宗教名山作为旅游目的地?晚明出现文人佛寺旅游风盛社会背景是什么?文人佛寺旅游类型有何类型及特征?本质为何?对今天的宗教旅游开发有何借鉴意义?这一系列未被关注的文人佛寺旅游问题成为笔者思考的缘起。因此,本文围绕晚明文人佛寺旅游原因、类型、特点及其本质展开分析以丰富晚明文人旅游风气的研究,弥补学界对晚明文人宗教旅游研究的薄弱,以期对今天宗教旅游的规划开发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
一、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潮
明代文人在游历生活中大多与寺院结下不解之缘,多选择宗教名山作为旅游目的地。就其身份而言主要可分为仕宦型寺庙游历之游和布衣型寺庙修学之旅;就其目的而言,主要有山林式心灵修行之旅和城镇式庙会娱乐之旅。
(一)仕宦型寺庙游历之旅
宦游者,或为在任官员,有章缓之荣,不忘山水之乐,他们或公差,或迁滴,宦辙所至,顺道搜览一地风景,乘兴则一一观赏。或为官员罢官致仕成为乡士(乡宦、乡绅),他们谢事归休后,无所羁绊,得以肆情登阶,踏遍家乡山山水水,一来了却青壮年忙于奔走仕途,无暇顾及家乡古迹之愿,二来寄情于山水,告慰寂寞之心。如著名宦游家王士性先后在河南、山东、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山东、南京等地做官,“官辙几遍天下”,所到之处“登高揽胜,寰中佳山水”,且不忘文人雅兴“入其品题”[5]25,他常亲历其境,细致考察,认真研究,作出科学的结论。他在宦游过程中写下许多游记和记游诗,后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对游历和考察加以整理成就两部杰出的地理学著作:《广游志》与《广志绎》。时人称:“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之文笔如先生者,古今亦无几人”[5]20。
南京、扬州、镇江、苏州等地,或据交通孔道,或为繁华之区,来往途经或特意造访的官员不计其数,以致“府县官日以迎送过客为事”*(明)海瑞:《海瑞集》上编《被论自陈不职疏》。,官府衙门承担大量的旅游接待工作。如吴门苏州“凡为吴邑者,率以其力什之二三守官,而以什之六七事人”*嘉靖:《吴邑志》,《吴邑治雁图说》。。对于富庶而交通便利的苏州、南京、扬州等地的名胜古迹,无论春秋冬夏, “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乾隆:《元和县志》卷10《风俗》。。宦游中,由于古代中国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官员在旅行途中同样可以享受种种的特权。如嘉靖间,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游著名景点善卷洞时,当地县尹、县丞“置酒设馔,歌吹并作,声彻于外,山林童臾,咸伫听焉”*劳亦安编:《古今游记丛钞》卷15《游宜兴二洞记》。,并加派巡检领兵数十人护从。官员出行虽然具备良好的交通、饮食和住宿条件,铺张的排场,但也受到一定限制,无法自由安排行程,以服从朝廷任命为首务。如一生历仕四朝,以清直闻于时的尹伸在游昆明西山时道出宦游的不便:“望数峰更不可径,始知胜情为俗钠所结。宦中游眺,往往如此”[6]。
(二)布衣型寺庙修学之旅
李日华所云:“游道之盛,无如孝廉。”[7]其所谓孝廉即是指当时的生员辈,多是未取得功名的科考者或是绝意仕途者,即布衣文人。正所谓“破庙好读书”,清幽的寺庙氛围正是读书人理想的读书环境,是失意文人最佳的心灵寄托,也是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绝佳的社会实践方式。
1.应考者借住寺庙读书之旅
寺庙清静的自然氛围与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无数读书应考者暂住寺庙学习。江南寺庙多因其名气,借宿文人甚至为此付出相应代价。如王思任记载借宿南京栖霞寺的情境:
至寺,则郑使移尊褥于苍麓上人房矣。其楼倚青玉之壁,松涛鸟弄,流泉在其户下,胜不可言。陈父言秋闱租此者,一日三金。予曰:“三金而买一日,有此贱日哉?”元秿曰:“或将鬻身削发,住此间矣。”于荥曰:“何至乃尔?”约异日再游,归。[8]
2.科场失意者寺庙游历之旅
寺庙清幽的自然环境与与世无争的人情实况给在人世中苦苦挣扎的失意文人一个很好的逃遁空间。以晚明袁中道为例。袁中道,字小修,从小才华横溢,仅十余岁时,即作《黄山》,《雪》二赋,达五千余言,长益豪迈。可是小修的科举道路异常坎坷,在二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小修先后十次参加科举考试,直到四十六岁那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了进士。袁中道重要游记作品之一《游居柿录》记录了小修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高中进士这段科场失意期,对湖北、湖南、江苏、京师不同地方的19家寺庙作过访问,且多与诗僧有心灵的唱和。如《游居柿录》中提到:至兴德寺,般若庵僧如贤卓锡处,颇清寂。出石刻《四十二章经》,予亦书一段,已勒石矣。寺后看水,浩然一湖晴雪,宛似江南。[9]
3.绝意仕途者寺庙科考之旅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吏治日下,部分文人放弃“科举入仕之路”,一改过去那种侈谈理性、不务实际的风气,开始注意探索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在旅游审美愉悦的同时,向科学化的实地考察方向转变,明代旅游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科学文化内涵。其主要代表有:明代著名医学家、书画家王履。王履,字安道,号畸叟,江苏昆山人。他认为书画真正的创造不是“仿”而是“去故而就新”,深入自然,并由此提出了“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精辟名言。 吴门画派的始祖沈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等人的成就也是与亲临仿画自然山水分不开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字学先,号玄扈,上海人。他最著名的著作《农政全书》就是通过旅游考察实地调查取得的辉煌成果。徐霞客年轻时应试科举落第后就放弃仕宦之念。他通过“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要高蹈之迹”,“搜古人逸事,与丹台石室之藏”[10],立下游览名山大川的宏愿。徐霞客在出游途中除进行自然景观的欣赏、考证之外,寺庙之旅也是其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徐霞客在鸡足山时在僧人帮助下得以遍览鸡山名胜,如指掌其地形山势,从而自如地驾驭素材,生动而详实描写了鸡足山一带的人文地理及僧人寺院分布情况,为后人研究留下丰富而可信的史料。
(三)山林式心灵修行之旅
明代长江三角洲地区侨寓众多文人,他们或为孤傲清淡,不谙世事,不乐仕进;或有济世之愿而未能就举子业;但却都喜探幽胜,临山水,好吟咏,享受山林之乐,以此修身养性。如朱存理、宋懋澄、俞允文、沈周、史鉴、王宠、王稚登等皆常作山水客。晚明文人走入山林,吟咏山水间,追求山水之乐,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情感的满足的同时,也在与大德高僧的禅机对话中寻求心灵的宁静与自适。如袁宏道濡染晚明禅悦之风,参禅礼佛,甚为诚笃。他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也好游佛殿禅房、僧寺古刹,如开先寺、黄岩寺及德山、庐山、华山、篙山诸名寺。其游途之伴者,如陶望龄、江进之、方子公等人亦皆禅客,且常有僧侣相伴,如西湖、桃源、开先寺、华山、万山寺之游皆有僧为伴。
袁中道的《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曾记载中郎与陶望龄游山玩水之中谈禅问道、商证禅理的事迹:“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先生与石箫诸公商证,日益玄奥。先生之资近狂,故以承当胜;石笋之资近捐,故以严密胜。两人递相取益,而间发为诗文,俱从云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了不与世匠相似”。从中可见两人于旅途中商证禅理,慧悟优美的诗文篇章。
(四)城镇式庙会娱乐之旅
晚明文人在心学思潮激荡和佛教世俗化趋势综合作用下,他们日益融入世俗的宗教活动之中,他们不再固守文人清高姿态,而是以市民的热情融入城镇式庙会娱乐活动之中,并留下大量相关的文字记录。杭州佛教历来发达,相关庙会活动亦很兴盛。杭州佛教,始自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杭州的径山、灵隐、净慈、三竺等佛寺均名列佛教禅、教、律三宗“五山十刹”前列。苏轼诗中“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哺”,以及《天竺山志》所称“凿山增室、广聚学徒、教苑之盛、冠于两浙”,都描绘了当时佛教盛况。晚明,杭州曾以净慈寺为主,形成南山香火。每年正月六日为“定光(即燃灯佛)诞辰”杭城男女倾城出游,成为旧时风俗,俗称“赛爆竹”,游人取道净慈寺至法相寺进香,“沿途张筵,笙歌杂奏”,多以爆竹相互斗放。每遇除夕,则官府设筵寺中燃放焰火,全城男女来观者摩肩接踵,不下数万人。
二、晚明文人佛寺旅游原因解析
(一)寺庙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热闹的社会景观吸引文人前往旅游
天下名山,僧占多。正所谓,“山之胜,莫大于寺*(明)邵宝:《慧山寺》,卷2《寺》。。许多历史名刹皆是钟灵毓秀之地,据得山水佳妙处。寺院选址不仅风景优美,更为讲究风景的风水,即“形胜”,即先要形势重要,然后才是景色优美之地。这种观念深深反映在各类寺志中的“山川考”。通常,各类寺志会单列一卷,专论山川形势,并做到寺院在创寺、殿堂增建、拓新,以形势结合堪舆作为规划原则。如《天童寺志》中记载南宋绍兴初,住持宏智禅师为使天童寺名扬于时,听从阴阳家献言,拓旧维新,广构殿宇,井拢其门为杰阁,前为二大池,曰万工,中立七塔。时人又议天童路径如斗形,双池并深,中筑七塔以象斗,四白三赤,白以生水,赤以厌火。……由是天童不特为四明甲刹,东南数千里亦皆推为第一,游观者必至,至则忘归,归而诧于人,声闻四方,江湖钠子以不至为歉*(明)杨明辑:《天童寺志》,《千佛阁记》。。经过改造后的天童寺成为东南地区四大名刹,游者纷踏而来。浙江普陀山甚至对关系风水的后山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任何有损风水之事都将受到惩罚:“后山系寺之来脉,堪舆家,俱言不宜建盖。故常住特买东房基地,与太古堂相易。今留内官生祠外,其余悉栽竹木,培荫道场。后人永不许违禁建造。其寺后岭路,亦不得仍前往来,踏损龙脉。一应行人,俱从几宝岭下旧路行走。犯者摈治”*(民国)王亨彦辑:《普陀洛迦新志》,卷8,山中旧规。。
讲究“形胜”的前提下,还要追求独特的人文“境致”。明人张岳在《信芳亭记》一文中指出:盖凡湖山以胜名,则必带林麓,穷岩壑,有宫室亭榭之观,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传……然后其名始盛,而游者踵至。这也契合了晚明文人“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清)钱兆鹏:《述古堂文集》,卷7《游北山记》。。王思任也指出优美自然山川离不开人的因素即“山川之须眉,人朗之也”[11]7。前世帝王、名人所游、所居之处,即使景致一般,如若保留大量历史遗迹,也值得一游。王思任游皖南时说:“滁阳诸山,视吾家岩壑,不啻数坡耳,有欧、苏二老足目其间,遂与海内争千古。”[11]7平庸的滁阳山地景色,因了欧阳修、苏轼的人文色彩,其价值远超其自然观赏价值,遂致争千古。
文人在追求寺庙人文景观的同时,随着晚明佛教和文人生活世俗化,他们不再固守传统文人不语鬼怪传统儒家思想,放下文人清高生活格调,纷纷融入世俗宗教生活中,热情参与宗教节庆活动,他们不仅以旁观者身份观察社会民俗、体察社会民生,更以世俗的欢乐融入寺庙的节庆活动之中。杭州西湖向来是文人骚客必游之地,其香市更是名闻天下。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评述。如袁宏道在《湖上杂叙》一文中说道:“过西湖凡三次”在湖上住昭庆寺五天,法相、天竺两寺各一夜。但是他对天竺山信徒进香的活动印象特别深刻:“天竺之山,周遭攒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烧香男女,弥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气如烟不可近。”*(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10,《湖上杂叙》。他以客观的笔法记录天竺山信徒进香盛况,并没有对其多加批评或指责。
诚如研究中国寺庙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段玉明先生所言:在不动摇信仰根基的前提下,中国寺庙在尽可能宽泛的方面向世俗靠拢向文化升华,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世俗靠拢、向文化升华,以此缩短与俗众的距离。而由于这个倾向,中国寺庙在把自己装点成圣所的同时,也把自己世俗成为了民众的文化娱乐中心[12]。
(二)晚明士僧互动社会新风,促进文人佛寺旅游
著名历史学者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认为:“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13]。晚明文人多在其文集中提到晚明社会士僧间的交往与互动。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率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明)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7《愿学记》二。陈龙正也载:“或曰:近见大族妇人,入寺拈香听经,拜高僧为师。”*(明)陈龙正:《几亭全书》,卷22,《政书》,《杂训》。蒋德憬在《理学经纬十书序》中指出:“故今世士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饭依净土。”*(明)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29,蒋德憬《理学经纬十书序》。
甚至于多有学者对佛学的研究较为精到。如杨起元(贞复)“居闲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鉴之风,遂结屋韶石”*(清)彭际清编:《居士传》,卷44。。薛元初(太春)“习举子业,始见老,庄书及《维摩》、《园觉》诸经,辄以孔孟之语解之,一夕豁然有醒,自是慧辨无碍”*(清)彭际清编:《居士传》卷38。。并著书传世,如陆树声的《禅林余藻》,陶望龄的《宗镜广删》,王肯堂的《参禅要诀》,袁宏道的《宗镜摄录》,萧士玮的《起信论解》,钟惺的《楞严如说》,小修自己也有《禅宗正统》传世。
有些士人甚至不讳言自己“佞佛”。如何允之书房中悬挂条幅:“勿谓何次道好佞佛,好佞佛亦奚病哉!”*(明)顾大韶:《炳烛斋稿》《峄县知县何公暨元配钱夫人行状》,康熙十年顾晶、顾淼刻本。佛道思想的盛行甚至使很多士人沉酒于佛道之中,最后竟然弃儒归佛道,如李贽弃发为僧;钟惺临终受戒,自法名断残。
僧道与士人的交往不只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明中后期江南结社之风中,僧道与士人所共同结成的团社也大量出现[14],其中比较著名得有“月会”“金粟社”“放生社”等等。《金陵琐事》载:“顾清甫,究心禅理,与高僧结西方社,别号宝幢居士。”*(明)周晖:《金陵琐事》卷3。罗逸,字苑游,“建立莲花庵于桃花源,与僧印我及郑重郝璧诸人结社参禅,鼎革后为僧,法名真沐”。*(民国)《款县志》卷10,《人物志·诗林》,中国方志丛书。士人也积极参加僧人的举会即僧社。如汪道昆曾提及过肇林社,即是僧人之社,所讲为《楞严经》,而参加者中有不少是汪道昆的丰干社的成员如方羽仲、程子虚。这类僧会,在晚明颇为流行,像管志道这一类主张三教合一的讲学者就曾参加过这类讲会,耿定向的弟子李士龙也参加过这类讲经社。当时的士大夫还会在寺庙中担当斋主,发起华严会,比如:“自为斋主,于三圣阁起华严会。时禅堂袖子宝方、怡山而下五六人,本寺戒僧本空而下数十人,皆聚于阁。三时念佛,二时诵华严经各一卷。”[15]
在士人积极主动接近并融入佛学与佛教活动的同时,僧人们,特别是一些得道高僧更是看到晚明儒道释三教融合发展趋势,也积极倡导儒佛相交。晚明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都是儒学出身的僧人,他们极力主张佛儒结合。云栖祩宏著述的《竹窗随笔》中阐述《儒佛交非》的论点[16],对佛学界影响巨大。藕益智旭在《四书益解》自序中说:“解《论语》曰《点睛》,开出世光明也;解《庸》、《学》曰《直指》,变不二心源也;解《孟子》曰《择乳》,饮其醇,存其水也。佛祖圣贤皆在无实法缀人,但为人解粘去缚,今亦不过用楔出楔,助发圣贤心印而已。”[17]紫柏认为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为佛,而佛教达到最高境界即为儒,并以儒释合一看法消解某些敌视佛教言论*(明释)紫柏大师:《紫柏老人集》卷9《长松茹退》。。
晚明佛教的复兴与儒佛相交社会背景下,士僧互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正如钟惺在《善权和尚诗序》一文中即叙述了僧人习文,与士人交往的社会风气:
金陵吴越间,衲子多称诗者,今遂以为风。大要谓僧不诗,则其为僧不清;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为雅,而僧之为诗者,得操其权,以要取士大夫。
僧人通过与士人的交往获得社会认可,便于弘法。晚明士人一方面通过与僧道的谈禅讲经来体验超脱世俗和生命之外的轻松,另一方面又可不为佛道教规的绳墨所限,在与僧道的交游中享受着一种非僧非俗,闲适又不空寂的生活。再者又可通过与僧人的交往博取雅号。于是乎,在这股强大的士僧互动洪流中,士人们纷纷走向寺院,委心自然,清净本心,追求佛道中人谈禅论道的清净而闲适的生活。如袁宏道:“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含苍鲜色,窗满碧畴风。适性迎花石,书方去鸟虫。酒人多道侣,醉里也谈空。”*(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29,《柳浪杂咏》。士人李严也与僧道交往,“字筑夫,号南山,善写真钩,画栈道及骡马之属,特工橄,初师同里张鸣,晚年与道士刘敏交善”*(光绪)《青浦县志》卷21,《人物艺术传》。。隐士徐弘泽,虽然意绝进取,但却广交海内名士、山人、居士、佛道之人,吟诗品茗,互为唱和*(明)李日华:《恬致堂集》卷25。。苏州士人刑量,终生以读书乐道为事,“闭门静坐,黯校诸经及博观子史百家,座中之客,惟禅人道侣。”*(明)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卷45。
(三)寺院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使其成为晚明文人言论自由与安全保障的适宜之地
明中后期的讲学风尚是明王朝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讲学运动遍布大江南北,尤以南方南直隶、江西、浙江为最。明代各地讲学之处如书院、会馆、精舍、山房、宗祠、贡院、寺庙、道观等本身即是风景名胜地。晚明文人讲学之处在书院未形成发展之势的前期多选择寺庙道观。如徽州歙县的《紫阳书院志》卷16记载到:
星溪汪氏曰:其时六邑大会录,纪载混淆,罔有宗尚,故其时人人口说紫阳,而足迹不践字样紫阳之堂。往往于歙则斗山(书院)、汪村、向聂寺、等觉寺、福田寺,于休则天泉(书院)、建初(寺)、汶溪(许祠)、落石、山斗、还古(书院)、白岳(功德堂),于婺则福山(书院)、虹东(书院)、雪源、普济寺、天仙观、三贤寺、黄莲山房,于黟则中天(书院)、延庆,于祁则东山(书院)、十王山、洞元观、谢氏、方氏、马氏诸宗祠,于绩则”太平山房、许氏家祠。
经过统计可知在这份汪星溪提供的讲会场所名单中,以寺观最多,其次为书院、宗祠。那么,为何寺院能够在诸多地点中脱颖而出,成为文人讲学的主要地点?
其一,寺院本身优美而丰富的景观吸引文人前往讲学。正所谓“梵刹霖宫,虽缁流羽士所潜踪,大约处邑之形胜者居多,以故历代名贤高士多游息矣。”*(清)项维正等纂修:《江浦县志》,卷7。
其二,寺庙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保护文人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如晚明的灵济宫之会,成为当时京城为官的官僚、上计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国子生们,政暇或治学之余的聚会中心,“及在政府,为讲会于灵济宫,使南野、双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7《文贞徐存斋先生阶》。。寺院较之于书院,政治立场更为中立,而书院也因其公开化的政治意义多次遭到统治者的镇压乃至销毁。正如卜正民先生所言:“因为书院没有中立的光环,不能超越与以前机构相联系的世俗事务。由于任何儒家问题的讨论都不能避免行驶公共权威的意义,那么在书院聚会或讲学的那些人就难免受到聚众讲学图谋不轨的指责。事实上,在寺院的宗教环境之外进行公共讨论的行为就可能构成对国家特权的侵犯。这样,16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其前后兴建的书院,紧跟着在该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遭到压制也就不足为奇了。”[18]110而寺院同样能够提供如书院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之外,还拥有广阔的空间以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雅士,最重要的是,寺院中立的政治立场保护文人言论的自由与人身安全,甚至还可以借鉴佛教公开讲经和戏曲佛教口语注释经典等诸多形式宣扬道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量寺院空间16世纪供公共讲学之用”[18]110,极大地推动文人雅士的寺庙之行,从而促进文人的佛寺旅游活动。
三、晚明文人佛寺旅游特点
(一)参与范围广泛,社会影响巨大
佛寺景观因其以宗教建筑、宗教经典、宗教绘画、宗教雕塑、宗教饮食、宗教音乐、宗教舞蹈、宗教节日庆典和宗教神话、传说等为主的宗教景观和以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等宗教精神成为晚明文人出行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文人多参与到佛寺旅游活动之中。在地域分布上,以经济为先的江南地区为胜,京师地区有一定发展,即使是西南等较为偏远的地区也因为宦游、游学风潮和独特而丰富的佛寺旅游资源影响,其旅游活动得到一定的发展。
遍布全国,广泛参与的文人佛寺旅游活动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促进晚明游记文学的复兴和繁荣。正如钱谦益在《越东游草引》一文中评述当时流行写游记的风气:“余尝闻吴中名士语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记”,甚至到了“今杭城刻名山记累积充几案”的程度*(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2,《越东游草引》。。其次,文人丰富的题咏和数量众多的摩崖石刻亦成为寺庙新的人文景观,提升寺庙知名度的同时,又促进了文人佛寺旅游的发展。如《乐山历代诗集》卷67至卷74中所辑录明人峨眉山诗,高达93人258首之多。诸陈文灿、范涞、毛起、王士性、袁子让、曹学铨、尹伸、胡世安等明人游记,对宣传峨眉山的秀美风光和传承峨眉山的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全面记载峨眉山历史文化的“山志”,更是不可多得。第三,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潮带动了民间佛寺旅游的热潮。“风俗之变,自贤者始”。*(明)顾华玉:《息园存稿文》,卷1,《关西纪行诗序》。精英文人的一言一行,成为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一种效仿模式,进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形成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从晚明旅游消费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中,Arjun Appadurai教授认为晚明社会已进入“风尚体系(fashion system)”亦即社会流动已非停滞,或是消费上也不再有许多限制以保障少数人的身份地位,而是下层社会愈来愈多人有能力模仿上层社会的消费,而且消费物品的创新与品味更新的速度也愈来愈快[19]。
(二)清雅的文化性
在文人选择佛寺旅游中,多数文人并非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参与,而是以寻古寺、访名僧,与之参禅问道为荣,为时尚,侧重士僧文化交流,是一种社会精英意识的标榜,并非真正参与宗教迷信活动。正如张岱在他写去普陀参访的文章中确切地表达了他和那些与他一起摆渡“村中夫妇”的不同。正如卜正民先生考证张岱与佛教关系一样:“张岱与佛教的关系就像晚明士绅中大多数有这方面兴趣的人一样:是一个不断去参访佛教圣地的人,浸润佛教文化,能轻易地引证佛经,去世之后喜欢用佛教礼仪而不用儒家礼仪祭祀。他关心僧伽之都的健全,积极地捐助和支持佛教的道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佛教道场是士绅精英生活的文化环境。但他的母亲所拥有的那类虔诚、无休止地念诵一部佛经,似乎没有激发张岱的兴趣。他多方面参与佛教的世界并不需要信仰佛教作他的一种宗教世界观。”[18]52
且文人雅士参与寺庙旅游活动时,多主张避开民间“哄游”,独自寻幽。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在游武当山时,就曾对同行的僧人说:
游,他山人迹不接,从本路出入,稍曲折,即幻矣。此山有级有锁有絙,一待天下人,如人门前路。天下人咸来此,如省所亲,足足相蹑,目目相因。请与师更其足目,以幻吾心[20]。
这是一种不同于“天下人”的游趣。而这种趣味的特点,就是追求山本身所带的幻象,需要避开“天下人”游踪独自探幽。游记写作名家李流芳在《游虎丘小记》一文中记载到: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予初十日到郡,连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风亭月榭间,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亦复不恶。然终不若山空人静,独往会心*(明)李流芳:《檀园集》,《游虎丘小记》。。
李氏甚至嗤之以鼻喧闹的市井游乐场景,觉其“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诗人只有在夜半无人之际前往游览,方 “见虎丘本色耳”。同样地李流芳在《江南卧游册题词·虎丘》中也表达此观点,认为世人喧哗之游是“秽杂不可近”,应“掩鼻而去”*(明)李流芳:《檀园集》,《江南卧游册题词·虎丘》。。
总而言之,晚明文人朝山习俗多或欣赏优美的自然风景和深厚的寺庙文化底蕴;或为追寻历史名人足迹;或因社会考察之效;或登名山拜名士而登临寺庙,他们较少参与宗教活动,宗教色彩及其信奉程度较为淡薄,明显区别于民众虔诚而功利的朝山活动,正如谢肇淛评论泰山民众朝山进香的原因是:
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交相愿而神亦靡诚弗应的无所不能的神灵了*葛延英:《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12。。
(三)世俗的娱乐性
寺庙本是个清静之所,但晚明文人的恣情纵意,使得有些时候寺庙也成为一个热闹的娱乐场所。如崇祯二年(1629)中秋节,张岱曾带家中戏班到充州为父亲祝寿,当晚泊船在金山寺,半夜时分突然戏瘾大发,竟在肃穆寂静的寺院中张灯结彩,让家优在大殿上演出剧目《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寺内的和尚被喧天的锣鼓惊醒,各自揉着惺忪的睡眼起床观看。待戏唱完时,天已破晓,和尚们尚出于晕昏阶段,分不清到底是梦是真?竟纷纷猜测他们是人是鬼?
在寺院娱乐者不只张岱一人,而是晚明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如邹迪光在游吴门诸山时雇了11人扛轿者,其中7人为邹氏及其友人服务,4人服务童子,因为“诸童善歌,不欲以筋力败咽喉,故于诸酒肴二担,衾被三担,从者四五人,循松萝而进。”*(明)邹迪光:《郁仪楼集》,卷36,《游吴门诸山记》。而带上歌童的主要入任务就是为了在登山访寺的时候愉悦主人。晚明情欲释放的开放时代,携妓上路也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如谭元春在《再游乌龙潭记》一文中对“姬”的描述,其云:
下雨霏霏湿幔,独无上岸之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盖立幔中,湿透衣表。风雨一时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罗袜无所惜。客乃移席新轩,坐未定,雨飞自林端,盘旋不去,声落水上,不尽入潭,而如与潭击。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处……忽一姬昏黑来赴,始知苍茫历乱,已尽为潭所有,亦或即为潭所生。而问之女郎来路,曰不尽然,不亦异乎。*(明)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11,《再游乌龙潭记》。
明代江南地区称妇女为“姬”*(明)钱希言:《戏瑕》,卷1,《称姬》。,但是在游记中陪客人旅游的“姬”应该是妓女或优人。
与僧侣的交往本该是一件严肃之事,可在袁中郎眼中却以男女之事来笑僧,也体现文人佛寺旅游过程中的娱乐因素。袁中郎在《灵岩》一文中戏谑一僧人:
登琴台,见太湖诸山,如百千螺髻,出没银涛中,亦区内绝景。山上旧有响展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冲咫至,声若飞涛。余笑谓僧曰:‘此美人环辔之声,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谓。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排徊色动。碧臆钩,宛然石灰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稍心死?色之于人甚失哉!
不仅文人在参与佛寺旅游活动中带有娱乐性质,寺院也相应增加娱乐项目供文人游乐。如袁小修在《西山记》之四一文中记载碧云寺的金鱼:
朱鱼万尾,匝池红酣,烁人目晴。日射清流,写影漂底清慧可怜。或投饼于左,群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声。然其跳达刺泼,游戏水上者,皆数寸鱼。
惟妙惟肖的金鱼呼之欲出,其色红酣,灼人眼目,而见饼赴食之动态尤为生动,可谓妙趣横生。而由小鱼跳达、大鱼沉潜联想到人的老少静躁,哲理丰富。袁伯修在《上方山》之二一文中也记载寺庙种花植竹来吸引文人:
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三百余级,始登毗卢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皆精绝,杆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时牡丹花正开,院院红馥,沾熏游据。寺僧争设供,山肴野蔬,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独不解饮茶,点黄茶芽代,气韵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王则之、黄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山林寺庙中尚有如此热闹的娱乐因子,更何况于城镇式庙宇的庙会节庆活动。江南城乡缙绅士庶多崇信各寺观、宫观及神庙神灵,善男信女终年不断。迨至各教纪念日(庙会),朝山进香游者更是络绎不绝。
(四)科学的考察新风
晚明社会历经心学、禅学和狂禅的思潮激荡,文人转而注重心的舒张、情的释放,掀起一股文人于放纵中寻求感性自适的风潮,相应地表现在文人宗教旅游的恣情享乐中。而随着晚明佛教禅净双修与东林党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晚明文人逐渐由心的感性自适风潮转向实学思潮和理性自适,表现在山水领域则为“因人而景”山水审美观向“因景而人”的转变,尤以晚明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以身许山水的科学考察观为代表。如其游记中不仅以客观叙述手法真实记载山水、佛寺等景观原貌,还科学考察了山水的来源去脉,而非将个人情感凌驾于山水之上。
晚明科学考察山水风潮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现象,更是一种群体、社会现象,晚明涌现出一批以科学考察著称,在旅游实践活动中成就的学识著作。如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的王士性在从政路上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及《玉岘集》等。实学家顾炎武足迹半天下,所撰《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和谢肇淛的《北河经》、《五杂姐》等,进一步将文人山水科学考察观推向新的发展高峰。
四、结论
晚明社会,文人大规模、大范围的佛寺旅游活动呈现其文化性、娱乐性和科学性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文人宗教旅游风潮兴盛的本质是晚明文人在“报国无门“政治情境下,失意心境的无奈寄托;是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主动融入佛寺旅游休闲娱乐生活的表现;也是晚明佛教龙象复兴之后,士僧交往社会新风的体现。
总的而言,晚明文人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被动和主观双因素拉动下走入佛寺。佛寺也因其特有的景观特色和中立立场主动地融入文人生活之中,文人与佛寺及僧人互动密切。
同样地,今天的佛寺在大众旅游休闲时代和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卷入商品经济开发浪潮,我们应该以平和心态看待佛寺参与经济开发,不可一味苛责佛寺应保留其不食人间烟火的“山林性”,亦不可对其市场性开发一味地非议或否定,应该坚持二元评价方法。既要看到佛寺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发展趋势,看到佛寺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功能的发挥;也要注意佛寺特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传承、创新与保护。同时,在旅游利用和开发中,应该借鉴晚明文人佛寺旅游的文化性与娱乐性特征,挖掘区域人文与寺庙文化底蕴,综合设计相关文化产品,提高游客寺庙旅游宗教文化与休闲娱乐的深层体验,塑造差异化、人文化的佛寺旅游品牌。
[参考文献]
[1] 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3-76.
[2] 滕新才.明代中后期旅游文化论[J].旅游学刊,2001,(6).
[3] 陈建勤.风尚、环境、文士——明清江南游风炽盛原因[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4] 魏向东,李蓓.晚明文人旅游行为特征之文献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6).
[5] 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5.
[6] 于希贤,沙露茵选注.云南古代游记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20.
[7]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6[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85.
[8] 王思任.游摄山记[M]//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78-79.
[9]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3[M]//坷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76.
[10]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36.
[11]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96:17.
[12] 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第五章第一节《寺庙旅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 陈垣.士大夫之禅悦及出家第十[M]//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34.
[14]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348.
[15]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6[M]//坷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34.
[16] (明释)莲池大师.竹窗随笔[M].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106.
[17] (明释)益大师.益全集[M].台北佛教书局,1989:1098.
[18]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0.
[19]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25.
[20] 谭元春.谭元春集:卷20[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546.
(责任编辑:闫卫平)
A Study on Literati Buddhist Temples Tourism in Late Ming Dynasty
CHEN Hui-li
(School of Tour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Literati Buddhist Temples Tourism was booming in Late Ming Dynasty. This thesis gave an explanation to the type, historical reason and nature of Literati Buddhist Temples Tourism in Lat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realiz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i Buddhist Temples Tourism in Late Ming Dynasty was a spread ethos of Decadent Sentiments in Late Ming Dynasty due to Crisis Politics, implie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Buddhism cultural development as well.
Key words: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i Buddhist Temples Tourism; Booming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5)02-0065-09
[作者简介]陈晖莉(1980-),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致力于闽台区域宗教旅游文化和明清旅游史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GL110),福建省社科项目(2013C021),福建省教育厅项目(JA10121S,JB13052S),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青年旅游学家扶苗支持计划。
[收稿日期]2014-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