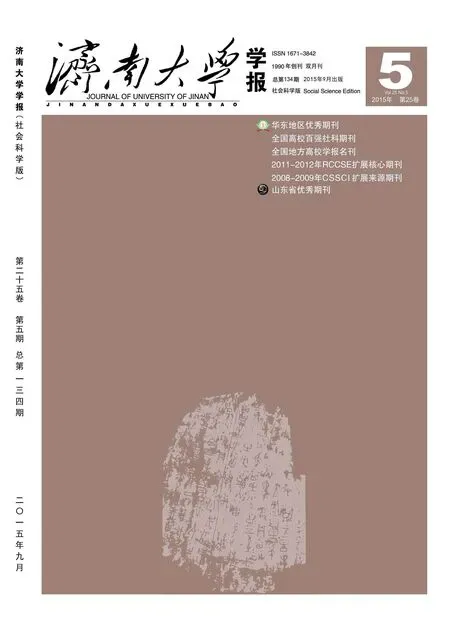鸳鸯蝴蝶派的编辑策略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
2015-04-15鲁毅
鲁 毅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一、缘起:清末民初女性小说研究中的问题
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文学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现代性成为前进的方向与目标,其中女性小说家成规模的涌现便是重要的表征之一。她们的涌现,首先,是在晚清改良主义思潮下,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废缠足,兴女学”的女性解放运动,使其突破了宫闱罗帐,获得了广泛的知识阅读面,开始了表达自我的漫长旅程。其次,近现代传媒业与文学消费市场的迅猛发展,让这些女性“智识者”有了言说自身的媒介与场域,传播的进程得以实现并延伸,她们渐为大众认识并接受,最终在清末民初呈现为“前五四”时代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学现象。
对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的介绍与研究,已出现了相关的硕士论文(沈燕《20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作家研究》)、博士论文(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以及郭延礼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女性文学转型期(1900—1919)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史意义研究”,他们对近代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文学史地位做了探讨,认为“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女性作家开阔的视野和新的价值观,……开创了女性文学的新时代”[1]。具体而言,则指涉内容方面的题材扩大、关注民间疾苦、描写爱情婚姻悲剧、关注底层女性命运等,以及艺术层面上的小说体制、叙事模式变革等。但这种表述是否存在着遮蔽呢?实际上,与同期鸳蝴派①男性作家的创作相比,这些方面并非独特,只可看作是男性文本的扩张与延伸,那么女性写作之所以为“女性”的基点何在?从这一维度出发,又应当做怎样的价值重估呢?
本人认为,还应当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及性别话语研究层面观照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也诚如郭延礼先生所言:“我这篇文章只是初步勾勒了20世纪初女性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至于对这一时段女性小说从思想意蕴到艺术变革的论述,……只有留待研究女性文学的专家了。”[1]以这种思路与相关的研究方法审视她们,会发现,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的涌现并非简单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呈现,其历史细节处,更有着诸多外在因素的推动,其间执掌印刷文化资本的鸳蝴派对这一群体的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对清末民初鸳蝴派报刊编辑策略的考察提供了切入同期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的独特视角。那么在由编辑、作家、读者构建的“现代”文学场域中,编辑是如何塑形并规约女性小说家生成的?女性小说家又是如何在由印刷资本象征的男权话语主导下言说的?其间女性小说家有无逸出规约之外的现代女性话语及叙事模式?以此最终探讨本时期女性小说家的创作在近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整体链条中应当占据怎样的位置。
二、想象女性:被“包装”的女性小说家及其创作
纵观清末民初的印刷媒体,尤其是上海的文艺报刊,鸳蝴派涉足其中甚重,并充当着主编、主笔、发行人、撰稿人等多重身份,可以说鸳蝴派及其创作在民初的繁荣是与近代报刊业的发达及其报人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晚清少数文人的办报实践,民初鸳蝴派报人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并促使众多文艺刊物及报纸副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尤其在赢得受众方面,为后世的文学实践提供了诸多借鉴。然而这种经验并非天然习得,他们多出于生计考虑,作为江浙籍移民涌入“十里洋场”并加入这一行业,在初来乍到时,需要转变的第一重思维,即缓释报人与文人之间的身份“误差”。版权之争似乎成为他们的梦魇,如徐枕亚曾义愤填膺地登报启事:“《玉梨魂》登载该报,纯属义务,未尝卖于该报,有关系之个人完全版权,应归著作人所有,毫无疑义,嗣假陈马两君出版两年,以还行销达两万以上,鄙人未沾利益,至前日始有收回版权之议,几费唇舌,才就解决,一方面交涉甫了,一方面翻印又来,视耽欲逐,竟欲饮尽鄙人之心血而甘心”[2],而众多作家在文末标记的“不受酬”则遮羞了“卖文为生”的职业尴尬。其转变的第二重思维,即认识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当他们娴熟地设计着报刊上的文艺栏目,百感交集地阐发着刊物的文化定位时,表明他们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其所掌控的印刷文化资本,并将其作为一个文化产业进行经营,形成了“作者—编辑—文本(小说)—媒介(报刊)—读者”这样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条。在以往的研究中,讯息传播过程中的“编辑”一环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他在其中充当了制定规则、协调秩序、“把关人”的角色,这对于作家的文学道路乃至成名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恽铁樵之于张恨水,包天笑之于周瘦鹃等,不胜枚举。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的涌现显然经过了鸳蝴派编辑的“把关”,并且在她们的艺术水准之外,还覆盖了一层浓郁的“包装”痕迹,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影像推介,即鸳蝴派编辑创意性地将诸多女性小说家的影像刊载在报刊的插画中,图文并茂地向大众进行传播,如《女子世界》(第1期)与《游戏杂志》(第4期)中的温倩华;《女子世界》(第3期)、《小说丛报》(第10期)、《香艳杂志》(第4期)中的吕韵清;《女子世界》(第2期)中的汪咏霞;《妇女杂志》(3卷9号)、《香艳杂志》(第10期)、《中华妇女界》(1卷10期)、《小说丛报》(第10期)中的徐张蕙如;《女子世界》(第1期)中的陈翠娜;《香艳杂志》(第8期)、《女子世界》(第4期)、《中华妇女界》(2卷6期)中的吴忏情;《小说丛报》(第18期)中的姚琴媜;《小说丛报》(第19期)中的朱畹九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推介这些女性小说家的影像呢?
首先,这契合了晚清以来盛行的女性解放思潮。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自强”成为整个社会认同的核心语汇[3](P534),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便是“启蒙”,于是“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被发现”了,并整合进思想启蒙与民族国家认同的时代主旋律中,但深隐其中的是象征着社会支配者的男权话语对女性的俯视与规约。一旦女性被启蒙,便获得了进入男性立法的社会秩序,不但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可以启蒙大众,如小说中的黄绣球(《黄绣球》),在通晓世界大义后,便四处发表演说,在现实中,也如《妇女杂志》中借助“公共空间”发表言论的女校学生。这便是男权社会的“立法”,从开始就预设了理想女性的成长之路。而鸳蝴派报刊上的女性作家影像即在晚清以来的启蒙主潮下,作为被立法与被规约的社会范型推出的,她们为大众,特别是“被启蒙”的女性受众做了标榜。
其次,在社会启蒙思潮之外,还隐含着时尚文化的诉求。在清末民初鸳蝴派编辑的刊物封面及插画中,女性影像占有极大的比重,却呈现为两种极端:一类是女作家或文艺家的影像,以《小说丛报》等为代表;一类是妓女的影像,以《小说新报》等为代表。研究者往往将其误读为鸳蝴派内部的张力,即主编徐枕亚与李定夷编辑理念的差异,但实际上,报刊中所传播的妓女影像并非新文艺家所诟病的媚俗文化,而是与女性作家的影像一道并置为“新型都市女性的样板”[4](P87),成为清末民初社会文化潮流中的时尚因素,既“为现代人提供了整合与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5](P256),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建构着自身的“鸳蝴气息”及其社会角色,使其成为“洋场”中一个具有身份识别性的文学(文化)流派。
再次,名家效应的营造。处在现代市场语境中的鸳蝴派编辑已充分意识到名家之于媒介生存的重要意义,而与名家约名稿又并非易事,于是女性作家再一次被观照,她们需要被“包装”成名家,以扩大其所附属媒介的文化资本,这与“五四”时期《晨报》副刊之于冰心的“包装”如出一辙。于是在鸳蝴派的编辑策略下,女性小说家逐渐浮出水面,并获得了轰动效应,从反复被提及的顾明道曾化名为“梅倩女史”为《眉语》撰稿的经历便可见一斑:“不料登徒子某,竟认梅倩为扫眉才子,写信以通情慷,明道用女子口吻致复,直使某大大的风魔,遥向梅倩求婚。”[6](P280)
那么鸳蝴派编辑为女性小说家塑造了怎样的媒介形象呢?在横、纵向维度上,他们对女性作家的影像范型做了提升。晚清“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对大众女性的期待仅仅是能对小说“手之口之”[7](P37)即可。清末民初流行的“贤妻良母”主义则强调“家庭教育,为我女界唯一之天职”[8],在承认男性主导的前提下,将女性的角色设定为“贤内助”,这仍是在践行传统儒教中男性、文学、政治权利所属公共领域,女性、生育、劳务所属家庭领域的规范。而鸳蝴派编辑对女性作家的视觉传达则提升到了精英标准,即“近日女学界中之凤毛麟角”[9],要求其对传统、现代各种文类均要涉猎。此外,从影像者的身份来看,社会名流、编辑妻友占主要分量,如瑶卿女史为吴双热夫人,曾兰为吴虞之妻,高剑华为许啸天的夫人,徐畹兰为赵苕狂母亲等。通过女性影像传达出的精英意识源自鸳蝴派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将独特的传统文化记忆添加进现代语境中,加之启蒙文化主潮,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为鸳蝴派所规约的女性范型。
其二,名家评论,即借助于报刊这个“公共空间”,主编将刊发作品的意图及对作品的阐释附识于文末或为序向读者进行推介。清末民初鸳蝴派报刊的编辑理念直接决定着文人作家、投稿者的准入,如《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在执掌该报之际,主张以高雅的古文入小说,因此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得以编发,为了突显作品的价值和编辑的良苦用心,恽铁樵还以其名家身份在文后附志:“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辞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10],以增加作品的分量,扩大小说的受众影响。这一编辑策略也出现于女性小说的编发中,如幻影女士在《礼拜六》上共发表12篇小说,其中主编王钝根就写了3篇评语。从鸳蝴派编辑所作的附识或序的内容来看,重点突出的是:
第一,女性作者形象的文学描绘,如“黄翠凝女士者,余友毅汉之母夫人也。余之识夫人在十年前,苦志抚孤,以卖文自给”[11],“遭逢拂逆而不自失望,牺牲富贵而服事贫贱,惟基督徒能之,幻影女士当是基督徒”[12],在此之余,编辑还加入自身的阅读体验:“(黄翠凝)善作家庭小说,情文并茂。今自粤邮我《离雏记》一篇,不及卒读,泪浪浪下矣”,“敬告世之有母之儿,当知无母之惨凄,有若此者”[12],从而为女性作家建立起影像之外更加鲜明的媒介形象。
第二,作品的现实意义。“劝世”与“救世”是鸳蝴派作品及其发刊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尽管就其实际创作、办刊方针及编辑理念来看,作为转型时期的文人,他们游走于“寿世”与“售世”之间,甚至倒向了后者,但是晚清以来的救亡主潮、“新小说”的启蒙范式、民初的“共和”语境,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他们时时提及文学的社会功用,因此女性小说家作品中的“劝世”题旨与话语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即“有功世道之文”[12]。他们不但自己按照这样的理念解读女性作家的作品,还导引着读者的思路:“作者意存劝世,不仅为游戏小说而已。”[13]甚至对诸多女性小说的评论存在过度阐释的倾向,乃至抬升到教科书的高度。他们期待通过这样的“包装”手段,女性文本的价值功用可以发挥到极致:“深望女士此文,普及中华妇女界,渐知济人为天职,失意者竭其力,得意者助以资,使震旦前途,不致为怨雾所阻塞,国家进步之曙光,庶几可睹矣。”[12]
总之,无论是通过视觉文化传达的影像推介,还是由传统文学中的私人评点模式转变而来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名家评论,鸳蝴派编辑按照自身的构想“剪辑”着待传播的女性小说家形象,规范、约束着女性小说的大众传播轨道,最终为读者“包装”出了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的群像。那么女性小说家在这种由印刷资本象征的男性话语场中又是如何言说自身的呢?
三、女性想象:男性话语的文本实践及“越轨”书写
如前文所言,诸多鸳蝴派作家兼具报人及编辑身份,因此其小说的创作范式与美学样态基本上可以囊括进鸳蝴派刊发作品的编辑理念与策略中。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的实际创作来看,在整体上可以认为是这种编辑策略与理念的话语实践,具体表现为:
第一,言情模式的承袭。鸳蝴派以言情小说闻名,并揭起了民初哀感顽艳的唯情主义小说浪潮,其模式大致可概括为“开篇之始,以生花笔描写艳情,令读者爱慕不忍释手,既而一波再折,转入离恨之天,或忽聚而忽散,或乍合乍离,抉其要旨,无非为婚姻不自由,发挥一篇文章而已”[14]。这种模式在同期女性小说中也被娴熟地运用起来,如《一声去也》(许毓华)中侬与陆郎的爱情止步于“父母之命”,《我之新年》(吕韵清)中的琴姑与芹哥、《他生未卜此生休》(谢幼韫)中的婉仙与陆生,其婚恋悲剧皆受阻于小人、恶绅、强盗等鸳蝴派小说人物原型;以及由这种模式延展出的女子受难模式,如《萧郎》(柳佩瑜)中的吴纫秋在旧式婚姻中的隐忍与牺牲,《声声泪》(幻影女士)中孤儿寡母的殒命与美好人伦关系的毁灭等。种种叙事连同频繁出现的疾病、哭泣、死亡等病态意象[15],使女性小说文本沿袭着男性话语,并生成了一股浓重的悲凉、阴郁之气,甚至延展至历史、域外等类型的小说中。然而这种叙事氛围在鸳蝴派的大本营《民权素》及其刊载的小说中却早已做了“立法”:“昙花一现,泡影幻成,徒留兹《民权素》一编,以供世之伤心人凭吊。”[16]总之,清末民初的大部分女性小说仍旧囿于鸳蝴派的言情模式和叙事氛围,缺少新的悲情模式的开拓,以至束缚了女性意识的独立表达,她们尚不能建构女性自身的精神属地,这有待新的文学、文化质素的出现为其提供契机。
第二,民族国家叙事话语的延续。鸳蝴派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国族叙事话语可以追溯到晚清“新小说”,其内容不仅包含反复出现的国族独立话语:“哀我支那,生乃与犹太为伍,不知这部书出来,能够千年睡狮一旦梦醒否?”[17](P117)社会现实批判话语:“广州城里没清官,上要金钱下要钱,有钱就可无王法,海底沉埋九命冤。”[18](P417)还包括社会诸方面革新、开智识的启蒙话语等。尽管这种话语的架构因民初“共和”语境的出现发生了新变,除了添加革命叙事及其悼亡话语外,其基本内涵大体一致。同期诸多女性小说文本将这种具有启蒙特色的国族叙事话语片段式地添加进来,如小说《债台物语》开篇即大发感慨:“新年消遣,何事不可?必要拿钱混赌,有何趣味?况且民生穷蹙,国势愈危,从前我国虽弱,各国为了均势,还戴上这维持东亚和平的假面,现因欧战一开,日本趁各国不暇东顾,就作种种无理要求,允他呢,便是朝鲜之绩,不允呢,又有许多为难,危机一发,我们百姓多有责任的,岂可装没事人一般,推在政府身上?”[13]《郎欤盗欤》中的盗贼鲸刚将自己的“盗”义阐释为:“诚愤于世界之不平等,公理人道,日就湮没,奸诈者出其金钱势力以欺虐忠厚,犹文过饰非,以上流君子自居,须知世界愈繁华,强权愈发达,而人心愈凶恶。”[19]其他还如对都会中金钱异化人心、道德堕落等的批判话语俯拾即是,甚至她们还塑造了诸多恶女人、新式女学生等形象去诠释这种思想。需要注意,晚清以来的国族叙事话语具有强烈的性别统合色彩,亦或说渗透着一种“雄化”修辞策略,转化为文学形象即如《女娲石》中的金瑶瑟、《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夏震欧等性别缺失的“英雌”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微弱的女性意识及女性形象的生长构成了消解。
尽管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的创作在整体上可以看作鸳蝴派男性话语的文本实践,但如《德国诗集》等个别文本已鲜明地呈现出对这种话语实践的“越轨”,逸出了鸳蝴派编辑所设定的潜在叙事范本,这种“越轨”主要表现为女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有了全新的突破:
第一,女性形象的嬗变。清末民初鸳蝴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想象为具有坚忍品格、恪守传统道德的女性,亦或贤妻良母,以表达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与对本土文化的坚守,同期诸多女性小说文本实践了这一话语范型,如《声声泪》中的孀妇“明大义,抚孤守节,藉十指支兹残局,且甚贤惠”[20]等。而《德国诗集》中的主人公婉姑与这些女性形象相比,尽管从属于同一时空,但更像是现代与古典的分野,西方学识成为她们人生际遇中的判断依据,或者说更强调现代知识构成对形象建构、叙事所起的作用,如婉姑“主张不嫁,靠着学问之力,却是能够独立生活”[21],还有主人公反复提及的莱奈乌氏的诗透出的悲戚:“欢乐难持久,相亲仅一时”所给予人生的隐喻等。此外,婉姑形象的呈现不再依托于男性叙事所惯常的受难、成长模式,及其规约的“孝女”“节女”“贤妻”“良母”等角色,而是将叙事时空更多地让位于女性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两性思考与内心冲突,这种叙事新秩序提供了女性表达自身的依据。
此外,个别小说所提供的另类女性形象也对鸳蝴派男性话语模式构成了消解,如幻影女士在小说《回头是岸》中提供了中国文学中较少见到的女基督徒形象,她将男性作家笔下理想女性所固守的传统道德置换为异域宗教思想,于是小说模式开始逸出大众轨道,即不再重复小人离乱、婚恋不自由的悲剧,转为张扬博爱主义的宗教叙事,而由小说中女士珍藏的剪报:“星期六日下午二时半,天文家某君,与某女士结婚于圣约翰礼拜堂”[12]透出的象征着男性话语的言情因子却已是“前尘如梦”,退出了主体叙事之外,这也是作者叙事的自觉:“惟近观小说,凡失意者,皆以一死自了,绝不念父母邦家,诚恐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也,不忖谫陋而作是篇。”幻影的另一部小说《坟场谈话录》可看作这种突破的前奏,尽管还是鸳蝴派的模式,但作为主人公知识构成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资源,不仅使小说的叙事消解在了情节的演进上,更进一步建构起了宗教恶魔形象“撒旦”,将一切无常与美的消逝归结为“撒旦所拨弄者也”[22],并誓言“吾愿借天帝伟力,灭绝撒旦,勿令芸芸众生,为其颠倒也”。这种“反抗绝望”的抗争话语在清末民初女性小说中实属难能可贵,彰显出女性形象的突破所带来的女性意识的萌芽与觉醒。
第二,女性主体意识的突显。在清末民初鸳蝴派及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中,女性形象往往特别突出,但并不代表女性主体地位及主体意识的浮现。从话语修辞角度讲,在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女性在两性对照的修辞中是被动和从属的,她们在恋爱中压抑自己的情感,在旧式婚姻制度中牺牲自己的幸福,在家庭生活中隐忍着苦难。此外,男性与女性作家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存在着一种“被看”“被欣赏”“把玩”的视角,甚至是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即“女性的身体或特征常被刻意地与物件(甚至动物)相提并论,共同展示,也有以物隐喻女性特质,从而达到将女性降为‘玩物’和‘性尤物’(sex object)的目的”[23](P97),如《玉梨魂》开篇,梨花之于主人公白梨影、辛夷之于小姑筠倩的象征,再如《坟场谈话录》中对谢韵薇的描述:“二九年华,荣花始茂,岂意兰方挺秀,横被霜摧,月正腾辉,遽遭云掩也。”[22]而在《德国诗集》中,这种“被看”的潜在写作已然消失,置换为女性怎样“看”男性,怎样主动地运用智慧与学识,理性地观察世界,看待两性关系,深刻地思考着由婚姻危机带来的焦虑:
丈夫虽向我忏悔,向我谢罪,我听了这一番话,心中究竟舒服不舒服,我丈夫竟忘了家中有妻有女咧,想到这种地方,却是心中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再想他是个大文学家,无论遇见的是怎样的美人,是怎样的薄命女子,他竟把心移到一个乡间旅店中的一个女子身上去,未免太觉浅陋了,我胸中不禁热如烈火,又想到那少女在春雨连绵之日,离乡背井,连安慰她的人也没有一个,我又悲伤不堪。[21]
这种叙事“越轨”的发生,究其原因,一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中女性知识谱系的更替;二是小说叙事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全知叙事转换为第一人称主观叙事,这不包括设置超叙事层的第一人称叙事,即“我”听某人讲述主人公的故事,《德国诗集》采用的则是“我”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事新秩序不仅使小说由情结模式过渡为情绪模式,也为女性言说自身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三是叙事空间的转换,在鸳蝴派内部由古典言情向日常家庭生活书写的开拓中,女性作家逐渐摆脱了固有的言情模式及人物原型的负累,在琐碎的生活中不断开掘着女性的角色定位及人生意义。尽管清末民初女性小说中的“越轨”书写数量不多,却已经彰显,它所指向的是与“五四”同声部的“人”的发现,是一种现代性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与借助于西方文化资源生长的“五四”女性小说不同,它的根基却是以本土资源为给养的鸳蝴派小说,正是在对它的模仿与超越中将近代女性小说涌向了现代门槛。
四、结语
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晚清以来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潮,鸳蝴派男性作家所掌控的文化资本及其创作,乃至“五四”女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等都在不断地将她们消解。此外,她们还面临着另一重困境,即小说《灯前琐语》中的姐妹对话所隐喻的:姐姐倡导的是贤妻良母主义:“予念不为人妇则已,即为人妇,即当尽妇职,不敢为一己之学问,放弃家庭之责任也。”[24]妹妹则致力于振国兴邦的社会改革:“我国家庭,以贵族豪富之家为最纷乱,所谓家长主妇者,每以赌博为消遣,子女髫龄,即染恶习……哀哉中国!家庭如是,尚何望乎振兴也?”但最终妹妹的社会理想不仅为姐姐的训导所消解:“我国家庭,大抵如是,求其雍雍睦睦者,百不得一,长姊处境虽拂逆,然无负于人,无忝于职,问心无愧,自有真乐,且儿已长成,苦尽甘来之日不远矣。”同时鉴于友人读书为妾的经历走向了幻灭。在这里,女性分明已经意识到主体的存在,却梦醒了无路可走,转型时期的社会尚不能提供给她们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思考,更遑论将这种体验转换为文学形象。
尽管如此,近代女性小说家群体的创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仅是作为被发现的史料,亦或填补了古代女性叙事文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越轨”书写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不可缺失的关键一环,即本土资源的现代性开掘,它提供了“五四”范式不可能有的一种路径。
[1]郭延礼.20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家群体论[J].中山大学学报,2011,(2).
[2]徐枕亚.枕亚启事[J].小说丛报,1916,(18).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M].杨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
[5]刘传霞.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秋翁.二十年前之期刊[G]//芮和师,范伯群.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7]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撷华女士.家庭教育简谈[J].妇女杂志,1915,(3).
[9]名画家包胡振玉女士之影[J].小说丛报,1914,(6).
[10]周逴.怀旧[J].小说月报,1913,(4).
[11]黄翠凝.离雏记[J].小说画报,1917,(7).
[12]幻影女士.回头是岸[J].礼拜六,1915,(48).
[13]韵清女史.债台物语[N].申报,1915-02-17.
[14]蒋箸超.白骨散[J].民权素,1914,(1).
[15]鲁毅.民初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背后的潜流与漩涡[J].东岳论丛,2014,(11).
[16]沈东讷.序三[J].民权素,1914,(1).
[17]犹太移民万古恨.自由结婚[M]//章培恒.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18]吴趼人.九命奇冤[M]//章培恒.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19]姚淑孟.郎欤盗欤[J].眉语,1915,(3).
[20]幻影女士.声声泪[J].礼拜六,1914,(22).
[21]徐赋灵.德国诗集[J].小说画报,1918,(16).
[22]幻影女士.坟场谈话录[J].礼拜六,1914,(19).
[23]陈顺馨.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M]//陈慧芬,马元曦.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4]幻影女士.灯前琐语[J].礼拜六,191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