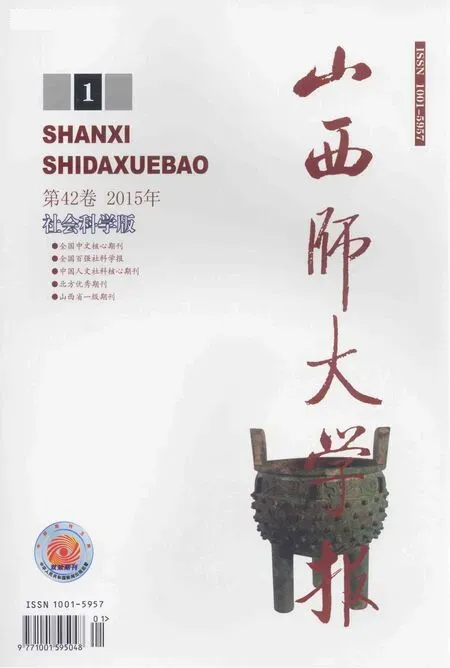陈叔宝与江总诗歌比较
2015-04-10张慧玲
张慧玲
有学者认为,陈代诗歌在梁代宫体诗的影响之下发展,终不出宫体诗的樊篱,其本质是以华艳之诗游戏人生,诗风多偏尚“淫丽”、“绮艳”。陈叔宝(陈后主)和江总作为陈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更是陈叔宝文学集团的领导人物,诗文风格自然趋于一致,故而在对这两人各自的诗歌研究中,常有论者将两人相提并论。但这二人的诗歌在哪些方面一脉相承,又是否真的同出一辙、无甚差异呢?本文试从两方面来对二人诗歌做一比较。
一、诗歌主张
陈后主酷爱诗酒,友善文士,独特的政治地位,自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这个诗人群体的诗歌主张总体倾向于追求诗歌表现的细微精妙,以吟诗作颂作为把玩生活享乐的手段。虽然陈后主宴饮时多有“言志递为乐”的诗句,但他所言之志,不再是传统的“诗言志”,要求诗人肩负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之志,而是一味表现如何把玩生活之美、把玩情趣之美。这一点在陈叔宝和江总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而江总曾在陈叔宝东宫太子期间担任太子詹事,又时常与后主共同参与文学诗歌活动,再加上他温和的性格和举世无双的文采深得后主喜爱,所以其文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主。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江总的诗歌主张。
江总由梁入陈,年少之时正值新变派风靡,他本人出身南朝氏族,从小就因文名而受到梁武帝赏识,因此他接受新变派的文学思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但如此江总在新变派文学思想的基础之上走的更远。总的来说,江总的诗歌主张包括:
“诗歌创作要以‘美’为中心,表现‘美’、抒发‘美’的感受,注重诗歌形式美,语言、句式、词章均要突出美感,诗歌要流畅、音韵要和谐。”
陈叔宝在写给江总的《与江总书悼陆瑜》这一信件中明白表露了对这一诗歌主张的应和:
“吾监抚之暇,事隙之辰,颇用谈笑娱情,琴樽间作,雅篇艳什,迭互锋起。”
此文是陈后主为了悼念陆瑜而写给江总的信件,本是表达了对陆瑜去世的悲恸和怀念,却也在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陈叔宝对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可以看成是对江总文学主张的细化和深入。这种诗歌主张所强调的是对美好事物的瞬间感受,极尽品味之能事,是对“诗言志”这种诗歌主张的背离;最后,重视外在形式,所谓“连情发藻,且代琢磨”。要精心选择辞藻,斟字酌句,最后形成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陈叔宝与江总笔下的景物多围绕着游玩和宫廷内外展开,对美景的欣赏本质上与对女性的欣赏如出一辙,几乎都是在深入挖掘那些美丽的事物带给人们的感官愉悦,大多文人学者因此而指责他们恣纵情意、荒废朝政,指责他们在文酒与政治之间错误取舍。但撇开政治不谈,他们的这种诗歌主张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附带在文学上的政教道德枷锁,使得诗文得以回归本质,尤其是陈叔宝,他以自己独特的纤细触角,将生活中美丽事物的细微之处描绘给人看,以愉悦的心情品味那种美,这也可算是一种对美的珍视。
二、诗歌的内容与风格
穷研极丽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流取向,发展到梁陈更是如此,除了个别人之外,大多数诗人的个性风格都不是很鲜明突出,但他们二人毕竟是陈代文学集团的领导人物,单从诗歌本身来讲,其风格在“淫丽”之外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尤其是江总,其创作历程贯穿了梁代后期、陈代以及隋初长期发展阶段,其作品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其诗歌创作在表现群体的审美理想、时代风格的同时,还包含着一定的个性内涵。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后主以绮艳相高,极于淫荡。所存者只是绮落粉黛。”许学夷《诗源辩体》:“陈后主五言,声尽入律,语尽绮靡。”陆时雍《古诗镜》:“后主声色俱况,所存者只是绮罗粉黛精。”三人对陈叔宝诗歌的评论都指出其诗歌具有绮艳、绮靡的特点,由此可见,陈叔宝诗歌的主体风格是绮艳明丽。
明人谭献在其《复堂类集》中云:“陈之诗荡而不反矣,而江总其人也靡,其言也哀而挚。”清人陈祚明在其《采菽堂古诗选》中云:“江总持诗特有清气,校张正见大殊,其与后主酬唱诗反不多见,大抵入隋后作一往悲长。”又云:“江总持诗如梧桐秋月、金井绿荫之间,自绕凉气。”又云“情境悲切,大佳”。清王士祯在其《古诗选》中云:“总持流品,视徐未宜并论,然华实兼美,殆欲过之。”综合以上说法,我们可将江总的风格特色总结为:“华实兼美”、“自绕凉气”、“情境悲切”。
陈叔宝艳情诗歌的绮艳明丽,首先在于他“用浓艳笔调的堆砌来描摹女性及女性所处的环境”。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笔下的女性;女性所处的环境;直接以“娇”写女性之美艳。
陈叔宝宴饮诗的绮艳明丽,主要体现在其对宴会场面及其周围景物的描写上,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春天明丽景色的体现。例如《七夕宴乐修殿各赋六韵》:
玉笛的声音伴着弦乐响起,觥筹交错的宴席间,有娇媚生香的女子嵌着金花首饰坐在那里。有美酒佳肴,有佳人相伴,人生享乐的高境界也不外如是。这种豪华的宴会场面,是诗人自己的生活在诗歌中的鲜明体现。
史书记载,陈叔宝“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即位后,生活奢侈,不理朝政,日与妃嫔、文臣游宴作艳诗,因此朝政混乱,终于亡国。正是这种生活造就了陈叔宝诗歌创作的绮艳明丽。他的艳情诗和宴饮诗,大多产生于与诸妃嫔、文臣一起游宴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陈叔宝是在集体活动的氛围中创作诗歌的。在这种氛围中,很难出现一些不悦的、甚至深沉的情绪。所以这种愉悦轻松的心境就自然而然表现到了诗歌中,在他的宴饮诗和艳情诗里,诗人所表达的多是愉悦和享乐之情,在描写那些感官可以抓得住的“美”时,诗人的心态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所以诗歌描写的那些景色即使细致入微,感悟独到,却因为没有更加深厚的东西作背景,比如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感,也只能沦为仅供赏玩其明艳的廉价艺术品。
江总却不同,虽说他时常与陈叔宝共同参与一些诗歌的创作,但他毕竟是历经梁、陈、隋三代的诗人。丰富的生活阅历给了他更广阔的创作题材,也给了他除享乐之外更深刻的人生感悟。所以,即使是一些艳诗或者宴游诗,也称得上“华实兼美”。
不可否认,江总所作艳诗不在少数,更有几首艳诗与该篇一样直白袒露,所以其诗歌才被划入陈叔宝文学集团的首席代表作之中,被斥为“浮艳”。这也正是他与陈叔宝推行共同文学主张下的产物,是他们诗歌内容的接合点。
但江总艳诗创作并没有停留在单单描摹女性的外表上,他更多的艳诗写的比较干净,并以表现妇人的思念和闺怨之情为主,深入到内心,真实而生动地描写出女性深沉细腻的情感体验和悲苦哀怨的心灵世界。感情较为真挚,内容较少关注女色,更多的是表达女子的内在心理,也正是这些诗歌体现了“华实兼美”、“自绕凉气”的风格。正如某学者所言,“江总的诗歌,其侧艳中也夹杂着悲凉。”
对比陈代后期二人山水诗歌的风格可以看出,在江总山水诗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江总诗歌的“华实兼美”和“情境悲切”。他晚年曾作《咏采甘露应诏诗》,诗曰:“徒知恩礼洽,自怜名实爽”,也曾引晋陆阮自比:“以我为三公,可知天下无人矣。”
不可否认,陈叔宝的山水诗歌与他的艳诗相比,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机,让人感觉凄清与孤独,但这种凄清与江总的比起来少了悲气、凉气。不得不说,诗歌的意境与诗人自身的品性、阅历有很大关联,诗人自身视野开阔、心怀万物,所写出的诗歌才能更有张力。
且江总崇尚佛理,温和中又多了几许沉静,即使心中悲苦万分,在诗歌表现上也徐徐图之。再加上他历经侯景之乱,在年岁的累积中逐渐深谙世事,骨子里无法避免国将灭亡的深沉悲哀,所以才发出“人生复能几,夜烛非长游”的感叹。我想,这才是他诗歌“自绕凉气”的本质原因。
入隋以后,江总的诗歌创作反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脱去了南朝特有的阴柔风格,显得苍老而深沉。如《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别南海宾化侯诗》、《在陈旦解醒共哭顾舍人诗》等。
陈叔宝与江总的诗歌每被后人提及,总是批判者居多,他们的诗歌被冠上了“浮艳”、“低俗”等贬义词汇,但本文旨在还原二人的诗歌真实,通过对二人诗歌的比较,更加深入挖掘二人诗歌的特色。陈叔宝与江总沿袭宋梁诗文主张,并将其主张往更加贴近内心感受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由于二人的性格、生活阅历不同,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尽相同。陈叔宝诗歌“绮艳明丽”,时常以美景、佳人、宴乐入题,表达他对感官享乐的终极追求。这种风格与当时同属其文学集团成员的江总一脉相承,江总诗歌的主导风貌延续了陈叔宝的“绮艳”、“绮丽”风格,即“华实兼美”之“华”。入隋之后,陈叔宝虽逐渐明白世事悲凉,但由于长期养成了享乐的性情,所以他宁愿成日醉酒逃避而并不面对,致使作为亡国之君的他,少了该有的气度。他的这种逃避与江总的深沉苍凉一对比,更让人觉得齿冷。不过,这大概也正是陈叔宝诗歌被后人所批判、甚至遗忘的原因之一。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3]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A].顾廷龙,傅璇琮.续修四库全书:1591册,集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阮忠.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演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葛晓音.八代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马海英.陈代诗歌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8]杨勇.江总诗歌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钟翠红.侧艳与悲凉交织的诗歌旋律——江总诗歌研究[J].孝感学院学报,2008,(3).
[10]严绘.陈叔宝及其诗歌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1]陈世飞.江总的诗歌及其与陈代诗歌发展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2]董连祥.江总诗歌创作及其与前后诗人的比较[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9,(2).
[13]马海英.陈代诗文研究综述[J].文史知识,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