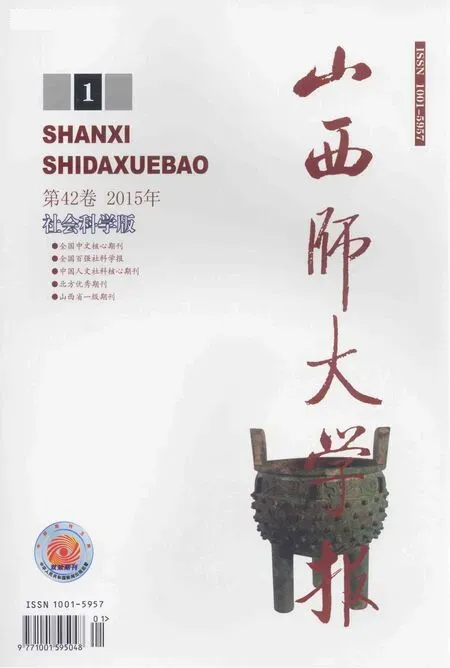“我们”如何讲述民工故事——王安忆小说《民工刘建华》再解读
2015-04-10谢燕红
谢燕红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农民进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关注这一题材,试图从哲学、文学,乃至社会的层面解读这一现象。早期的《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上演了一出农民进城的“闹剧”,但陈奂生只是城市的“过客”,城市对陈奂生而言还只是一个象征财富的符号,让他上城是为他提供一个遇到“高官”的机会,陈奂生不是“民工”。路遥笔下有知识的青年农民高加林,一心向往城市,渴望在城市立足,这是心高气傲的乡村青年试图改变命运的渴念,在当时的乡村还是少有的异类,高加林也不是民工。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批怀着对“光明”的现代之城的向往的农民,结伴而行,淹没在“进城”的滚滚洪流中,“民工”这个称谓也就有了特指。
写农民离开乡下进入城市,就涉及城乡问题,而城乡问题很容易放到一种格局中来写,即城乡对立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描写,可以是很浪漫的现代化的写法,或浪漫或谴责式的写法,均延续了中国文学中“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城市/乡村、城里人/乡下人二元对立的叙述,手法虽然成熟,却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当前的城乡关系了。王安忆短篇小说《民工刘建华》叙述的也是农民进城的故事,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写“我”家里装修,请了一个木匠,就是民工刘建华。这个故事写得很特别,在三十多来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个异类。
一、“看”与“被看”
如何站在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城里人的立场上来写民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民工刘建华》以写“我”与民工刘建华的第一次见面开篇,“我”注意到的是刘建华的眼睛:“第一次看见刘建华,我就注意到他那双眼睛,特别地亮,烁烁地看着你,看到你先转开眼睛,他才转开。”叙事者“我”(雇主)与民工刘建华(雇工)在对视中传递了微妙的权力关系。
“看”与“被看”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对视关系,谁可以看,谁只能被看,这中间蕴含着一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事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看’。它同时也是探查和控制。”[2]139当雇主与雇工在对看,谁更在意被看?显然是雇主。小说中的雇主、叙述者“我”与被雇来的民工刘建华第一次见面就在对看,“我”对刘建华的“看”很在意,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叙述者“我”是雇主,对方是被雇佣者,被雇的人盯着雇主看,主客位置颠倒了,或者说主客发生逆转了;第二,“我”是城里人,对方是乡下人,“我”是上海人,对方是外地人,一个来自外地的乡下人凭什么盯着“我”这个本地的城里人看呢?叙述者在意的正是这一“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作为城里人的“我”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当这种优越感受到挑战时,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也让“我”心里极不舒服,之后当“我”再看刘建华时,心里便异样了:“这样的眼神,使得他原本清秀的长相,变得尖刻起来。”长相“变得尖刻”是叙述者“我”心里感到不舒服的主观评价,带着主人和城里人的偏见。小说还写到刘建华老婆的长相:“他老婆小潘我们也见过,长得很俊俏。见她时,就穿了商厦发给的夹克式的蓝色工作服,长发在颈后束一把马尾。这样的朴素反使她显得自信,有了一种坦然的风度。倒是耳垂上一对成色很足、分量也很重的金耳环,流露出一些乡气。”带着金耳环就是乡气,特别是带着成色很足、分量很重的耳环就是乡下人的标志,这是叙述者“我”所代表的城里人对于乡村的成见。再加上刘建华的老婆也用那种直直的眼神来看“我”,更让“我”感到不适,小说写道:“她也有刘建华那样沉着的眼神,与你说话时,也对直了看着你的眼睛。”显然,“我”认为作为民工的刘建华和他的老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眼神来看“我”的。那么,对作为雇主、作为城里人的“我”来说,被雇佣的民工究竟该有什么样的眼神呢?我们自然联想到鲁迅笔下祥林嫂的眼睛。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家,被带到鲁四老爷跟前时,鲁四老爷见是个寡妇便很反感,但鲁四太太不顾老爷的“皱眉”,将祥林嫂留下了,因为祥林嫂“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祝福》)。因为“只是顺着眼”,就是“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因为“烁烁地看着你”,就是“尖刻”,连戴着的金首饰也显出“乡气”来。城乡对立、城里人与乡下人的权力关系,在眼神的“看”与“被看”中得以呈现。这种城乡对立不仅体现在“我”与民工刘建华的关系之中,小说还写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刘建华终于同意和我们一起去买装修材料,到了建材市场,刘建华与卖木材的福建人很快谈拢了价格,却在是否将货物送上楼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小说写道:“刘建华是江苏海门人,与上海话略有些接近,所以,他言语中就不时要露几个上海单词,显示出一种地域优势。”刘建华与福建人都是到城市打工的外地人,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个族群,一般被认为都是社会的底层,只是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在刘建华心里,自己是靠近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人,再加上自己在上海打工已经十来年了,自觉对城市很了解,所以心理上就有了几分“城里人”的优势,气势上也不觉抬高了几分,最终福建人“敌不过刘建华,败下阵来”。刘建华与福建人之间在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上,也构成一种层级关系。这种无法排除却又无处不在的意识层面的默契,无疑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
二、民工中的“人尖”:不一样的底层叙事
刘建华这样的民工在一般意义上当然属于底层的范畴,然而,王安忆笔下的“我”与刘建华的关系,突破了其他阶层与“底层”交往时的固定模式。刘建华在与福建人的交锋中,赢得了城乡对立的完胜;而“我”作为城里人在与刘建华的对抗中,却没占到什么便宜,在这样的叙事中,读者既有的城乡对立的想象被打破了,小说的底层叙事也就显出独异来。
“我”与刘建华的第一次交锋是讲价钱。“我”请来的监工老黄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工龄的上海人,老黄让刘建华报价,结果刘建华报了个天价。按照行规,或者说游戏规则,接下来应该是老黄杀半价,然后刘建华重新报一个价,双方折中,最后成交。但让人意外的是,刘建华第二次报出的还是原价。老黄自然不答应,但刘建华也很坚持,就是原价,一分不少。双方相持不下,主人出来调停,说就居中价吧,但刘建华还是不松口,最后只好依了他。这一段不容主人或监工讨价还价的价格论战,充分展示了刘建华这个农民工的精明与强势。刘建华的精明在于:他看得很清楚,主人家装修所需的工匠都请好了,独缺一个木匠;强势在于:老黄和刘建华之前并不认识,刘建华自认为手艺很好,对于主人请个不如自己的人来做监工,心里很不服气。所以“老黄向他交代如何如何做时,每一项,他都要反着来,或者,提出难题,样样事情要对着来。我们的装修工程就在这样敌对的气氛底下拉开了帷幕”。后来的一系列事情表明,刘建华不是单纯来做工的,而是来报仇的——什么都要按他的来,不按他的一套来,就撂下一句话:“要有问题我不负责!”
去买装修材料,是刘建华与老黄、与“我”的第二次较量。刘建华坚决要退掉老黄之前买好已经运来的地板。主人千请万求,刘建华才答应一起去买材料。后来主人自己还多次去买材料,可每一次只有刘建华亲自出马,福建人才同意把材料送上楼。这么精明与强势、让主人备受折磨的民工,辞退不行吗?首先看刘建华的态度,“他一直作出这样的姿态:谈得拢谈,谈不拢不谈”。一副无所谓干不干的样子。可是“看见刘建华干活的样子,不由地,你又被他感染了”。刘建华带着一帮人干活,工具齐整,技术又好,连老黄都说:“小赤佬基本功是好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听淮剧,“逢到副歌式的段落,刘建华和他的兄弟们便大声应和:哦唷喂,嗬嚯哉,咿兹唷嚯哉!他们穿着旧衣服,额头上冒着汗气,眼睛里放光,使你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骄傲”。再看他们的“吃”,不是那么马虎,还隔三差五去澡堂泡澡。刘建华他们不像一般的民工,生活不是那么受罪,而且“自尊,上进”。
刘建华不是那个去城里卖油绳、买帽子的陈奂生,更不是意气十足、心比天高的高加林,随着城市的愈益开放,农民有了光明正大的赚钱致富的机会,进城的刘建华不再是到此一游的胆怯访客。刘建华到上海已经十年了,老婆也来了,在商厦做清洁工,自认为在城市的生活比城市那些下岗工人还要好一些。事实上,他们有了更多立足的机会,甚至在这座城市逐渐丰满了羽翼——当初刘建华是跟着亲戚到上海打工的,现在他也带人出来了,“他的兄弟、小舅子、表侄,都跟着他在做”。或许“底层”的标签还贴在刘建华的身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生存状态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底层的认识与想象。
尽管已经在上海立足,刘建华一家还是在乡下盖起了楼房,“三层,上上下下的家什,全是自己打,不用一根钉,全用榫”。对刘建华来说,在城市中无论如何发展,乡土情结依然牵扯着他,不管如何狡黠、能干,也不管在城市中赚了多少钱,远方的乡土依然是“底层”的宿命,即便有了在城市立足的资本,对这些“底层”的民工来说,回归乡土是必然的选择。但当他们回到乡村,他们的地位便大不同了,叙述者“我”不由感慨:“这对夫妻挺般配的,在乡下,大约都可算上人尖了。”
三、“我”是谁:城里人的困境
有学者认为,底层是一个社会分层概念,其间较少有阶级成分,或者说底层一词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反动,因为阶级在这儿不再起作用,而归为一个自然群体的划分,按个人占有资源的多少,进行量化分割,很自然地形成上、中、下的社会层次,最下的就是底层。[3]107按照这种理解,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并不一定是其他阶层与底层的对立,因为就小说中的“我”而言,在因为装修而与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占有的资源不仅不多于民工刘建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反而显示出“我”的困境。小说中写到刘建华之前说过年也不回去的,却在小年夜突然提出要回家。当“我”提出质疑时,刘建华却笑了:“过年能不回家吗?”“这是他第一次对我们笑,虽然是带着狡黠,可我们心里还是软了。”民工们心里都很清楚,年底很难找到活儿干,过完年回到城市也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活儿,所以刘建华及时抓住了“我”家的这个跨年度工程。况且,主人不同意他回家过年他就真的不回了吗?其实不管主人同意不同意,他都是要回去的了:车票二十天前就订好了,老婆、兄弟都已经先回去了。在过年回家这个问题上,刘建华比“我”更拥有话语权,这个时候,到底谁是受压抑的“底层”,似乎含糊了。
小说又写到:刘建华走之前,把工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切有条不紊,没有一点邋遢相”。“我”心里不由感慨:“倘若不是和刘建华这样的雇主关系,又弄得有些僵,那么,刘建华这样的劳动者,其实正是我们喜欢和欣赏的:勤劳,智慧,自尊,上进。”因为刘建华临走之前的清扫,“我”又产生了虚妄的优越感。实际上,刘建华如愿回家了,而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打扫干净的工地,就刘建华而言,他的目的达到了,还用一种对他来说微不足道的付出留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则在一个清爽的工地上,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满足,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自说自话地赞美了刘建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更悲哀?
小说在最后设计了这样一个结尾:过完年,刘建华如期回来了,也按工期结束了装修工程,然后就是结账,走人。大约一年之后,“我”才发现刘建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纪念:“他将热水器百叶箱的门框打小了一圈,使得我们无法将热水器的铁罩拆下来,清除里边的煤烟,以示对我们的教训。”这些叙述中的不和谐,让我们质疑:这个抒发了一段浪漫的感受、作为叙事者的“我”的身份是什么?是雇主吗?它代表一个简单的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看法吗?好像都不是。这是一个在底层的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的看法,在这样的知识分子眼中,劳动者应该是勤劳、智慧、自尊、上进的。我们的文学中不乏这样的表述:“他们的基本的东西,是勤劳勇敢,他们用他们的手和脑创造了世界,养活了人群。”[4]但我们会发现,用“勤劳、智慧、自尊、上进”的眼光看待刘建华的叙事者的观念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刘建华最后留给“我”一个教训。刘建华为什么要教训“我”?刘建华对自己的手艺很骄傲,所以要的是高价,而且“脾气好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打张八仙桌,不用一根钉,全用榫,要不要?”刘建华对自己的木匠手艺是有充分的自信的,而“我”居然找个不如他的上海人来当监工,这让刘建华很不服气。刘建华最后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这个题是出给监工的,也是出给主人的。按传统习俗,工匠是不能得罪的,否则他总会给你一个教训,这当然是旧手艺人的陋习。可以想象,刘建华出了这个题,而监工没看出来,当刘建华拿了钱出门,心里一定很美吧?很解气吧?以后也该是个吹牛的资本吧?可这并不是底层小人物通过戏谑手段占到的当权者的便宜,毕竟“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毕竟“我”对刘建华的行为无能为力。王安忆叙写了一个新型的民工,通过几组对抗关系的叙述,衬托出当下一类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悲哀,或许“民工刘建华”的另一个标题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我”。
王安忆笔下的民工刘建华似乎不是流行模式中的一种,想来王安忆是有经历、有观察的,所以能在三千多字的篇幅中,写出这么一个有特点的人物。一般来讲,写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很容易落入俗套,一个俗套是现代化思维下的俗套:城乡差异,“肉食者鄙”,写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另一个俗套是新左派的思维:用“底层”、“弱势群体”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打工族群,甚至写出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化倾向,即所谓‘底层秀’”。“‘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5]。在这样的模式化创作背景下,也会很容易地把王安忆的这篇小说放在这些模式中去解读,即城乡模式或底层叙事。事实上,王安忆本人对文学创作缺乏与生活的“距离”有着清醒的认识:“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6]王安忆写的这个民工有特别的地方,作家以生活经验为基础,写出了不落俗套的、撇开了模式化的意涵。
当底层文学这一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存在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底层文学是要替底层说话,但写作品的人是不是底层人物?显然不是;如果不是,怎么替底层说话?他们写的底层的痛苦是不是就是底层人的痛苦?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么底层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社会的文化、语言都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人在接受教育、享有文化的过程中,无形中就被统治阶级在精神上给”收买”了。社会的主流话语不是底层语言;底层语言也是不能进入主流流通的。当一个作家用流通的语言来叙述的时候,底层的语言还剩几何?因此当一部分人试图为底层代言,尤其是知识分子试图去做代言人,其实是很可疑的(当然,有人给底层代言,那也不错,起码有道德的勇气,虽然得益者往往是代言人自己,比如说获得某种道德上的满足)。《民工刘建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叙述者就站在知识分子或城里人的立场来叙述,无需伪装,不用代言。“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我写了我个人的痛苦,我写了我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我写了我一个人的感受,那么很可能这就会具有普通的意义,代表了很多的感受。”[7]31但以这样的身份来叙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叙事中不免充满了城里人的偏见和知识分子的误解。这就要求作为知识分子和城里人的叙述者具有一种反思、反讽的精神,意识到作为一个知识者,作为一个城里人,在叙述底层故事时很难不为偏见所左右,并不代表普遍的结论和看法。
小说《民工刘建华》在叙述中的不和谐是作品的独特之处:叙述者一方面对“看”与“被看”的关系很在意;另一方面把民工称为“一个劳动者”,赋予他“勤劳、智慧、自尊、上进”的内涵,但又认为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不能客观地看问题。但我们不禁要问:没有这种关系,就能客观地看问题吗?与结尾刘建华留下的一个教训结合起来看,王安忆的叙述中还是有复杂性的。知识分子看农民,看到他们身上的勤劳、智慧、勇敢、上进,这是一个自设的看法,小说对这个自设的看法是反讽的,构成一种张力。
[1]王安忆,民工刘建华[J].上海文学,2002,(3).
[2](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J].文艺报,1952,(11、12期合刊).
[5]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历史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6).
[6]王安忆.生活的形式[J].上海文学,1999,(5).
[7]莫言.碎语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