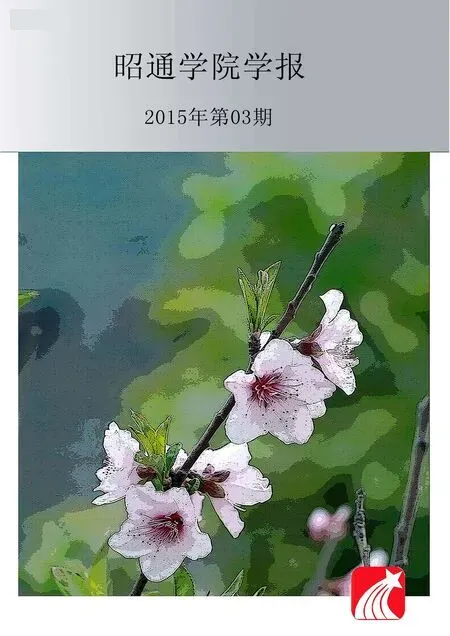庄子《逍遥游》注译问题的辨析
2015-04-10王中昌
王中昌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语言学研究
庄子《逍遥游》注译问题的辨析
王中昌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庄子行文意蕴丰富,历来解说纷纭。论文通过对庄子《逍遥游》的几家较为通行的注译(如《庄子注译》、《庄子集释》、《庄子补正》、《庄子内篇新释》、《庄子今注今译》、《庄子注疏》、《庄子译诂》等)的比较,试图对其中几处的注译“鲲”、“天池”、“息”、“小知不及大知”、“汤之问棘”、“数数”、“致福”、“宋人与尧”、“大樽”等加以辨析,以求得到更为合理的注译。
庄子; 逍遥游; 注译
《庄子·外物》有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故庄子之为文也亦天马行空,毫无拘碍,于道之阐发,恍兮惚兮。笔者初读之时不免难睹端涯,遂寻来各家注释加以参详。然后世解庄者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大相径庭处反更加重心中的疑惑。盖庄子行文需以“意会”去填补方能有所得。近日读《逍遥游》,对照各家注释,发现多个不易索解之处,遂不揣浅陋,一一列出以求正于大家。
一、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1]其中对于“鲲”字的解释,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今人张默生先生的《庄子内篇新释》,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等,皆从《尔雅·释鱼》,作“鱼子”讲,以为泯灭其小大,凸显庄子齐物的思想。而杨柳桥先生《庄子译诂》注曰“朱骏声:鲲,即‘鰥’之或体。《诗·敝笱》:‘其鱼魴鰥。’《毛诗传》:‘鰥,大鱼也。’”认为鲲当作“大鱼”讲[8]。其实我们分析原文就会发现庄子这里是要通过描写鲲鹏之间的变化,增加文章气势,将人引入一种非凡的境界并引出后文。庄子没有必要在这么一个字上作文字游戏,显示他的齐物思想,况且他后文又明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1],若将“鲲”解作极小的鱼子,岂不是自相矛盾。故此处“鲲”当作“大鱼”讲为是。
二、“天池”。“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1]其中“天池”一词的解释多从成玄英《庄子注疏》“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6],即天然的大池。这样注解浅显易懂,本没有问题,但对其翻译如:王世舜先生《庄子注译》译为“南海是天然形成的池”;陈鼓应先生译为“那南海,就是天然大池”。就未免过于生硬,失去其原有的艺术旨趣。张默生先生在其《庄子内篇新释》中言“这南海,如同所有的海是一样,都是天然而成的,所以叫做天池”,则又稍显繁琐。这里,“天池”是对“南冥”的一个判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嵇康之言训“冥”字:“取其漠漠无涯也”[3]。直书“天池”二字恰能现其漠漠无涯之意也。如果强作翻译不免失其意趣。故而不若不译,只在注释中注明更好。
三、“息”。“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1]关于“息”字,历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作“风”讲,谓鹏借此六月间的大风而飞(张默生先生、王世舜先生持此说);一是作“休息”来讲,谓鹏一飞需六月而止(刘文典先生、杨柳桥先生从郭象注)。分析这一争议,我们还是要回归原文,找出庄子写这一段话的用意:大鹏一动则水能击于三千里以外,言其大也;一飞而上者九万里言其飞之高也;故按行文逻辑看下文六月当指时间段,言其时间久、飞之远也。有空间,有时间,这就更能体现出鹏的“大”,也符合庄子此时的文意。再联系下文“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正是时间之说。六月既指“时间段”,那“息”字作“止”讲就是行得通的了。因此这里的“息”字应该是停止或休息的意思。
四、“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关于这一句的翻释,王世舜先生译为“才智小的赶不上才智大的,寿命短的赶不上寿命长的”[1]。陈鼓应先生译作“小智不能比匹大智,寿命短的不能比匹寿命长的”[3]。杨柳桥先生译为“见识小的不如见识大的知道得多,年龄小的不如年龄大的经历的多”[8]。其他庄子译本也多作类似译法,然参照成玄英《庄子注疏》“夫物受气不同,禀分各异,智则有明有暗,年则或短或长”[6]并文中之言“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兼及《秋水》北海若之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1]可知,是由于自然天性的限制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在庄子的心中是不存在小不如大或大不如小的,因为无论大小,他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达逍遥之境的。故此处当作“物类智量不一,年限亦不一”[5]以泯除其小大之分为是。
五、“汤之问棘也是已”。郭象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2]。成玄英《庄子注疏》云“棘既是贤人,汤师事之,故汤问于棘,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殷汤请益深有玄趣,庄子许其所问,故云是已”[6]。今人刘文典、张默生二先生皆从此说。闻一多先生在其《古典新义·庄子内篇校释》考证“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案革、棘古字通…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3]陈鼓应先生据此说补入,并将“穷发之北”至“彼且奚适也”一段作为棘答汤问之语。先不说《列子》一书本就真伪杂从,即联系上下文来看,“汤之问棘也是以”一句当是总结上文,作为对“众人匹之,不亦悲乎?”的应答,意在借此重言规劝世人莫囿于小大之见,却并无引领下文之意。而下面数句与文章开头几近重复,庄子开始不让棘代为立言,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故而郭象所注更贴切文意。
六、“数数”。“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1]据成玄英《庄子注疏》“数数,犹汲汲也。宋荣子率性虚淡,任理直前,未尝运智推求,役心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6]。刘文典、陈鼓应、王世舜等先生皆以此说为是,而张默生先生则以“数数”为“频频屡屡之意,此言求之当世,不常常见如此者也”[5]。对于这一分歧,笔者以张先生之说为是,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庄子在此处举宋荣子与列子的例子,就是要告诉人们修行如二人的境界已是世间少有,但二人皆有所待,无从达至高境界,为下文描写神人作铺垫,以起到层层递进的作用,因为对二人描写愈是神乎其神,愈能表现神人的莫测高深,不同凡俗。另外庄子已明确说出宋荣子能够“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再说他对世间的荣誉并没有汲汲追求,岂不有画蛇添足之嫌。所以这里应是说宋荣子这样境界的人世间少有,不应作“汲汲”或“迫切”讲。
七、“致福”。“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中对“致福”的翻译,陈鼓应先生作“他对于求完善的事,并没有汲汲去追求”[3];王世舜先生作“他对于幸福,从来不去努力追求”[1]。杨柳桥先生作“他对于追求人世间的享受,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迫切要求的了”。这几种译法都稍欠妥当。成玄英云“致福,谓备致自然之体”[6],张默生先生案“福,备也。无所不顺谓之备”[5]。故“致福”应是列子顺应自然,泠然御风的一种悠闲自得的状态,与幸福、完善或享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这里应当译为“像列子这样能够任意所之,无往不顺的人,在世间也是不多见的”。
八、“宋人与尧”。“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1]此段话初读之时不免不知所云,遂翻检前人注解:成玄英《庄子注疏》云“尧既体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尧之无所用天下为,亦犹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6]。陈鼓应、王世舜二先生于此处的注解及翻译都相当简略,并未说明这段话与上下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读庄子必须要前后贯通,而非一些碎片化的理解。张远山先生在其《庄子奥义》中指出“章甫”寓言是庄子为避免宋康王诛杀其身、剿灭其书而故意支离其言,隐晦其指的,其言“已被尧舜之类俗君僭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尚未被尧舜之类俗君僭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庄子的批判矛头直指母邦又不限母邦,而是针对一切君主专制的古代缘起——尧舜,阐明“大治”之弊,对君主专制提出终极指控:即便是实行所谓“仁政”的圣治明君尧舜,也把民众整治得脱离了天赋自由,成了离开君主就无所适从的奴隶”[7],将宋人及尧的故事看做是庄子的政治寓言。或许庄子在其《逍遥游》中真的透出了些许政治的意味,但描述政治以达讽刺之指,本身就是以物为事,非逍遥之真意也,故政治寓意断然不会是庄子写作这篇文章的本意。故而此虽可备一说,但却未免牵强。还是回归文本,庄子整篇文章由鲲鹏寓言引入而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主旨已然得以阐释,而后所述不过是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进一步论证。张默生先生认为宋人与尧的故事是对“至人无己”的进一步阐释,他说:“当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时,还是有心去治民,有心去为政,这样便不能算是忘己,及至他拜见了得道的四人之后,忽然顿有所悟,才知天下原乃身外之物,实是不足为治,更不值得恋恋的。”[5]但是张先生只看到“至人无己”,却没看到其实此处还包含了“神人无功”的意旨,即承接上段“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在神人而言,尧的汲汲焉以天下海内为务即是“以物为事”,实是不足取的。
九、“大樽”。《逍遥游》的最后是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其中庄子劝惠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成玄英云“虑者,绳络之也。樽者,漆之如酒罇,以绳结缚,用渡江湖,南人所谓腰舟者也。”[6]刘文典、张默生、陈鼓应等先生皆然其说,谓为腰舟。笔者以为不然,庄子在最后讨论物之用与无用,实则要表现物之无用之用,若讲此瓠用作腰舟,则依然是有“蓬之心也”,只有彻底忘记它,让它自己浮游于江湖方是真正理解逍遥无为之真谛。正如庄子在《秋水》中说“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浮于江湖亦大樽之乐也,此不以己之心量物也,一任自然,方是正道。
以上只是笔者在比对各家注解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惑,以及针对它们的辨析。而古今解庄者众多,各家对《庄子》一书中的词句的注译也往往相互歧异,因而对那些相互歧异的注译加以辨析,以求得更合理的注译,也就很有意义了。
[1]王世舜. 庄子注译[M]. 济南:齐鲁书社,2004:3—11.
[2]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4:3.
[3]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38.
[4]刘文典. 庄子补正[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36.
[5]张默生. 庄子内篇新释[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0:4—29.
[6]成玄英. 庄子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1:2—18.
[7]张远山. 逍遥游奥义[J].社会科学论坛,2007,():—.
[8]杨柳桥. 庄子译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21.
[9]王先谦. 庄子集解[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1—3.
The Analysis of ZhuangziXiaoYaoYouNote translation problems
WANG Zhong-ch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ina West Normal Un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Zhuangzi had very rich implication, the explain about him always different diversel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is some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 such as “Kun”, “Tianchi”, “xi”, “little knowledge less than more knowledge(小知不及大知)”, “soup asked spine(汤之问棘)”, “count”, “wish”, “people song and Yao(宋人与尧)”, “dazhun” etc, in order to get more reasonable annotation by comparing different note translation ofxiaoyaoyou,such asZhuangzinotetranslated,zhuangzijishi,zhuangzibuzheng,zhuangzineipianxinshi,zhuangzizhushu,zhuangziyiguetc.
Zhuangzi;xiaoyaoyou;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2014-11-26
王中昌(1990— ),男,山东嘉祥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H159
A
2095-7408(2015)03-00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