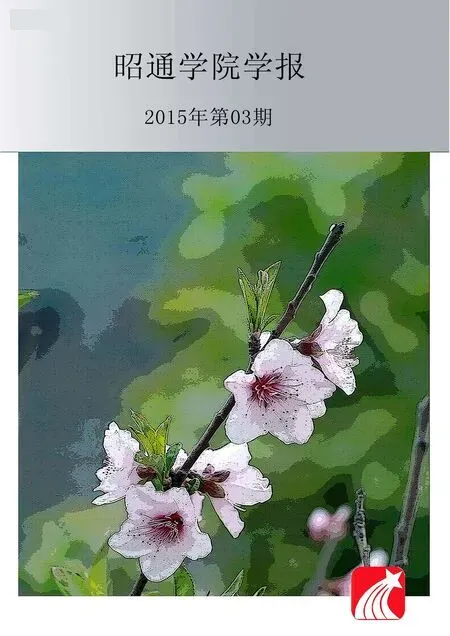建国前天主教会昭通教区状况及公益事业回顾
2015-08-14邹立莉
唐 靖, 邹立莉
(昭通学院a.管理学院,b.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云南 昭通 657000)
民国时期的1938年,卢金锡修、杨履乾等纂成的《昭通县志稿》,由昭通新民书局印刷出版。在志稿卷六《宗教》的部分,编纂者于前言中对近代昭通宗教作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文中说道:“宗教者,无论何教,随其人之信仰,认一教为宗主者也。中国古时无所谓教,自秦汉以来,崇尚黄老,故始皇、武帝并求长生之术,而后世道家者流竞称道德经。自清末基督旧派侵入,名曰天主教。其时根蒂尚浅,及通商立约后,新派耶稣教继来,其势渐张。愚民无知,相与仇,迭酿巨案,割地与和,迄今日久,亦相安无事。然其教系劝人为善,与释道之取人财物者不同也。昭居边鄙,地当冲繁,各教俱备。及信教自由之令出,亦随人投入教堂,俱未行禁止。爰考各教之宗旨,以述其源流焉。志宗教。”[1](P.19)从中可以看出,在经历了晚清以来的风风雨雨之后,民国年间的昭通宿儒们已经完全站在一个平和的立场来看待曾经被前几代人仇视的“洋教”,着重指出其“劝人为善”之处。本文主要参考民国《昭通县志稿》、黄锐《昭通天主教简史》、《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中的天主教专题以及第二十一辑何品军《云南天主教发展述略》等文章编写而成,对建国前天主教会昭通教区的教派情况及其公益事业作一个简单回顾,并对其中相矛盾的说法予以适当考证补充,特此说明。
一、天主教在昭通的教派情况
天主教传入云南最早的地区是昭通的盐津县。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设主教公署(又叫定座主教)于盐津县龙溪村,1867年(同治六年)在昭通县城设立第一座天主堂——真原阁。《昭通县志稿》中也说:“天主教于明时即传入中国,昭通之有教堂于同治年间,设立于城内府街。自庚子后,始拨相近之五属公馆与之,由马、晏两司铎,亦称神父,信奉耶稣。其入教者及各地人皆有,惟司铎则由欧洲法国嬗派而来,主持教务以及念经办事之任。盖彼教无论在何地方,悉隶于罗马统治之下,此则称为老教,与他新教迥然不同也。”“该教崇奉天主,敬礼耶稣,以爱人如已为教纲,以圣经为根据,以十戒为教规”。但《县志稿》对天主教内部派别的区分不是很准确,只是笼统地说:“昭通教会只城中一处,自设教堂以来,已经数十年,入教之人不分国际种族均结合成一大团体,名曰:圣教会。以前者无论,依最近调查,昭之信彼教者,现有六百余人民。”[1](P.22-23)实际上,天主教会内部教派纷繁复杂,并非一个“圣教会”所能涵盖。
在表面的一个云南主教范围来看,内部昆明、大理、昭通三个教区,都各有许多不同的修会会士在区内工作,在国外有其各自的总修会。他们彼此间并无隶属关系,一般都得经罗马教廷批准才能创建,各有侧重的创建目的。如圣会撒肋,重在青年教育;灵医会重在医药事业,管理麻疯院等;圣保禄会重在医药并管理孤儿院等;方济各会则重在医药,诊所和幼儿教育;圣衣会则重在静修与手工(刺绣)等项工作。各修会的经济独立于教区,由他们各自的总会供给,人事调动权也在总会。唯有传教活动方针及其它规定,才听从于所在教区主教的领导。
在云南范围内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有巴黎外方传教会、慈幼会、圣保禄会、圣方济各会、圣衣会的男女修会和两个修道院。此外,还有圣苏尔比斯会会员洪文灏到昆明创办大修院,1947年天主教昆明总主教德维能创设的圣心会等。在昭通地区传教的最初只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此后又有圣方济各会的分会和意大利灵医会神甫到昭通传教、行医。
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56年由法国人巴吕和郎伯尔两主教发起,1663年在巴黎建立修道院,遂成为该会中心。会员不发修会誓愿,有会规,过共同生活,终身为传教服务。规定三十五岁以下的神职人员可申请入会,在传教区工作三年以上始得成为正式会员。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到中国福建传教。1702年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雷勃郎神父被罗马教庭委任为云南(教区)的主教,但很快因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而被驱逐。此后1730年(雍正八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又由四川宜宾派传教士到云南盐津长期潜伏传教,并于1843年在盐津龙溪建立教堂和主教公署(当时称“真原阁式公济堂”)。1867年(同治六年)外方传教会在昭通县城设立第一座天主堂——真原阁。此后,主教公署迁昆明,昭通地区的教务先设监牧区(即组织未完善教区),由昆明主教区领导。1935年4月8日正式成立天主教昭通主教区,管辖昭通、会泽、巧家、奕良、镇雄、盐津、绥江等县,陈达明任宗座监牧。昭通主教受罗马教廷领导,每五年向教宗口头报告一次。
教区的基层组织是本堂区,每个本堂区设一常任司铎(神父)主持该堂区一切事务。本堂区是天主教活动中心,每年须向主教汇报工作。数个本堂区组成总本堂区。昭通教区辖有总本堂和本堂,总本堂管各县传教事务,本堂管本县传教事务,总本堂和本堂都设在昭通城内毛货街天主堂内。外国传教士在昭通进行传教活动所需的经费,其来源有四:一是罗马教廷每年一次的汇款;二是各国教徒捐赠的传信金汇到罗马,再由教廷统一分配汇寄;三是教会在当地购置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地租;四是教会医院的收入所得。
灵医会由意大利神甫于1554年创办。它通过举办医药事业进行传教活动,总会设罗马,下设省会。1946年意大利灵医会传教士到昭通,先后在会泽、巧家开办医院,成立“灵医会中国修院”,属意大利米兰省会管辖。中国修院下设会泽、巧家、彝良、昭通四个分院,有会员十人。活动经费除医疗费收入外,余由总会补助。
圣方济各会“第二会”,是圣方济各会后来分化出的教派之一,分化各派都为女修道者设“第二会”,并为还俗教徒设有“第三会”。该会到昆修女是南斯拉夫圣方济各会“第二会”派来的,在昭通设立惠东医院,修会和礼拜堂均设在惠东医院。共有中外籍修女十五人(中国籍八人,后退出二人),全部在惠东医院工作。经费靠医院收入。①《外国教会在云南的传布情况》,《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2~114页。
值得一提的是,灵医会和圣方济各会“第二会”在昭通的出现,都与南斯拉夫人纪励志有关。1935年,滇东北地区教务从昆明教区分出,正式成立天主教昭通主教区,亦称为昭通国籍监牧区,负责昭通、盐津、会泽等地教务。昭通教区列为华籍教区,即华人管理教会事务,陈大明神父任第一任主教。1935年陈到昆明,按照教会法典宣誓,正式接受了昭通教区监牧之职。到任不久就因与当地神职人员意见不合,1938年遂退职回四川,不久便因病去世。罗马教廷重新委任了纪励志代理昭通教区的主教职务,中国神父黄仲良为副主教兼本堂神父(1946年黄调任盐津成凤山本堂后,由中国神父陈慕舜继任副主教兼昭通总堂的本堂神父)。此后,昭通教区虽先后推举汉中人牛若望、贵阳教区神父范介平担任主教,但二人均未到任,仍由 纪 励 志 代 理 主 教 至 1950 年。[2](P.431)纪励志是慈幼会神父。他接任后不久,便向罗马教皇汇报了昭通教区的情况,又先后请了意大利一批灵医衣会神父和南斯拉夫一批方济各会修女,来昭通行医。可见,医疗事业是天主教各派在昭通传教的重点工作,故在下文中予以重点讲述。
二、医疗事业
从利玛窦开始的来华西方传教士就已经认识到,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要想打开在中国传教的大门,必须走间接的路线。其中,在中国民众中普及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及开展医疗卫生事业,是最常用的两种手段,二者之中又以医疗工作最能够为中国广大群众接受。
早在天主教于昭通府街建立教堂不久,就在其内设置了简单的医疗机构。民国《昭通县志稿》中记载说:“该教堂立有医馆一所,专治小儿科,并牧养遗弃婴孩,雇乳媪抚育。数十年来,赖以存活者 其 数 亦 不 少 矣。”[1](P.23)对 此 给 予 了 很 高 的评价。
随着天主教在昭通传教事业的扩大,原有机构不敷使用,才又修建专门的惠东医院。该医院由纪励志和陈慕舜代主教经办,于1941年在北城郊动工,1942年建成。由于该医院对昭通人民的意义重大,所以其经费来源就超出了教会的范围。其中,南斯拉夫方济各修会投资二万美元,教会又出售昭通后海子的土地,收入10.5万元(旧币),云南省主席龙云捐款2万元,卢汉也捐了电器设备约值2万元,上述款项集中使用。万国红十字会送了药品,提供服务。医院尚未完工,就开始投入营业。差不多与医院建成的同时,该地也建成方济各第三修道会。不知内情的外人,往往将该修会与“惠东医院”混同。实际上,医院只是修会的附属部份。
全院除修女的宿舍和经堂外,有病床64张。其中传染病床12张。医务工作人员30多人,由1936年至1937年来昭通的南斯拉夫籍方济各第三修道院修女露兴荣、沙石美、马希珍、希修桀,纪励芝,叶丽平六人和医生杨若望主持全院工作。杨若望医生长于外科,当时有人誉为“世界第三把刀”,其名称从何而来不得其详。1947年又先后请来香港医科大学毕业的广东医生王维廉和广东信教医生张华湘,后者从军医学校毕业,并负责院内业务。此后又有外国护土、医生南斯拉夫籍和英国籍若干人补充进来,中国籍在院内修道兼工作的修女也有十人。所得经费除维持正常开支外,还解决方济各第三修会及李子园中小修院的经费问题。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建立后,外国传教土和医务人员陆续回国,惠东医院即由中国籍信教医生张华湘负责并任院长。1952年昭通县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后并入昭通地区人民医院,剩余外籍神职人员被遣送出境。①黄锐:《昭通天主教简史》,见《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93年),第146~151页。
在惠东医院之外,天主教还经营有麻疯病院,原地址在水塘坝乡象鼻岭的小山包上。该院于1936年即筹建[3],最初由基督教管理,李约翰牧师当名誉院长,时常去传教和看望病人,定期派人送粮送药。但由于管理麻疯病人的特殊性,没有专人住院管理(因无人愿去),导致麻疯病人到处乱跑,有的经常外出乞讨,甚至到水沟里洗澡,严重污染水源,周围群众十分怨恨。为此,昭通县县长杨鹤龄出面,同天主教纪励志、陈慕舜协商,委托天主教把麻疯病院100多病人义务管理起来。天主教教会此后与县长杨鹤龄办了接交手续,病人的吃穿及医疗费用,均由天主教收取的地租解决,教会派医生常住,给麻疯病人治病。1946年秋,纪励志代主教去罗马请嘉美禄修会(嘉美禄是意大利天主教灵医会创史人人名,该会是天主教下属以治病救人为主要宗旨的医疗慈善团体,并专门以医治护理麻风病人擅长)来协助医治和管理,得到回应。民国三十五年冬(1946)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间,嘉美禄修会受梵蒂冈天主教皇的指派,分批派遣郭尔定、高若望等六位神父(多为医学博士),外加修士四人,修女五人来到昭通,并修建灵医会医疗机构(地址在原昭通地区石油站内),很受当地人们的欢迎,解放后由当时的昭通县人民政府接管。
灵医会来昭人员增加之后,便分散于昭通、昆明、会泽等地分别建立起各类相应机构以行传教、行医、办学等活动,由此而扩大教会的影响,满足教会传教布道需要。其中,1946年派了2~3人到昆明金马 寺 帮 助 受 理 麻 风 病 院。[4](P.121)会 泽 的嘉美禄医院亦属昭通教区灵医会建立的教会医疗慈善机构之一。该院的筹建工作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负责筹建医院的是7名意大利灵医会教士,他们均于当年末和次年春由昭通主教区分两批派至会泽。经过数月筹备,院址选于原东城外74号天主教堂处(今会泽县第一人民医院内),工程于1947年动工,建设投资约合美金4 750元,均分次由意大利灵医总会于当年内汇兑到会泽。嘉美禄医院工程历时9月竣工,于1948年7月18日正式开业,设有门诊部和住院部。开业后所用的药物器械除少量由昆明购进外,大多均由意大利或香港购置补充。院内共有住院病床28张,院内业务技术力量逐渐增强,主要以范宣仲和巴类思等医学博士为主要技术骨干,在职外籍人员共9名,开创了会泽医院外科手术的先例。当年末,部分神、医职人员又分别调往宜良和巧家传教。[5](P.29-31)
三、其他社会慈善事业
天主教在昭通举办的慈善事业除医疗外,还有学校、赈灾等。天主教传播的主要目的是向所谓的“异教徒”传输宗教知识,采用学校教育的方式乃是基于“不办教育,就不能立脚”的生存策略。民国《昭通县志稿》说:“该堂向来已设有男女学堂,并教以经文。近则遵依部章设立小学校,照科学授课外,仍酌加经典以应教友之普通常识。”[1](P.23)教会在当地站住脚跟后,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经言学堂,要求教徒及子女入学,并免费提供笔墨纸张。最初主要是讲解《圣经》文句及意义。民国年间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兴起后,其宗教教育受到批判和质疑,所以也渐渐在其学样教育中加入中国历史文化和科普知识的讲授,课本也被迫采用民国较通用的版本。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教会还是可以根据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宣讲教义,传授教规教理,教唱赞美诗等。虽然其教育宗旨主要是服务教会需要,灌输宗教思想,巩固教民的信仰,但对于提高一部分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仍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主教会还于清朝光绪末年成立善终会,万吉堂、童光汉先后任过会长。善终会又名临终会,在1910年至1950年间有会员100多人。其宗旨专为教友办理丧葬事务,每当教友中有人去世而又无力购买棺木,该会就代其支付棺木费用,并帮助安葬。善终会还特意把每年的11月2日设为“追思已亡节”。在这一天,会员就到经堂为死去的教友念经做弥撒。临终会的经费来源一般为会员内部捐赠,此外还在蒙泉白坡塘买了三十四亩土地,租给农民,通过收取地租来解决部份经费问题。
除了养老送终的善终会,天主教会还于1902年开办了孤儿院,先后收养13个孤儿,由教会供养,男女分开生活,除学习普通知识外,并教其念经;成人后,由教会帮助找职业。1952年时院内尚有6个孤儿,后由人民政府安排就业。[6](P.233)
此外,1925年(即民国14年)时逢大饥荒,粮价暴涨,苞谷高达大洋五元一斗(折60市斤),饥民无钱买粮,饿死了很多人。当时法籍欧心畲神父任彝良本堂,见此惨景,慨然将天主堂内的积谷,煮粥在街上多处向饥民施放。
1929年(民国18年),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争夺云南领导权时,曾率军围攻昭通,和昭通驻军龙云的警卫团大战于北门外李子园,双方士兵死伤甚多,而伤员却无人抢救,尸横遍野更是无人掩埋,加上天气炎热,臭不可闻,时间一长,还会传播疾病。城内天主堂神父本着人道主义,为了救治伤员和不使瘟疫发生,主动组织担架队出城到李子园双方战场上进行救护和收殓。所幸交战双方见到红十字的旗帜后还能遵守战场规则,各自停火,得以让担架队将尸体掩埋,伤员则抬回天主堂临时救护医院医治,得到昭通县各界群众的好评和称赞。1949年解放前夕,又发生龙奎垣攻打昭通城的战争。当时昭通的医院都设在城外,伤员无处医治。天主教又在毛货街天主堂内成立临时医院抢救伤员,先后共收了十多人,①黄锐:《昭通天主教简史》,见《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93年),第152~153页。为伤员的医疗救护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

附表 天主教昭通监牧区附属事业一览表②《外国教会在云南的传布情况》,《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 0辑,第1 1 9页。收入本书时对其中一些明显的字误作了修改,比如惠东医院,原书将地点写为“昭通东门”,现改为“北门外”。
四、以外国人的眼光看教会公益事业在传教中的效果
综合来看,基督宗教在华的新旧两教传教士们,都希望通过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来激发中国人对上帝的感激之情,从而期望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在事实上,公共事业确实非常成功,但传教效果仍然并不理想。为此,不少传教士抱怨中国人没有感激之心。正如1894年时,一位在昭通传教的法国神甫告诉旅行经过昭通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所说的那样:”和中国人说起宗教、神、天堂或地狱,他们就打哈欠。和他们讲做买卖,他们都会注意听。”[7](P.73)这位牧师已在中国 8年,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用来宣传他的宗教,但皈依的教徒非常少,一个教徒还趁其外出的时机,入室将神甫的所有财产洗劫一空。这样的结果确实很难让神甫们保持淡定。
但一些同为西方人士的旁观者,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察,却有不同于神甫们的观点。前章提及的莫理循即是其中之一,他对传教士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却并不赞同的看法。他认为当地人对教会的慈善工作还是心存感激的,只是他注意到并理解中国人表达感激的方式所具有的含蓄隐晦的特点,认为中国人对这些传教士的工作有不同的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来自对人类伟大无私的爱(而这正是他到中国来不容置疑的动机),而是想为他自己在看不到的冥冥世界中积阴德”。中国人在做好事的时候,确实常有一种“积德”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以自己做慈善的动机,来理解教会所做一切公益事业的宗旨的。中国人虽然没有以西方习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感激之情。事实上“没有其他民族比中国民族更具有真诚的感激之心”。
除了这种含蓄的民族性格之外,莫理循还看到了中国人的鬼神崇拜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之间的差异,并从中国人的信仰角度解释中国人表达感激的方式,认为中国人的感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实利的思想观念,这使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抱着一种实用的目的。所以莫理循引用一位牧师的话说:“从佛教发展而来的这种观念已经在中国广泛流行。任何人只要相信某种宗教,就会依靠它生活。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成为基督教教徒,他就期望依靠基督教生活。”他相信许多到教会来问道的人都是为了讨碗饭吃,他们皈依基督教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中国人内部也经常指责某些教徒“入教”只是“吃教”。[7](P.7)这种讲求实利的特性使中国当地的传教士难以取得成功,因为中国的观念是:“你吃耶稣的饭,当然就得说他的话”,所以莫理循有时常忍不住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将传教的失败归结为中国人的固执和不开化。但如果据此认为中华民族只讲究功利主义,似乎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换一个观察者,他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E.A.罗斯就指出,其实中国人也是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功利主义是由艰难的经济条件造成的,是长期以来担忧生存问题的产物。[8](P.73)
此外,莫理循还认为传教效果不理想与各种教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以及他们的传教方式有关。比如各宗派在华传教士关于“上帝”敬称的争论就难以解决。他以不同教派和《圣经》的不同汉译本对“上帝”不同译法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耶稣会给神取的名字叫“上帝”,后来叫“天主”;新教则常使用另一些不同的汉译名称,在不同汉译本的《圣经》中,就有诸如“神”、“主”、“最高统治者”、“上帝”、“上天”等名字,莫理循认为这些不同的名字会使中国人茫然不知所从。当然称呼问题仅是一件小事,但却反映出各教派在教义上的分歧和不可调和的对抗,非常不利于教会对华的传播。
当然,一些传教士在方法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云南,莫理循提到18个传教士在8年的时间内的传教业绩,就是从500万到700万人中皈依了11个中国人。而在其他一些省份,一批又一批传教士也曾连续不断地工作了二十多年,而他们总共才使大约20个中国人信教。原因何在呢?莫理循认为是他们用晦涩难解的术语教导人们,使基督教的教义和基督的教诲变得含混不清。他们竭力用图表阐明启示录和罗马书,不仅使中国人感到迷惑,就连一些外国人士也同样感到困惑不解。[9](P.292)莫理循的这种认识,或许对于那些努力其传教工作的神职人员显得不那么公平,但对了解中国近代民教关系问题,确实有一定的可资参考之处。
[1]卢金锡,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卷6)宗教志[Z].昭通:新民书局,1938.
[2]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宗教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3]云南昭通麻疯院行将成立[J].麻疯季刊,1936,(10)3:31—32.
[4]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98卷)《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5]会泽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会泽卫生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6]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地区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7]莫理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M].窦坤,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8]E.A.罗斯.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M].张彩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9]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M].檀东鍟,窦坤,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