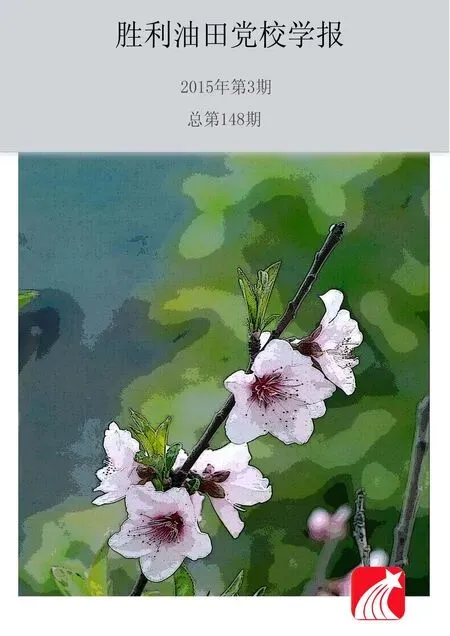也谈环境犯罪的制裁思路与刑事政策定位
——以《刑法》第338条中对“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视角
2015-04-09刘楚琪
刘楚琪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也谈环境犯罪的制裁思路与刑事政策定位
——以《刑法》第338条中对“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视角
刘楚琪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环境和经济发展存在特殊的关系。国家在制定环境刑事政策时必须考虑经济性因素。多数学者致力于捍卫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的独立性,倡导破除长久以来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依赖关系,推崇扩张解释的方法、确立从严惩处的环境刑事政策,对现有罪名进行解释及适用。从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概念梳理出发,继而通过对其运行现状的阐述,以《刑法》第338条中对“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视角对我国应当秉持环境犯罪的制裁思路与刑事政策进行定位,进而更好地运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
环境政策;环境刑事政策;环境犯罪;经济;污染环境
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警告虽然不绝于耳,环境污染区域严重化、范围扩大化、承载能力进一步弱化的样态依旧是照常进行。行政、民事、经济手段捍卫环境起到的作用,似乎只达到了“应尽”的水平,而刑法手段扮演环境保护的最后防线角色才刚有起色。虽然所有的犯罪都侵犯了法益,但是相比之下,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更为严重和深远。环境犯罪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表现为破坏了国民的生存环境,而环境犯罪社会危害的深远性则表现为环境犯罪不仅侵害或者威胁国民的现时利益,而且会侵害或者威胁到国民未来的利益和未来国民的利益[1]。
一、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概念梳理
界定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概念,首先必须厘清其与环境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关系。尽管,关于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甚至有些走向了充耳不闻的极端,但必须承认的是,至今对其与环境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关系梳理问题仍然莫衷一是。主要表现如下:
1.不同学者对环境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刑事政策是环境政策和刑事政策的结合体。它既是环境政策,也是刑事政策,是环境政策下的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下的环境政策。环境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保护环境,而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环境保护政策理所当然地涵盖了环境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刑事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刑罚和其他各种措施保护各种重要权益,环境权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权利,也顺理成章地要受到刑事政策的保护,所以,刑事政策之下必然有保护环境权的环境刑事政策[2]。从刑事政策所包含的外延范畴来讲,环境政策角色和刑事政策角色,环境刑事政策兼而有之。可以说环境刑事政策是属于刑事政策下的分支,但是将环境刑事政策的目的与环境政策的目的,利用环境权这一概念,作为相互适用的链接点,或者将这两种目的完全等同,笔者尚且不能认可。
有的学者直接指出,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是环境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手段和目标上。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是环境政策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对环境犯罪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和措施在刑事领域是环境政策众多方法和措施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与环境政策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安全[3]27。
另外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既具有与其它犯罪相同的特征,也具有与其它犯罪相异的特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环境犯罪与其它犯罪相同的特征;犯罪行为的累积性(潜伏性)、持续性、间接性、复杂性、侵害行为一定程度上的可容许性、后果的极其严重性等是环境犯罪不同于其它犯罪的特征。因此,作为环境犯罪反应对策的环境刑事政策,应当既与国家总的刑事政策、环境政策协调一致,又具有能够解决具体环境问题的特质[2]。由此,环境刑事政策在国家实施总体刑事政策、环境政策方面,展现出的协调一致性表现在:环境刑事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刑事政策的总体目标在环境领域的具体化——惩防环境犯罪。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环境政策是基于通过民事、行政、经济、刑罚等手段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制定的;环境刑事政策是基于通过刑法手段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制定。然而,环境政策与环境刑事政策在手段上的重合,并不代表两者的关系可以引申出:涉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程度、手段采取所顾及的因素条件、实施手段所持有的价值理念等等,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达到无缝重合的效果。
2.笔者对环境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首先,正视环境刑事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正确梳理环境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条件,而其中关键在于环境刑事政策的定位,即其充当着最后解决环境问题的角色。与其说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解决的是环境问题,不如说解决的是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历史遗留问题”。其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一面,需要对当今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做出严阵以待的姿态,对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严惩不贷;另一方面,面对失而不再复得的环境状态,明知无论多么严厉的刑罚也挽回不了局面的无力叹息。然而,造成这种并行相悖情形的原因,无外在于,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特殊关系。国家在制定环境刑事政策时必须考虑经济性因素。环境刑事政策的经济性牵掣到众多价值选择:第一,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优先选择何种价值。第二,在多种法律手段中优先选择哪一种手段。法律手段有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在行政手段、民事手段也可以保护环境、控制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刑事手段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究竟如何。第三,国家必须大致预测刑事手段控制环境犯罪的成本。刑法干预太多,成本太大,法律的经济性显然不够,某种程度上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刑事手段的成本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总之,环境刑事政策既要考虑环境刑事手段的公益性、目的性,也得站在经济性的视角进行建构,否则会顾此失彼。
其次,理性看待学者提出的保持环境刑事政策的独立性的问题。对许多学者来说,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接受程度比环境刑事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接受程度相比之下,要容易的多。的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过分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了“经济发展必然产生环境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造成了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对漠视,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相关主体的污染行为,并且没有及时在社会中形成“污染有罪、污染可耻”的道德风气,也在客观上使环境刑事政策失去了社会根基,使得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方面呈现出不作为的倾向,从而减少了刑法的适用。因此,“忧心忡忡”地提倡保持环境刑事政策的独立性,破除环境政策对刑事政策的制约,对环境污染采取“零容忍”政策,并采取多种手段坚定不移地进行环境污染的防治。可实践至今,“抓大放小”既判案件数量极少;实行非监禁多、实行监禁较少;缓刑适用率高等现象似乎并没有随着从严政策而改观。不禁应当加以反思:一味地确立严格的环境刑事政策,而不对刑事司法认定,其所包含的入罪标准、主客观认定方面、量刑规范和判例经验等等进行充分合理的论证分析,只能够让公民继续维系着以牺牲环境换取财富的“平衡感”;只能够让企业继续维持着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铤而走险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使命感”。
二、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运行现状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运行,主要强调的是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中的贯彻执行情况[3]。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立足于我国新旧刑法典修改与变迁的角度,分析与梳理刑法规范在基本环境犯罪具体规定方面的演变与现状,是厘清我国刑事立法对环境问题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政策倾向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据此建立科学和合理的刑法保护机制的基石。进而,新旧刑法中具体条文的修改与变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刑事政策的指引、导向功能也日益凸显。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刑事立法既包含定罪,又包含量刑。换而言之,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所指引、导向价值既表现为扩大或者缩小刑法干预社会生活的范围以及确定刑法干预社会活动的重点取舍,其自然地决定了一个国家犯罪圈的大小以及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又表现为严厉或者宽松地指导、调节刑罚适用从而决定某些犯罪惩罚的力度。不少学者认为,梳理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历史,从1979年旧刑法到1997年新刑法,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刑事立法对环境保护的理念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嬗递过程:即从盲目抵制犯罪化到积极推行“降低入罪门槛、扩大规制范围”;从立法宜粗疏到严密刑事法网;从“惩恶于已然”到“预防于未然”[4]。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秩序法益保护为主向生态法益、秩序保护并重的转变。从1997年《刑法》在第6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确立了“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专节当中,表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秩序法益一方倾斜,国家所建立的包括环境资源管理秩序在内的社会管理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刑法对其进行保护本是无可厚非。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较大修正,其中不仅包括对罪状本身,而且罪名也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订为“污染环境罪”。理论界认为,修正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生态法益的独立性[5]。但是纵观在修改条文所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一章节内,仍然以“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为入罪前提,其中所规定的主要罪名的具体构罪标准大多以“财产损害”与“人身伤害”为标准,表明立法及司法过程还是将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作为环境犯罪的实质客体。《刑法修正案(八)》对第338条的修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生态法益的存在,但在构罪的具体判定中我们仍可管窥到人们对传统法益的坚持与对生态法益的漠视[6]。由此断定我国环境刑事政策下的环境刑事立法的理念,在法益保护上的生态化,还为时过早。
2.条文规定的危害后果模糊化。即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是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11]。这也有效地扩大了刑法的制裁范围,严密了刑事法网。但也同时带来了,对污染环境罪的“严重污染环境”认识存在的严重分歧。《刑法》第338条中“严重污染环境”的表述内包含着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要求。在定性上,本罪的不法行为需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在定量上,本罪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达到“严重”的程度。而该用何种标准判断环境是否被严重污染不仅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也成为众多学者们绞尽脑汁,费力解决的难题。因为如何认定“污染环境”,关系着“污染环境罪”罪名形态、入罪标准、既未遂形态、主观方面认定等一系列问题焦点的争鸣。虽然不少学者在此等方面论述颇丰,针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见解可谓字字珠玑,或者更多的是对现有的立法现状“忧心忡忡”,并亟待于司法解释能够加以完善。但极少能有站在环境刑事政策中环境与经济的牵掣关系的角度谈及一二。
3.环境监管失职罪设置功能弱化。大部分环境犯罪案件最初不是以环境违法的面貌出现的,只有这些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超出了行政法规所能调整的范围和一般民众所能容忍的范围,才会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就为环境监管部门预置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同时,由于许多环境犯罪案件都与环保主管部门的监察不力有关,甚至常常伴随着环保主管部门渎职犯罪。这就意味着,当一部分环境犯罪发生时,环保主管部门与犯罪主体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为了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环保主管部门向公安、检察机关移送的涉嫌构成环境犯罪的重大环境污损案件数量自然屈指可数。更甚,秉承着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要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宣传模式,当重大污染事件发生以后,公众的注意力将被官媒从事故原因背后的环境监察机关的渎职行为,“顺利”地转移到事件抢救进展过程中出现或者事先刻画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群体进行表彰上。从而,忽略了行政责任的追究;司法机关也由于介入延迟缺少相关证据,而无法对环境污染企业及存有监管过失的环境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刑事追责。
通过对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中的贯彻执行情况的了解,笔者将结合多方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解答关于 “环境污染罪”认定问题的疑惑,针对刑法第338条是否存在立法缺失一说,又是否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补救一说[8],提出些许想法和观点。
三、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下解读 “严重污染环境”
1.学术困惑。关于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的问题,学界一般在探讨环境犯罪时一并论述,鲜有单独讨论。依学者关于环境犯罪结果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的争议来看,多数学者主张污染环境罪的性质时往往陷入了以下几点困惑:
首先,实然与应然相互混淆、不加区分。有的学者认为,尽管《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原条文作了修正,但修正后的条文(污染环境罪)仍然规定了实害结果作为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9]。另一方面,在学界一直建言本罪应当增设危险犯的背景下,但修改后的条文并未采用“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引起……严重危险的”或者“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等常用的危险犯的立法方式,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一言以蔽之。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这样的表述理解为本罪由实害犯修改为了危险犯[10]。依学者关于环境犯罪危险犯或行为犯的讨论来看,多数学者主张污染环境罪应当设立为危险犯,其中有人主张具体的危险犯,有人主张抽象的危险犯。在我国当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罪应当选择行为犯作为既遂的模式[11]。
其次,讨论环境犯罪是否危险犯时,往往先预设是否危险犯,后依据是否危险犯推导出行为人的责任形式。在德日刑法中,危险犯的概念是在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中被讨论的,因此,其可能存在于故意责任形式中,也可能存在于过失责任形式中。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危险犯是作为犯罪的既遂形态之一,而在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中被讨论的。因此,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当提及危险犯的概念时,首先意味着已经预设了故意的责任形式,并且是直接故意的责任形式[1]。当然如果构成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的话,岂不是和降低入罪门槛,扩大规制范围,增设危险犯的初衷意旨相违背,因此,提出将“严重污染环境”表述理解为危险犯的学者,往往又陷入改造“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泥沼。
最后,每当面临司法解释与法条本身、司法解释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解释时,寄希望于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判定。从宏观看,些许学者秉持着污染环境罪这一结果犯的结论,可是也不得不认可《解释》对法律条文原意或有误解之嫌,从《解释》中规定的,关于“严重污染环境”十四项情形中的前四项表述以及第八条的规定,已突破了刑法条文结果犯的规定,使污染环境罪变成了兼具危险犯与结果犯性质的“双重犯”。“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对立法者付以重任。从微观看,纵使承认,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在法律具体适用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默认《刑法》第338条的立法缺失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救。而针对该用何种标准判断环境是否被严重污染,这一司法实践的难题,“两高”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12]。
2.困境突破。从污染环境罪的类型来看,刑法条文在本罪罪状的表述中明确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而并无使用“足以造成(引起)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危险犯的惯用词,并不能一言得出,该罪的成立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构成要件,仍然属于结果犯。但是,也不能另言得出,属于危险犯这一结论。立法者采用不同于常用的表述,将《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明确的罪状表述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以“严重污染环境”一言概之,如同上文所述,其体现了对于有生态法益性质的行为或者对象作为犯罪客体或侵害对象,而加以保护,试图将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涵盖在这一“环境”之内的立法构思。初衷甚好,也实属不易,但是面对传统的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的保护历史沿革,是否真的就能够弃置一旁,追求法益观念的现代革新?这也恰恰是“严重污染环境”这一句话带来的尴尬抉择境地。
字面意义上,“严重污染环境”理解为广义的危害结果,它既包括实害的损害结果,也包括危险状态,甚至可以包括具体的污染行为[13]。“污染环境罪”设置在破坏环境资源这一章节,实害的损害结果表现为对环境资源——生态法益的损害。危险状态表现为通过对环境资源的损害造成对人对生态(或者环境)的利用过程出现障碍,其一,阻碍了人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利用,例如,污染可供呼吸清洁的空气、污染可供饮用清洁的水源,以及污染、破坏适合人类生存在的气候或外部环境等;其二,阻碍了人对生态环境的间接利用,例如对人本可利用自然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源,进行破坏、污染,导致其所能够转化成为的财富减少、价值降低,甚至付之一炬。污染环境行为所侵害的两个层面的生态法益一般又可以分别转化为人的人身法益与人的财产法益。而司法实践中,又是通过对人的人身法益与人的财产法益的侵害来表现是否造成对环境生态法益造成足以刑法评价的结果。
笔者认为,单纯地说“严重污染环境”理解该罪为实害犯,或者应当设置为危险犯,都是欠缺对“严重污染环境”罪状设置前沿、现今层面的考虑。既然“污染环境罪”源自“重大环境事故罪”的前身,其就必然携带着传统法益和生态法益双重法益的特征;既然被赋予了生态法益保护的责任,又不得不与实践中对人的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侵害的认定标准挂钩。如此考虑,该罪是否危险犯、实害犯,其所保护的法益主次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结 语
同样地,针对环境犯罪的客体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有的认为是公民财产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环境权;也有的认为是国家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还有的认为保护的是不特定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等等。无论哪种观点,只是从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上对侵犯客体的揭示。犯罪,是对一个社会的侵犯;环境犯罪,是对社会横向、纵向的侵犯。犯罪不可能只侵犯社会关系而不侵犯这种关系背后的利益。如果将基于对环境保护形成的多种关系中的一个关系,看作唯一受保护关系而忽视其他关系的存在,或者只看到一种关系而看不到关系背后的利益,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对环境保护实践来讲,也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从制裁环境犯罪的定性思路来看,不仅体现了环境污染犯罪的罪名形态、既遂标准、罪过形式,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今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方向。面临环境污染犯罪日益高发的犯罪态势,罪名体系普遍属于概括性规定及实害犯设置,是积极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对现有罪名进行解释及适用,严厉制裁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还是承前启后,确立环境刑事政策代表和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承认无法破除受国家环境政策的指导和制约这一现状,站在经济性的视角进行建构。笔者毅然选择后者。
[1]王良顺.应当确立从严惩处的环境刑事政策[J].环境保护,2013(Z1).
[2]蒋兰香.试论我国环境刑事政策[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李希慧,董文辉,李冠煜.环境犯罪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4]郭世杰.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理念嬗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8).
[5]焦艳鹏.法益解释机能的司法实现: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判定为线索[J].现代法学,2014(1).
[6]焦艳鹏.我国环境污染刑事判决闽如的成因与反思:基于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J].法学,2013(6).
[7]王楠.环境污染罪的法律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3(12).
[8]王江.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失及司法解释补救: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9]姜俊山.论污染环境罪之立法完善[J].法学杂志,2014(3).
[10]孟庆华,王法.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若干问题探讨[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10).
[11]高峰.污染环境罪法律适用困境之破解[J].人民检察,2014(7).
[12]王江.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失及司法解释补救: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3]陈庆,孙力.有关污染环境罪的法律思考:兼论《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修改[J].理论探索,2011 (3).
A Talk about Sanction Thinking on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Positioning of Criminal Policy——With the Interpretation to Serious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Article 338th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Perspective
LIU Chuqi
(Law School,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There i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nation must consider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policy.The author opposes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committed to defend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crime,and proposes to eliminating the depend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promotes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 for expans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policy with severe punishment,and explain and apply the existing accusations.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crime of criminal policy from environment crimes,and then position the sanction thinking of environment crime and criminal policy by expounding its operation situation and taking Article 338 of"Criminal Law":"Serious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as a perspective,hence using the criminal means to bett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olicy;environmental criminal policy;environmental crime;economy;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914
A
1009-4326(2015)03-0068-05
(责任编辑 王先霞)
2015-03-30
刘楚琪(1992-),女,江西高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解释学。
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5.03.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