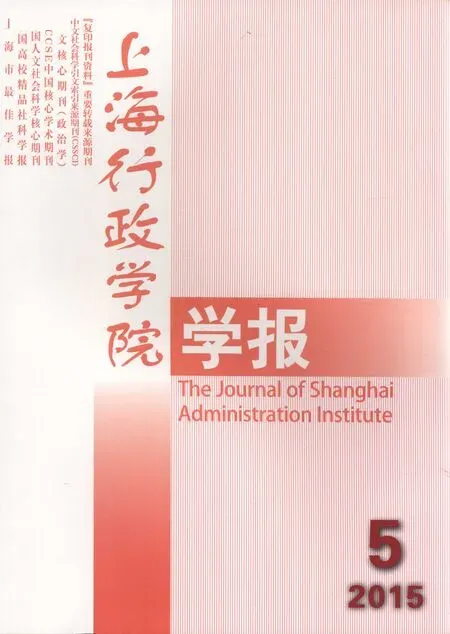“分离权”和民主权利关系辨析
——简评西方学界的“分离权”讨论
2015-04-09雷勇
雷勇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610066)
“分离权”和民主权利关系辨析
——简评西方学界的“分离权”讨论
雷勇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610066)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分离主义势力经常援引“民主”、“自由”、“平等”为自己的行为正名,提出所谓的“分离权”,并主张“分离权”也是一种民主权利。西方学界也相应掀起了“分离权”的讨论。本文认为,“分离权”主张不仅存在着根本的理论困境,它直接挑战“人民主权”原则,对“自由”的理解有失偏颇,违背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则;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危害性,它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整合和人民的福祉,容易刺激民族分离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分离,即使有少数几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分离权”,或在现实政治中认可了“分离权”,也是出于特殊的政治考量。因此,我们应警惕“分离权”主张的理论动向。
“分离权”;民主权利;国家认同
分离主义①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分离主义势力经常援引“民主”、“自由”、“平等”为自己的行为正名,提出所谓的“分离权”,并主张“分离权”也是一种民主权利,以此论证分离的合法性。西方学界也相应掀起了“分离权”的讨论。
中国是一个深受分离主义困扰和危害的国家。“疆独”、“藏独”、“港独”、“台独”②等分离主义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对地区稳定和国际政治秩序都构成挑战,影响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分离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相关的规范性研究明显不够,尤其是对“分离权”主张未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仅不适应我国反对分离主义的形势需要,而且也不利于我们在国际上赢得话语权。分离应被视作一种民主权利吗?“分离权”主张在理论上是否存在着困境?“分离权”主张对现实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生活中国际社会对待“分离权”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分离权”和民主权利概念分析
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即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前,世界各国人民都不认为民主权利应包括分离权。③从80年代开始,在“第三波”民主化背景下,分离主义势力找到新的理论突破口,经常援引民主、自由、平等,提出所谓“分离权”也是一种民主权利或曰基本人权,以此证明分离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学术界也相应掀起了有关“分离权”的讨论。
主张“分离权”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把分离看作一种基于自由、民主的基本权利,包括选择理论和公民投票理论。选择理论认为分离的合法性基础是个人自治权利和政治联合的自由权利,只要某一地区的多数居民采取民主的方式(通常表现为投票)进行分离,其分离就应该被看成正义的,至于国家是否存在对该地区的少数族群的不公正行为并不重要。如,哈维·贝兰(Harry Beran)假定存在个人自治的权利,即个人自我决定其政治关系的权利,个人联合组成国家是自愿的,因此,凭借个人自治权利,国家的一部分从国家中分离出去也应该被允许。[1]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丹尼尔·菲尔波特(Daniel Philpott)等。克里斯托弗·韦尔曼(Christopher Wellman)是公民投票理论的主要代表。韦尔曼认为,政治联合权(也被他称为政治自决权)是分离的合法性基础,只要一个国家的某一区域的大多数居民选择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分离就是合法的,而不论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族性特征。[2]第二种观点对分离持审慎的态度,把分离视为一种“补救性权利”或“救济性权利”。如阿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认为,通常情况下分离不应被提倡,只有当某一群体遭受不正义的征服、剥削,面临种族灭绝的威胁,或文化消失的威胁时,分离才能被视为一种权利,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3]尽管安东尼·伯奇(Anthony H.Birch)的分析框架和布坎南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立场和布坎南是一致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分离权的理论基础,民族自决权包含分离权。如凯·尼尔森(Kai Nielsen)认为,只要一个民族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特征,其民族自决权就应当包括分离权。[4]
需要指出的是,分离在国际法上并未被确立为一项权利,在国际法上也没有“分离权”这个概念。但从国际实践层面来看,国家内部的弱势群体在遭遇“严重不公正待遇”时,国际社会基于人道主义理念和保护弱势团体人权的考虑,通常会视其拥有救济性分离权。救济性分离权是弱势群体免遭毁灭、最后不得已而行使的一种救济性权利。但这项权利也有其局限性,如“不公正”标准如何认
定,由谁来认定,这些都容易导致“救济性分离权”被滥用。[5]
此外,学界对于民族自决权的讨论较多,讨论也较为深入,取得的共识也较多。学者们普遍认为,民族自决权行使的合法性前提是出现殖民统治,其功能是去殖民化。换言之,民族自决权是殖民地人民或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权利。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如果理解为“人民”,应为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而非部分人民;如果理解为民族,则应为政治民族(nation),而非文化民族(nationality)。因此,民族自决权不能被滥用,更不能成为分离主义的理论基础。[6]由于本文主要从民主权利的视角讨论“分离权”,因此不对救济性分离权和民族自决权做进一步讨论。对西方学界基于自由、民主视角提出的“分离权”主张,我们究竟应作何看待?
二、“分离权”主张的理论困境
有的学者基于自由、民主、平等的立场,主张把分离权纳入民主权利的范围,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精神,但从根本上讲,该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洽,存在着理论困境。
为充分发挥框架结构整体的抗震能力,在结构破坏机制下较合理变形模式为:保证框架节点基本不遭到破坏,而梁的屈服要比柱的屈服早发生和多发生;在同一楼层中,要保证各柱两端的屈服历程越长越好,底层柱底塑性铰要最晚发生变形,且梁端和柱端的塑性铰发生变形不宜集中。
首先,“分离权”主张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否定。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民主政治通常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范围内进行的,这里的共同体通常由一定数量的人口和领土所构成。换言之,民主政治是服务于一定区域范围的“人民”的。正如英国学者凯诺文所指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民主预设了某些社会排斥的原则,其运作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即一个拥有清晰地理边界的、稳定的人民群体。民主制度越复杂,厘定成员标准就必须越仔细。”[7]国家的存在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如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所指出的,“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形式。”[8]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民主政治通常是在特定的主权国家里进行的,是服务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的。
同时,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源于人民主权原则或主权在民原则的确立。人民主权原则是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和民主理论的核心。民主权利观念从根本上讲就源于人民主权学说,民主权利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延伸,从根本上讲,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是统一的。一方面,人民主权原则必然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权利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人民民主权利的确立及其实施,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度也会不断提高,对由一定数量的人民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分离主义试图“将国家的管辖权和政治权威限制在自己群体及其控制的领土范围之外”,是对国家主权的直接威胁和破坏。在民主制度下,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将分离权纳入民主权利的范围,将直接挑战和拆解国家主权,也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否定,这违背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初衷。
其次,“分离权”主张对“自由”的理解有失偏颇,会导致无政府主义。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是人民签订契约的产物,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组成国家;同理,为了自身利益,一部分人可以退出国家,在其所占据领土上组成新的国家,或连同所占据领土并入其他国家,或和其他国家组成新的国家;这是人民自由意志的表达,也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笔者以为,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解释国家的形成和分离行为,貌似十分合理,其实不然,该观点的症结在于没有很好地理解“自由”。自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现实社会中的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实中的自由是具体的,它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及其水平的制约。正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指出的,“政治自由绝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在一个国家里,即在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想要去做的事。……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
的权利;倘若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权利。”[9]即是说,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自由必须保持在国家法律的限度内,而不能随心所欲。主权国家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和法律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性,反对分离主义。即使少数几个国家有分离的相关规定,要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么对分离的相关实施程序规定相当严格,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分离权”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自由的极端化理解,忽视了民主权利和自由实现的现实社会基础。而且,如果分离权被主张,自由度被无限放大,势必影响政府的权威,影响政府正常工作的开展和职能的履行,势必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出现。
再次,“分离权”主张违背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则。民主政治在现实中遵循多数决的原则,即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遵循多数人的意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多数决原则很容易造成对少数人权利和自由的忽视,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曾表达了对当时美国民主中多数的无限权威的担心,在他看来,“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10]所以,民主政治在遵循多数人意见的同时,必须注意倾听少数人的意见,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否则,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本意,即把维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作为自身的重要内容和原则,就容易出现在维护一部分人权利和自由的同时,造成对另一部分人权利和自由的伤害的情况,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主张一部分人或地区的“分离权”,从表面上看,是这部分人或地区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他们中的“多数”的决定,是他们集体意志的结果。然而,现实中任何一区域内都有不主张分离的人存在,这些人的利益也应得到保障。从民族分布的特点来看,世界上很少有单一民族聚居的区域,民族混居是民族分布的经常状态,在维护该区域某一民族尤其是主体民族的利益的时候,其他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利益也应得到保障。换言之,在维护欲分离地区的多数人(常常表现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的利益的同时,却忽略甚至是伤害了该地区少数人(常常体现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从本质上讲,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违背了民主政治的本意。以中国的“疆独”分离主义为例,就新疆的民族分布而言,维吾尔族是该地区的主体民族,除此之外,还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乌孜别克族、汉族、满族等民族。如果“疆独”被允许,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维吾尔族人的利益,但是却忽略了长期居住在新疆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等其他民族的利益。而且,即使是在维吾尔族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疆独”,那些反对“疆独”的人的利益实际上将遭受伤害。
而且,一个国家是在长时间的历史变迁和演变中形成的。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国家的形成是各民族、各地区长期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发展。主张一部分人或地区的“分离权”,在维护所谓欲分离地区利益的同时,却造成了对该国其他地区及其人民利益的伤害,也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平等原则。
三、“分离权”主张的现实危害
“分离权”主张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自洽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分离权”作为对分离行为的合法性证明,必将刺激民族分离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的膨胀,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将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第一,“分离权”作为国家认同的解构性力量,影响国家的政治整合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最终影响人民的福祉。建构统一的国家认同,施行有效的政治整合是一国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国家从事各项改革、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有效地统合在统一的政治屋顶之下,使国家得到公民的广泛认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改革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分离权”主张将分离看作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公民具有随时从国家分离出去的权利,这实际上为分离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国家有被分裂的危险。国家发展前途的不确定性迫使政府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保卫主权和领土安全,这就不可避免地分散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精力,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同时,政府对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和建设将变得更加谨慎,甚至不作为,这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分离权”主张为一些民族和地区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提供了方便,一些民族和地区会以分离相要挟,向中央寻求更多的政策和支持,这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不利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化。再者,“分离权”主张将导致政治秩序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人民生活将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成本,而且人民对未来生活将变得不可预期。
第二,“分离权”主张将激发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矛盾,引发民族冲突和地区冲突,严重时甚至伴随民族仇杀、清洗、暴力冲突,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分离一旦作为民主权利被主张,分离就具有了合法性,民族分离主义和地区分离主义就会不断膨胀。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随之伴随的是领土、人口如何分割,财产如何分配,依据什么原则分配。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围绕领土分割、财产分配、资源分配等问题将产生分歧和矛盾,引发政治冲突,严重时触发社会动乱直至流血冲突。众所周知,世界上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很少,多民族共存是现代国家民族分布的普遍情况。就一个国家的民族分布特点而言,不仅存在民族“聚居”的情况,即一个民族的成员聚居在某一特定的领土范围内;而且更多地是存在民族“杂居”的情况,即不同的民族在长时间的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局面。就分离行为而言,在单一民族聚居的情况下,相关问题解决起来或许会简单一些。但是,在民族杂居情况下,矛盾将变得错综复杂,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以及跨界民族对各自权利和利益的主张,如果再加上不同的民族精英的民族主义式的宣传和鼓动,极易爆发民族冲突,严重时甚至导致民族仇杀和清洗。
第三,如果“分离权”被确定为一种民主权利,而且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碎片化,引起国际关系的重组,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影响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主权国家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当一部分人或地区通过行使分离权从所属国家分离出去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通常表现为国家)后,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人或地区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从新的政治共同体中再分离出去。以此类推,分离权的主张和无限行使,将使国家越来越微型化,出现大量的“袖珍”国家。这不仅将改变既有国家的领土范围,削弱既有国家的实力,改变世界和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引起国际关系的重组,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原有的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由谁来继承,原有的财富如何分配,领土究竟如何划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由谁来继承,既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分割……这些问题一旦协调不好,极易引发政治冲突,给既有的国际秩序、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使整个世界处于无序动荡状态。而且,一旦一国的分离主义获得成功,将对其他国家的分离主义产生“示范”效应,将使一些国家蠢蠢欲动的分离主义公开化,或使已有的分离主义不断膨胀,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四、“分离权”的现实考察:国际社会对“分离权”的态度及少数国家对“分离权”的规定
“分离权”主张本身不仅违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危害性,所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中明确反对分离主义,更没有将其规定为一种民主权利。当然,也的确有少数几个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了“分离权”及其实现的程序。这些国家对“分离权”是如何规定的,这些规定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它是否具有特定的目的,以及分离权在实际中被行使过吗?为此,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加拿大法学家蒙纳罕(Patrick J.Monahan)和布兰特(Michael J.Bryant)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根本不承认任何族群、团体、地区拥有分离的权利。[11]在他们研究的89个国家的宪法中,只有7国宪法有与分离相关的条款,而22个国家的宪法(包括澳大利亚、圭亚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巴拿马等国)特别明文强调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分割,其中科特迪瓦和喀麦隆的宪法甚至禁止任何将来涉及领土变动的修宪。
即使是民主的历史较长,民主化程度较高,崇尚自由和个性的美国,也没有把分离当作民主权利。不仅如此,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美国政府都坚决反对分离。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明文规定:“国会得准许新州加入本联邦。但新州不得建立于其他任何州的管辖区域内;又未经有关各州的立法机关及国会的许可,不得并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或各州的一部分以建立新州。国会有权整理并制定关于属于合众国所有的土地或其他财产的必要法规与条例。本宪法所述一切,不得对合众国或某一州的任何权利要求作不利的解释。”[12]这表明美国只允许增加新的领土,但不允许任何领土从美国分离出去;国会有权制定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的法律法规;宪法的解释不能对国家的一切权利(包括领土完整)不利。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对分离主义的战争。19世纪60年代,当南北双方在“南方奴隶制”的废存问题上发生冲突,南方各州企图分离出去独立建国时,美国总统林肯发表了著名的“裂屋”演说,强调“一座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反对使“房屋倒塌”、使“联邦解体”的分裂,表明了美国政府反对分离的坚定决心。最后,美国人民在林肯的领导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世界上也有少数国家将“分离权”载入了宪法,如上文提到的蒙纳罕(Patrick J.Monahan)和布兰特(Michael J.Bryant)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在宪法中规定了分离权利或涉及可能的分离程序的7国宪法中,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有允许分离的条款且依照这些条款的规定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均已解体。在奥地利、法国、新加坡、埃塞俄比亚和加勒比岛国圣西斯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圣西斯宪法中规定了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分离,其他宪法只是有相应的有关承认有关领土和国界变动的条款或地方分权的条款。其中,法国有关分离的条款主要针对其海外殖民地。
苏联在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中赋予了各民族从苏维埃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权利。但是,苏联宪法之所以规定各民族有分离的权利,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各民族从苏联分离出去提供合法性,相反,其目的恰好在于通过允许“分离”达到联合的目的,使各民族感到分离是受宪法保护的,加入联盟和退出联盟都是自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各民族加入联盟的后顾之忧,有利于联盟的扩大。关于这一点,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允许“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的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分离,并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将来爱尔兰能同英国自由结盟”[13]。换言之,分离只是手段,联合才是目的。
又如,加拿大魁北克在1980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就“魁北克独立”(在本质上属分离)问题进行
了公民投票。1995年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就魁北克独立问题在政策和法律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事实上赋予了魁北克以其单方面投票达成分离的权利。但是,2000年5月通过的《公决明确法》,规定今后魁北克若再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民投票,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而且还就脱离联邦的具体程序作出了严格而复杂的规定,使魁北克试图通过单方面投票实现分离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
英国在1998年签订的 《英爱和平协议》在原则上认可了北爱尔兰在全民公决基础上分离的权利,但是,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2012年,英国政府允许苏格兰在2014年下半年就苏格兰是否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分离出去进行公民投票。但是,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苏格兰人都不想“独立”。笔者以为,英国政府允许苏格兰就是否独立进行投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大多数民众反对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意基础,英国政府或许不会简单地同意进行公投。英国政府希望苏格兰尽早举行公民投票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14]
由此可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分离,更没有把分离视作一种民主权利;即使有少数几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分离权”,或在现实政治中认可了“分离权”,要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特殊的政治考量,要么只是在理论上或法律上认可了其存在,由于实施条件相当苛刻,程序相当复杂,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注释:
①分离主义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从所属国家脱离出去的主张和行为。在英语中,涉及分离的主要有两个词汇,一个是secession,一个是separation。学术界通常认为,separation比secession含义更广一些,它不仅包括分离,而且包括地方自治、分权等。所以西方学界较多地使用secession来表示分离。中国学界常常将分离主义称为分裂主义。从两个词的使用频率看,分裂主义高于分离主义。在汉语中,“分离”和“分裂”意思比较接近,都有“分开”之意。从感情色彩来看,分离(主义)更为中性一些,分裂(主义)则暗含挑战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性的贬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行为的非法性。但在国际法中,“分离”和“分裂”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原有主权国家即母国是否继续存在。分离使原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遭到部分破坏,但原有主权国家的国际人格继续存在;而分裂使原有主权国家的人格消失,即母国不复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内学界所使用的“分裂”、“分裂主义”概念,实际上表达的是“分离”、“分离主义”的内涵。因此,为了使表述更为科学、严谨,也为了跟国际接轨,本文采用“分离”和“分离主义”的概念表述。
② 需要指出的是,独立(independence)通常是指包括殖民地在内的非自治领土、托管地领土以及附属领土实现自主,如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就是独立。目前学界对“独立”概念的使用有时并不是十分严谨,有的地方的“独立”概念表达的并不是独立的本意,如“台独”、“疆独”、“藏独”、“魁北克独立”等,本质上就属于“分离主义”的范畴。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本文仍采用惯用的表达方式。
③苏联1936年“宪法”赋予了各民族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权利主要是出于特殊的政治考虑(下文有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而且分离也并没被视为民主权利。
[1]Harry Beran.A Liberal Theory of Secession[J].Political Studies,1984,Vol.32,No.1:23-26,28.
[2]Christopher Wellman.A Theory of Secession:The Case for Political-Determin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3]Allen Buchanan,Justice.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Moral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Margaret Moore,ed..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王英津.有关“分离权”的法理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2):19-37.
[6]朱毓朝.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J].国际政治科学,2005,(2);王英津.自决权:并非分离主义的挡箭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张友国.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主义的误读[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7]Margaret Canovan.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M].Cheltenham,UK;Brookfield,Vt.:Edward Elgar Press,1996:17.
[8][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7.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5.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82.
[11]Patrick J.Monahan,Michael J.Bryant and Nancy C.Cote,"Coming to Terms with Plan B:Ten Principles Governing Secession," CD Howe Insititute Commentary 83,1996,June,http://www.cdhowe.org/pdf/Monahan.pdf.
[12]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83-284.
[13]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5.
[14]英国内阁希望苏格兰就独立尽快举行公投.人民网,2012年1月11日,http://news.sina.com.cn/w/2012-01-11/000023781960. shtml.
Right for Separation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c Rights:a Brief Review on the Discussion of Right for Separation in the West
Lei Yong
Influenced by the third wave for democracy,separationist have always refer to democracy,freedom and equal to justice their behavior.Right for separation was claimed to be a democratic right.Western researchers have widely discussed this issue.In this paper,we believe the concept of right for separation has theoretical difficulty,and directly challenges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and was practically dangerous.It can put 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wellbeing in danger,and impact international stability.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against this,only a few countries support it because of political concern.Therefore we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the trend of related theory.
Right for Separation;Democratic Right;National Identification
D51
A
1009-3176(2015)05-063-(8)
(责任编辑 方卿)
2015-6-8
雷 勇 男(1976-)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