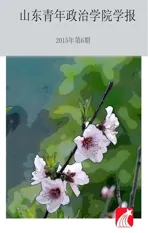浅议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
2015-04-09冯雪里
冯雪里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济南 250104)
浅议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
冯雪里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济南 250104)
公共利益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特征,一直是法律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公益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常常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事,令公众有不同意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公共利益立法界定应主要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一要明晰宪政精神下公共利益立法功能定位;二要解决在宪法基础下如何确立公共利益界定立法模式;三要加强公共利益界定立法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
公共利益;立法界定;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利益界定的复杂性来源于其自身概念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公益界定的必要性源于公共利益需要是公益征收的前提。我国宪法第10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在公益征收过程中,公共利益是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法律概念,增加了内涵界定的艰巨性。仅就公共利益概念本身而言,对“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每一个细化概念界定都存在着不同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形成内涵和外延比较周全的权威统一概念。在此困境下,最好的界定方式就是追本溯源,探求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和原则。这样看来,通过立法从源头上和根本上来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显得尤为必要。
单纯从立法技术而言,对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界定有其科学合理性,那就是保证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公共利益的抽象应用应建立在法治政府的真正形成基础之上,执法者具有较高法律素养,并能自觉有效维护法治精神和实施法治政策。仅就目前我国法治环境下,在公益征收实践中,许多案例和事例都在反映着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许多公权机关借公益之名行之事,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私权。在公益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症结有:一是公共利益概念立法抽象性,使得行政机关无法清晰辨别公共利益的内涵;二是公益征收程序不合法。公益征收实质是公权对私权利益的分割,不能期许公权机关能自觉恪守法定职能,不为非法侵犯私权之事。公共利益的界定话语权往往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公权机关的不正当行为,严重损害了法治政府的公信力,使得官民关系也非常紧张。
为了更好地处理好官民关系,更好地维护法治精神,在现今法治背景下,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切实规范公权,保障私权,有助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二、公益界定的宪法意义
对公共利益立法界定必须符合宪法精神。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法治国家构建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国家首次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一系列司法体制深化改革举措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和行动力。这更需在立法界定公共利益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诊断式合宪性审查,以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增强公民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
针对公共利益,我国《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所涉及,针对不同的法律规范的不同效力,有必要对公共利益内涵进行“顶层设计”。此处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根据宪政精神,通过宪法立法、法律规范立法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内容,为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树立明确的裁判标准,避免适用和执行法律规范的恣意。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效力等级,处于法律规范的“最顶层”,因此宪法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性和原则性作用。
“宪法体制内的法治国家,其法律体系所追求的公益,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直接由宪法导源派出的公益理念。这个公益理念拥有宪法层次,也可称为宪法公益理念。宪法是一个价值理念,而以立法技术方式予以成形的结合体,故欲穷究宪法内的公益价值,必须以宪法整体的精神以观之”。[1]“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其他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离不开宪法的授权许可。
正是由于宪法在中国法律体系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在界定公共利益的时候,必须遵从依法治国基本理念,必须遵从宪政精神,必须为了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借助宪法内核,帮助我们探求公共利益的真正内涵和精髓,以便更好地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首先,宪法是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任何与宪法精神、原则和内容相冲突的法律规范是无效的。宪法是对公共利益进行立法界定的依据。
宪法也是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的法律尺度。宪法的本质内涵在于划定公权的界限,把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里,基于主权在民之理念以便更好地保护“国之主体”的私权。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不能超过宪政的范畴。在中国现今法律实务中,宪法还无法直接适用,更多通过具体法律规范来实现宪法内涵。对公共利益而言,更多通过《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规具体展现公共利益内容,进而提高公共利益适用的可操作性。在公益征收过程中,“公共利益必需”事项是公共权力剥夺相对人财产权的前提条件也是公权机关实现行政权能的物质保证。在公益征收中不断呈现的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即公权与私权不断博弈的景象。德国行政学家毛雷尔认为:“许多法律规范都要考虑有时相互一致,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2]在公益征收过程中,如何实现公权和私权的关系的平衡是处理土地征收矛盾的关键。
三、宪法精神下的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模式选择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根据宪法精神立法界定公共利益最终目的在于规制公权,保障私权。“公益概念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是为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内容不确定性,可以表现为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3]”公权机关在进行征收过程中会基于自身不当利益的考量,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这样会严重破坏官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如何对公共利益进行立法界定一直是立法研究的难点和重点。对公共利益进行立法建立在对公共利益概念具有相对一致性界定的基础上,进而更好地进行立法界定模式的探索。
(一)公共利益的概念界定
公共利益至今尚无一个内涵确定、外延周全的概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公共利益实现的工具载体——公共权力其自身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扩张性,使得公共利益界定面临困境。一方面为了更好满足变化万千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事态,提高法治政府管理能力和管理机制构建,建立权威高效、公正遵法的“有限政府”,更好地发挥“有形之手”的政策功能,公共利益界定不宜过于太局限,这样会束缚政府积极作为,最终损害公共大众之根本利益。
在对公共利益阐述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学说,力求全面概括界定公共利益概念,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基于学术研究和实务应用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肖顺武认为,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主体所享有的、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发展性的重大利益。[4]“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公共利益即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5]”“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就整个共同体而言)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可以说符合功利原理,或简言之,符合功利。如果公权机关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或者减少最大多数人的痛苦就符合公益。[6]”
基于以上不同学说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雏形有了基本的勾勒。通过基本概念来掌握公共利益本质内涵具有积极的帮助作用,对公共利益概念进行相应的界定也具有实际意义。相较而言,学者肖顺武关于公共利益概念的定义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为了实现国家福祉,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基于不特定多数需要(在特定情形下,按照法定程序除非基于个体正义、民权保障需要除外),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立法界定模式选择
正是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界定的错综复杂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利益界定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进行类型界定成为一种新的尝试。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主要观点有三种,即列举式、概括式和列举概括式。姜明安教授对例句概况式进行了深化解读,提出 “列举+排除+概括模式”路径选择。“我国现行生效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①[7]”。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②对公共事业的范围进行了一定尝试。
在对公共利益界定的过程中,在通过概念界定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个路径可以选择,一是全面列举公共利益事项,一是设立原则性(兜底性)条款,一方面是保证法律灵活性和事态随机性,另一方面是作为实现个体正义之时的法律依据。
笔者赞同通过“列举+排除+概括”模式对公共利益进行立法界定。
四、公益征收过程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建议
土地征收作为典型的公益征收行为,对国民私益影响较大。尤其是近年来拆迁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官民和谐关系。 “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之所以滥用,是因为《土地管理法》中没有对‘公共利益’明确化③。” 也有作者认为, “集体所有土地征收中的问题,并非完全归罪于普通立法的疏忽,而是我国的土地使用制度造成了‘公共利益’的稀释[8]”。在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征收、征用过程中,务必区分“公共利益需要”和立法精神与基本原则的契合性,“任何建设用地都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现实中,这种建设用地主要有三种情况:(1)国家进行公共设施及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2)国有企事业单位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3)需要办理出让手续的土地。从上述三种情况来看,只有第一种情况是属于公共利益,后两种情况均属于经营性的和主要追求经济利润的利益,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原则[9]”。
为了提高公益征收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程序性问题,真正解决法律实务操作过程中公共利益界定难题,主要建议如下: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界定全国性公益类型
通过公共利益类型清单的形式对公共利益界定意义重大。一方面全国性公益类型涉及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为了规制公权,更好地保障私权实现,通过立法途径对全国性公共利益事项或范畴进行界定十分必要,这样有益于避免公权机关假借公益之名,行非公益之事,也有助于通过“法治”而非“人治”,真正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克制有权任性行为。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公共利益并不必然优于个人利益 ,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成立 ,必须以各种利益的均衡和比例原则的适度为前提。[10]”要做到科学、合理的界定,需做到以下几点:
1.通过立法列举全国性公益类型
明确全国性公益范畴,通过权力清单,释明公权界限,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侵害私益空间。在对公共利益类型进行界定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委托第三方中立调查机构全面调研、结合司法机关实务案例聚焦的共通性类型以及公众参与等多元途径,对全国性公共利益类型进行公开界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批评和建议。现今,通过法律实践,对国家公共利益类型有了较为成熟稳定的认识,如“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④” 这就为清晰界定公共利益类型提供了可靠性参考。
2.通过立法排除非全国性公益事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充分担当,代表人民充分调研,代表人民利益作出主张,代表人民摒除公益征收非法程序和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科技优势,做好开门纳谏的工作。
3.通过立法设立原则性条款
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公共性法律规范随着时代变迁更新较频繁,这是由行政权力的特征决定的。在给予公权机关公权权能的同时,应首先给予其在特定为了实现个案正义的情形下享有一定的裁量权,这也体现了公权机制发展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发展性需求。
4.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公益类型合法性
公益类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何判断公权机关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是否真正实现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最权威的评价主体是中立的法院。全国性公益类型价值判断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比较合适。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决定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本行政区域内的公益类型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保证人 ,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并使各经济人所作决策的社会效应比国家干预之前更高。”[11]为了和全国性公益类型相适应,同时符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实际需要,在服从全国性立法的前提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类型,对本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尤为重要,也真正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奠定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现如今,多数国家都确定只有在出于公共利益的情况下 ,国家才有可能发动土地征用权,其目的也在于防止公共权力无限扩大而损害私人财产权益。尽管宪法财产不允许受到侵害 ,但财产不能不受对共同福利至关重要的法律之规制[12]。”
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有助于体现地域发展不平衡性特色发展需要,同时有助于制约作为行政机关基础单元的县级行政机关滥用公共利益名义行事。
与此同时,借鉴全国性公益界定“积极列举+消极列举+概况”模式,根据地域实际,通过公众参与、调查研究等多形式形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益类型。
“公共利益的内容拘束力,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用以论证一个公益可能达成目的与否之资讯,必须广为大众所周知,大众藉此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来影响立法者之立法行为。”[13]公共利益的判断必须考虑人民大众的公平正义感受。在个案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域内公益类型的实施是否合法应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较为适宜。
注释:
①根据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订,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内容,即第12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3条 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
②参见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208条:国家因左列公共事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围,应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 国防设备。二、交通事业。三、 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六、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事业。
③《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只是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1]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7.
[2]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编.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15-416.
[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2.
[4]肖顺武.公共利益研究:一种分析范式及其在土地征收中的应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8.
[5]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3.
[6]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59.
[7]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82
[8]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J],中国法学,2005.(1).
[9]朱道林、沈飞.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原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J],国土资源,2002.(11).
[10]余少祥.论公共利益的行政法律保护[J],环球法律评论, 2008.(4).
[1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9.
[12]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3.
[13]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95-196.
(责任编辑:杜 婕)
The Analysis about Legislation of Public Levy on Defining the Public-interest
FENG Xue-li
(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Jinan 250104, China )
The public-interest, because of its own uncertainty,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the emphasis and difficulty in legal academic circles study.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Levy,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often borrows the name of public interests to do non-public matters, so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s sometimes very nervous,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public-interest. Defining the 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mainly from three basic aspects: to clear under the spiri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function orient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public-interest legislative model,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basis and to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research of public-interest legislation.
Public-interest;Legislation Defining;Proposals
2015-08-18
冯雪里(1985-),男,山东鄄城人,助教,主要从事行政法研究。
D912.1
A
1008-7605(2015)06-01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