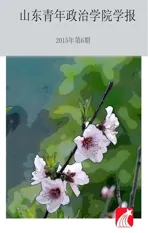比较视野下中美高校公益慈善模式研究
2015-04-09井海明
井海明
(山东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比较视野下中美高校公益慈善模式研究
井海明
(山东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一直受惠于各种慈善捐赠。二战后以慈善文化和捐赠制度创新为先导,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日益发达的捐赠基金管理系统和公益慈善模式,为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和高等教育中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借鉴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经验,培育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建立健全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文化传统的公益慈善模式,提升高校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美高校;公益慈善;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宗教文化;基金会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强国,以拥有如哈佛、耶鲁、MIT等一批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相比,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美国高等教育400年的发展历程一直受惠于各种公益慈善捐赠。二战后以公益慈善文化和捐赠制度创新为先导,兴起了一场美国大学筹资运动,催生出现代美国大学日益发达的捐赠基金管理系统和公益慈善模式,由此所筹措的雄厚办学资源已成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战略基础,为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科技与高等教育中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考察公益慈善的文化内涵、特点及其运作模式,以期更好地借鉴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的发展经验,加强和改善我国高校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办学的物质基础,提高办学层次与水平。
一、文化维度比较:从宗教文化、文化心理角度切入,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美高校公益慈善事业之前提
就现代意义上言,慈善是个体自愿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或公众福利的无偿捐赠行为,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特征。发达的慈善事业是公民社会的标志之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1]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有了现代慈善之基因。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会慈善是慈善的主要形式,但亦孕育出了现代慈善的博爱和责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慈善传统成为现代公益慈善的两个源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宗教教会慈善开始朝着世俗方向演变。 1601年,英国议会开始为捐赠行为立法,以《伊丽莎白法规》的颁布为标志,西方的公益慈善真正迈向了世俗化的轨道,形成了以法律体系为保障,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公益慈善系统,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宗教文化及其文化心理,已成为我们观察美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视角。
首先,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文化直接继承了欧洲的大陆文化,全国盛行基督教。事实上,最早飘洋过海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批清教徒,在抵达新世界的头两件事就是建立教会和开办教育。在这批清教徒眼里,教育与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捐赠教育由此成为宣扬宗教教义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教教相连”的理念,长久以来左右着美国公益慈善事业。基督教信仰中所倡导的慈善观念深刻影响着全体国民。就普通百姓群体而言,《圣经》中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护社会”、“爱你的邻居”等观点,对人们的捐赠产生非常广泛影响;就富人群体而言,基督教教义关于“富人原罪”的说法,例如,“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等,确实让一些富豪具有负罪感,他们希望通过行善和捐赠,祈求上帝的宽恕,以此净化自己心灵。历经五个世纪,公益慈善业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优良传统,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宗教文化的熏陶下,公益慈善慢慢变成了人们的自觉行为,继而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乐善好施的美德,不论是低收入者,还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彼此都一样热心于公益慈善,更涌现出一批诸如洛克菲勒、卡耐基、比尔·盖茨等享誉全球的慈善人士。在许多人看来,慈善捐赠确实是回馈社会、救济穷人、支持教育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
其次,从文化心理特征看,一方面,美国人民族性格特点体现在,个性既豪放,又张扬。实用主义思想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受此影响,在文化心理及社会行为方面往往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例如,人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自己的投入能有多少回报,但更关注这些投入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是否有效果,实际上,大家抛弃的是自我欲望,强调的是利他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价值观上,美国社会强调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个人主义并不等于利己主义,从内涵上说,亦包含着深刻的民主自由思想,亦强调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正的集体责任。[2]与这种个人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相并存的,尚有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同情心和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源自于基督教精神的文化理念,经过若干代人的实践,逐步升华、凝练为美国公益慈善事业赖以发展的社会思想渊源和传统。这种思想在实践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人为公众服务的志愿精神。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所倡导的即是个人奋斗、自由竞争和个人成功。每个成功人士对摆脱贫困、取得财富和承担社会责任都有着特殊的认识,他们更愿意通过公益慈善捐赠教育的方式,使得更多有才华的人能够公平地接受教育,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另外,不同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能够对这种慈善捐赠行为在税收政策和相关法律条款方面给予保护和规定,使得每个公民的公益慈善行为有法律保障。在美国社会里不存在所谓的世袭门第观念。例如,在对待遗产问题的态度上,他们认为巨大财富往往会宠坏自己的后代,助长其坐享其成、懒惰、不思进取等坏习气,有悖于美国精神的弘扬。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就是让大家学会履行公益慈善传统,学会懂得回报社会。
相比之下,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一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并存,并深远影响了国人思想。例如,儒家文化追求中庸之道,也强调私有财产保障;道教追求自然无为,强调个人修为和出世,但并不关注世俗社会,因此信仰道教的人一般很难谈慈善捐赠的事情;佛教主张因果轮回,强调的是慈悲为善、因果报应,在现实生活上往往大部分信徒热衷的是捐钱修庙宇、塑金身,以求得报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里缺乏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的精神。[3]从文化心理上讲,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投入后的回报而忽视实用,导致人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另外,我们民族传统性格中既强调保守和谦虚的一面,又有“藏富意识”与“仇富心理”的一面,这种双重作用,导致许多人在实践中以“中庸”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不敢露富,阻碍了慈善氛围的形成,影响着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二、历史维度的比较:始于哈佛学院的外行董事会之大学治理制度,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美高校公益慈善模式的基础
应该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有史以来在国家制度安排方面对高校慈善捐赠行为的运行一直给予了支持和法律保障。[4]但就大学管理制度而言,与欧洲大学传统相比,殖民地时期的学院没有延续中世纪大学学者行会自治的传统,没有采取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那样的学者行会治校的制度,而是移植了英国的学术法人制度,同时采用了加尔文教派外行管理协会和大学的理念,以及英国的信托制度。[5]这一制度,虽然美国的加尔文教会和私立的基督教团体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学院仍然具有公共服务的功能,体现了学术法人的相关属性。殖民地时期的学院所形成的以学术法人为基础的外行董事会的自治模式,经建国初期新的国家制度认可,到19世纪中期扩展到各州立大学,奠定了现代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结构的基础。因此,有的教育史家把这种美国大学治理模式称之为“外行控制” ,成为颇具美国文化特色的大学制度[6]。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美国著名高教专家J·V·鲍德里奇指出的那样,理解校外人士的管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是理解当代美国学院和大学管理的关键。
美国学者乔治·M·马斯登在讨论哈佛学院创立之缘由时指出:“美国大学在创建之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俗机构,而是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只有考虑到教育对于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整个领导阶层的重要影响,才能理解这所站在西方文明的前沿的著名学院的创建意义。”[7]宗教,特别是加尔文教在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决定着教会与政府对待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态度和策略。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教会和政府一样,都是一个公共机构。所谓“公共”(pulic),实际上是指少数可以凭借他们的地位、土地所有权或者其他身份来参与社会管理的人。正是教会或政府所谓机构性质的公共性特点,在殖民地时期,创立学院的目的和宗旨可同时为教会和世俗社会培养领导人。这样,无论是哈佛,还是耶鲁,在尚未成为独立的法人之前都是被界定为公益性的慈善信托。按照英国法律,公益信托是无需得到皇家特许的。其中,体现教会、政府及捐赠人合作关系的学院董事会作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以公共信托的方式管理学院的财产等。例如,威廉玛丽学院较之哈佛学院最早获得了英国女王的办学特许状,享有完全的法人地位,但也同样当作一种信托,将监事会作为学院的受托人。后来,考虑到纯粹信托制度设计的局限,许多学院又在信托基础上通过法人的方式强调了学院的法律地位。尽管取得法人地位后,作为法人机关的董事会还会接受学校创立者——教会或政府的信任委托,托管学院的财产,负责学院的管理经营,二者之间仍然是一种信托关系。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赠地法案的实施及大量州立大学的兴起,因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干预的缘故,就美国公立大学来讲,从治理结构上看,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代表,该校在弗吉尼亚州,既被视为州机关,又被看作是公法人。二是以密歇根大学为代表,该大学是密歇根州宪法设立的,董事会由全州人民公选,它所承担的该州人民的“公共信托”。 这种灵活的信托制度与法人制度的有机结合,使得美国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关系:一是确立自主权,保持了学院(学校)的独立,免除了教会、政府及大学捐赠人对学校自主办学的渗透与干预;二是保证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精神的延续,规约了董事、校长和教授在大学决策中角色、地位和作用,体现出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鲜明特色。
以哈佛大学初创时期为例。1636年,哈佛大学前身哈佛学院成立于马萨诸塞州的纽敦,1639年因约翰·哈佛慷慨解囊而易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才更名为哈佛大学。哈佛创校之初衷,体现了英国人热心教育的情怀,同时更是清教徒传播宗教教义的产物:一是为了增进学问以利子孙后代;二是担心从英国迁移来的牧师去世后会给教会留下一批不学无术的牧师。[8]哈佛学院完全是仿照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模式建立起来的,从学院章程、各个年级的名称、学生纪律及课程设置,都沿袭了伊曼纽尔学院的做法,可谓是伊曼纽尔的翻版。尽管哈佛学院仍沿袭英国大学传统,但在结构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创新。就大学管理体制而言,第一,哈佛学院的创立,并未获得英王室的特许状,仅由马萨诸塞议会同意并由地方政府首批拨款而成立,完全不是围绕学者产生的。到了1650年,学院才从马萨诸塞议会得到了特许状,成为真正的“哈佛法人(Harvord Corporation)”。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的拨款是学校经费的主渠道,哈佛学院不具备维持自治或独立的财政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哈佛更像一所公立性质的学院,但按照特许状规定的权力,学院又明显具有私人社团性质,必须求助于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学院的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公理会手上,由外行人士行使管理权。19世纪初,“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之后,哈佛大学的私人性质才得以明晰和确定,逐步成为美国东海岸常青藤高校的翘楚。第二,在管理模式上,哈佛学院没有延续英国大学的做法,而是于1642年设立由校外人士组成的校监委员会,校监会由校友会普选,也称监事会,全权管理学校事务。因监事会不能具体管理学校日常事务,1650年,按照马萨诸塞州颁发特许状的规定,哈佛学院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校内人士组成,这是经监事会同意的哈佛法人,包括校长、司库和5名教职工组成,董事会拥有人事、财务、教育政策等权力,处理学校日常事务,但同时特许状还规定监事会又有认可或否决董事会的决定等权力。 这样,监事会与董事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共同治理学院,形成了独特的由校外人士和校内人士共同管理学校的双董事会制度,也称“外行控制”制度。哈佛学院成立初期的“外行控制”治理模式上的创新,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后来美国众多高校争相模仿复制的样本。
从殖民地学院时期开启,成熟于美国建国时期小型学院发展时期,前后运行了一百余年的外行董事会(Lay-board)制度,奠定了美国大学由外行人士治理的文化基调与自治模式。这些董事来往穿梭于大学与政府之间,调节大学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保障大学的自治法人地位,维护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挑选、任命校长,平衡、协调学校内部关系,筹措教育经费。有的学者曾对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名校的董事会成员来源情况进行统计,这10所大学的298位董事会成员中,来自校外人士达276位,占总人数的92.6%。 由外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处于大学自治管理机构的顶点,容易使校外各利益相关者之需求与校内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达成一致,利于学校在办学目标、办学战略和具体措施等方面形成共识,利于大学在激烈竞争中争取更多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更大发展。当然,校外董事会的职责与权限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在公立院校,州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在私立院校,公司法人的有关条款以及州议会或政府颁发的特许状里规定了他们的权限,此外,州公司法或信托法亦对他们的权限进行了规定。第二,随着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世俗化,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广泛,慈善、捐赠等法律不断完善,特别是对信托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外行董事会组成结构的变化,董事中更多的来自于大学之外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和校友,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应该说,此时的“外行”与殖民地时期学院之“外行”,二者在内涵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与信托文化契合的外行董事会制度,则构成了美国独特的大学治理模式。从目前美国高校情况看,数额巨大的社会捐赠基金及其管理,不仅成为美国大学校长年度报告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带来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且支撑着美国大学使命的履行。这种新的变化,既提供了学校财政的稳定性和学校发展的自主性,又创造了创新教育。[9]正是如此的大学治理模式,才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系统,为高校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办学资源,支持和保障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这是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科技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因素。
与美国相比,我国高校在办学体制和财政拨款机制方面与美国大学完全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学习苏联模式,高校是事业单位。在高度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办学经费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高校定位、目标与专业发展完全受制于政府经费多寡,国家计划分配给多少,大学就办多大的事,学校是没有自主权的,当然也谈不上从社会上寻找办学资源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财富的快速积聚,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拨款机制和大学评价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得以深化,逐步形成了今天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新局面。199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率先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教育基金会,标志着我国大学依法规范从海内外筹集社会办学资源新阶段的开始。随着筹款工作对促进大学发展发展效果的日益凸显,我国高校多元化筹集社会资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增强。[10]需要指出的是,2004年以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门放宽了对基金会登记注册的条件,国内大学基金会数量迅速增加,高校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格局。
尽管如此,我们要承认中美高校在公益慈善捐赠方面的巨大差异。仅从捐赠数量上比较,迄今为止,我国高校接受的海内外各界慈善人士的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还不足3%,总体社会捐赠的规模还不到美国高校的1%。[11]可见,我国高校公益慈善事业任重道远。我们应在理念、策略、体制、工作机制以及具体措施上,学习研究美国高校社会筹资等公益慈善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三、实践维度的比较:校友会和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的有效运作,是理解和把握中美高校公益慈善模式的关键, 营造了高校的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提高了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
考察、梳理百余年来美国高校公益慈善捐赠的历史,我们发现:除了有完善的公益慈善制度和捐赠文化,以及多元的筹资渠道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适合它的筹款平台、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正如美国学者威廉姆斯所说的,一个慈善机构要想通过投资来达到成功理财目的的话,这个慈善机构必须致力于“提供一个可供资助机构的代理人处理其基金而适用的理性架构。”这个组织架构目前主要是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它们是大学公益慈善捐赠工作的主要抓手。美国大学基金会一般是非独立的法人,多数隶属于高校。在管理架构上,校董会或校基金委员会负责捐赠基金的决策,基金会负责运营和管理,也有的大学将全部基金委托给校外公司运营。[12]
就校友会而言,校友捐赠是美国大学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大学捐赠与校友组织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美国高校的第一个校友会是成立于1821年的威廉姆斯学院校友会。从校友工作体制和公益慈善情况看,一般美国高校校友工作和社会筹款工作分别由学校校友会和发展办公室(类似我国大学的教育基金会)承担,分别由两个校长主管;工作分工上亦有所侧重:校友会负责联系和服务全体校友,后者负责为学校的战略目标筹集捐赠,两个部门密切互动与配合。[13]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斯坦福大学1892年才成立校友会,但最初仅是一个独立于学校的非营利性机构。106年后的1998年,斯坦福校友会才回归学校,成为大学管理机构。其定位、宗旨是一个面向斯坦福大学的所有校友和学生、在学校与毕业生之间建立起终生的知识和情感联系、为学校赢得最大声誉和支持的公共关系平台。从组织管理架构上看,校友会是直接对校长负责 ,下设宣传与营销、校友联络、校友业务、战略规划、财务和行政等不同业务模块。主要活动方式是通过策划、组织不同系列的校友活动;校友会工作主要考核指标是校友参与率、校友满意率。实际上,校友会自身并不是一个筹款部门,而是为全体校友服务的,在价值取向上,倡导的是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相比之下,大学发展办公室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斯坦福大学,其发展办公室的功能定位是为了学校的战略目标和不同阶段发展任务募集捐赠,争取社会办学资源。具体而言,通过与学校的学术领导层及志愿者通力合作、密切互动,与在校生、校友、学生家长、企业家、企业集团、基金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以争取更多的社会办学资源。大学发展办公室一个系统,在组织体制上分学校和院系两级,形成了内部结构清晰、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筹款能力。经过多年发展,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会和发展办公室都有十分完整的体系、明确的定位、科学的分工、规范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行。
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高校公益慈善事业是一个系统的生态工程,组织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密切互动协调,保持了美国高校校友组织旺盛生命力和校友捐赠的长盛不衰。上述斯坦福大学的经验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虽然30多年来我国高校公益慈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学校友工作和公益慈善捐赠工作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例如,一般的“985”、“211”高校都建立起校友组织机构和教育基金会,立足国内,放眼海外,逐步开展了一系列校友活动和各类筹资项目等,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和令人羡慕的业绩。但同美国高校相比,我们在筹款总额、校友参与率、校友贡献率、尤其是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大学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我国高校校友和基金会工作仍然存在着领导层面思想重视不够,公益慈善文化培育不足,组织机构设置不健全,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不完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下,人员缺乏等尴尬局面。
应该看到,一方面,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民间财富的持续集聚,为高校筹款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 2015年下半年国务院公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一方案将“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作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关键环节,无疑为我国高校如何争取社会办学资源,大力开展公益慈善捐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我们要抓住机遇,虚心学习和借鉴美国高校公益慈善捐赠的经验与做法,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在学校广大师生中加强公益慈善宣传教育,大力营造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提高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要解放思想,高度重视校友工作,充分认识校友工作对学校社会筹款工作的重要性,把校友看作学校最宝贵的财富,提升校友对学校活动的参与率和满意度,同时重视和加强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学校、校友会和基金会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文化传统的公益慈善模式,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为学校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办学资源。
[1]史竞艳.现代慈善的起源、发展及特征[J].思想战线,2012,(3):47.
[2]赵雯君,支希哲.文化视野下中美高校社会捐赠的差异比较[J].生产力研究,2014,(7):156.
[3][10][13]邓娅. 校友工作体制与大学筹资能力——国际比较的视野[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141,143,144.
[4]张继华. 美国大学社会捐赠良性生态系统形成及特征[J].比较教育研究,2014,(12):32.
[5]甘永涛.美国大学共同治理制度的演进[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6):25.
[6]刘爱生.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基础[J].外国教育研究, 2014,(8):62.
[7][美] 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0.
[8]刘宝存.大学的创新与保守——哈佛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路[J].比较教育研究,2005.1:35.
[9]张伟.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管理实践及经验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12):70.
[11]易鑫,孟彦,莫蕾钰. 我国高等筹投资何以动力不足[J].中国教育新闻网,2015,(3):23.
[12]魏礼庆.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及其管理[J].世界教育信息,2011,(10):34.
(责任编辑:王淑玉)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arity Pattern of Chinese and US Universities
JING Hai-ming
(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
The development of US higher education has benefited from various donations, which stimulates increasingly developed administration system for endowment funds and charity pattern, and plays unreplaceable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S universities. With the aim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working efficiency and benefits,and to strive for more social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domestic universities’ capability of raising social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nd to perfect universities’ charity pattern that suits leg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rough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endowment of US universities.
Chinese and US Universities;Charity;Higher Education; Religious Culture; Foundation
2015-11-1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少年公益慈善意识的培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11CJYJ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井海明(1963-),男,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易学哲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G641
A
1008-7605(2015)06-0100-05